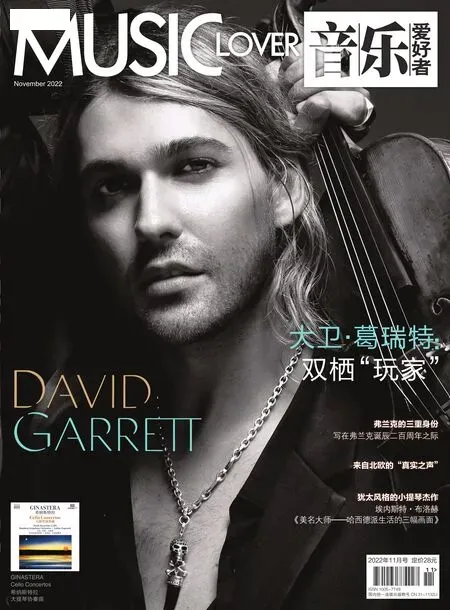西方音樂作品中的中國 東方·智慧·女性:貝齊·喬拉斯與室內(nèi)歌劇《望江亭》
文字_王夢琦
說起“西方音樂作品中的中國”這一話題,聽眾一定都會聯(lián)想到普契尼的《圖蘭朵》。
其實,“中國情結(jié)”在西方作曲家心中由來已久,在西方音樂作品中,類似這般以中國主題為立意的作品還有許多,它們凝聚著作曲家對遙遠而古老的中國的幾許好奇與遐想。
近年來,法國作曲家貝齊·喬拉斯(Betsy Jolas,1926— )逐漸回歸當代音樂視野。
作曲家·喬拉斯
喬拉斯生于巴黎,是家中長女。1940年,十四歲的她隨父母移居美國。1946年,喬拉斯回到巴黎。
喬拉斯的父母與文化名流交往甚密,他們曾與小說家埃利奧特·保羅(Elliot Paul)共同創(chuàng)辦了巴黎文學(xué)評論雜志《轉(zhuǎn)變》(Transition),推動了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發(fā)展。我們大概很難想象,在喬拉斯青少年時期,她的家中竟時常往來著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歐內(nèi)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等名士。
在這樣一個充滿“先鋒”氛圍的家庭浸潤長大的喬拉斯擁有著敏銳的藝術(shù)眼光,但許是因為與她同時代的“先鋒新星”皮埃爾·布列茲(Pierre Boulez)備受矚目,喬拉斯與她的同窗保羅·梅法諾(Paul Méfano)一樣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被大眾所忽視,即使她在這段漫長的時間里已經(jīng)創(chuàng)作了長笛獨奏《第一尾奏曲》(épisode I),為女高音和弦樂三重奏而作的《四重奏II》(Quatuor II)以及為男高音、高音薩克斯和大提琴而作的《大部分時間II》(Plupart du temps II)等代表性作品。

貝齊·喬拉斯的部分作品專輯

時至今日,成熟作曲家喬拉斯的力量得以真正釋放。于喬拉斯而言,她與娜迪亞·布朗熱(Nadia Boulanger)和莉莉·布朗熱(Lili Boulanger)姐妹,以及法國新古典主義樂派“六人團”(Les Six)成員熱爾梅娜·塔耶芙爾(Germaine Tailleferre)所處的境遇不同,當下人們不再僅關(guān)注她的女性身份。沒有人會否認,喬拉斯是一位擁有獨特音樂語匯的作曲家,其室內(nèi)歌劇《望江亭》(Le Pavillon au Bord de la Rivière)正是這種音樂語匯的絕妙言說。
腳本·關(guān)漢卿
《望江亭中秋切膾旦》(也稱《望江亭》)是關(guān)漢卿創(chuàng)作的雜劇劇本,全劇以一段婚戀故事為開端,最終引向公平與正義的話題。1958年,由翻譯學(xué)家楊憲益、戴乃迭編譯的《關(guān)漢卿戲曲選》(Selected Plays Of Guan Hanqing)一經(jīng)問世就得到了法國戲劇導(dǎo)演伯納德·索貝爾(Bernard Sobel)的關(guān)注,他向喬拉斯推薦了這部作品。在并不了解中國古典戲劇的情況下,《望江亭》的內(nèi)容仍然引起了喬拉斯的興趣:“在女性主義運動的高峰時期,那些美好的女性尤其吸引我。她們憑借著自己的智慧,尋求世間的公理與道義。”
1975年,西歐女性主義與東方主義正值發(fā)展盛期,喬拉斯的室內(nèi)歌劇《望江亭》應(yīng)運而生,一經(jīng)首演便引起轟動。同年,該作分別在倫敦、巴黎、布魯塞爾等地上演。隨后,這部承載著西方對中國想象的歌劇自歐洲大陸啟程去往美洲,在華盛頓、費城、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等地上演,反響熱烈。《望江亭》因其凝練的戲劇形式和豐富的音樂色彩,在業(yè)界廣受贊譽。
喬拉斯的室內(nèi)歌劇《望江亭》基于同名雜劇劇本寫成,全劇時長約九十分鐘。劇中共包含八位戲劇人物,主要講述了聰明的譚記兒用智慧化解丈夫的困局,并戲耍了想將她據(jù)為己有的反派角色的故事。這是一部充滿女性主義文化傾向的作品,劇中的女主角譚記兒是父權(quán)統(tǒng)治下的他者——女性,也是西方文化中的他者——中國人。作品所強調(diào)的傳統(tǒng)歌劇中的異質(zhì)要素通過對譚記兒的音樂刻畫予以呈現(xiàn),這讓在西歐歌劇傳統(tǒng)中處于邊緣的中國元素走向了中心,也讓建構(gòu)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露出全貌。
在整體結(jié)構(gòu)上,歌劇與原劇本并不完全相同。雜劇本子共四折,不分幕次。歌劇為四幕,第一幕共三場,第二幕和第三幕分別由四場構(gòu)成,第四幕獨成一幕。整部作品喬拉斯采用了將故事分幕、逐場呈現(xiàn)的傳統(tǒng)歌劇基礎(chǔ)樣式,在保留西方傳統(tǒng)歌劇中幕與場布局的基礎(chǔ)上,于兩幕之間加入間奏片段,形成連接,以此構(gòu)成新的框架形式。除此之外,喬拉斯還以雜劇的線性敘事為暗線,在結(jié)構(gòu)上形成了每一幕和每一場之間的不對稱性。

年輕時的貝齊·喬拉斯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先鋒派”充滿實驗精神的音樂語匯基本已與傳統(tǒng)歌劇形式分道揚鑣,《望江亭》便誕生于這樣一種年輕作曲家渴望改革歌劇的激進氛圍之中。整部作品器樂編制靈巧,且在一定程度上結(jié)合“念唱”等藝術(shù)手段,因此這部作品在創(chuàng)作之初便被定義為“音樂劇場”(Theatre Musicale)。
由于《望江亭》講述的故事發(fā)生在古代中國,喬拉斯在歌劇序幕中用聲音建立了一個象征著東方的時空。喬拉斯雖不了解中國傳統(tǒng)戲劇,但她在少年時曾與東方音樂“邂逅”——巴黎世博會印象以及巴厘島的旅行經(jīng)歷,其中克恰克(Kecak)成了喬拉斯難以忘懷的東方象征。序幕構(gòu)建的喧鬧場景即近似于克恰克式的“猴子吟唱”(Monkey Chant)——不斷重復(fù)吟唱無語義的音節(jié),節(jié)奏錯位,富有即興特質(zhì)。這種音樂形式起初并不具備審美功能,主要用于驅(qū)趕鬼神或哀悼逝去的親友。在歌劇中,它似乎也起到了類似的效果,克恰克的即興特質(zhì)從人聲轉(zhuǎn)移到了室內(nèi)樂隊中,為形成一個自由的聲音空間提供可能。
在短小的序曲中,音樂的節(jié)奏與力度變化十分豐富。但喬拉斯并沒有在樂譜中對音樂的力度或情感色彩進行過多標記,她希望能給予演奏員或喜劇演員一些即興發(fā)揮的空間。此外,由喜劇演員構(gòu)成的合唱團需要“將手指放在張開的嘴唇之間,用非常快的速度移動”,這種特殊的演唱方式構(gòu)成的顫音為樂隊添加了新音色,而其所產(chǎn)生的近似于中國戲劇的唱腔也喚起了聽眾對東方/中國的想象。
東方·女性
喬拉斯對偶然元素和非傳統(tǒng)的樂器極為偏愛,這體現(xiàn)了她對多元音樂文化的包容態(tài)度。她在《望江亭》中使用了疊音鈸、腳踏鈸等大量爵士樂常用的樂器,以及帶有東方韻味的邦戈鼓和筒鼓等。非傳統(tǒng)的打擊樂配置帶來了充滿即興特質(zhì)的音色,這一貫穿始終的異質(zhì)效果與合唱團作為克恰克延伸的無語義的喊叫形成呼應(yīng),描繪出了喬拉斯心目中自由的東方世界。

關(guān)漢卿畫像
與此同時,喬拉斯對西方音樂藝術(shù)中非傳統(tǒng)要素的關(guān)注與其通過《望江亭》的創(chuàng)作而喚起的女性形象譚記兒交織在了一起。這首先體現(xiàn)在喬拉斯對人聲音色的選擇和寫作上,其次也反映在歌劇中對經(jīng)典女性形象的呈現(xiàn)與刻畫中。
喬拉斯首先根據(jù)劇中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選擇了不同的人聲類型:譚記兒由輕女高音演釋,白士中是一位男高音,白姑姑是一位女低音,楊大人是假聲男中音,其余男性配角都由男中音演釋。此外,她還特意選擇了不同身份的演員來表現(xiàn)劇中的人物形象,比如譚記兒的詮釋者是所有演員中唯一一位專業(yè)歌唱家,而其他角色則是由演唱水平參差不齊的喜劇演員來扮演,用非專業(yè)的人聲音色賦予音樂隨機的特質(zhì)。從演唱方式來看,念唱旋律(sprechgesang)貫穿始終。除了譚記兒的詮釋者需要演唱許多音高復(fù)雜的唱段之外,其余角色的“唱”保持在一定的自由空間內(nèi)。
譚記兒一出場,她口中所唱的詠嘆調(diào)便為人物形象奠定了基調(diào)。“鳳只鸞單,繡裊香散,深閨日沉……”輕柔音樂和之,極有“傳統(tǒng)”的女性氣質(zhì)。人聲的音高始終圍繞著某個并不存在的中心逐步延展,而器樂部分的音高和節(jié)奏則是基于法語念詞的音調(diào)創(chuàng)作而成的,其總是出現(xiàn)在人聲之前或之后,以指向人聲的音高。與其他探索現(xiàn)代語匯的作曲家一樣,喬拉斯刻意模糊了人聲與器樂之間的界限。長笛的音色與輕女高音相契,展示出譚記兒“年輕”的特質(zhì),喬拉斯在此處標記著“唱腔輕柔,近似裝飾”,以輕柔與縹緲的音色賦予聽者對女性柔弱、優(yōu)美的想象。
接著,在同一段詠嘆調(diào)中,喬拉斯選擇用念唱的方式來配合不同的器樂音色,揭示出譚記兒不同于傳統(tǒng)的特征。在第一幕譚記兒詠嘆調(diào)的末尾處,其音高更趨于自由,配器音色也發(fā)生了變化。邦戈鼓和筒鼓的音色伴著突快的節(jié)奏,在譚記兒表達對男性看法的同時透露出反抗之聲。在關(guān)漢卿的雜劇本子里,譚記兒就是一位有勇有謀的女性,喬拉斯用音樂強化了這一特征,進一步表明譚記兒不僅僅是一位充滿智慧的女性,更是一位努力與命運抗爭的尋常人物。她作為雜劇群像中的重要一員,以自身的智慧與勇氣揭示出當時社會現(xiàn)實中的不公。

貝齊·喬拉斯

貝齊·喬拉斯的作品手稿
此外,在放大傳統(tǒng)歌劇中異質(zhì)要素的同時,喬拉斯保留了詠嘆調(diào)和二重唱等傳統(tǒng)的唱段,并通過對舊傳統(tǒng)的革命式回溯,改變了歌劇中刻板的女性形象。譚記兒的詠嘆調(diào)《珠寶之歌》(Air des Bijoux)與古諾(Gounod)歌劇《浮士德》(Faust)第三幕的著名唱段《珠寶之歌》同名。在古諾的歌劇中,這個唱段還有另一個名字——《真高興見到鏡中如此美麗的自己》(Ah! je ris de me voir si belle en ce miroir)。劇中,瑪格麗特見到梅菲斯托菲勒斯帶來的精美珠寶后喜笑顏開,珠光映著臉頰好似自己重獲新生。然而,在《望江亭》中,譚記兒對即將要收到珠寶佯裝開心,樂隊僅用零星的音色來伴襯她的念唱,直到她與楊大人對詩,音樂節(jié)奏才又規(guī)整起來。這種音樂上的變化一方面展現(xiàn)出了譚記兒的沉著冷靜,另一方面也著重強調(diào)了她的智慧。
通過對譚記兒音樂形象的構(gòu)建,一幅自由、平等的中國印象素描浮現(xiàn)在我們眼前。西歐傳統(tǒng)歌劇中的異質(zhì)要素在喬拉斯的歌劇中興起,一種被倒轉(zhuǎn)的傳統(tǒng)秩序獲取了自身的主宰地位,照出了女性的真實命運,也照出了西歐人眼里的中國。
譚記兒·喬拉斯
《望江亭》原本并不在關(guān)漢卿最為經(jīng)典的戲劇作品之列,但自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它不斷被人們重視起來,不僅在1958年上映了由張君秋先生飾演譚記兒一角的京劇電影《望江亭》,還在同一時期通行著川劇、贛劇、昆曲等幾個版本。事實上,關(guān)漢卿筆下的譚記兒本就具有超越時代的智慧、勇敢等脫離了男權(quán)社會傳統(tǒng)的特質(zhì),而這一作品被重新激活則反映了時代精神。在七個世紀之后,這些特質(zhì)在女性主義運動的高峰時期被喬拉斯接管。
如今,即將邁入九十七歲高齡的喬拉斯仍在堅持創(chuàng)作。作為西方作曲家的喬拉斯始終關(guān)注著東方女性身上已經(jīng)覺醒的自由平等意識。在當今文化界與大眾對女性議題重新予以重視的時代背景下,喬拉斯的成功不僅意味著她作為個人作曲家的成功,更意味著現(xiàn)今藝術(shù)家們女性意識的覺醒,以及智慧、勇敢的“譚記兒”在當下社會的又一次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