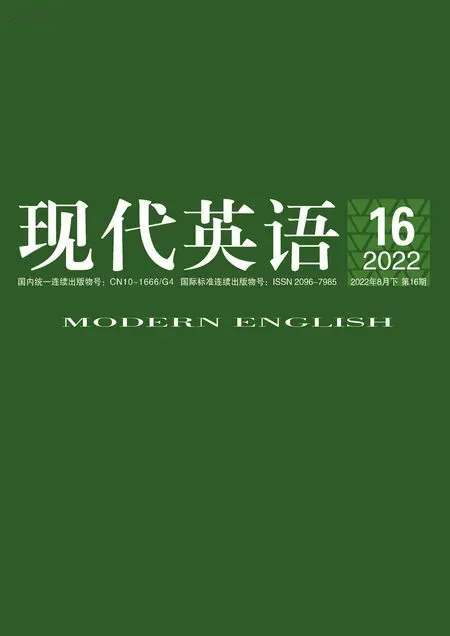古詩英譯的識解操作
吳 雋
(西安翻譯學院,陜西 西安 710105)
一、引言
一直以來,古詩翻譯是翻譯的難點。不同譯者將理論解悟與身體力行相結合,立足中西方不同翻譯理論,進行了大膽的嘗試。但怎樣準確理解原詩的意義?怎樣將原詩的意義忠實地植入譯本,并營造出原詩悠遠的意境?對于這些問題,他們都未能給出具體、明確的答案。近年來,國內外已有學者將認知語言學的理論應用于翻譯研究,形成認知翻譯學這一新興研究領域。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能力不是獨立自主的,而是人的一般認知能力的一部分,“是建立在人類有關現實世界的經驗基礎之上的,并且反映了人類認知系統對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空間的、物理的、社會的)的理解”。[1]所以,語言是人與世界互動的心理表征。
認知翻譯學認為翻譯是一種認知活動,語言轉換僅是外在的、表面的,認知運作才是內在的、深層的,因此翻譯研究更重要、基礎的是應考察認知層面上的運作[2]。認知翻譯學是翻譯學的一種新范式,是在認知科學及認知語言學的框架下研究翻譯理論、翻譯實踐以及翻譯現象的有關問題[3]。
二、認知語言學與翻譯
認知語言學為翻譯的認知研究與過程研究提供了強大的闡釋力與可行性,運用其相關理論研究翻譯實踐的熱潮持續不退,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目前已有研究可分為理論探索和具體文本分析兩大類。
肖坤學[4],王寅[5]基于識解理論探究如何在翻譯過程中識解原作者在原作中的意圖,從認知角度來簡析翻譯中的常見方法,以期能為翻譯過程研究提供一個更為具體的新視角。陳吉榮[6]探析了譯者存在的認知不足與認知過度的表征與動因,認為譯者認知不足與翻譯語境的轄域和背景有關,而譯者認知過度則與“焦點與場景”翻譯框架緊密相連。金勝昔,林正軍[7],基于體驗哲學思想和構式語法理論嘗試構建認知翻譯模型,認為翻譯是認知主體(譯者)進行的體驗性認知活動,強調譯者在認知等效原則的轄制下,結合譯文讀者的認知水平和方式,進行創造性翻譯。文旭,余平,司衛國[8]運用認知文章基于認知語言學的范疇化理論,構建翻譯的范疇轉換模式,探討翻譯的范疇轉換過程,并揭示翻譯范疇轉換的認知基礎和認知機制。
除理論研究,部分學者從不同文體出發,探究了認知語言學相關理論在翻譯實踐中的應用。就古詩翻譯而論,權循蓮,田德蓓[9]應用概念隱喻理論研究了古詩中的意象翻譯策略。張紅深[10]運用概念整合理論以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英譯本為例,對嚴復的“信、達、雅”進行重新解讀,分析了原作和譯本生成的認知活動。李亞培,王義娜[11]從名詞短語和定式小句的情境植入方式入手,對《兵車行》原文和十篇國內外譯文進行考察發現原文和譯文在植入方式上具有各自的語言特點,但在功能上基本對等,相比較而言,國內譯者更能領會詩歌中隱含的情境植入特征。金勝昔[12]認為唐詩中存在大量隱轉喻和轉隱喻現象,是詩人隱喻思維和轉喻思維操作互動的結果,翻譯時要以追求“認知等效”為首要原則。
簡言之,將認知語言學理論應用于翻譯研究,為翻譯研究和實踐注入了新的活力,提升了翻譯文本和翻譯過程的解釋力,豐富了翻譯研究方法。
三、《江雪》原詩的識解解析
文章基于認知語法語義觀的相關理論,以古詩《江雪》的英譯本為例,旨在探究古詩翻譯過程中原詩和譯本經歷的識解轉換。首先,分析原詩意義傳遞和意境構建所涉及的識解操作。其次,通過對比分析原詩及其三種譯本識解方式的異同,解析譯者的識解過程差異對其翻譯技巧選擇的影響,以及不同譯者的識解差異可能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約。
認知語法理論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由美國著名語言學家Ronald·Langacker創建,是認知語言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描寫和分析語言現象的一種新范式。其核心觀點為語言能力是人的一般認知能力的一部分,對語言的描寫必須參照認知過程,該過程被稱為“識解”(construal)。面對同一場景,識解方式不同便會產生不同的描述內容。所以,話語的意義既取決于客觀事實,同時又受制于人的識解方式(How people conceptualize the facts),映射到語言上就會有不同的語言形式。
這一點對翻譯尤為重要,翻譯的原文意義建構涉及作者的識解過程,同時譯者在理解原文及翻譯的過程中也涉及一系列識解操作,所以翻譯需考慮作者、譯者的識解過程,且對翻譯過程進行科學的解釋。
識解的維度主要有:詳略度(specificity)、圖形/背景(figure-ground)、視角(vantage point)、突顯(prominence)、話語的主觀性與客觀(subjectivityobjectivity)、心理掃描(mental scanning)、顯影(profiling)等。這里以Langacker[13]的經典例句來說明說話人的認知識解差異對同一場景的語言表征影響:
a.The road winds through the mountain.
b.The road is winding through the mountain.
a,b兩句話描述的是同一場景,但語言表征存在很大差異,其原因在于說話人的視角不同(vantage point)。a句基于整體視角,描述的是一個客觀的情形,而b句是說話人所在位置的視角,是局部視角,這里可以以指路的情境理解這句話。此外,兩句的謂語動詞是wind through,并不符合路和山都是靜止的這一實際情況。這是因為說話人在識解情境的過程中應用了心理掃描(scanning)
這一認知操作,想象著路在動,并表現在了語言上。它們的譯文應該如下:
a.這條路彎彎曲曲地穿過這座山。
b.這條路從這兒開始彎彎曲曲地穿過這座山。
古詩《江雪》為詩人柳宗元謫居永州時期所做,以白描的方式勾勒出一幅“雪中寒江垂釣圖”,寓意深邃,意境深遠。該詩題目“江雪”使讀者眼前出現雪中江景這一寒冷凄清的景色,為全詩所描繪的景色和意象提供“背景”。該詩前兩句“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描寫了萬籟俱寂,寥無人煙的雪中靜態世界。其中“千山”“萬徑”并非詩人眼前真實存在千座山和萬條徑,而是詩人對畫面中“山”“路”的心理掃描(scanning),即詩人對周圍環境的環視,含有動態感。這兩句凸顯出“背景”“江雪”空無一物的蕭索,也為后兩句是人借景抒情奠定了一個凄清的“背景”。
該詩后兩句“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詩人的視角由上句中的“千山”“萬徑”轉向江面上的“孤舟”,又以孤舟為參照點(reference point),將視角由“孤舟”轉向獨自垂釣的老翁,基于前兩句所營造的蕭瑟嚴冬的‘背景’,凸顯出意象“孤舟”“垂釣老翁”。詩句結篇三個字“寒江雪”又重新強調畫面背景環境,引起讀者對寒冷天氣的心理經驗與身體感知從而加強了環境的凄清肅殺之感,愈發襯托出垂釣老翁的孤獨感與遺世獨立感。另外,下句中“孤”“獨”“寒”三個帶有明顯感情色彩的字眼又反過來加強了讀者對外在寒冷環境的感受,使讀者融入畫面,感同身受。
四、譯本識解操作對比分析
古詩《江雪》寓意深邃、意境悠遠,是古詩中的經典佳作。文章中作者根據譯者的身份、譯文產生的時間及譯文的代表性等因素選取了《江雪》的許淵沖等三種英譯本作為分析文本。主要分析譯者是否將詩人對場景的識解方式恰當地轉化譯入語,從而盡可能接近地表現出詩人構建出的主觀世界,傳遞出原詩的意境。
1.Fishing in snow(許淵沖)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straw-cloak'd man afloat,behold!
Is fishing snow on river cold.
2.River-snow(Witter Bynner)
A hundred mountains and no birds,
A thousand paths without footprint.
A little boat,a bamboo cloak,
An old man fishing in the cold river.
3.Stream and snow(趙甄陶)
O'er any hills no birds are seen,
In any paths no footprints show.
On a boat old man in cloack and hat,
Angles alone in stream and snow.
根據原詩的分析中可知“江雪”是詩中描繪畫面的背景,其認知范疇是關于江中雪景的經驗和身體感受,因此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要將這一意象的認知范疇恰當地移植入譯入語;否則就會造成全詩缺少背景,影響讀者的閱讀體會。許譯版“fishing in snow”與原文的認知范疇不同而是譯者在閱讀全詩之后做出的改譯。而Bynner譯版“river-snow”則直接對應原詩題目表現出靜態的江中雪景。趙譯版用了連接詞“and”同時突出了“江”與“雪”,與原概念范疇也不同。
同時,上文提到首句中的“千山”“萬徑”并非詩人眼前真實場景,實際上是詩人對畫面中山與路的心理掃描,在許的譯文中,使用了介詞結構“from sth.to sth.”來轉化原文對場景的識解,在認知語法中典型介詞表達的是兩個成分的空間關系,包含詩人視角的移動,包含著詩人對山、徑的心理掃描。趙譯在轉化原文的識解方式時采用了與許譯相同的方式。而Bynner的譯文則是用并列的名詞短語結構,名詞在認知語法中表示為抽象的“物”(thing),所以Bynner的譯文沒有體現出原詩中的心理掃描這一認知操作。詩文的第二句是建立在上文詩句構建的萬籟俱寂、天寒地凍的世界之中。詩人在描寫中通過不同的參照點來轉換視角與凸顯的對象。因此,在上文構建的背景之中突出的對象為“孤舟”“垂釣老翁”“寒江雪”。許譯版中,將“孤舟”這一具體意象用“afloat,behold”兩個詞轉化,將孤舟這一意象省略。“孤舟”在原詩中不僅僅指小船,更帶有詩人的主觀情感傾向,象征著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因仕途不順而背井離鄉四處漂泊,因此,許譯版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原詩意義表達。Bynner譯版“a little boat”與原詩的概念范疇亦有差別。“翁”一詞在漢語文化的心理經驗之中指“男性老人”包含有歷經滄桑之感,而許譯卻將其譯為“man”(An adult human male)與“翁”概念范疇不同。
五、結語
文章基于認知語法的識解理論視角探究了詩歌《江雪》分析原詩的意義是如何構建的,涉及詩人的哪些認知過程。另外,篩選《江雪》的三種英譯本,分析不同英譯本的表達差異背后譯者所涉及的認知過程,通過對比分析譯本探究不同譯本與原詩意義的忠實程度,進行翻譯批評,可以看出為了盡可能傳遞原詩歌的意義,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要恰當轉換原詩的識解方式。識解理論通過分析原文和譯本透視作者創作和譯者理解及翻譯的認知過程,對原文的理解和譯文的檢驗提供一個更為客觀的評價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