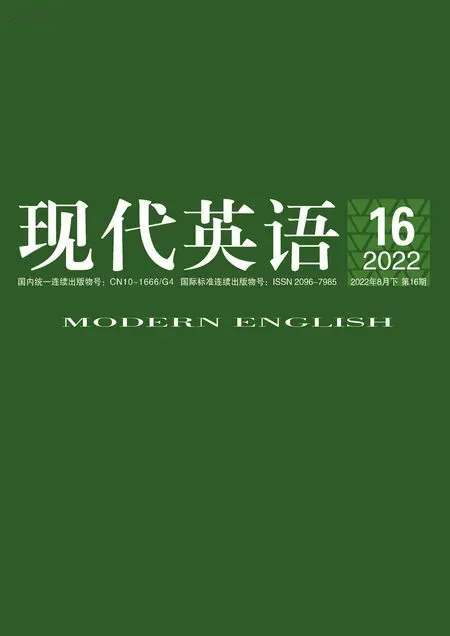關聯理論框架下《江雪》英譯本的對比賞析
白依帆
(河北工業大學,天津 300401)
一、引言
(一)詩歌內容簡介
《江雪》是唐朝詩人柳宗元所作。詩中運用象征、襯托、概括等手法,如千山、萬徑、鳥絕、人滅這種宏微觀結合的描寫,來表現山野嚴寒、靜謐宏大的景象;隨后用“孤舟獨釣”勾畫孤獨清傲的漁翁形象,表達了作者在遭到貶謫之后內心的孤傲。從風格來看,整首詩構思獨特,動靜結合,節奏鮮明,語言簡潔凝練,文化意蘊豐富。隨著經濟全球化以及翻譯研究的不斷發展,不同民族間的文化交流愈發密切,《江雪》也被眾多國內外學者翻譯到了世界各地,推動了不同語言、精神與文化的交流。近年來,也有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江雪》英譯本進行賞析:張軼、王彬從美學的角度對該詩的數詞翻譯進行了研究,發現其不僅有一種朦朧、含蓄的“意美”,在數字和數字對照之間,還形成了一種“形美”[1];鄭錦懷從意象的視角下對其英譯本進行了評析,認為林健民先生的譯本受制于“整齊美”譯詩觀,過分追求譯詩形式上美感,以致在譯詩的意象重構方面未能做到盡善盡美,但仍有值得肯定之處等[2]。
(二)翻譯賞析
從翻譯的角度來看,翻譯學科已由從屬走向獨立[3],而隨著翻譯的不斷發展,翻譯批評也在探索中不斷進步。司顯柱教授曾說:“當下的大多數翻譯批評都是一種非科學意義上的批評,缺乏一種較為科學、客觀和系統的翻譯批評模式。”[4]近年來,盡管翻譯批評理論不斷發展,但其重要意義仍在不斷吸納其他學科理論,以應用于翻譯批評活動,關聯理論便是其中之一。中華古典詩歌濃郁優美,蘊含著超越語言的精神力量,承載著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詩歌翻譯批評不僅有利于促進翻譯實踐的發展,還有利于傳承民族文化精神,推動中華民族文化對外傳播。從關聯理論的角度對詩歌英譯進行研究,更符合詩歌英譯中的認知推理活動,對古詩英譯過程有全面、深入的理解。由此可知,文章在關聯理論框架下,從認知語境、交際意圖以及最佳關聯三個角度對《江雪》許淵沖和林健民的兩種譯本進行對比賞析。
二、關聯理論與詩歌翻譯批評
(一)關聯理論
關聯理論提出人們的認知和交際取決于關聯。1986年,由斯珀伯與威爾遜(Sperber & Wilson)在《關聯性:交際與認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中提出,以關聯性概念與關聯原則為基礎分析言語交際中的話語理論,其中關聯原則包括認知原則和交際原則[5]。
在翻譯中,德國學者Gutt最先把關聯理論應用于翻譯,并與1991年出版了《翻譯與關聯:認知與語境》,提出了關聯翻譯理論;他認為翻譯是兩種語言之間進行的一種特殊形式的言語交際行為,是與大腦機制密切聯系的推理過程;人類交際在本質上就是話語的產生和闡釋,為了達到最佳交際效果,人們會考慮聽話者或讀者的認知語境,使之能夠用最小的努力理解話語的意義[6]。語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s)以及讀者在結合原有信息形成新認知中所需的努力(processing efforts)是影響關聯性的兩個重要因素。關聯性的強弱取決于努力和語境效果,在同等條件下,推理努力越小,則關聯性越強,語境效果越大,則關聯性越強。而交際行為包含兩個明示—推理過程:一是原文作者向譯者明示其交際意圖,譯者根據原文的信息、邏輯以及積累的百科知識,以讀者的身份通過認知獲得最佳關聯。二是譯者以交際者的身份在譯文中向譯文讀者轉達原文作者的明示和交際意圖,而讀者則要根據譯文所提供的信息等進行推理,以最小的推理努力獲得最佳關聯[7]。
1988年,沈家煊將關聯理論引入中國。1997年,何自然對關聯理論有所研究并出版《語用學與外語學習》。2005年,趙彥春出版了我國第一部關于關聯理論的翻譯理論著作《翻譯學歸結論》,促進了關聯理論與翻譯學的進一步融合[8]。
(二)詩歌翻譯批評
中國古典詩歌是一種具有獨特且具永恒意義的抒情語言藝術,這種品質讓其在翻譯研究中占有相對重要的位置。詩歌作為文學的一種形式,除了具有本身的美感外,對民族文化精神的傳承還有很大的意義。
中國古典詩歌英譯是翻譯的重難點之一,詩詞詞語豐富、獨特押韻,內含豐富的文化負載詞,濃縮了中國幾千年多樣的文化內涵。
翻譯批評作為連接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的重要渠道,是促進翻譯實踐發展的有力推手。但在翻譯批評領域,鮮少學者涉及詩歌翻譯批評的研究。
(三)關聯理論與詩歌翻譯批評的關系
關聯翻譯理論從物質的角度為詩歌翻譯批評這一富含主觀意味的過程提供了更加客觀的物質視角,同時為詩歌翻譯批評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科學宏觀的理論框架,拓展了翻譯研究的深度與厚度。理論來源于實踐,詩歌翻譯批評也對關聯理論提出了新的要求,對其在翻譯領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路徑,進一步豐富了關聯翻譯理論的內涵,二者相輔相成,共同發展。
三、關聯理論框架下對《江雪》兩種譯本的評析
原文:
江雪
柳宗元(唐)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在純電動車維修中,不到萬不得已不會輕易拆開高壓電池組。當確定故障部位在動力電池組內部時,應按維修手冊及相關資料進行拆裝,檢修過程較復雜且危險,涉及到安全問題。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譯文一(許淵沖譯)
Fishing in Snow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lonely fisherman afloat
Is fishing snow in a lonely boat.
River Snow
Birds disappeared amidst thousands of mountains,
Not a single man is seen on the countless paths;
An old manwith straw hat sits on the lone boat,
He is fishing alone along the cold snowed river.
全詩僅用短短二十字就勾畫出了一幅寂然無聲、幽沉刺骨的寂靜江鄉雪景圖。隨后,作者通過自比老漁翁,表現出自身不屈不撓、剛毅不屈的品質,突出自身意志得不到滿足以及孤寂清苦之感。結合關聯理論,以下從認知語境、交際意圖以及最佳關聯三個角度對《江雪》的兩個譯本進行對比評析。
(一)認知語境
認知語境包括信息、邏輯以及自己原來積累的百科知識。《江雪》短短的一詩中傳遞了很多意象和景物信息,如題目中的江和雪,以及正文中的千山、鳥、萬徑、人蹤、孤舟、翁等。這些信息組合起來給人一種強烈的畫面感:四周寂寥無聲,水面上大雪紛飛、悠白寒冷,只有孤舟上的老翁在獨自垂釣。其實作者要描繪的很簡單,但為了襯托并突出主要的描寫對象:老翁,也就是內心外顯的詩人自己,也為了寄托自己的感情,不惜用這首詩一半的篇幅去描寫其獨釣的環境,且從宏觀的角度,讓這一環境千山無鳥、萬徑無人、寂寥無邊。而描繪的背景越空闊,主要的描寫對象就越突出。“千山”“萬徑”這兩個詞,與“孤舟”和“獨釣”對比,極大地增強了孤獨無依、寒冷寂寥的感染力。此外,天上飛的鳥和路上走的人蹤是很常見、籠統的信息,詩人卻把它們放在“千山”“萬徑”的后面,加之“絕”和“滅”這兩個毫無生命力的詞匯,這就把最常見的動態環境,一下子變成了孤寂靜謐、空闊絕望的靜態景象,形成一種動靜對比強烈、感官沖突明顯的印象。這種強烈的矛盾使得下面兩行原本是靜態的描述,在這種絕對靜寂、沉默的環境下顯得有堅毅和活力的因素在其中。就是這些信息(“山”“鳥”“徑”“人”“舟”“翁”和“江雪”)、邏輯(從一般化的動態環境到特殊化的靜態景象)以及百科知識(“孤舟”“寒江”等詞匯背后的隱喻意)共同組成了這首詩的認知語境。
在譯文中對題目的翻譯方面,譯文一的翻譯為“Fishing in Snow”,突出了“fishing”,也就是漁翁獨釣,這一作者想要表達的主要內容,還表現了一種孤寂清高之感,符合原文想要呈現給讀者的認知語境。譯文二中的翻譯為“River Snow”,直譯的處理雖與原文在字面上更加對應,但沒能突出“釣”這一動景。詩人用“江雪”借景抒情并進行象征,這些手法在漢語中較為普遍,但在翻譯時如果采用直譯的方法,會讓譯文讀者與自己已有的知識產生沖突,從而心生疑惑,喪失了原詩中的審美與意蘊。在前兩句的翻譯上,原文中的“千山”以及“萬徑”為虛指,旨在突出寒冷寂靜的環境,但譯文讀者并不能理解中國文化中的虛指,譯文二中用“thousands of mountains”和“the countless paths”具體的數字來譯,使譯文讀者能在千山和萬徑的實意中看到空闊的背景。相比之下,譯文一中的“from hill to hill”以及“from path to path”用相同的介詞加單數名詞的方式,雖節奏相同、鮮明,但并沒有譯文二直譯下“thousands”和“countless”的沖擊力大。而譯文二“no bird in flight”以及“no man in sight”中“flight”和“sight”的選用,相比于譯文一中的“disappeared”和“seen”,不僅對仗更加工整、韻律更加整齊,跟原文中動態轉靜態的沖突描寫也更加貼合。由此可以看出,兩位譯者通過對作者的意圖進行理解和推斷,分別與自己的已有知識相結合,從而獲得了不同的認知語境,在貼合原文的認知語境方面,譯文二和譯文一在不同語句有不同的特色和優勢。
(二)交際意圖
結合認知語境,詩人想要傳遞的交際意圖為:①前兩句通過景物描寫,突出環境的孤寂和寒冷,從而突顯自己的孤獨和失落。②后兩句用“遠鏡頭”突出描寫的對象,給讀者一種清靜、空遠的感覺,進而傳達詩人以超然物外的心境來進行斗爭的清高孤傲之感。
就孤 獨 感 來 看,在 譯 文 一 中,“a lonely fisherman”以及“in a lonely boat”中兩次“lonely”的選用比譯文二中的“lone”和“alone”更能凸顯人物的孤獨之感。譯文二中“蓑”未能表現出來,譯文一中“蓑笠”皆未能表現出來,這種“漏譯”雖沒影響交際意圖的傳達,但若能在兼顧整齊和節奏的基礎上將其譯出,則更能完整的傳達原文的信息和語境。
在“遠鏡頭”方面,譯文一通過“afloat”以及后面的“fishing”巧妙地表現出在水中靜待垂釣的形象,體現了漁翁的清靜、空遠。譯文二通過“along the cold snowed river”將“鏡頭”拉遠,更加直接地體現出水面的空闊以及漁翁的孤獨。筆者認為,相比于譯文一,譯文二將作者想要表達的意圖更直接地從遠距離的角度傳達出了詩人超然物外的心境。
(三)最佳關聯
原詩的認知語境在熟悉中國文化的讀者中能產生強烈的語境效果,達到預計的交際意圖,產生最佳關聯性[9]。譯者需要充當作者和讀者之間的紐帶,通過提取出信息以及作者意圖,傳達給讀者,調動讀者原有的百科知識與信息,讓原詩中描繪的元素成為新認知語境的一部分。這一過程讓讀者的新、舊認知相互融合,從而創造出強烈的共鳴和同理感,進而實現預計的交際意圖,并讓讀者用最少的努力實現最佳的關聯效果。
在譯文中,譯文一將題目譯為“Fishing in Snow”,相比于譯文二的“River Snow”來看,描寫得更加 具體,畫 面感 更強;結 合譯 文 一 中 的“fisherman”和“fishing snow”,譯者將詩中描繪的場景以及作者的意圖簡單巧妙地提取出來,它避免了上述通過過多的努力降低相關性的問題。另外,譯文一結合譯者對原文的理解,準確地翻譯出作者想要表達的要點,顯性推理得更為合適。
詩中的“寒江雪”,是一個特殊的意象。江,不會存雪,但詩人用“寒江雪”,把“江”和“雪”這兩個意象合并到一起,在使詩中主要描寫的對象更突出之外,還對當時詩人所處的政治環境進行了隱喻。而“寒”字,在點明氣候的同時也凸顯了漁翁的精神世界。譯文一中用“is fishing snow”表達“釣寒江雪”,“snow”作為“fish”的賓語,即“釣雪”,這是一個非常抽象的表達,不免會讓譯文讀者產生疑惑;譯文二中把“snow”處理成環境地點“the cold snowed river”,畫面具體且譯出了“寒”,與前文中烘托出來千山無鳥萬徑無人的寒冷環境相互照應,調動讀者腦中的舊有信息,讓譯文讀者腦中的新舊知識互相作用,突出全詩的重點新場景“fishing alone”,表示在寂寥極寒的情況下,漁翁依然堅持垂釣,反映作者對當時政治環境的抵抗,以及對內心抱負的堅持,這讓譯文更加完整,場景也更加清晰易懂。
由此可知,在最佳關聯性方面,譯文一的標題以及譯文二最后一句的關聯性更優,更準確地實現了預計的交際意圖。
四、結語
在關聯理論框架下,許淵沖先生和林健民先生《江雪》的英譯本在認知語境、交際意圖以及最佳關聯三個角度中各有千秋,二位為中國古典詩歌的英譯以及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通過上述比較研究,可以看到關聯理論對詩歌翻譯批評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詩歌翻譯表現出顯著的“異人異譯”現象大大推動了翻譯活動的發展。詩歌翻譯要能準確地傳達原詩的意象,精準把握作者的意圖。此外,譯者要廓清翻譯過程中的各種障礙,謹慎處理詩歌中豐富的文化負載詞、隱喻以及背后隱匿的思想情感,綜合運用各種翻譯技巧和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