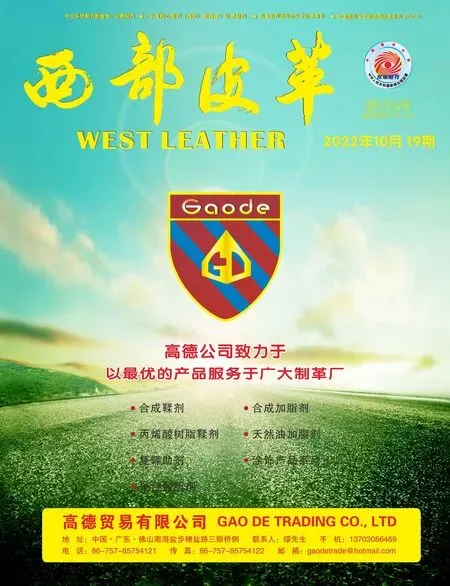鄉村振興背景下越西彝繡的傳承路徑研究
楊芳,劉美瑩
(西南民族大學,四川 成都610041)
鄉村振興戰略是黨和國家的重要戰略部署,明確了要建設“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型農村,為我國新時代的鄉村建設與鄉村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指導。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然要求,亦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支撐。刺繡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中一顆璀璨明珠,在我國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1-2],從其制作材料的選擇到紋樣的取舍無不蘊含著民眾的認知與智慧,但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些民族瑰寶都受到了程度不一的沖擊,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則為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本文試以涼山州越西縣的彝族刺繡為例,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探討其在傳承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在鄉村振興背景之下的傳承路徑。
1 越西彝繡概況
越西轄區內17 鎮3 鄉,全縣總人口約37.4 萬,縣內有彝、漢、藏、回等十多個民族,是一個以彝族為主體的多民族聚居縣①。文中的“越西彝繡”是指在涼山州岳西縣彝族聚居地的特定自然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一種刺繡藝術。彝族刺繡多以圖案的形式體現在五彩斑斕的彝族服飾上,常用圖案紋樣有日、月、星、彩虹、白云、山、水、波紋、雞冠、羊角、牛眼、樹葉、花卉、什物器皿、幾何圖案等,根據圖案需要再用以紅、紫、藍、黃、綠、灰等色彩搭配。彝裝常用彝繡的部位主要是男子的項背、衣襟、袖臂、褲筒,女子的頭帕、衣領、項背、袖臂、煙包等。2021 年7 月,筆者有幸在成都參加了由岳西縣政府牽頭舉辦的“‘美麗鄉村·手藝先行’彝族傳統手工藝傳承發展與鄉村振興主題展”,展覽中所見繡品工藝之獨特、技藝之高超、紋樣之豐富令人嘆為觀止。
越西彝族刺繡是越西縣人民千百年來的智慧結晶,凝結著代代越西人的價值觀念與精神信仰,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蘊,對彝繡的傳承是賦能于鄉村文化建設的重要途徑。同時也能以其為著力點發展經濟,繼而以點帶面,促進鄉村產業發展。
2 越西彝繡的傳承困境
伴隨經濟社會的高度發展,越西彝繡的生存環境已發生極大改變,這為越西彝繡的傳承和發展帶來了諸多挑戰,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2.1 生存空間弱化
這里的“生存空間”是指彝繡產品需求的減少和市場的縮減。過去彝族服飾作為人們生活的必需品,女性均需習得刺繡技藝以為生活所需。然而,外來市場的介入為越西帶來了更多物美價廉的商品服飾,與此同時,人們的思想觀念也逐步發生著變化,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到市場上購買現代服裝。越西籍的一位校友向筆者敘述:“現在的越西,除了農村里的老人還有穿著全套彝族服裝外,其余多數為彝裝和外來流行服裝混穿,學生和兒童幾乎都穿現代流行服裝。”②此般現象就導致了彝裝需求的減少,亦使得愈來愈少的人從事刺繡活動,越西彝繡的傳承漸露危機。可見,當全社會的主導經濟發生變化,某項大眾消費減弱時,原本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某種技藝也就逐漸衰落成為僅有少數人掌握的技藝[3]。
2.2 傳承主體出現斷層
刺繡作為一項口傳心授的“活態”技藝,傳承主體的作用不言而喻。過去,刺繡作為彝族女性的一項必備技能,女孩們從小便開始學習刺繡,而如今孩子們很小就進入學校學習科學文化知識,不再有充足的時間學習刺繡技藝。此外,商品經濟對人們的價值觀亦造成極大影響,越西的年輕人更多選擇外出就業,而少有人決心留在家中學習彝繡、傳承彝繡。筆者在調研過程中就發現,在越西的繡娘群體中多為中老年人,鮮有30 歲以下的繡娘。老一輩傳承主體年歲漸長或離世,而年輕一輩基于主客觀原因不愿意繼續學習刺繡,越西彝繡的傳承人出現了斷層。
2.3 市場拓展不足
就目前而言,越西彝繡的市場主要被定位在彝族群體,針對彝族之外的人群市場生產的成品還不多,然而其精湛的工藝,精美的成品完全具備“走出去”的能力。就筆者所見,越西彝繡2021年于成都舉辦的主題展參展人員主要是部分政府工作人員、媒體機構及部分彝學學者和彝族同胞,很少其他民族和社會領域的人員參加。此外,筆者在訪談過程中一位彝族阿媽也透露出他們的繡品主要是售賣給自己民族人士的信息。越西彝繡若僅僅將受眾定位于本民族本地方之內,其消費市場將受到極大限制,也勢必會影響越西彝繡的傳承與發展,故而筆者認為市場拓展不足是越西彝繡傳承中存在的不可忽視的問題。
3 越西彝繡的傳承路徑
3.1 融入現代生活,拓展適用范圍
非遺之所以會衰落,主要在于它的生產方式、產品審美樣式、管理模式等方面與當下的城市化進程、社會發展已經不太相匹配,急需在傳承非遺的圖形和色彩之美,以及文化符號和手工技藝特征的同時,與當代設計、藝術和現代生活對接,通過改革和創新,適應當代人的審美觀念和實用需求[4]。千百年來,越西彝繡作衡量女子聰慧的標尺,成為越西女性群體的必備技藝,而伴隨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人們對彝繡的使用頻率下降,傳承的必要性亦隨此消減。彝繡傳承過程中最突出問題也正是因為人們生產、生活實踐的改變而帶來的繡品需求減少,致使其不斷被邊緣化。然而,生活方式的改變既是導致越西彝繡式微的原因,也是彝繡創新發展的契機——即從消費群體的現實需求出發,提取越西彝繡的核心元素進行創新生產,打造適合當代生活的產品,進而拓寬彝繡的適用范圍。
彝繡技藝要實現長遠發展,重中之重就是盡可能地融入當下的社會生活,在尊并利用傳統元素的前提下創造符合當下生活方式和審美趣味的繡品。例如選用傳統彝繡的紋案和技法制作外套、披肩、圍巾、提包等現代服飾產品;選用日、月、花草等元素繡制適宜框裱的收藏品等。當彝繡能夠獲得更多受眾,并成為我們在生活中的常見事物時,于其傳承而言就有了更加堅實的基礎。
3.2 關注傳承主體,助力彝繡傳承
傳承人是非遺傳承的核心要素,沒有傳承主體,彝繡的傳承便無從談起。對此,我們一方面要關注彝繡現有傳承人的生存境遇,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對彝繡傳承人的培養。
3.2.1 關注傳承人的生存境遇
過去越西女性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勞作時間相對自由,有足夠的時間從事刺繡活動,但如今女性的職業已發生很大轉變,她們或為家庭經濟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選擇外出就業,或因外出求學而脫離本鄉本土,再無暇從事刺繡手工藝創作。故而我們在探究如何傳承越西彝繡時,要充分利用好鄉村振興的機遇,努力發展彝繡產業,為更多繡娘提供工作崗位和生計來源,進而走出一條既能傳承好彝繡技藝又能關照到傳承主體的雙贏之路。
3.2.2 推動彝繡傳承進校園
據筆者田野調查所知,越西的中小學會邀請部分非遺傳承人前往學校開展主題講座,但是因講述次數不多、時間有限,學生很少能夠和傳承人進行比較深入的交流,這就導致學生對其講述內容僅僅停留在淺顯的認知層面。筆者認為可將彝繡知識納入越西現有中小學美術課與勞動課課程教學范圍,聘請有資歷的傳承人作為專項教師,為學生教授有關彝繡的理論知識和制作技藝,讓學生體驗、學習倍具魅力的彝族刺繡,并在實際操作中提升對彝繡的認識,培養對彝繡的興趣。
3.3 拓展銷售范圍,轉變市場定位
現有彝繡產品多將消費群體定位在彝族群體內部,這極大阻礙了越西彝繡銷售市場的擴大,因此,越西彝繡應轉變銷售策略以走出越西,走出涼山。首先便是生產適應市場需求的產品,除上文中所論述到的創意生產之外,還應對消費群體進行分級,即根據消費者的消費力度和需求采取“手工+機器”相結合的制作模式。柳宗悅在《日本手工藝》中談道:“手與機器的根本區別在于,手總是與心相連,而機器則是無心的。所以手工藝作業中會發生奇跡,因為那不是單純的手在勞動,背后有心的控制,手制作物品,給予勞動的快樂,使人遵守道德,這是賦予物品美之性質的因素。所以,手工藝作業也可以說成是心之作業”[5]。純手工技藝產品凝結著更多的無差別人類勞動,價格必然居高,此時,消費群體受到限制。但若采取“手工+機器”的模式,用機器生產胚樣,再由繡娘在關鍵位置繡制紋案,不僅可以提高生產效率,還能大大降低繡品的價格,讓更多人能夠消費得起彝繡產品。
其次就是提升越西彝繡的對外知名度,對此可以充分利用網絡自媒體平臺,通過抖音短視頻、直播、微博等平臺記錄彝繡的生產制作過程,同時配以口頭或文字解說,展示越西繡娘的匠人精神和精湛技藝,從而達到良好的宣傳效果。
3.4 增加文化知識教學,豐富培訓內容
在越西,政府與相關行業協會已將技能培訓納入彝繡傳承重要途徑,但是現有培訓多是針對繡娘的刺繡技藝進行技能方面的輔導,缺乏對彝繡文化知識層面的教學。此外,個性化的市場要求也對繡娘提出更多挑戰,因此,筆者認為還需加強對彝繡創意與設計理念方面的培訓,只有這樣,越西彝繡才會有更好的發展和更廣闊的出路。
3.4.1 增加越西彝繡的文化知識教學
所有的刺繡作品,都不只是一種祝福,一種愿望,還滲透著中華數千年的傳統思想,集傳統文化、風俗、地域特征于一身,每件刺繡作品都承載著厚厚的文化內涵[6]。越西彝繡正是因其特殊的淵源、地理環境與歷史發展,而造就了其獨特的藝術風格。故而彝繡的傳承不僅僅需要技藝的沿襲,獨具魅力的越西彝族文化作為彝繡靈魂所在,亦是越西彝繡傳承發展過程中的急需關注的重點。訪談過程中,每當筆者向繡娘問起她們所繡圖案含義以及色彩選取原因等問題時,得到的總是諸如“一直都是這樣”“就這樣傳下來滴”一般的答案,可見,繡娘對于刺繡文化的內涵知之甚少,所以在培訓過程中應當增添這方面內容,提升繡娘對彝繡文化內涵與文化價值的了解,反之,傳承下來的技藝也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3.4.2 增加創意與設計培訓
彝繡技能的培訓,提升了繡娘的刺繡技能,但于彝繡產業發展而言,越西彝繡創意產品的開發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就要求繡娘們不只是要具備良好的刺繡功底,同時還需要有創意的思維和一定將傳統彝繡與當下生活相結合的能力。對此,在培訓課程中,首先需要為繡娘及時提供現行市場流行的紋樣、款式等,豐富繡娘現有的刺繡內容,啟發她們的創作做思維;其次針對傳統彝繡沒有的設計內容,則需專人教學,指導繡娘們學習新事物的刺繡技法。對此,可采取與高校合作的方式,利用高校師資資源為越西繡娘培訓設計知識,還可協商建設高校校外實踐基地,一方面為越西彝繡發展注入活力,另一方面也可起到對外傳播作用。還可帶領繡娘們前往成都等大城市開闊眼界,了解市場流行趨勢。
3.5 數字化記錄,永久性傳承
數字化記錄,通俗地說,就是以各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作為記錄對象,通過錄入、掃描、攝影、轉錄、攝像等方式生成數字資源[7]。刺繡技藝是高度動態化的過程,數字化手段剛好契合這一需求,這就使得數字化記錄成為彝繡傳承不可替代的途徑之一。由于刺繡手藝高深的繡娘年歲漸老,一些獨門技藝存在消失的風險,對此,可以邀請資深繡娘演繹刺繡的整個流程,并講述刺繡方法要點、顏色搭配、圖案意涵等內容,利用相機等工具進行影像錄制,如此,無形的記憶則變成了“有形”的實體。這種方式不僅有利于對彝繡技藝進行永久性記錄,避免技藝失傳。與此同時,采錄的影像、文字等還能供技藝不足者學習和相關學術研究之用。
4 結語
越西彝繡產生于越西獨特的歷史文化環境,承載著越西民眾的精神信仰與價值追求,“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傳承好彝繡既能夠使其經濟價值得到更好實現,也可推動越西地方文化與習俗的傳遞,助力鄉村振興。但目前越西彝繡傳承還存在諸多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堅持圍繞彝繡核心元素進行創意生產,注重傳承人的培養、文化內涵的沿襲和市場的拓展,同時,也要認識到數字化應用對越西彝繡傳承的重要意義。
注釋:
①截至2022 年3 月數據,https://www.yuexi.gov.cn。
②訪談時間:2022 年3 月10 日;訪談地點:成都;訪談人:伍各莫,彝族,23 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