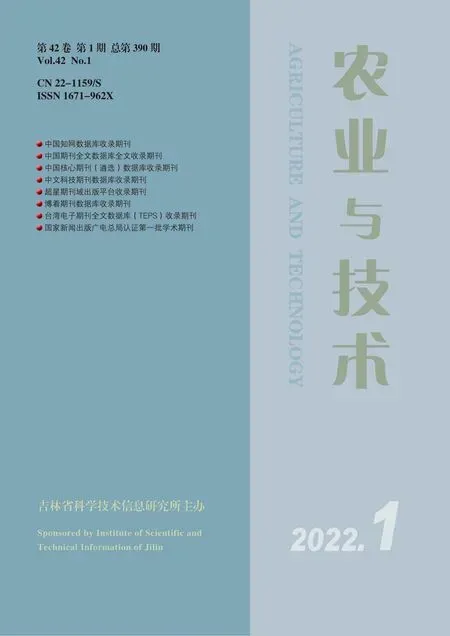和田荒漠化地區種植苜蓿現狀
任 然
(和田師范專科學校,新疆 和田 848000)
1 和田地區荒漠化現狀
沙漠化是世界十分重視的環境問題之一,我國的荒漠化形勢非常嚴峻,新疆是我國荒漠化最嚴重的地區,其中,最嚴重地區在南疆和田。和田地區下轄1個縣級市、7個縣,北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南臨昆侖山,東西距離670km,南北距離570km,總面積24.89×104km2。綠洲占3.7%,山地占33.3%,沙漠戈壁占63%。和田屬干旱荒漠性氣候,全年降水稀少,多風沙天氣,年均降水量35mm,年均蒸發量高達2480mm。四季多風沙,每年浮塵天氣220d以上,其中濃浮塵(沙塵暴)天氣在60d左右。春季極為缺水,水資源時空、地域分配不均勻等,致使農業發展受到嚴重制約。
文獻資料顯示,沙漠化主要原因是自然條件和人類不合理活動導致。國內外學者通過遙感技術分析植被覆蓋度、土壤類型、水資源、沙丘活動、沙源擴散路徑等,研究沙漠化成因及防治對策。孫紅梅等[1]對和田河流域綠洲荒漠過渡帶土地荒漠化過程研究得出,風動力是和田荒漠化的主要動力原因,本質是土壤的風力侵蝕、堆積、沙粒遷移;植被是和田土地荒漠化的重要決定因素,固沙植物主要是胡楊、紅柳、駱駝刺;受人文環境影響,植被破壞嚴重。王景新等[2]利用紅柳大蕓改良荒漠化土地,生態效益和經濟價值顯著。漢瑞英等[3]通過“源-匯”理論,應用生態阻力面模型厘清和田地區沙源擴散路徑,和田地區一級源地面積占73.57%,分布和田地區西北部民豐縣,沙源擴散作用最強;二級源地面積占17.35%,分布和田地區東南部于田縣、皮山縣,沙源擴散作用集中;三級源地面積占9.07%,分布零星綠洲、荒漠交錯區,沙源擴散作用最弱,是沙化防治關鍵區域。宮靜等[4]通過“壓力—狀態—響應”框架模型得出一致結論,和田地區生態環境嚴重脆弱是洛浦縣和民豐縣。孫智斌[5]利用RS、GIS技術對1990—2015年和田地區土地利用變化得出,2000年前和田地區耕地、草地分別增加413.75km2、377.24km2,之后隨著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和田經濟快速發展,草地、林地減小顯著,導致草地退化、土地荒漠化。
第3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提出,要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決守住生態保護紅線,統籌開展治沙治水和森林草原保護工作,讓大美新疆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和田人民積極開展治沙工作,種植胡楊、紅柳、大蕓、苜蓿等固沙植物。
2 苜蓿研究現狀
苜蓿在我國已有兩千多年的種植歷史,西漢時期通過絲綢之路引入我國,自古代起就被廣泛種植。苜蓿是一種多年生豆科牧草,分布廣,具有耐旱、耐寒、耐貧瘠、再生性強、產量高、品質好、適口性好的特點,能為家畜提供優質蛋白飼料,同時其根系利用根瘤菌固定氮素,起到提高土壤有機質的作用,改善土壤理化性質,可作為綠肥改良土壤,因此被人們稱為“牧草之王”。我國苜蓿種植以牧草為主,隨著苜蓿新品種的廣泛應用、栽培水平的提高、畜牧業生產的發展以及國際市場上牧草需求量的增加,栽培面積不斷擴大,主要集中于內蒙古、甘肅、四川、黑龍江、吉林等地區。
2.1 苜蓿種植技術研究進展
苜蓿種類多樣,分為紫花苜蓿、褐斑苜蓿、天藍苜蓿、小苜蓿、南苜蓿等,由于我國地域遼闊,氣候類型多樣,不同地區適宜種植苜蓿品種有差異。俞雪等[6]通過隸屬函數、氣候綜合分析得出,適合石河子地區種植越冬苜蓿品種為肇東和敖漢。程貝等[7]研究得出,隨著硒濃度的升高,苜蓿發芽率苗長鮮質量活力指數都呈現減小的趨勢。李威等[8]研究得出,苜蓿—玉米間作和苜蓿—燕麥草間作模式產量高于苜蓿單作,苜蓿—燕麥草間作模式下產量最高。藺芳等[9]通過研究紫花苜蓿與禾本科牧草間作模式下光能特征得出,紫花苜蓿與小黑麥(C3植物)間作模式的產量優勢最顯著,間作模式下小黑麥和玉米的產量表現優勢,紫花苜蓿的產量表現劣勢;禾本科牧草通過提高CO2的羧化固定能力,增強凈光合速率,紫花苜蓿提高葉片中葉綠素b的含量,增強對光能的傳遞,提高在弱光下的光合速率,保證其正常生長。劉選帥等[10]通過研究滴灌條件下苜蓿不同花期農藝性狀與產量關系得出,隨著花期推進,紫花苜蓿單茬產量呈增高趨勢,盛花期達到最高,但總干草產量較低,綜合考慮苜蓿的營養品質、總干草產量、種植成本等因素,初花后期(開花10%)刈割效果最佳。
前期現有報道關于施肥對苜蓿影響的研究主要是在單一或間作對不同施肥時期、施肥量、施肥方式、不同氮磷鉀肥配比影響;近期文獻綜述報道集中在生物有機肥和微肥對苜蓿影響的研究。李春容等[11]研究得出,微生物菌劑相比復合肥對牧草的分蘗數、株高、單株鮮重等生長性狀更高,復合肥(60g·m-2)和微生物菌劑(60g·m-2)混施康藏高原牧草產量最高124.78t·hm-2。彭琪[12]研究得出,不同土壤類型和硒處理對苜蓿的發芽率影響不顯著,硒酸鹽對苜蓿幼苗生長的抑制作用比亞硒酸鹽更顯著。紫花苜蓿根系和非根系土壤速效鉀含量最高,速效鉀能提高植株糖的合成、氮素的利用、蛋白酶和淀粉酶的活性。
2.2 苜蓿營養品質的研究進展
苜蓿的營養成分主要包括碳水化合物、粗蛋白、維生素、礦物質等,不僅可以在畜牧業生產中作為飼料,而且苜蓿的嫩葉嫩芽人們可以鮮食,同時在生物制藥方面有重要的應用價值。苜蓿屬于清涼性植物,具有清熱利尿功效。苜蓿素和苜蓿酚等物質有止咳平喘的功效。苜蓿維生素K含量高具有凝血功能,可用于止血。苜蓿鐵元素含量高,同時富含維生素B,具有預防貧血作用。苜蓿粗纖維促進腸胃蠕動,具有通便排毒功效。苜蓿多糖能增強免疫調節功能,具有抗腫瘤、抗病毒等作用;苜蓿多糖作為飼料添加劑,還能夠增強畜禽免疫力,促進其生長和繁殖,降低疾病死亡率,同時無藥物殘留,提高畜產品品質,確保食品綠色安全;苜蓿多糖的提取方法有微波輔助提取法、超聲波提取法、超濾提取法、酶解提取法、熱水浸提法等[13]。苜蓿粗蛋白含量高,碳水化合物含量低,甜高粱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粗蛋白含量低,單獨飼喂畜禽不能滿足營養需求,苜蓿與甜高粱按混青貯比40∶60時,卡拉庫爾羊消化道內消化蛋白、淀粉、脂肪、纖維素的酶活性最高[14]。
3 和田地區苜蓿種植現狀
畜牧產業在和田地區歷史悠久,作為和田地區傳統的基礎產業之一,傳統養殖業收入在農民收入中占比超過33%。政府積極引導通過“十萬”、“百萬”、“千萬”、“億”工程,開展特色產業助力鄉村振興;2019年將帶動形成驢10萬頭的“十萬”規模;多胎肉羊100萬只的“百萬”規模;鵝1500多萬只、兔1500多萬只、鴿1580多萬只的“千萬”規模;菌包、香菇2億袋的“億”規模。近年來,隨著和田畜牧業發展迅速,飼料短缺,苜蓿作為優質飼料被廣泛種植。新疆是中國紫花苜蓿的主要種植區域之一,隨著畜牧產業的集約化快速發展,種植面積逐漸增加。當前我國的苜蓿種植業處于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2020年我國苜蓿種植面積633hm2,苜蓿干草總產400萬t,雖然國產苜蓿還有很大缺口,但是整體產量得到提高。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對奶產品、禽蛋和牛羊肉等動物性食品的需求明顯增加,苜蓿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和能量,是畜禽主要蛋白質飼料來源。根據中國海關數據統計,2020年我國進口苜蓿干草135.81萬t,從美國進口量為118.52萬t,占苜蓿總進口量87.27%,優質苜蓿主要從美國、西班牙等國家進口。
新疆和田地區位于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極度干旱少雨,導致人均耕地面積低于667m2,是全疆人均耕地最少的地區。開墾荒地種植苜蓿是助力鄉村振興的重要措施,種植苜蓿政府補貼100元·667m-2,調動農民種植苜蓿的積極性,為和田畜牧業發展提供飼料保障,同時提高土壤肥力,防風固沙,降低沙塵暴,水土保持,改良土壤鹽堿化,維護生物多樣性,是改善生態環境的重要舉措。
和田地區農民種植苜蓿存在以下問題。播種量存在隨機性。農民根據自己的經驗種植,播種量2~5kg·667m-2,導致出苗密度低或密度過高2種極端情況,不利于機械化操作。施肥存在盲目性。前期整地施肥,一般情況撒施尿素20kg·667m-2,部分農民增施農家肥。農民為節約成本,整個生育期不施肥,造成產量低,部分農民在苜蓿生育中期撒施尿素10kg·667m-2,并進行大水漫灌,造成水肥流失,降低肥料的利用率。傳統模式澆水。采用大水漫灌模式澆水,不僅浪費寶貴的水資源,而且造成土壤鹽堿化。人工收割。由于農戶種植面積小且分散,無法實現機械化生產收獲,靠傳統人工收割、打捆,勞動強度大,種植效益低。苜蓿生產管理方面,農民缺乏種植技術,田間管理水平落后,播種后對苜蓿不管不問,雜草叢生,導致苜蓿產量低且品質差。
企業大面積種植苜蓿采用噴灌模式,實現水肥一體化,節約用水,提高肥料利用率,但最佳施肥量不確定;田間管理技術成熟,機械化作業,降低勞動成本,提高種植效益。
為實現和田地區苜蓿種植科學高效,組織農民學習苜蓿種植技術,加強科學技術的宣傳,提高田間管理能力。從檢索到的文獻資料來看,一定產量目標下苜蓿合理施肥技術等方面的研究較多,而針對和田沙漠地區苜蓿養分吸收、運轉、分布規律缺乏系統研究,因此,在施肥實踐中存在憑經驗盲目施肥現象,農民往往重氮肥、輕磷肥和有機肥,使得苜蓿產量和肥料利用率較低。為了提高苜蓿產量和品質,克服盲目施肥,提高肥料利用率和經濟效益,開展和田地區苜蓿養分吸收、運轉、分布規律研究,旨在探明和田地區苜蓿生育期植株需肥規律,確定苜蓿最佳施肥量,實現水肥一體化精準施肥澆水,對于和田地區節約用水、促進當地農業種植結構調整、提高苜蓿產量和改善品質、提高肥料利用率和降低生產成本、增加農民收入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應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