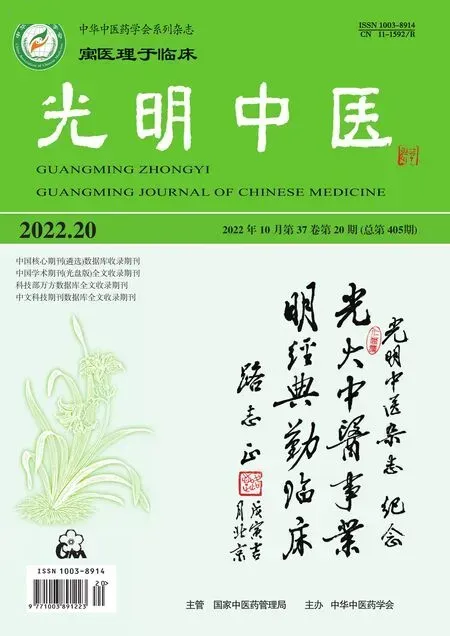唐代醫學交流初探
——以敦煌醫學卷子為例
張冀豫 梁尚華
敦煌醫學卷子是指敦煌古籍中與醫學相關的古籍著作,成書于六朝與隋唐時期。按《敦煌遺書遺書總目索引》[1]載總敦煌文獻約2萬多種。具體與醫學相關文獻《敦煌古醫籍考釋》[2]中載其有104種。醫方達1100余首,居現有醫學出土文獻數量上占據首位[3]。其相關內容中,除醫經、本草、診斷等醫學書籍,更有非漢語醫學文獻的傳譯與佛教醫學等相關內容。其醫學文獻數量相對集中,且能呈現一定時間內敦煌醫學活動的全貌提供理論基礎,因此對完善中醫學唐代與唐以前交流發展提供了新的視野。本文以近些年來敦煌醫學研究為載體,以醫學理論、醫籍融合、醫者形象、醫學互動、藥材使用為方向,立足敦煌醫學卷子,探究唐代域外醫學的交流情況。
1 醫學理論
敦煌出土張仲景《五藏論》署名張仲景撰,已知抄本4份P.2115;P.2378;P.2755;S.5614。書中論述以黃帝與耆婆并提,四大五常并用[1]。顯示出濃厚印度醫學與中原醫學的交融。其中P.2115V《張仲景五藏論》原卷題作“五臟論一卷,張仲景撰”。依其題目可知,五藏理論來源于中醫,但同時其內容中亦有“四大五蔭,假合成身。一大不調,百病俱起”[4]。關于四大說法,可與印度阿育吠陀醫學尋找淵源,其四大指地水火風。吳天竺沙門竺律炎共支越譯《佛說佛醫經》:“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風”。闡述了地水火風理論與身體的聯系。而同時,關于張仲景《五藏論》是否為托名所做,目前尚未有定論。但五藏與四象理論的同時出現說明,敦煌地區醫學的相互交融。尤其中印醫學的交匯編纂,奠定了唐代醫學交融的特點。
敦煌本P2675《新集備急灸經》云:“四大成身,一脈不調,百病皆起”。參照《大正新修大藏經》,此書為日本大正13年高楠順次郎和渡邊海旭發起的佛經編纂合集,收入中國歷代各版藏經目錄和日本各寺院所藏的寫本和刻本藏經目錄。其中《說無詬稱經疏》卷三經文“四百四病者:一大不調,一百一病生”。此處二者記載文字類似。關于“脈”與“大”的區別,有學者考證后,認為此處灸經為人體經絡穴位所灸之處,灸經強調脈的重要性,因此作者便將“一大”改為“一脈”[5]。印度醫學認為,構成人體的四大因素保持了人體的平衡,這與中醫陰陽五行理論相類似,四大理論在中醫灸法中的吸收應用,強調灸法治療疾病之多,與灸法脈的重要性。
2 醫籍融合
2.1 《醫理精華》《醫理精華》由公元7世紀印度醫學家拉維笈多編纂。《醫理精華》(Siddhasara)音譯悉曇娑羅,是印度生命吠陀(Ayurveda,音譯阿輸吠陀) 醫學體系中的一部古代醫學著作。記載了阿育吠陀醫學理論及相關疾病治療。其最初由梵語書寫,隨著書籍流傳,轉譯為多種語言。其中于闐語本出自敦煌藏經洞,現收藏于大英博物館東方寫本及印度事務部。另可見該書籍,回鶻文醫學殘卷(Si.22.10;Si.6.31).回鶻本與梵文本存在差距,這可能與流傳過程中多種醫學(民間,印度,中醫)等交叉融合相關[6]。
2.2 《耆婆書》《耆婆書》作為一部印度古典醫學著作,是一部藥方集。于闐—梵語雙語寫本出自敦煌藏經洞(IOL Khot87-110)轉手斯坦因,藏于大英圖書館。可看作是敦煌地區醫學交流的融合產物。敦煌在一段時間內屬于于闐,因此該地區醫學出現印度阿育吠陀醫學融合。是與于闐本土醫學的交叉融合[7]。
2.3 醫學殘卷敦煌醫學卷子中,以藏語書寫的醫學殘卷有醫療術殘卷,火灸療法寫卷,針灸穴位圖,藏醫方殘卷,脈診殘卷等。其中“火灸療法”(P.t.1044)部分還明確指出:“本醫方是從印度王土搜集的外科手術療法之一”[8]。其中有“取自府庫的治療各種疾病的醫方”以及“本外科手術療法醫方,并非出自庫藏,是在搜集所有醫方的基礎上,再結合象雄的療法而寫成”[9]。這些寫卷不僅體現了當時藏族人民的醫學成就、宗教(苯教、佛教)與醫療的關系以及藏醫療的民俗特點,也體現了藏醫與印醫、中醫之間的交流,甚至還反映中亞對其影響。
3 醫者形象
活躍于敦煌地區的醫者形象可大致分為中醫,僧醫,胡醫。據現有醫學材料可將醫者以此暫且劃分。
3.1 唐醫唐代醫學教育完善,唐太醫署的設立為唐代醫學教育標準化奠定基礎。有文獻指出,敦煌地區的醫療已與長安無恙[10]。包括醫療場所,醫學官職的設置。P.2657載《唐天寶年間敦煌郡敦煌縣差科簿》:“令狐思珍,載五十一,翊衛,醫學博士”。此為敦煌卷子中記載惟一敦煌地方醫官[11]。醫學博士在敦煌的設立,是唐代對州道地方區域醫療的重視,同時依照卷子標題,敦煌縣差科簿而并非單設于敦煌郡。可看作是唐代官方醫療在郡縣范圍的普及。
3.2 僧醫敦煌地區由于佛學東進的影響,大量僧人活躍于敦煌地區。由于僧人佛學的影響,敦煌地區的寺院樂善布施也成為其區域特點。在具體的醫療實踐中,敦煌文獻中記載10余人。僧醫借助寺廟,以佛教為載體,中古時期的佛寺僧尼,在醫療活動中承擔過較為重要的社會角色[12]。
比較顯著的例子是,佛教徒在救治麻風病人時,能夠身心投入,給予關愛。道宣《續高僧傳》記載了數位高僧這樣的事跡。如天臺山瀑布寺釋慧達:“有陳之日,癘疫大行,百姓斃者殆其過半。達內興慈施,于楊都大市建大藥藏,須者便給,拯濟彌隆”。慧達法師為癘疫百姓在楊都設立大藥藏,進行免費施藥,救助了眾多的普通患者。北齊的僧稠法師:后移止青羅山,受諸癘疾供養。敦煌齋愿文類型的文獻中,有一類是患文,主要針對患者而用,旨在祈禱神靈,祝愿患者早日康復。北京大學圖書館藏BD192《諸文要集》的第72~78行,也是“患差”和“婦人患差”的內容[13]。
3.3 胡醫胡人在敦煌的出現伴隨絲綢之路,粟特人生活與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一帶,自東漢至宋代,往來活躍在絲綢之路上 此處關于胡醫的記載,敦煌文獻中可見粟特人史再盈醫療記載。S.4363載其“習耆婆秘密之神方”“效榆附宏深之妙數”[14]。耆婆之術來源于印度,榆附為上古中原名醫,中印兩處醫學匯聚于粟特人史再盈。其身上體現了粟特,中原,印度的三重特質。S.367《沙州伊州地志》伊吾縣:“火襖廟,中有素書形像無數,有襖主翟槃陀者……以發系其本”。翟槃陀是粟特人[15],此段記載腸外科手術相關,作為粟特人醫療實踐的示例。
4 醫學互動
敦煌作為絲綢之路上的交通要塞,溝通了西域與長安經濟的同時,也同樣存在醫事相關活動的互動。這其中就包括醫藥貿易、醫籍以及藥方相關。
于闐國(前232—1006年)是古代西域佛教王國,中國唐代安西都護府安西四鎮之一。于闐位于塔里木盆地南沿,處于長安,中亞,西藏交匯之地。圣彼得堡所藏敦煌文獻中,至少有3件漢語醫學殘卷出土于麻札格地區。其中Or8212/720殘簡中出現“婦人不用”“兩枚”“以骨石,雞子”[16]。據陳國燦[17]推測,其內容涉及相關本草藥物說明,但未涉及具體醫書。除于闐地區出土資料外,敦煌地區亦出現先關于闐語書寫卷方[14]。陳明對比了印度醫學著作《醫理精華》,發現敦煌出土的IOL Khot S.9“糖蜜與牛奶合煮。它應該溫服。它(此劑藥)可利尿”[13]。值得討論的是,敦煌地區出土的該醫簡以于闐語書寫,其內容由于印度醫學《醫理精華》內容存在相似性。因此有理由相信,唐代敦煌西域醫學的交流已經出現,并且伴隨經濟,貿易,交流呈現出融合態勢。
由于吐蕃在公元7世紀強盛后,敦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吐蕃的領地。因此在出土的相關醫學文書中,可見到醫學典籍與民間驗方的集合。P.t.1057《醫療術》“取開自府庫的治療各種疾病的醫方”此處,府庫即為官方庫藏。另有民間火灸療法等療法收集。如p.t127.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地區流傳的吐蕃醫學相關中,半數以上的植物藥名為波斯梵語音譯而來。說明其與印度阿育吠陀醫學的深遠聯系[17]。
5 藥材使用
中醫學治療強調三因至宜,即因時,因地,因人。因此不同區域的藥物使用便出現一定的差別。敦煌本《張仲景五藏論》中引用敦煌道地藥材“藍田玉屑,中臺麝香,河內牛膝,上蔡防風,晉地龍骨,泰山茯苓”[18]。此類藥材的使用在中醫中占有較大比重。藥物治療功效涉及解表、活血、安神、健脾等功效。
除相關本草類著作中所見藥物。P.2882殘卷亦有相關唐代醫學方劑記載[19],其中染發方中涉及阿愚濡潬泥,其名稱來源于印度。因此在藥物的使用中,具體的治療已經涉及中外藥物的聯合使用。
而同時關于另一味藥物石蜜的使用,是中印,中波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20]。其在敦煌醫學中用作眼疾,上氣,咳嗽,吐血等諸多方面。P.3930醫學卷子中載“治眼風赤癢方”“治上氣氣斷方”“治上氣咳嗽方”。以醫方推測,其使用原理來自對蜜潤下功能的發揮,因此對于咳嗽,風燥等一類需滋潤類藥物進行治療,具有良好效果。而同時由于,外來藥物在使用過程中,存在一定使用功能的改變。此外,在印度醫學中,《大正新修大藏經》:“若令人轉老作少者,取生石蜜和藥涂面及涂發,即如三十五男女相似”[21],此處石蜜單獨使用,用作養生延年佳品,在藥材不同的使用背景下產生了差異。
6 結論
敦煌醫學的出現伴隨絲綢之路的興盛。其發展考量可從2個維度進行考量。①六朝到隋唐時期見證了中古時期的發展,醫學卷子見證了唐代的醫療與發展。②地理跨度,由于所處西北地區的區域獨立性,使得敦煌成為絲綢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樞紐。連接成為連接西亞與西藏,印度的重要樞紐。加之歷史上,敦煌地區曾被于闐、吐蕃等占領,因此亦受少數民族等醫療文化的沖撞。因此醫學卷子的出現常根植于中原文化,亦受外來因素的影響。這對研究唐代醫學與域外醫學的研究提供了文獻的重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