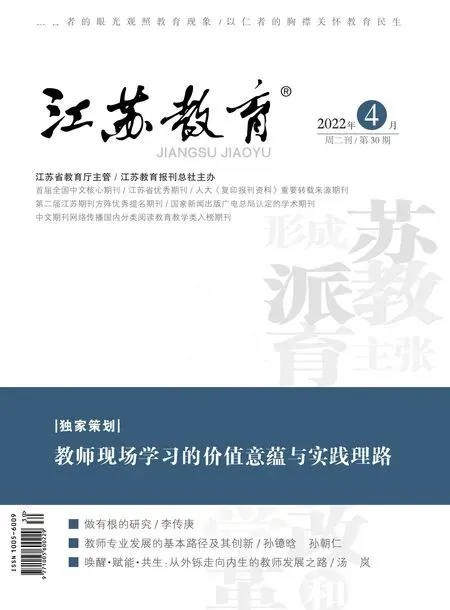回到現(xiàn)場:在育人中實(shí)現(xiàn)教師的真正成長
張曉東
2018 年1 月,中共中央、國務(wù)院正式出臺《關(guān)于全面深化新時(shí)代教師隊(duì)伍建設(shè)改革的意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中央頒布的第一個(gè)教師隊(duì)伍建設(shè)文件。關(guān)注教師發(fā)展已經(jīng)成為世界性潮流,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特別強(qiáng)調(diào):“我們必須比以往任何時(shí)候都更加看重教師和教育工作者,將他們作為全面推動(dòng)變革的力量。”[1]教師發(fā)展已經(jīng)成為這個(gè)時(shí)代的重要主題,不過教師的發(fā)展離不開學(xué)生的發(fā)展,沒有學(xué)生的發(fā)展就沒有教師的真正發(fā)展。教師與學(xué)生是教育共同體,在本質(zhì)上是我與你的關(guān)系,而“這種我與你的關(guān)系是人類歷史文化的核心。可以說,任何中斷這種我和你的對話關(guān)系,均使人類萎縮”[2]。教育是師生之間的人性對話和精神敞亮,離開了任何一方的發(fā)展都不能體現(xiàn)教育存在的意義。回到教育的發(fā)生現(xiàn)場,深深扎根于教育的大地,從育人的角度審視教師發(fā)展,可以充分體現(xiàn)教師獨(dú)特的存在價(jià)值,從而最終達(dá)成師生生命的同構(gòu)共生。
一、以道德人格為邏輯起點(diǎn),重塑育人的價(jià)值內(nèi)核
幾千年來,中國人一直把德性作為立身之本。2014 年5 月,習(xí)近平總書記在考察北京大學(xué)時(shí)強(qiáng)調(diào):“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這是站在時(shí)代發(fā)展的角度對我們提出的道德要求,是“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wù)”的教育工作者必須堅(jiān)持的基本準(zhǔn)繩和價(jià)值尺度,可以將其濃縮為教師的“道德人格”。“道德人格就是一個(gè)人的道德品質(zhì)、價(jià)值、尊嚴(yán)以及道德影響力等的綜合體現(xiàn),也就是說,道德人格是個(gè)體道德素質(zh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整體展現(xiàn),道德行為對他人的影響,他人對此人的評價(jià)。”[3]道德人格是教師整體道德風(fēng)貌的呈現(xiàn),而其中的內(nèi)在線索就是價(jià)值,是教師長期沉淀下來的道德認(rèn)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為,并經(jīng)過漫長歲月的淬煉,而成為教師穩(wěn)定的價(jià)值觀、世界觀、教育觀和教育哲學(xué),幫助教師在一個(gè)又一個(gè)人生的十字路口進(jìn)行正確判斷和抉擇。更為重要的是,教育從本質(zhì)上看就是價(jià)值觀教育和人格教育,是把國家意志和核心價(jià)值觀轉(zhuǎn)化為學(xué)生的價(jià)值信仰和價(jià)值追求,對學(xué)生進(jìn)行價(jià)值傳遞和價(jià)值培育,實(shí)際上就是在回答“培養(yǎng)什么人、怎么培養(yǎng)人和為誰培養(yǎng)人”這一根本問題。
蘇霍姆林斯基說:“只有在教師關(guān)懷學(xué)生人格尊嚴(yán)時(shí),教導(dǎo)才能成為教育。就本質(zhì)而言,教育的核心就是關(guān)懷學(xué)生,讓他經(jīng)常具有作為智力勞動(dòng)者的自尊感,作為公民的自尊感,作為自己父母兒女的自尊感,作為因自己崇高的意向、激情和成績而變得美好起來的個(gè)人的自尊感。”[4]沒有對學(xué)生的人格培育,恐怕難以稱之為教育,或者說,這樣的教育一定是不完整的,也沒有把握住教育的根本所在。要讓學(xué)生具有人格尊嚴(yán),實(shí)現(xiàn)理想中充滿人格的教育,教師自身要有人格尊嚴(yán),要有高尚的道德人格和道德情操。如果教師沒有強(qiáng)烈而堅(jiān)定的價(jià)值信念,用什么來引領(lǐng)兒童的發(fā)展?我們一直強(qiáng)調(diào)“德高為師、身正為范”,是把教師作為學(xué)生學(xué)習(xí)和仿效的榜樣。更準(zhǔn)確地說,孩子們不僅僅是來跟教師學(xué)習(xí)知識和技能的,更是來跟教師學(xué)習(xí)如何做人的。學(xué)做人就是形成自己成熟的價(jià)值觀和世界觀,形成自己的道德人格。所以,我們一定要充分關(guān)注價(jià)值塑造和價(jià)值關(guān)懷,將其作為師生相伴而生的邏輯起點(diǎn),共同展開富有內(nèi)在魅力的價(jià)值之旅。
二、以兒童研究為重要抓手,實(shí)現(xiàn)育人的核心關(guān)切
當(dāng)代著名教育家李吉林把自己比作“長大的兒童”,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畫卷。和藹可親的李老師站在一群孩子中間,洋溢著幸福而天真的笑容,在此刻,瞬間變成了永恒。童年深深地刻在了李老師的生命里,李老師的生命在童年中實(shí)現(xiàn)了延展,以其卓越的一生告訴我們一個(gè)道理:教育永遠(yuǎn)都要親近兒童。的確,“成人應(yīng)該牢記,童年絕不是有意為難教育者而存在的,它是造物主給人的恩惠,為的是讓人永遠(yuǎn)去認(rèn)識無限。”[5]童年和兒童不是讓人生畏的麻煩,不是讓我們頭疼的調(diào)皮,而是需要我們進(jìn)一步深入認(rèn)識的對象。我們要勇敢地向兒童學(xué)習(xí),在認(rèn)識他們的過程中認(rèn)識無限,回歸教育的初心使命和基本規(guī)律。一些偉大的人物往往是孩子氣的,在生活中顯得很率性,某些時(shí)候還有點(diǎn)“不成熟”。但是,恰恰是這種率性和“不成熟”,讓他們更像一個(gè)“大寫的人”;也正是因?yàn)榧冋娴暮⒆託猓沟盟麄兗葌ゴ笥挚蓯劭捎H。認(rèn)識兒童是為了更好地認(rèn)識自己,葆有童年帶給我們的純真和清澈,一方面幫助自己實(shí)現(xiàn)最真實(shí)的存在;另一方面進(jìn)一步明確自身的職責(zé),引領(lǐng)兒童生動(dòng)活潑地成長。
我們要努力走進(jìn)兒童的世界,陪伴他們一起享受教育的幸福與快樂,因?yàn)橥曛挥幸淮危仓挥幸淮危@兩者都不能從頭再來。所以,我們一定“要愛護(hù)兒童,幫他們進(jìn)行游戲,使他們快樂,培養(yǎng)他們可愛的本能。你們當(dāng)中,誰不時(shí)刻依戀那始終是喜笑顏開、心情恬靜的童年?你們?yōu)槭裁床蛔屘煺鏍€漫的兒童享受那稍縱即逝的時(shí)光,為什么要?jiǎng)儕Z他們絕不會(huì)糟蹋的極其珍貴的財(cái)富”[6]。每個(gè)教師心中都應(yīng)該住著一個(gè)鮮活的兒童,都應(yīng)該有一種強(qiáng)烈的童年情結(jié),總是想多了解一些關(guān)于兒童的事情,總是想給孩子們提供最好的教育生活。成尚榮先生更是強(qiáng)調(diào)把“兒童研究作為教師的第一專業(yè)”。盡管我們天天都和兒童在一起,盡管我們都從童年中走來,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就了解兒童,很多時(shí)候越是熟悉反而越是陌生,我們往往只是熟知而不是真知,兒童對于一些教師來說恰恰就是“熟悉的陌生人”。反觀教育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往往是因?yàn)槲覀儗和恼J(rèn)知出現(xiàn)了偏差,這種偏差導(dǎo)致教師和兒童擦肩而過。而真正的教育卻是教師與兒童的相遇,相遇讓教育變得更美好,讓師生都從對方汲取養(yǎng)分,實(shí)現(xiàn)各自孕育美好的生命綻放。
三、以實(shí)踐知識為安身之本,找到育人的重要武器
教育是一種非常復(fù)雜的生態(tài),涉及的主體、維度、要素很多,可以說是牽一發(fā)而動(dòng)全身,它不是簡單的工作流程和機(jī)械執(zhí)行,更不是對照使用指南的按部就班;它需要教師擁有豐富的實(shí)踐智慧,需要教師擁有令人驚嘆的教育想象力,進(jìn)行充滿藝術(shù)性的教育創(chuàng)造。“教師是學(xué)校中發(fā)揮核心功能的教學(xué)實(shí)踐者,教師的專業(yè)性集中體現(xiàn)在日常的教學(xué)工作中,而支撐教師教學(xué)工作的,就是教師的‘實(shí)踐知識’。教師的‘實(shí)踐知識’是基于種種經(jīng)驗(yàn)而形成的。要解開內(nèi)在于教學(xué)之中的種種語脈,教師就得通過向兒童學(xué)習(xí)、向同僚學(xué)習(xí)、向社區(qū)文化學(xué)習(xí),從而創(chuàng)造出無愧于‘反思性實(shí)踐家’的教師的教學(xué)。”[7]有許多“實(shí)踐知識”是高等師范院校里學(xué)不到的,也是在書本中學(xué)不會(huì)的,甚至我們可以說,書本里也許就沒有這些特別需要學(xué)習(xí)的“實(shí)踐知識”。“反思性實(shí)踐家”是對教師身份的準(zhǔn)確概括和定位。教師的工作具有強(qiáng)烈的實(shí)踐屬性,這就決定了作為一名教師必須扎根實(shí)踐、深耕課堂而成為經(jīng)驗(yàn)豐富的教育工作者。經(jīng)驗(yàn)生長的過程,是教師專業(yè)水平提升的過程,更是用經(jīng)驗(yàn)培育兒童、把經(jīng)驗(yàn)傳遞給兒童的過程。
教師的經(jīng)驗(yàn)很重要,但是只停留在經(jīng)驗(yàn)層面是不夠的,那樣就會(huì)成為“經(jīng)驗(yàn)型”的教師,經(jīng)驗(yàn)就會(huì)成為發(fā)展的“陷阱”和停滯的“溫床”。所以,教師需要進(jìn)行經(jīng)常性的“深度反思”,反思我們有沒有找到教育的起點(diǎn),反思我們的育人過程是否真正發(fā)生,反思我們的育人方式是否變革。經(jīng)驗(yàn)需要不斷地提煉和提升,需要用理論對經(jīng)驗(yàn)進(jìn)行改造和結(jié)構(gòu)化,最終成為教師所擁有的實(shí)踐智慧。但是,長期以來存在著一種誤區(qū),認(rèn)為理論與實(shí)踐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存在。比如,“西方語言中‘理論’一詞來自古希臘文theorein,該詞原指旁觀、觀看公眾節(jié)日。這種公眾節(jié)日的旁觀者叫theoros,只看而不參與。”[8]理論絕不能成為實(shí)踐的旁觀者。馬克思特別強(qiáng)調(diào):“哲學(xué)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9]不在場的理論恐怕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理論,不能對實(shí)踐產(chǎn)生積極的作用,也會(huì)被實(shí)踐者無情地拋棄。當(dāng)然,理論應(yīng)該以不同的方式影響實(shí)踐。教育學(xué)是一門實(shí)踐哲學(xué),是用來發(fā)展兒童的學(xué)問,具有哲學(xué)屬性和實(shí)踐指向。哲學(xué)屬性意味著要有理論指導(dǎo),合理超越原有經(jīng)驗(yàn);實(shí)踐指向意味著要有轉(zhuǎn)化操作,教師要作為在場者進(jìn)行實(shí)踐闡釋并采取改進(jìn)行動(dòng)。“實(shí)踐知識”本身就是理論與實(shí)踐的耦合體。
四、以豐富情感為生命催化,架起育人的橋梁紐帶
情感是教育生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我們應(yīng)該讓教育變得越來越有溫度和人性的關(guān)懷,或者說教育世界本身就是情感世界。但是,在這樣一個(gè)技術(shù)至上的社會(huì)中,物欲消費(fèi)與外在符號掌控著我們,人把自己封閉在自我的虛擬世界里,甚至借助網(wǎng)絡(luò)和技術(shù)手段,可以不與其他人直接面對面交流就能夠活下去。這就導(dǎo)致人與人之間越來越冷漠,人類越來越工具化和模式化,最終如趙汀陽所說:“把生活問題和情感經(jīng)驗(yàn)?zāi)J交瘜?shí)際上等于是建立一種內(nèi)心的官僚體系,最終會(huì)使人類失去心靈的美學(xué)意義或者文化德性,甚至厭惡人類自己。”[10]而在教育生活中,這種模式化的“內(nèi)心官僚體系”也一樣存在,分?jǐn)?shù)、成績與狹隘的知識同樣宰制著學(xué)生的心靈,把他們的世界日益局限化,導(dǎo)致過度激烈的競爭成為生活常態(tài)。伙伴不再是伙伴而是殘酷的競爭對手,你的進(jìn)步就意味著我的落后,你的成功就意味著我的失敗,你的入圍就意味著我的出局,豐富多彩的情感被一點(diǎn)一點(diǎn)地從教育中抽離,升入好學(xué)校、找到好工作成為唯一的學(xué)習(xí)目的,排他變?yōu)椴坏貌贿x擇的歸宿,生命不斷地走向僵化、萎縮。
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情感對于教育的價(jià)值,“教育者應(yīng)當(dāng)感受到人類能夠具備的一切美好與可愛的品質(zhì)。”“應(yīng)當(dāng)以各種人道的態(tài)度將學(xué)生作為人來對待,并也許應(yīng)當(dāng)以應(yīng)有的充滿愛撫的情意將他們作為可愛的孩子來對待。”[11]正是在這樣充滿人性的過程中,在充滿情意的良好氛圍中,學(xué)生享受到了人的尊嚴(yán),擁有了積極的學(xué)科情感,教育才可能真正地展開。情感是一個(gè)人社會(huì)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情商在某些場合比智商還重要。情感學(xué)習(xí)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學(xué)習(xí),是對知識學(xué)習(xí)的重要促進(jìn)和補(bǔ)充。情感是教育的手段,情感培育是教育的目的。只有當(dāng)師生成為具有良好情感的個(gè)體,相互之間才能產(chǎn)生情感交流和情感慰藉,如此,真正的教育可能就在路上了。
五、以精神氣質(zhì)為人生底色,達(dá)成育人的崇高追求
整個(gè)人類發(fā)展史就是一部精神成長史,精神世界是人類的故鄉(xiāng),是生命棲息的迷人港灣。人就是一種精神的存在,不能以為兒童年紀(jì)小就不需要精神,而是精神永遠(yuǎn)伴隨著他們成長。精神培育是教育的核心組成部分和終極追求,“兒童不僅作為一種物體的存在,更作為一種精神的存在,它能給人類的改善提供一個(gè)強(qiáng)有力的刺激。正是兒童的精神可以決定人類進(jìn)步的進(jìn)程,也許它甚至還能引導(dǎo)人類進(jìn)入更高形式的一種文明。”[12]對精神的追求把教師自身帶上了一個(gè)更高的平臺,尤其是在這個(gè)奮發(fā)向上的偉大時(shí)代,特別需要精神的鼓舞和召喚。精神的力量是這個(gè)世界上最讓人敬仰的力量,教師這個(gè)重要群體的存在就是偉大精神的體現(xiàn)與折射。
精神是教育生活的重要維度,關(guān)注精神不是對教育其他生活的放棄,實(shí)現(xiàn)人類的精神追求,達(dá)成對兒童的精神培育,這與知識的學(xué)習(xí)一點(diǎn)都不矛盾,而“只有當(dāng)知識變成精神生活的因素,吸引人的思想,激發(fā)人的興趣和熱情的時(shí)候,才能稱之為真正的知識”[13]。這種知識觀可以幫助我們消除當(dāng)下許多誤解,克服由于知識狹窄化所導(dǎo)致的一系列問題,讓孩子們生活在更為豐富的教育世界中,在愜意的交往中感受到愉悅,進(jìn)而達(dá)成一種具有自由和解放意味的審美狀態(tài),共同創(chuàng)造屬于師生的“偉大作品”。因此,我們要把知識學(xué)習(xí)作為教育線索,讓精神牢牢地附著于知識之上,從而讓知識有了精神意蘊(yùn)和生命品質(zhì);同時(shí),精神也有了存在的基本載體。這樣一來,兒童接受教育的過程,既是知識獲得的過程,更是精神拔節(jié)的過程,在知識與精神的相融中,真正達(dá)成知識和意義的編碼,實(shí)現(xiàn)人的全面而完滿的培育。換言之,只有在精神的滋養(yǎng)下,教師和學(xué)生才能真正相互悅納、相互啟迪、相互喚醒,才能建構(gòu)起充滿精神力量的教育時(shí)空,才能把人類的文化基因代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