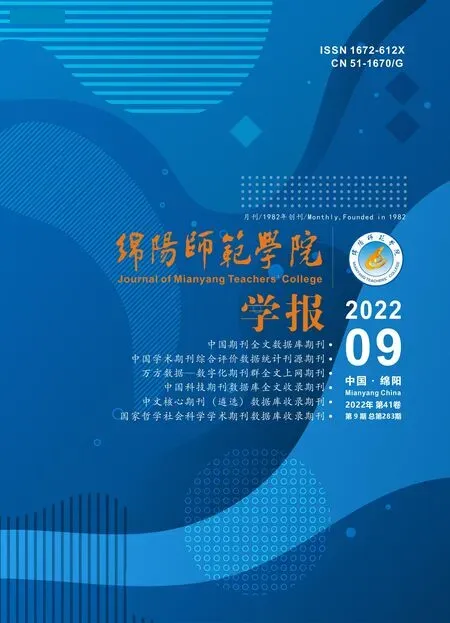元代苜蓿發展初探
張英冉
(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河北保定 071002)
苜蓿是苜蓿屬植物的通稱,俗稱金菜花,是一種多年生的開花植物,一般用作牧草。苜蓿的種類有很多,大多是野生的草本植物,在我國已發現的有8種,其中栽培較多的是紫花苜蓿和黃花苜蓿(即南苜蓿)。紫花苜蓿主要在我國西北、華北、東北各地栽培,淮河流域也有零星栽培,是我國主要的多年生豆科牧草;黃花苜蓿主要在長江流域和長江以南栽培,以江蘇、浙江、上海等地栽培較多,是南方的主要冬綠肥之一[1]1。我國自古以來就有種植苜蓿的傳統,到現在已有兩千多年的栽培歷史。
國內對于苜蓿的研究已取得豐厚的成果,其中以孫啟忠、柳茜為代表的學者,他們系統研究過漢代、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明清及民國苜蓿的物種、栽培與利用,尤其關注苜蓿在漢代的引入過程①。郭建新等學者在梳理我國苜蓿的傳播歷程后指出,苜蓿在我國不斷發展,除了其自身特征與食用價值外,也與政府支持等社會因素有關[2]。既有研究關注了苜蓿傳入中國后的大多數時期,但對元代苜蓿種植和發展的探討相對較少,因而對這一時期的相關問題認識不足。究其原因,元代立國時間不長,有關苜蓿的文獻記載不多,制約了學術研究的深入開展。通過梳理元代苜蓿的種類、分布范圍、用途及種植管理,結合當時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狀況,可以對探討苜蓿在元代社會中的歷史形象起到積極作用,彌補元代苜蓿相關的研究缺失,深化我們對苜蓿發展及元代社會的認知。
一、苜蓿的起源和引入
目前,人們普遍承認的苜蓿起源的地理中心是伊朗,但由于在亞歐大陸很多地方以至北非地區均有野生苜蓿種群分布,因此對于具體的起源中心的論定比較困難[3]。有學者認為苜蓿有兩個不同的起源中心,一個是外高加索山區,一個是中亞細亞[4]1-34。前者是現代歐洲苜蓿的起源地,這個地區的苜蓿比較抗寒,可以很好地適應歐洲寒冷的天氣;后者抗寒性不強,但在灌溉區,抗蟲病很強。這兩種苜蓿各自的特性不同,因此,世界各地的人們會根據當地氣候的特征,選擇合適的苜蓿進行種植。
目前學界對我國苜蓿的引入過程仍然存在分歧。關于引入者,《史記》記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余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于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聚,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5]3173-3174這是最早記錄苜蓿傳入我國的史料,司馬遷雖然指出是“漢使”將苜蓿引進,但卻并未具體說明漢使是誰,因此學界對苜蓿的引入者就形成了多種觀點。石聲漢先生曾指出應為張騫[6]16-33,這一觀點確有一定文獻支持,如《齊民要術》引東漢王逸記載:“張騫周流絕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7]233這是最早記錄張騫將苜蓿傳入中原的史料,后來學者亦有支持此觀點者[8]。也有學者認為是貳師將軍李廣利[9]。另有部分學者則認為苜蓿的引入者難以確定[10]。孫啟忠等學者綜合既有研究與史料,提出“苜蓿是由出使西域的漢使帶回來的”,這一觀點最為真實,且易為眾人接受,而苜蓿引入者具體是誰,尚需進一步考證研究[11]。
苜蓿在漢武帝時期引入我國,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學界關于苜蓿引入的具體時間,同樣未形成共識。目前對苜蓿傳入我國的時間主要有四種觀點:一是圍繞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所確定的苜蓿傳入我國的時間;二是汗血寶馬引入我國的時間;三是張騫死后或其他時間;四是引入時間不確定。孫啟忠等學者考證指出,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帶回苜蓿的觀點明顯不妥;公元前126年帶回苜蓿的觀點還需做進一步的研究;苜蓿與汗血寶馬同時傳入我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張騫死后或其他時間、苜蓿引入時間不確定,這兩種觀點還需要進一步研究[12]。
二、元代苜蓿的種類與分布
古人對于苜蓿的分類,除了基于其生長特性外,花色也是其中重要一環。古代對苜蓿花色的記述存在差異,既有記載開紫花的,也有記載開黃花的[13]。吳其濬在《植物名實圖考》中指出中國古代苜蓿的種類分別為紫花苜蓿、黃花苜蓿和南苜蓿三種,其中黃花苜蓿和南苜蓿屬于野苜蓿[14]85-87。最早記載苜蓿花色的文獻,應是唐末五代韓鄂的《四時纂要》:“凡苜蓿,春食,作干菜,至益人。紫花時,大益馬。”[15]261其明確指出苜蓿開紫花。另外,宋代詩人梅堯臣在《詠苜蓿》中寫道:“苜蓿來西域,莆萄亦既隨,胡人初未惜,漢使始能持。宛馬當求日,離宮舊種時。黃花今自發,撩亂牧牛陂。”[16]120梅堯臣此時看到的苜蓿開黃花。
元代關于苜蓿種類的記載較少,而元詩中雖然多處提到苜蓿,但其中只有少部分關于花色的信息,因此所能利用的材料較少。如“天山水深寒入骨,苜蓿經霜吐花紫”[17]414和“蒹葭黃葉暮,苜蓿紫云深”[17]36,這兩句詩中提到的苜蓿花色為紫色。王沂在《宜春行贈別吳子茂鎮撫》中提到“沙場馬肥苜蓿黃,大夫秉節親戎行,征車戰艦遙相望”[17]174,此處的“苜蓿黃”應是黃花苜蓿。元詩中還有一處談到“苜蓿花白春云鋪,氣全或比新生駒”[17]188,這里的“苜蓿花白”應是初春苜蓿的生長期,并非成熟期,因而苜蓿花色并不明顯。
苜蓿自漢代引入中原以來,至元代已近千年的時間,民眾對其特性與用途已有充分認識,故而苜蓿在疆域遼闊的元朝境內分布尤為廣泛。王惲《玉堂嘉話》中記載:“二十六日過瑪勒城,又過諾爾桑城,草皆苜蓿,藩籬以栢。”[18]59瑪勒城和諾爾桑城大致是在現在新疆西部及阿富汗地區,上文已經指出,苜蓿原產西域,新疆地區應當比中原擁有更悠久的苜蓿生長與栽種歷史。《元史》提及“都城種苜蓿地,分給居民,權勢因取為己有”[19]4053,都城即今北京,這記錄了元代北方地區苜蓿的種植。元詩中也有很多關于苜蓿分布的內容,如“苜蓿春原塞馬肥,慶原三月柳依依”[17]363,慶原屬甘肅省轄地,這也是西北地區的苜蓿分布情況。“故人舊別向西川,移謫淮山苜蓿田”[17]477中的淮山大致在現在安徽省的北部,說明元代在淮河流域也有苜蓿種植。上引“沙場馬肥苜蓿黃,大夫秉節親戎行,征車戰艦遙相望”,該詩寫于宜春(今江西宜春)。可見元代時苜蓿在我國境內有著廣泛的分布,是十分常見且人們非常熟悉的植物。
三、元代苜蓿的種植
上文談到廣泛分布的苜蓿,這其中既有野生的也有種植的,如新疆、甘肅、宜春三例當為野生苜蓿,安徽一例中“苜蓿田”表明其應為人工種植的,都城中的“種苜蓿地”也顯然是種植。《農桑輯要》中指出:“此物長生,種者一勞永逸;都邑負郭,所宜種之。”[20]245苜蓿對于環境的要求并不嚴苛,種植起來比較容易,因而苜蓿的種植非常廣泛。種植如此簡單,且“此物長生”,野生苜蓿顯然同樣容易生長。此外,這條材料揭示出時人認為苜蓿生長“一勞永逸”,這種社會認知再加之下文將要談到的苜蓿與牧馬的關系,是社會因素對苜蓿種植的影響。故而在苜蓿的自身特性與社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工種植苜蓿在元代廣泛分布。
關于苜蓿的種植方法,元代文獻有明確說明,《元典章》中記載:“布種苜蓿,初年不須割刈,次年收到種子轉,轉分散務要廣種。”[21]466這是關于苜蓿種植的明確規定,介紹非常詳細,在種植苜蓿的第一年里,不強制收割,可以等到第二年,同時還指出要注意儲存苜蓿的種子,擴大種植范圍。這種詳細的苜蓿種植規定,表明當時的苜蓿種植已有一定的規模。《農桑輯要》系統地總結了《齊民要術》和《四時類要》種植苜蓿的時間和經驗:“地宜良熟;七月種之。畦種水澆,一如韭法”,“一年三刈;留子者,一刈則止”[20]245。提出種植苜蓿需要肥沃的土地,七月份種植,在低洼處種植并澆水,和種植韭菜的方法相似,且苜蓿一年收割三次,如果要留種子,一年收割一次就可以。該書中也反復提到種植時間:“七月、八月,可種苜蓿”,并指出“苜蓿,若不作畦種,即和麥種之不妨”。除了介紹苜蓿種植的時間和方法外,《農桑輯要》還記載了“燒苜蓿之地”,即“十二月燒之訖。二年一度耕垅外根,即不衰”[20]245-246。十二月份將地里的苜蓿燒完作肥料,第二年在燒完苜蓿的土地上繼續種植,還能生長。
此外,在養馬需求的推動下,元代還出現了主管苜蓿種植的專職官員。《元史》卷90中記載:“署令、署丞各一員,直長一員。掌宮苑栽植花卉,供進蔬果,種苜蓿以飼駝馬,供煤炭以給營繕……苜蓿園,提領三員。掌種苜蓿,以飼馬駝膳羊。”[22]2282這種專門用苜蓿飼養馬、駱駝和羊的官職,說明苜蓿作為牧草,用來飼養家畜在這一時期非常常見。同時宮廷中設有苜蓿園,交由專人管理,署令、署丞、直長這三類官員是掌管宮廷苜蓿園,專門為統治階級服務的,這也從側面說明了苜蓿在元代的應用較廣,其價值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
由此可見,元代苜蓿的種植和管理有著明確且詳細的記載,元代政府還專門設立了管理苜蓿種植等相關事務的機構和任命了官員,這說明了政府對苜蓿種植的重視,同時也體現了元代苜蓿種植的系統化。
四、元代苜蓿對于社會生活的價值和影響
苜蓿在元代最主要的用途,應當是作為牧草飼養馬匹。《農桑輯要》記載苜蓿“長宜飼馬,馬尤嗜之”[20]245,由此可見元代苜蓿作為飼料用時,主要用于飼馬。除此之外,元代的詩詞、散曲中也有很多關于馬食苜蓿的記載,如“呼鷹腰箭縱圍獵,苜蓿秋深馬正肥”[23]1217,“苜蓿能肥馬,蒲萄解醉人”[24]1410。這些都表明苜蓿在元代被廣泛用于飼養牲畜,尤其是喂養馬匹。
眾所周知,馬除了供人們騎乘、狩獵、游牧、遷徙以及行軍打仗外,還是生產生活、交通運輸和戰爭的重要工具。同時蒙古人還使用馬匹及其畜產品交易各種生產和生活必須品[25]。多桑在《多桑蒙古史》中記載“畜牧馬群為韃靼種族經濟之要源”[26]34,可見馬匹對蒙古族的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使得蒙古人尤其重視牧馬。元朝建立后,馬匹的使用更加廣泛,也愈發受到重視。如《元典章》中曾記載四川地區“三十家應當鋪馬一匹,每匹不下中統鈔十一余定,又況山路崎崄,每站相去百有余里,其馬馳驟,易于困乏死損。提調官司不曾立法,恣任站官弄權,將富勢之家馬匹作弊歇閑,其貧弱者連日差遣以致死損馬匹,消乏站戶近因成都蜀川驛站馬例損數多,慮有此弊”[21]630。這條史料談及馬匹折損對驛站影響頗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因為疆域遼闊,元朝對驛站建設與維護的重視。在蒙古人統治下的元朝,軍事、交通等許多地方都需要馬,因而馬料必須得到保證。
因此,作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其發達的畜牧業推動了牧草種植業的發展,而苜蓿作為“牧草之王”在當時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一方面,官方種植苜蓿的用途一般是為了養馬,上文談到的宮廷中的“苜蓿園”與主管苜蓿種植的專職官員,即是元朝政府重視苜蓿的直接體現。另一方面,牧草種植業的發展也在不斷促進畜牧業規模的擴大,馬的飼養作為畜牧業的重要一環,其水準也在不斷提升,進而又間接促進了元代驛站、交通運輸業等與馬息息相關產業的發展。
苜蓿除了用作飼料外,還可食用。元代關于苜蓿可食用的史料非常多,如《文獻通考》將苜蓿列為“薦新物”,并指出“凡薦新,皆所司白時新堪供進者,先送太常,令尚食相與簡擇,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以薦,皆如上儀”[27]2988,將這些“薦新物”交由專人進行擇選,選出與新物相適宜的進行搭配,這說明苜蓿已經作為一種菜肴在宮廷中得到應用。除了作為宮廷菜肴,馬端臨還將苜蓿列為谷物雜子之一,他認為“谷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稷,六曰菽,七曰雜子……雜子之品九:曰脂麻穈子、稗子、黃麻子、蘇子、苜蓿子、萊子、荏子、草子”[28]96。《農桑輯要》還介紹了苜蓿作為食物的不同吃法,“春初既中生啖,為羹甚香”[20]245,“凡苜蓿,春食作干菜,至益人”[20]246。苜蓿可以生吃,可以做羹,還可以做成干菜,可見元代苜蓿的食用方式是比較多樣的。元詩和元曲中也記載了很多百姓食用苜蓿的情景,如:“食余苜蓿承朝日,坐候棠梨過夕暉”[29]872,“蒲萄苜蓿味雖美,異方土俗殊鄉里”[17]157。另外,《元典章》中曾記載:“非止喂養頭足,亦可接濟饑年。”[21]466苜蓿不僅可以喂養牲畜,還可以救荒,在荒年糧食顆粒無收時拿來食用。《元史》卷93中也有類似的記載:“仍令各社布種苜蓿,以防饑年。”[30]2355這說明種植苜蓿可以應對饑年,緩解人口壓力等因素所帶來的糧食不足。
陳性定在《仙都志》中曾記載苜蓿可以作為一種藥材服用,認為苜蓿和書中其他植物“草木可藥者往往見,山翁野叟采取,形殊味別,莫識其名”[31]10。這說明在元代,苜蓿不僅是一種牧草,還可以用作藥材,具有一定的藥用價值。而苜蓿等草木作為藥材在當時很常見,山中老人沒有不知道的,這從側面說明苜蓿在當時具有普遍性。將苜蓿這種較為常見的草本作為一種藥材,大大降低了治療成本,有利于減輕百姓負擔。除此之外,《飲食須知》指出苜蓿的藥性及功效,認為“苜蓿味苦澀,性平,多食令冷氣入筋中即瘦人,同蜜食令人下痢”[32]11。《三元延壽參贊書》也曾記載“苜蓿利大小腸,蜜食下痢,多食瘦人”[33]28,苜蓿與蜜同食可促進消化。
苜蓿除了用于養馬、食用和藥用外,在元代的文化生活中也有一席之地。元曲是盛行于元代的一種戲曲藝術,廣義的元曲由元雜劇和元散曲組成,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元曲中有很多關于苜蓿的記載,有些詩人借用苜蓿表達自己豐富的感情,如“渥洼秋淺水生寒。苜蓿霜輕草漸斑。鸞弧不射雙飛雁。臂鞲鷹玉轡間。醉醺醺來自樓闌。狐帽西風袒。穹廬紅日晚。滿眼青山”[34]628。這首詩的作者用苜蓿結霜來形容天氣的寒冷,并進一步表達自己內心的孤寂。有些詩人還通過食用苜蓿來表達自己淡泊名利的處事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我國的飲食文化,如“閉戶讀書三十秋,一線為官十領職。天長令尹莫我知,苜蓿朝盤勝肉食”[17]365-366。另外,詩人通過苜蓿來表達馳騁疆場、報效國家的例子也有很多,如“陣前八駿血為淚,仰面不見咸陽門。祁連山頭堆苜蓿,將軍多馬今何贖”[35]1641,對于研究元代軍事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總的來說,苜蓿對元代社會生活方方面面都有著一定的影響。苜蓿作為優質牧草,在游牧民族統治的元朝得到了充分發展;苜蓿的食用功效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飲食習慣,元代記載的苜蓿的多種做法,也大大改善了人們的飲食結構,豐富了我國古代飲食文化,饑年時苜蓿還可解決糧食不足造成的危機;苜蓿的藥用價值對豐富我國醫藥學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元代詩人借用苜蓿來表達自己內心的情感,也為我們進一步研究元代社會歷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五、結語
元代在西北、都城等地大量種植紫花苜蓿,促進了元代交通運輸業和軍事實力的進一步增強。而且在這一時期,苜蓿的用途已經不僅僅局限在飼養牲畜上,人們對苜蓿的食用和藥用價值也有了一定的認識,這給后世尤其是明代人們對苜蓿所具有的生物學和營養學價值的認知,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借鑒。如明初編成的《救荒本草》中談道:“苜蓿苗高尺余,細莖,分叉二生,葉似錦雞兒,花葉微長,又似豌豆葉,頗小,每三葉攢生一處,梢間開紫花,結彎角兒,中有子如黍米大,腰子樣。”[36]355可見朱橚對苜蓿的莖、葉、花、種子都有了很詳細的了解,如此細致的介紹便于民眾能夠更好地利用苜蓿,也突出了《救荒本草》實用性的特征。
元代對苜蓿的種植和管理都有明確的規定,甚至還出現了專職官員,較之前代更加專業化和系統化。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除苜蓿自身所具備的自然條件外,與蒙古族是游牧民族,重視牧草種植業和畜牧業這一因素不無關系。同時,苜蓿對元代社會的影響也非常大,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飲食結構,讓百姓乃至貴族的食物變得更加豐富。同時,元曲中以苜蓿為意象來描述詩人心情的詩句,也極大地豐富了百姓們的日常生活。
注釋:
① 孫啟忠、柳茜聯合陶雅、李峰、徐麗君、那亞等人發表了多篇文章,主要有:《我國漢代苜蓿引入者考》,《草業學報》2016年第1期;《漢代苜蓿傳入我國的時間考述》,《草業學報》2016年第12期;《張騫與漢代苜蓿引入考述》,《草業學報》2016年第10期;《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苜蓿種植利用芻考》,《草業學報》2017年第11期;《隋唐五代時期苜蓿栽培利用芻考》,《草業學報》2018年第9期;《我國明代苜蓿栽培利用芻考》,《草業學報》2018年第10期;《清代苜蓿栽培利用芻考》,《草業學報》2019年第4期;《我國近代苜蓿栽培利用技術研究考述》,《草業學報》2017年第1期;《民國時期西北地區苜蓿栽培利用芻考》,《草業學報》2018年第7期;《民國時期方志中的苜蓿考》,《草業學報》2017年第10期;《我國古代苜蓿物種考述》,《草業學報》2018年第8期;《我國古代苜蓿的植物學研究考》,《草業學報》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