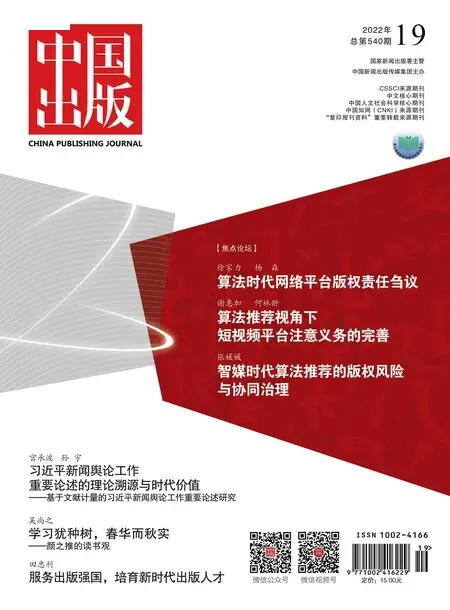數字媒體語境下“擬像”傳播探析
□文│張友軍 劉 強
“擬像”是人通過媒介建構的對世界虛擬化的表征方式,既蘊含了人所寄予的情感,也寄予了人對世界的想象與期待,由此達成了人與媒介的虛擬性互動關系。“擬像”實際上是媒介符號對現實的再現,但又不等同于現實。從詞典學意義上來看,“擬像”具有雙重含義,一是現實的影像,二是具有一定欺騙性的指涉物。這雙重含義也構成了“擬像”意涵在現實與虛擬意象上的二律背反。因此,現實與虛幻之間的間隙,是“擬像”具有的某種虛幻性或虛假性的特征。這一特征在不同的媒介中呈現出不同的表征形態。在數字技術的推動下,“擬像”更是已成為媒介建構的廣譜性傳播現象,在創造了全新的視覺體驗的同時,也導致了虛擬世界與現實的混同,人們越來越多地依賴于虛擬視覺體驗,由此引發了一些消極后果。因此,如何建構“擬像”傳播與受眾的和諧關系,是數字化媒介生產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數字媒體語境下的“擬像”表征
“擬像”原本是法國當代哲學家鮑德里亞基于后現代文化語境提出的一個概念,旨在闡釋人所構建的圖像與社會現實的關系,并作為對后現代社會的批判工具。在大眾傳播時代,如果說“擬像”傳播主要是以繪畫、攝影等現實的影像創造為基礎的話,那么數字媒體語境下的“擬像”傳播,與傳統媒體時代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以虛擬現實技術構建全新的“擬像”形態,呈現出廣譜性、視覺公共性的圖像形態等全新特征。
1.從傳統媒體到數字媒體,“擬像”特征的嬗變
匈牙利學者巴拉茲·貝拉于1913年在《可見的人——電影文化》一書中,最早提出了視覺文化概念, 他認為電影以“擬像”的形式創造出一種視覺文化范型,是對僵硬的毫無情緒的印刷術的反叛,“使埋葬在概念和文字中的人重見陽光變成直接可見的人 ”,[1]由此建構了一種基于媒介空間的虛擬現實,“電影將在我們的文化領域里開辟一個新的方向,每天晚上有成千上萬的人坐在電影院里不需要看到文字說明,純粹通過視覺來體驗事件、性格、感情、情緒甚至思想”。[2]對于“擬像”的闡釋,鮑德里亞指出,“擬像”表現出“人們對通過語言媒介對于世界的把握產生了某種懷疑,懷疑這樣所把握的世界是否僅僅是一個‘幻象(Simulacrum)’,懷疑語言媒介再現世界時的真實性、可靠性”。[3]因此,“擬像”是工業社會到后工業社會中大眾傳媒的一種視覺生產方式,從傳統媒體到數字媒體,“擬像”的特征隨著媒體的進化產生了很大的改變,逐漸由紙媒和電波媒體“擬像化”演變為數字“擬像化”。“擬像”的視覺呈現形式也從繪畫、攝影等符號演變為基于技術性的數字符號。“擬像”本質上是人與現實的虛擬化互動方式,而媒體在這一過程中成為構建“擬像”符號的載體。
從歷史的演進過程來看,鮑德里亞把“擬像”的進程分為3個不同的階段,即仿造(counterfeit)、生產(production)和仿真(simulation)。而“仿真”是與后現代工業社會的生產方式密切關聯的,即符號充當了人構建虛擬現實的媒介,并創造出“超真實”(hyperreality),它能夠借助技術的手段把人的所有想象轉化為現實表征。現實表征并非現實,而是基于媒介建構創造的一種新的現實。盡管這種現實是高度虛擬化的,但是卻消解和打破了真實的現實與虛擬的現實之間的界限,構建了人基于這種“超真實”場景的互動方式。鮑德里亞的“擬像理論”雖然有所偏頗,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后現代社會仿真視覺生產方式的特征與趨勢,尤其對新媒體語境下的視覺傳播的發生機制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
數字媒體已經成為當今圖像生產與傳播的最重要方式,也是構成“擬像”傳播的直接動因。數字媒體是基于數字技術手段處理和傳播信息的載體,包括經過數字化處理的文字、圖像、音頻和視頻等。與傳統媒體相比,數字媒體傳播由以傳播者為中心,轉向以受眾為中心,并具有極大的開放性、包容性、跨界性和普適性。就傳播技術層面而言,由于數字信息不需要占用電磁信號頻譜空間,傳統模擬信號傳播方式因頻道稀缺而產生的傳播技術性壟斷被徹底打破。傳統的大眾傳播模式,是以傳播者為出發點的線性傳播,媒介圖像也是根據傳播者的意圖而構建的,如傳播學家拉斯韋爾提出的著名的5W傳播模式。但這種線性的傳播模式在數字媒體時代下被消解了。因為數字媒體具有廣譜性的信息生產與傳播性質,在媒體傳播過程中,傳受往往是合二為一的。這種全新的傳播模式成為圖像傳播語境中“擬像”建構與表征的重要特征。
2.數字媒體的“擬像化”表征與傳播形態
基于技術化創新的數字媒體構成了“擬像”表征的新的圖像語境,即圖像建構形式與內容的多元化和豐富性。首先,數字媒體推動了媒介視覺傳播的全面跨界“擬像化”,即圖像表征整合了文字、圖像和視頻的不同元素。同時,圖像表現從再現現實全面轉向虛擬現實。如果說,圖像的再現現實仍然是以現實世界為藍本的話,那么圖像的虛擬現實則無須指涉現實,即鮑德里亞稱之為“超現實”,他認為擬象和仿真的東西因為大規模的類型化而取代了真實和原初的東西,世界因而變得“擬象化”了。人們通過大眾媒體看到的世界已經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而是由媒體的符碼所構造出來的“超真實”的世界,亦即擬像化的世界。
傳播學家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中曾提出與“擬像”概念相近的“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概念,這兩個概念都強調媒介圖像的虛擬性。“這種建立在媒介圖像基礎上的擬態環境不是現實環境‘鏡子’式的再現,而是大眾媒介通過對象征性事件或信息的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并提供給受眾的環境”。[4]李普曼在闡釋受眾與媒介的圖像關系時提出了3種關系:客觀現實圖像、主觀現實圖像和象征性現實圖像。媒介所構建的現實就是象征性現實圖像,即擬像化現實。另外,由于數字媒體語境下,傳受關系的改變,“擬像”建構并非是由傳播者主導的,而是由受眾主導的,因而這種“擬像”具有更加多元化和開放性的特性。
數字媒體不僅是一種傳播技術,更是一種普適性的圖像建構方式,創造了全譜系“擬像化”視覺表征與傳播形態。數字媒體的圖像建構是高度技術化的視覺表現形式,它打破了傳統的圖像生產機制,突破了傳統繪畫中仿真式地用線條、透視和色彩描摹圖像的方式,而是用軟件和程序在技術性框架下大批量地制造和傳播圖像,能夠自由而靈活地呈現創作者——受眾的審美意圖,從而為“擬像”生產與傳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媒體的普適性圖像生產機制強化了現代社會的“擬像”表征方式,這在網絡社交媒體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每一個手機媒體的使用者都可以隨時隨地進行拍攝、制作和傳播。這種基于社交場景大量的“擬像”傳播方式,在傳統媒體中是難以想象的。而數字媒體以其程序化的圖像生產機制,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擬像”的生產機制和生產方式,形成了新的“擬像”建構邏輯,使“擬像”成為無所不在的現實環境和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數字媒體的語境下,無論是現實的還是傳統文化的價值形態都被訴諸于數字化表達。而“擬像”表征作為數字化媒介傳播的基本方式,不僅具有了全新的傳播話語建構的意義,而且具有了現實的價值整合與重構的意義。
二、數字媒體的“擬像”文本建構
“擬像”文本建構是從大眾傳媒到數字媒體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其深層動因在于工業化文明中的消費行為驅力機制,更多地需要圖像來刺激人們的感官欲望,并在商品圖像的“幻覺”中去滿足受眾的消費需求。傳統媒體的“擬像”文本建構的主要特征是圖像的符號化和視覺的仿真化,形成了基于消費驅動的受眾與“擬像”的互動關系,由此開創了“擬像”文本建構的先河。數字媒體的出現,把“擬像”文本的建構推向了極致。
人們在各種電商平臺上通過瀏覽各種“擬像”文本的商品圖像,形成了消費狂歡的視覺盛宴。2021年雙十一期間,消費額達到9600多億元之巨。“消費者(受眾)—商品圖像(擬像)—網絡平臺(消費場景)”構成了“擬像”互動的商業模式。正因如此,鮑德里亞基于對工業社會中媒介商品化的批判主義立場,揭示了“擬像”本質上是大眾傳媒制造的一種仿真社會,整個社會都變得仿真化了。大眾傳媒所制造的仿真現實,實際上是一種“擬像”的虛幻現實,由此構建了與受眾的虛擬性傳播互動關系。大眾傳媒在真實與“仿真”的過程中充當了轉換器的作用。隨著數字媒介的迭代發展,傳統媒體的“擬像”文本被數字媒體“擬像”文本所顛覆了。在數字媒體語境下,“擬像”文本呈現出跨媒介的媒介融合的互文性特征,文字、圖像、視頻等文本形式被整合為數字化文本的形式。
19世紀末,隨著報紙、雜志等印刷紙媒的出現,繪畫和攝影被引入了大眾傳播媒介,開創了近代媒介圖像消費的先河。圖像生產成為一種媒介生產體制,彰顯了受眾作為視覺消費者的主體地位,當代法國哲學家福柯稱之為“眼睛的權力”,其目的在于引導受眾更好地理解圖像借以傳遞訊息的方式。羅蘭·巴特則認為,視覺信息的詞語化,表現為主導其解釋的感受選擇和識別選擇過程。
數字媒體解構了傳統媒體圖像文本形式,打破了紙媒與電波媒介的界限,使“擬像化”具有了廣譜互文性文本的特征,形成了文字、圖像、網頁、視頻、短視頻和直播文本相互交織的形態。但是可視化是網絡媒介文本的基本特征,尤其是隨著5G時代的來臨,高網速、大寬帶、低延時的優勢,大大提升了視頻傳播的速度和質量。同時,由于數字媒體已經成為泛在性的基本生產元素和工具,深深地滲透于各個生產領域和生活方式中,遠遠超越了傳統媒體的功能,把一切生產和生活流程都納入視覺圖像表征的范疇。手機作為最常見的移動媒體,既有制作、傳播的功能,也有美顏、編輯的功能,每個在照片、視頻中出現的人和對象都可能是通過編輯軟件加工過的。這些圖像看起來都是真實的存在,但實際上卻是經過技術處理過的高度仿真的現實。也就是說,哪怕是在屏幕對面的真實的人或對象,也是一種“擬像”的結果。
數字媒體的“擬像”文本建構還是一種獨特視覺修辭方法,劉強認為“擬像”文本建構還帶來了基于媒介與受眾關系重構的圖像修辭方式的重構。“靜態的符號是客觀世界的映像,然而客觀世界又是動態的,這就要通過受眾對符號解構來使靜態的符號動態化。電視是畫面與聲音的疊加。廣播是播音主持的聲音與音效、音樂的疊加。這些疊加大多是非自然的,是傳播者為達到傳播目的而營造的媒介世界。”[5]數字媒體決定了“擬像”文本對圖像修辭的功能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擬像”不再是簡單的受眾與圖像之間的凝視,而是各種符號互文性之間的意涵互現。
三、“ 擬像”傳播:從傳統媒體到數字媒體的跨越
“擬像”傳播的發展經歷了從傳統媒體到數字媒體的跨越,這既是傳播技術的進步,也是人類視覺傳播互動關系進化的過程。“擬像”作為視覺圖像的一種傳播方式,表征了人與外在世界互動關系的建構方式。而媒介的屬性與傳播技術的進化則決定了“擬像”傳播的特征。
對于“擬像”傳播的研究,最早始于匈牙利學者巴拉茲所提出的“視覺文化”的概念。他認為從古希臘視覺藝術到電影都具有“擬像”的屬性,或者說當現實被表征為媒介的再現形式時,就內在規定了它的“擬像”特征。“從古希臘到今天歐洲美學和藝術哲學始終有這樣一個基本原則:在藝術作品和觀眾之間存在著一個外在的和內在的距離一種二重性。這個原則的含義就是:每一件藝術作品都由于其本身的完整結構而成為一個有它自己規律的世界。藝術作品由于畫面的邊框、雕像的臺座或舞臺的腳光而與周圍的經驗世界產生了隔閡……使它能脫離廣大的現實世界而獨立存在”。[6]他強調了媒介在視覺文化傳播中的獨特作用,在紙媒傳播時代,印刷符號是可見的精神的文化表征;在電波媒介時代,電影“將根本改變文化性質,視覺表達方式將再次居于首位,人們的面部表情采用了新方式表現”。[7]因此,影像視覺媒體將取代印刷媒介成為社會文化的主流。這表明視覺文化的特征是隨著媒介的進化而不斷改變的。巴拉茲還總結出視覺文化的三大特征,即大眾性、可感性和虛擬性。這3種要素下相互關聯的,且在大眾傳媒中得到了統一,由此構成了大眾傳播中“擬像”的特征。
在傳播學意義上,虛擬性(virtuality)與“擬像”是具有高度同一性的概念,或者說虛擬性是“擬像”的另一種表述方式。視覺傳播的虛擬性是借助圖像,把人的意識中想象的場景延伸至人的心靈世界中,以喚起深刻的情感體驗。不同媒體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擬像”的建構與表現形式,并決定了與受眾互動關系的特征。
隨著數字媒體的迭代發展,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技術悄然崛起,把“擬像”傳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作為一種新的傳播媒介,它具有跨時空高仿真現場的效果,形成了沉浸式、交互式傳播的新特點,突破了傳統媒體的單一視覺維度的仿真“擬像”效果,能夠感知在真實環境中一樣的知覺體驗。這種虛擬現實的“擬像”沉浸式體驗,是受眾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將認知、知覺、情感投射于虛擬的場景中,并達到與真實場景相同的體驗效果。而交互則是指在虛擬現實技術條件下的人機互動,受眾能夠對虛擬場景中的對象進行操作并得到即時的反饋。虛擬現實生成的“擬像”傳播機制,消解了受眾對傳統媒體“擬像”的感知方式,訴諸于強烈的現場感的感官體驗,喚起受眾全身心地投入到文本敘事的情境中,這種身臨其境的效果相對于單調的語言文字或靜態的攝影圖片來說,所呈現的傳播特點是交互、渲染和美化,而不是說服和展示,因而具有更強的表現力和感染力。
四、結語
基于數字媒體的虛擬現實所構建的“擬像”傳播,取代了傳統媒體的語言公共性,創造了更加生動而豐富的視覺公共性。但是,數字媒介的虛擬現實技術的“擬像”傳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更多地應用在娛樂、游戲和電子商務場景中,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公共話語體系建構、傳統文化傳承等方面,仍然是比較缺位的。這其中既有自媒體語境中商業利益驅動的原因,也有對我國公共話語傳播體系認識不足的原因,而泛濫的娛樂化“擬像”傳播導致受眾更容易受到感覺刺激而沉湎其中,從而消解了“擬像”傳播對公共話語空間的貢獻。這是當今“擬像”傳播亟待解決的問題與必須面對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