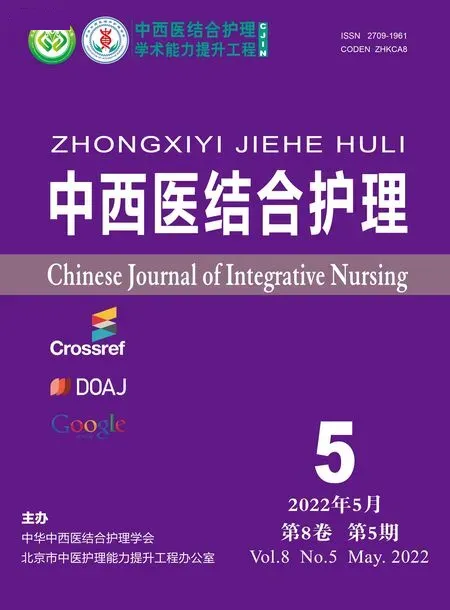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病恥感的質性研究
柯 珂,賀娟鳳,汪 維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湖北武漢,430030)
腦卒中又稱“腦血管意外”、“中風”,是由腦血管病變引起的一過性或永久性腦神經功能障礙疾病[1],具有患病率高、致殘率高、死亡率高的特點[2]。中國腦卒中的發病率已經超過379/10萬,位列世界第一,每年約190萬人因腦卒中而死亡,腦卒中已經超過腫瘤及冠心病,成為我國居民首位死亡原因[3]。我國腦卒中首次發病者有2/3是老年人,致殘率約為75%,腦卒中后失能的發生率為38.2%~62.8%,偏癱率高達30%[4]。有研究[5]表明,處于失能狀態的老人,在照護需求、康復護理和心理需求等方面更加突出,其中心理需求中的心理疏導需求占65%,陪同需求占61%。而失能這一應激性作用導致老年人在社會角色、家庭職能和自身軀體功能等方面發生改變,進而會使老年人出現嚴重的心理障礙,影響其生活質量[6]。
病恥感是指“被剝奪全部社會認可資格的個人情況”,其本質是把一個整體或正常的人貼上標簽、做上標記,標志著他們是不同的,導致他們在別人眼中貶值,被廣泛地詆毀,是一種廣泛的、消極的、刻板的社會現象[7]。據研究[8]報道,超過80%的卒中后幸存者表示曾遭受過中重度的病恥感,而年齡在50歲以上的腦卒中患者病恥感水平高于50歲以下的腦卒中患者[9]。腦卒中失能老人由于伴有不同程度的身體功能障礙,對照護的需求量大,導致主要照顧者需承受來自心理和經濟的雙重壓力,引起主要照顧者的“身心負擔”,而出現不良情緒[10]。然而,主要照顧者不良的認知行為和態度,會降低主要照顧者的生活質量,最終影響患者的早期康復[11]。目前,我國對病恥感的研究多傾向于腦卒中患者,而對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這一群體的心理問題關注較少。因此,本研究采用面對面深度訪談法,旨在了解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病恥感的形成過程,以期為醫護人員制定有針對性的心理護理和全面有效的干預措施提供理論依據,改善患者及其主要照顧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的生活質量。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對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樣法,選取2020年6月—12月在武漢市某三甲醫院老年科住院的腦卒中患者及其主要照顧者作為研究對象。老年腦卒中患者納入標準:①年齡≥60歲;②老年失能評估量表(EDAS)[12]得分<195分;③經CT或核磁共振成像(MRI)確認并符合1995年全國第4次腦血管病學術會議制定的腦卒中診斷標準[13];④神志清楚、具備一定的表達能力且愿意接受訪談者。排除標準:①溝通障礙無法獲取信息者;②病情嚴重無法配合者;③合并嚴重實質性器官病變者或腫瘤患者;④患有傳染性疾病者。主要照顧者納入標準:①符合納入標準病人的非正式主要照顧者,為其配偶、子女、其他親屬或陪護;②照顧患者時間≥3個月;③年齡≥18歲;④具備正常的認知和活動能力;⑤自愿參加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伴嚴重軀體疾病或精神疾病者;②藥物濫用者;③患有傳染性疾病者。為獲取更廣泛、更豐富、更多樣的訪談信息資料,盡量選取人口學背景特征多樣的人群。樣本量確定以受訪資料的信息飽和,沒有新主題呈現為標準。
最終確定樣本量為26例,其中患者13例,主要照顧者13例。13例患者中,年齡60~93歲;職業:均為離退休;男7例,女6例;文化程度:小學3例,初中及高中6例,專科及以上4例;婚姻狀況:已婚8例,喪偶5例;失能程度:輕度3例,中度6例,重度4例;照護模式:居家照護8人,機構照護3人,社區照護2人。主要照顧者13人中,年齡30~60歲;婚姻狀況:均為已婚;照顧時間6~36個月;男5人,女8人;文化程度:小學2人,初中及高中5人,專科及以上8人;職業:離退休3人,護工2人,技術人員3人,商業人員2人,服務人員3人;與患者的關系:夫妻3人,父子1人,父女2人,母子2人,母女3人,陪護2人。
1.2 方法
1.2.1 資料收集方法:以質性研究中的現象學方法為指導,本研究通過面對面半結構式深入訪談。首先通過查閱相關文獻初步擬定訪談提綱,訪談2對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后,調整訪談提綱,隨后邀請3名心理護理領域專家進行了兩輪修訂,形成正式訪談提綱。實際訪談中可調整提綱順序,保證訪談順利進行。本研究通過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訪談本著自愿、保密和方便的原則。
腦卒中失能老人訪談提綱:①“當您得知自己患有腦卒中時想法如何?”“您愿意告訴別人您患病的經歷嗎?”②“請談談您失能后有過被歧視的經歷嗎?”“會不會因為需要被照顧而覺得低人一等?”③“患病后身邊的人對您的態度有什么變化嗎?”“您是如何面對這些變化的?”④“您認為大眾怎么看待腦卒中后失能老人?”⑤“目前最擔心的問題是什么?”。主要照顧者的訪談提綱:①“當患者診斷為腦卒中時,您的感受如何?”②“當患者因為腦卒中而喪失自理能力時,您有什么想法?”“對您造成了哪些影響?”③“他/她患病后,您有過被歧視的經歷嗎?”④“身邊的人因此對您的態度有變化嗎?”“您是如何面對這些變化的?”⑤“您認為大眾如何看待腦卒中后失能老人?”⑥“您還有什么補充的嗎?”。當患者和主要照顧者感覺難以回答或偏離訪談目的時,將會采用引導式提問促進訪談的順利進行,訪談地點選擇病房多功能室,每次訪談約30~40 min,現場做筆錄和錄音,訪談結束后,對訪談信息進行編號,避免信息泄露,24 h內將錄音內容轉化為文字。
1.2.2 質量控制:訪談小組資質:①訪談者和記錄者具有本科及以上學學歷、護師及以上職稱;②前期均已接受質性研究相關培訓,并完成相關考核。訪談前,與研究對象進行溝通,取得受訪者的同意,向研究對象詳細解釋本研究的目的及方法。告知患者及其主要照顧者將采用編碼取代名字,采取保密形式,且告知研究對象研究資料僅供研究使用,并簽署知情同意書。訪談中避免誘導受訪者,靈活調整訪談順序和方式,適時采用傾聽、互動等訪談技巧。本研究采取現場全程錄音,研究者傾聽并對訪談內容給予記錄,同時記錄研究對象的非語言性表達,如語氣、語調、表情、動作等,對含糊不清的內容及時詢問明確并記錄,同時對受訪者的感受進行澄清,再次確認,不斷循環提問和證實,直到資料的采集出現飽和為止。
1.2.3 資料分析方法:每次訪談后24 h內將訪談錄音內容逐句轉換成文字,并結合訪談時受訪對象的表情、動作等相關信息,用Colaizzi現象學資料7步分析法[14]進行分析,包括反復閱讀轉錄信息、提取有意義的關鍵信息、對重復出現的信息進行編碼。由兩人分析收集資料,研究者將生成的編碼分組,形成潛在的主題。然后,研究者對生成的潛在主題進行多次審查和修訂,以形成內部一致的主題。最后,研究者對確定的主題進行命名。為保護隱私,患者及其主要照顧者分別用編號R1—R13、T1—T13表示。
2 結果
通過對26例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訪談錄稿的閱讀、分析、編碼,提煉出3個主題,9個副主題,分別是認知歸因(標簽認可、行為異常、他人態度、社會支持缺乏)、負性情緒反應(自責與內疚、感知異常歧視、自殺信念)、非適應性行為應對(回避社交、隱瞞病情)。
2.1 認知歸因
2.1.1 標簽認可:多數受訪者及其主要照顧者表示提到“中風”這個名稱會遭受歧視,令其感到難堪。T5:“不愿意別人說他中風了,會讓我覺得也受到了歧視。”R6:“我害怕周圍的人議論我是不是中風了,不想聽到這個詞。”R4:“以前看到一個朋友中了風之后,就跟植物人一樣,受到家屬的嫌棄,沒想到自己也中風了,肯定也會遭人嫌棄的。”
2.1.2 行為異常:腦卒中失能老人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礙,包括偏癱、偏盲、言語障礙、精神障礙和認知障礙等,本研究中有7名受訪者表示意識到自己的異常行為后而感到羞愧。R1:“就是上個月吧,老伴說你怎么把家里的水杯給摔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當時就覺得怪不好意思的。”然而,主要照顧者會因為這些異常行為影響日常生活而產生負面情緒。T2:“自從我媽中風之后,她時而清醒時而糊涂,有時鬧起來整夜都不睡覺,真拿她沒辦法(嘆氣)。”T3:“我的爸爸有次竟然在地板上大小便,太不可思議了,想想他曾經是那么愛干凈的一個人,怎么會變成這個樣子(搖頭)。”
2.1.3 他人態度:卒中后所致殘疾給患者帶來明顯的外形改變、口齒含糊等問題,使患者不能很好地融入社會,尤其是高齡患者往往被認為是社會的負擔,這些問題引起的社會歧視也會增加患者的病恥感[15]。本研究中有12名受訪者表示身邊的人會對他們產生無端鄙夷,甚至嫌棄的行為。T10:“老伴患病以后,街坊鄰居也不來我們家了,跟我也疏遠了。”R3:“我不能控制大小便,有時會弄到床上,兒子就非常嫌棄(嘆氣)。”R7:“以前我的朋友經常約我出去,自從得了病,再也沒人約我了。”R8:“平日里都是小沈在照顧我,因為吃喝拉撒都要靠她,她有時不耐煩還會吼我(哽咽)。”由此可見,腦卒中失能老人主要受到來自家人、鄰居、朋友、主要照顧者等不同人群的排斥。
2.1.4 社會支持缺乏:研究[16]表明,社會支持水平較低的患者病恥感水平更高。在本研究中,8名主要照顧者認為腦卒中失能老人認知和行為能力受損,于是減少其與外界的接觸,從而減少其社會交流,因此對患者采取一些消極的態度和行為。T5:“她現在走路都走不了,還想著出去玩,我們做兒女的每天要上班,哪有時間推輪椅帶她出去?(皺眉)”T10:“她說話講不清楚,記憶力也不好,我要她待在家里,怕她出去走丟了。”R12:“每天待在家里發呆,也沒人跟我說說話,心里老覺得憋得慌。”T11:“我照顧老太太有一年多了,她的子女住得遠,除了過節過來看一下,平時連電話都很少打,老太太經常一個人翻看他們小時候的照片。”由此可見,部分家屬對腦卒中后失能老人的關懷明顯不足,更加重了患者的孤獨感。此外,主要照顧者因為照護需求量巨大而導致社交受限,而產生不良情緒。T3:“每天照顧他都停不下來,根本沒有時間跟朋友聊天見面,這天天跟他待在一起,感覺自個兒快整出抑郁癥了。”因此,醫護人員應加強疾病的相關知識宣教,密切關注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的心理狀態,提高社會支持水平。
2.2 負性情緒反應
2.2.1 自責與內疚:本研究中有15名受訪者都表達了自責與內疚感。有研究[17]顯示,腦卒中發病與病人不良生活習慣有關,如吸煙、飲酒、飲食不均衡、缺乏運動等。腦卒中失能老人可能將患病歸因于不良生活方式,從而感到自責與內疚,產生病恥感。R7:“我以前就愛吃大魚大肉,好不容易生活條件好了嘛,誰知吃出了這個毛病,后悔都來不及了。”腦卒中失能老人還可能因為疾病導致家庭經濟負擔和生活負擔的加重而自責。R3:“得了這個病之后,經常要去醫院,花了不少錢,我姑娘掙個錢也不容易,是我拖累了她啊!(哭)”R13:“你說得什么病不好,偏偏中風了,大小便還得老伴幫忙,我太沒用了,心里難受(眼里含著眼淚)。”此外,主要照顧者認為其在生活中疏于對老人的照護,未能盡早發現老人的異常行為而耽誤治療,而感到自責。T3:“剛開始老聽他說頭暈,我想著是他睡眠不好引起的,總是讓他白天多睡一會,哎,沒想到是中風的前兆,要是早點帶他去醫院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了,都怪我!”這種不良情緒會導致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長期處于自責與愧疚的負性情緒當中,因得不到釋放和疏導,最終危害身心健康的發展。
2.2.2 感知異常歧視:有研究指出,人們與卒中患者進行社會交往活動時也會帶有排斥情緒反應和貶低歧視行為[18]。在本研究中,13名受訪者表示其受到過被排斥的經歷,而主要照顧者因為跟腦卒中失能老人有關系而受到歧視。T2:“媽媽患病后情緒很不穩定,有時大喊大叫,我總怕別人笑話我,說我母親是個神經病。”R10:“我走路有點跛,他們就會用很奇怪的眼神看著我。”R11:“我吃飯吃不了,得靠護工喂,有時弄到身上和地上到處都是,她嘴里就神神叨叨地念著,讓我覺得很沒面子。”R9:“養老院有次舉辦重陽節活動,我推著輪椅想參加,結果卻被幾個老太太笑話,說你的腿都這樣了,就別折騰了。”
2.2.3 自殺信念:有研究[19]結果顯示,老年人自殺意念發生率為11%,高病恥感的老年人其自殺意念也越高。在本研究中,有8名話受訪者表示其痛苦不堪,甚至有自殺的想法。R5:“這樣活著太痛苦了,死了就解脫了。”R8:“我自己什么都做不了,跟個廢人一樣,還經常被人嫌棄,這樣活著有什么意思(哭)。”R4:“這個病花了他們很多錢,要是死了就不用再拖累他們了(低下頭)!”T2:“吃喝拉撒都是我在照顧,像這樣下去,我快要崩潰了。”T6:“他經常發病,不管他又不行,住院費太貴了,我快承受不住了,可我還有家庭和孩子啊,有時想想活著太艱難了(掩面)。”腦卒中失能老人由于身體功能的障礙導致社會和家庭角色發生變化,導致其對生活產生悲觀態度。此外,主要照顧者因為生活質量的下降和經濟生活的壓力而產生絕望的情緒,因此,護理人員應理解并給予一定的心理支持,幫助患者及其主要照顧者走出心理困境。
2.3 非適應性行為應對
2.3.1 主動回避:有研究[20-21]表明,腦卒中患者害怕受到排斥,因而采取隱瞞病情、減少與外部社會接觸,甚至是完全退出社交場合的回避策略,從而保護自己的自尊心。腦卒中失能老人由于身體功能的障礙引起家庭以及社會角色的改變,導致患者及其主要照顧者難以接受卒中后的現實,不愿同他人進行社會交流,產生主動回避社交的行為。且腦卒中具有高致殘、高復發等特點,導致腦卒中失能老人需要反復入院治療,加上對疾病預后的未知性,使得患者及其主要照顧者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心理和經濟壓力,而采取回避就醫的行為。有研究[22]指出,52%有病恥感的失能患者不尋求醫療保健,而采取回避的社會行為,不僅嚴重影響患者的身體健康,還會降低其生活質量。在本研究中,13名受訪者表示不愿意參與社交或者就醫。R10:“我以前總喜歡跟朋友出去打打麻將,現在行動不方便,即使他們打電話來邀我,我也懶得出去了,說到底就是怕人家笑話。”R8:“不愿意親戚朋友過來看我,家里臭烘烘的,我自己都受不了,更何況別人。”R1:“我頭痛的時候就想吃點藥,不想去醫院,免得花錢。”T11:“每次帶他去醫院要花很多錢,也不知道這個病到底治不治得好,我覺得去藥店開點藥就可以了,沒必要去醫院。”此外,主要照顧者因為需要長期照護失能老人,導致生活質量明顯下降,從而不愿意與他人進行交流,盡量避免與他人接觸。T2:“天天照顧她,感覺自己像個保姆一樣,每天都快累死了,不愿意讓朋友看到我這種狀態。”
2.3.2 刻意隱瞞:腦卒中患者更加容易產生自卑心理,害怕別人知道自己的病情而故意疏遠,為了避免受到他人歧視,而采取隱瞞病情的行為[23]。在本研究中,11名受訪者表示不會將病情告訴他人。R4:“我才不會告訴別人我中風了,我又不是傻子?”R3:“看到她們都健健康康的,我心里就不是滋味,不想讓別人知道我得了病。”R10:“我是不會跟別人講我中風了的,就算現在腿不方便要用輪椅,我也只說是摔了一跤造成的。”主要照顧者還因害怕被他人責怪而遭受歧視,從而出現隱瞞病情的行為。T12:“我不會告訴別人他中風了,還不是怕別人在背后對他指指點點,而且我也怕別人在背后說我沒有照顧好他啊!”
3 討論
3.1 促進機體重建
在本研究中,訪談對象常常因為身體功能的障礙和自理能力的下降,導致社會和家庭角色的改變,而在人際交往過程中受到排斥,無法接受卒中后殘疾的現實,從而產生自責、羞恥甚至自殺等負性情緒,最終影響腦卒中失能老人康復的動力和功能恢復。因此,幫助腦卒中失能老人努力去適應身體功能的變化,促進其功能恢復,建立個體重建尤為重要。朱蓉蓉等[24]通過小組模式的豐富環境訓練可以有效改善腦卒中恢復期患者病恥感水平,增加患者康復的信心,提高生活質量。因此,醫護人員可針對腦卒中失能老人建立個體化康復治療護理,成立包括康復師、治療師、護士在內的豐富環境訓練小組,對住院期間的腦卒中失能老人進行感覺功能訓練、運動功能訓練和社會交往訓練,讓患者在訓練過程中,通過相互觀摩、學習和交流,增加康復訓練的信心,建立正確的認知態度,以降低病恥感水平。有研究[25]表明,在患者住院期間,在醫護人員的監督下,康復訓練效果明顯,但在患者出院后,由于康復指導和督促的缺乏,導致多數患者出院后鍛煉依從性明顯下降甚至中斷,最終影響康復效果。
居家照護是我國失能患者最主要的照護模式,主要由家庭成員(配偶、子女和兄弟姐妹)或雇請的護工照顧失能患者[26]。本研究中大部分腦卒中失能老人以居家照護為主,多數主要照顧者為家庭成員,不僅缺乏相關的專業知識,還承擔著來自照護腦卒中失能老人和撫養子女的雙重壓力,給整個家庭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因此提供有效的延續性護理較為關鍵。朱達斌等[27]通過對出院后的腦卒中患者進行互聯網+微信平臺的遠程康復指導,能有效地改善患者出院后自我康復的執行情況,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行為和功能鍛煉的依從性,促進功能障礙的恢復。因此,針對出院后的腦卒中失能老人,醫護人員應提供新型延續性護理模式。通過建立腦卒中失能老人康復治療微信公眾號和微信群,微信公眾號主要定期推送腦卒中相關知識和健康教育,例如腦卒中危險因素的管理、服用藥物的注意事項及不良反應、腦卒中并發癥的預防等;微信群為患者提供咨詢和個性化的指導,提高主要照顧者的照護能力,例如錄制照護者康復鍛煉視頻、指導照護者家庭支持系統、鼓勵患者及其主要照顧者之間互相交流與學習。鑒于部分腦卒中失能老人不會甚至無法使用智能產品,故延續性護理的實施主要通過指導和監督主要照顧者來完成。
3.2 提高心理彈性
本研究將腦卒中失能老人與其主要照顧者的訪談內容進行比較發現,大多數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普遍存在自責、感知歧視甚至自殺信念等負性情緒。嚴丹君等[28]研究表明,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不僅會影響老年人的生活滿意度,還會影響老年人疾病的治療和恢復。Zhang等[29]研究表明,心理彈性越好的腦卒中恢復期患者越能夠保持相對穩定的心理狀態,使其能與外界保持積極互動。因此,醫護人員應該重視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的心理狀況,針對此類人群應提供有效的情感支持和人文關懷,提高其心理彈性,來降低病恥感的水平。冀小飛等[30]通過對結直腸癌造口患者進行接納承諾療法的護理干預,結果發現能有效緩解患者的病恥感。接納承諾療法[31]是基于積極心理學、基本認知科學、基本獨特哲學的一種現代認知療法,強調接受和正念,而非取代錯誤思想,重點在于引導個體擁抱痛苦,接受“幸福并非人生常態”的觀念,從而提高個體面對逆境的能力。因此,在患者住院期間,醫護人員可通過指導患者及其主要照顧者進行正念呼吸、播放腦卒中失能老人的積極康復視頻、組織病友交流會、鼓勵患者互相吐露心聲等方式來促進內心的接納。積極語言“HAPPY模式”是具有正向肯定,提出指向未來的建議和有目標效果的行為的語言,負向肯定他人、不相信他人、帶有惡意的言語禁說或者不說[32],王容等[33]將該溝通模式應用于與老年腫瘤患者的溝通上,結果發現觀察組心理痛苦評分低于對照組。因此,醫護人員可在護理此類患者時運用積極語言“HAPPY”溝通模式與患者進行溝通與交流,對患者及其主要照顧者的配合及時給予肯定和表揚,為患者提供舒適輕松的溝通環境。倪菀景等[34]通過敘事護理干預讓患者敘述疾病故事,使得患者負性情緒得以宣泄,從而降低了患者的病恥感,提高患者的社會心理適應水平。盧威男等[35]通過共情護理倡導醫護人員與患者進行換位思考,從內心深處體驗患者的痛苦,從而掌握患者被尊重和被關懷的心理需求,可有效緩解患者的病恥感。因此,醫護人員可以采用敘事療法和共情護理對其實施人文關懷,重視感知患者及其主要照顧者的情感及情緒狀態,鼓勵患者講述其患病歷程,鼓勵主要照顧者表達其內心的負性情緒。通過使用心理痛苦溫度計評分表[36]評估其心境和認知,引導患者及其主要照顧者重新對自身進行定位,正確認識和分析他人對自己的評價,緩解因錯誤認知帶來的困擾,引導其心理認知重構,從而提高其心理彈性。
3.3 指導積極應對
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國人傾向于隱瞞患病和社交回避的情況[37]。本研究中,部分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存在回避就醫的行為,這可能與此類人群對疾病的認知不足導致對疾病的轉歸產生悲觀的想法以及對住院費用的擔憂有關。鄒明英[38]通過對腦卒中偏癱患者實施個案護理管理,發現能有效提高腦卒中偏癱患者的疾病知識的知曉率和治療的依從性。因此,基于腦卒中失能老人的需求,在患者住院期間,醫護人員應根據制定的疾病的診治方案,實施“一對一”的個案護理管理服務,出院后個案護理管理小組成員可采用電話隨訪的方式進行個案護理管理干預,從而加強健康教育,提高其對疾病的認知水平。目前,已有部分慢性病納入醫保范圍[39],因此建議醫療保險等相關部門根據腦卒中失能老人對醫療保險的服務需求,將腦卒中常用藥品及康復項目納入醫保范圍,以緩解患者及其主要照顧者的經濟壓力,從而提高治療的依從性。此外,本研究訪談結果顯示,大多數患者及其主要照顧者都存在隱瞞病情和回避社交的行為,這可能是因為此類人群都有過遭受他人歧視的經歷。李楊等[37]研究結果表明消極行為反應會加重患者的心理負擔,減少尋求社會幫助。然而隱瞞病情與回避社交的行為屬于消極行為反應,因此,醫護人員應促進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建立積極的應對方式,如指導其建立生理應對機制,包括瑜伽、藝術、物理療法、呼吸訓練和肌肉放松等,指導其建立認知應對機制,包括正念減壓、認知重組和冥想、音樂療法等;指導其建立環境應對機制:與自然接觸、與寵物親密接觸等,這與國外Harrington等[24]關于壓力、健康與應對的研究結果一致。
3.4 加強社會支持
蔣丹等[40]研究顯示,社會支持水平越高,腦卒中恢復期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也越高,使其越能夠適應疾病帶來的家庭和社會角色的變化。然而本研究訪談結果顯示,大多數訪談對象因為受到來自他人的歧視,導致社會支持不足甚至缺乏,使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處于孤獨閉塞的環境中,負性情緒長期得不到釋放和疏導,嚴重影響了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身心健康的發展。這可能是由于社會公眾和主要照顧者對疾病的認知不足,對殘疾人存在偏見有關。有研究[41]表明,人們總會優先選擇具有良好的社交能力的人結交,即避免與具有不良社交能力的人交朋友。因此,社會媒體應該關注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利用電視網絡及廣播等加大對腦卒中知識的普及,呼吁社會群體關愛腦卒中失能老人,消除社會歧視與偏見。醫療機構可通過新媒體途徑,如公眾號、微博、線上課堂等,宣傳腦卒中相關疾病知識。醫護人員應向患者及其主要照顧者講解疾病治療的新進展,定期開展腦卒中預后康復知識宣教的講座。廖君蘭等[42]通過研究同伴支持的自我肯定訓練,讓患者與周圍病友相互交流共性問題,彼此間形成互惠互助的良性循環,最終降低了患者的社交壓力和負性心理。因此,建議醫護人員采用同伴支持干預,通過小組同伴支持的形式,幫助患者獲得歸屬感及價值感。
本研究訪談結果顯示,部分患者還會受到來自家庭成員和主要照顧者的歧視,家庭成員或主要照顧者應給予腦卒中失能老人充分的理解和支持,經常陪伴患者,耐心傾聽和照顧患者[43],鼓勵患者參加社會活動,降低其心理壓力。此外,本研究中主要照顧者也存在內疚、被歧視甚至悲觀絕望等心理反應。有研究表明,患者的病恥感與家庭照護質量呈一定的相關性,家庭照護質量越高的患者病恥感越低[44]。祝夢婷等[45]通過實施陪伴者壓力管理方案可有效緩解陪伴者的壓力反應,有助于減輕患者及其陪伴者的病恥感。因此,醫護人員還應關注主要照顧者的認知及情緒反應,通過鼓勵主要照顧者敘述患者患病后的看法,主動與主要照顧者進行互動與交流,了解其真實的內心感受,運用情緒治療法對其不良情緒進行疏導,同時指導其通過書寫日記、閱讀療法、音樂療法等進行正確減壓,以減輕主要照顧者的生理和心理壓力,避免其生活質量受到影響,使主要照顧者以積極健康的心態對腦卒中失能老人實施高質量的照護,有利于降低腦卒中失能老人病恥感的發生,促進其疾病的早期恢復。
綜上所述,本研究通過對26名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進行深度訪談,發現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病恥感,病恥感的認知歸因會引起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出現一系列負性情緒,而負性情緒的發生會導致其做出非適應性的行為反應。因此,醫護人員和社會工作者應高度重視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病恥感的問題,深入了解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內心的真實感受,積極幫助該人群進行機體重建,提高此類人群的心理彈性,指導其建立積極的應對方式,增強對此類人群的社會支持力度,從而降低其病恥感的水平,促進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心理社會功能的恢復,提高腦卒中失能老人及其主要照顧者的生活質量。
利益沖突聲明:作者聲明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