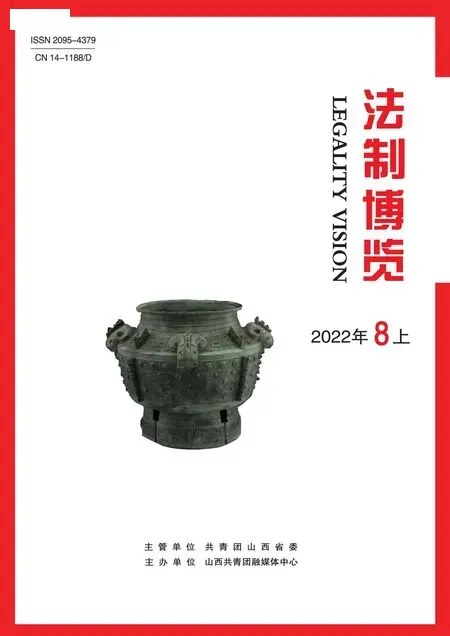建設工程實際施工人的法律保護
尤子旗
青島科技大學法學院,山東 青島 266000
一、實際施工人保護制度介紹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基礎建設投資的不斷擴大,建筑業帶動了全產業鏈的共同發展,為國家的經濟騰飛提供了強大動力。但與此同時,行業的快速發展也滋生了諸多問題。建筑市場不規范,社會信用制度不完善,在發包方長期處于優勢地位,建筑行業本身準入門檻低的情況下,承包方為了在招標投標環節中取得優勢,竭力降低投標價格,提升自身資質。在利益的驅動下,轉包、違法分包、借用資質等違法現象頻出,同一工程可能涉及多個主體、存在多份合同[1]。法律關系盤根錯節,即使最終建筑工程經過驗收合格,實際進行施工的主體也很可能不是與發包方訂立施工合同的承包方。轉包人、違法分包人以及借用資質承包工程中的出借方往往并不參與實際的施工活動,其利潤來源于取得工程后倒賣的行為。由于無需支付施工所需要的材料、人工等費用,也無需承擔組織施工、墊付資金的義務,在發包人拖欠施工款項時的催款動機也就并不強烈。有的工程幾經轉手,實際施工人如果想要盈利,就只能劍走偏鋒,建造豆腐渣工程,克扣農民工工資的情況成為一種必然。造成了實際施工的各種主體如包工頭、農民工等群體的利益難以保障。如果嚴格依據合同相對性原則來進行處理的話,實際施工人在其上手主體資格滅失或找不到人的時候,無法請求發包人支付工程價款。農民工討薪無門,不斷發生以生命相威脅的極端事件,引發巨大的社會問題,引起國家的高度重視。
在此背景之下,為了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加強對于農民工群體權益的保障,最高法在2004年制定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釋(一)》首次提出了實際施工人這一法律概念,分別出現在第一、四、二十五和二十六條中。實際施工人突破了合同相對性,直接向發包人主張權利。合同相對性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只有合同當事人一方能夠向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請求或提起訴訟[2]。這是人民法院在兼顧其他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前提下,對弱勢方當事人尤其是廣大農民工提供的司法保護。此后實際施工人制度在2018年制定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釋(二)》及配合《民法典》施行而制定的新的建設工程司法解釋中都得到了繼承、延續和發展。
二、實際施工人的范圍
實際施工人并非一個完全的法律概念。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釋(一)》出臺之前,無論是法律、司法解釋還是相關的政策法規,對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都沒有做出明確的界定。如果僅對司法解釋進行文義解釋的話,實際施工人應當包括轉包、違法分包的承包人,而對于缺乏資質借用資質與發包人簽訂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是否屬于實際施工人則存在爭議。這就導致了司法實踐在不同地區,不同層級的法院對于實際施工人身份的認定存在巨大爭議。
以陳某訴A公司、陜西B建設公司等勞務合同糾紛案為例①參見陜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陜01民終10601號民事判決書。。被告陜西B建設公司作為承包人從發包人中鐵C局處承包到了雅馨花園建設項目主體工程,并將其中的勞務工程分包給了被告王某所有的A公司。原告陳某是在王某承包的勞務工程中從事木工等工作。一審法院在查明陜西B建設公司存在欠付王某工程款項以及王某欠付陳某勞務費用的相關事實后,根據《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釋(一)》相關規定,支持了陳某要求該建設公司在欠付工程價款范圍內向其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的訴訟請求,即一審法院認為“實際施工人”包括為承包人提供勞務服務的自然人。二審法院則認為實際施工人包括非法轉包、違法分包以及借用資質與發包人簽訂施工合同的承包人。陳某屬于王某雇傭為其提供勞務服務的工人,并非實際施工人。實際施工人應當是王某而非陳某,并且陜西B建設公司也不是發包人而是總承包方,因此陳某只能向王某和A公司主張請求給付勞務費用,據此二審法院對于陳某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面對實際施工人范圍在司法適用中存在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該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一書中認為實際施工人一般指最終投入資金、人工、材料、機械設備實際進行施工的施工人[3]。包含借用資質訂立的施工合同中的施工人、轉包合同中的施工人以及違法分包合同中的施工人三類主體[4]。
三、保護實際施工人的理論依據
根據《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當事人之間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也就不存在合同關系,因此無權請求對方承擔合同責任。實際施工人對發包人的請求權基礎既有代位權說[5]也有不當得利返還說[6]。相關司法解釋所創設的實際施工人概念,是對當前社會背景下處于弱勢地位的包工頭、建筑工人以及農民工等群體利益的特別保護。該項規定突破了合同相對性以及契約自由原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以發包人為代表的群體承擔義務的不確定性,導致了相關主體之間法律關系的不穩定,但卻更好地實現了實質意義上的公平。
契約自由是指民事主體地位平等,并且有權按照自己的意愿實施民事法律行為。《民法典》第一百三十條也對契約自由進行了法律詮釋。契約自由的價值在于實現不同社會形態下各主體之間的實質公平,讓各種市場主體能夠公平競爭,激發市場活力,促進經濟發展。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完善,對于以合同為代表的契約制度的要求也不斷提高,不僅需要滿足效率方面的要求,也要實現公平方面的需求。從契約自由到契約公平主要是基于三個假設:(一)理性人假設,即人具有理性能力,能夠對自己的未來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安排;(二)充分協商假設,合同中的條款是經過合同雙方充分協商后的結果,能夠反映合同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也能夠實現合同雙方當事人所期待的利益;(三)契約地位平等假設,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地位完全平等,能夠公平地進行有效博弈,可以充分地爭取自身的利益。基于以上假設,合同所組成的契約將是具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夠在實現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實現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達到全社會的帕累托最優[7]。
然而現實生活中的情況卻并非如此,契約的絕對自由往往無法兼顧契約公平的實現。首先,市場中的所有主體并非完全理性。個體由于受到自身能力、情緒、經驗的影響,在實際決策中往往無法做出最為理性的選擇,表現在合同中則是無法充分體現自身所要從契約中獲得的所有利益。其次,并非所有合同都經過了當事人的充分協商。占據市場優勢地位的主體與其他主體簽訂合同時往往傾向于以提供格式合同的方式來達成契約。格式合同的接受方往往被迫接受合同中對自己不利的條款。最后,由于每個市場主體掌握的綜合資源并不相同,這就導致了簽訂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地位存在優劣。處于優勢地位的一方更能通過契約來實現自己的利益。
在建筑領域契約自由與契約公平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建設工程合同涉及的工期較長,合同內容較為復雜,同時受市場波動影響明顯,因此合同雙方很難在簽訂合同當時對于整個履行過程進行理性把握。建筑施工尤其是勞務分包領域的技術門檻并不高,導致擁有項目資源的發包方長期處于優勢地位。《建筑法》規定了建設工程施工主體應當具備相應的施工資質,擁有資質的主體較缺乏資質的主體而言在招投標環節更具優勢,有著巨大的尋租動機。合同雙方地位不平等,合同簽訂過程中就很難保證充分協商,最終傷害了實際施工人這個龐大群體的利益。
四、實際施工人的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
改革開放以來建筑市場的快速發展,常常伴隨著頻出的行業亂象。由于發包人較之承包人具有優勢地位,以及我國在建設工程施工領域長期存在的墊資承包方式,發包人拖欠承包人工程款的情形比比皆是。這一現象不僅嚴重影響了建筑行業的有序發展,也傷害到了實際施工人以及從業人員特別是農民工群體的利益。承包人權利之受損,必然會導致其雇用的實際施工人員利益損失。因此原《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條規定并確立了建設工程價款的優先受償權制度,平衡了建設工程市場各主體之間的地位,得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因此在《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條中得到了繼承和發展。
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不僅優先于普通債權,而且優先于建設工程上所設立的抵押權,本質上是對于發包人債權人順位的調整。在保護承包人合法權益,維護農民工利益方面取得重要作用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發包人其他債權人的合理預期,影響其債權的實現,因此應當對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的范圍加以準確界定,以維護市場經濟的有序發展。
建設工程領域合同無效往往是因為違反了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而引起的。因此筆者認為,實際施工人無權享有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首先,就承包人轉包與違法分包導致建設工程合同無效的情形而言,發包方對于轉包及違法分包的事實并不知悉,承包人與實際施工人的行為導致了發包方意圖讓承包方進行施工的目的無法實現,損害了發包方的利益。如果允許實際施工人主張優先受償權,則會使得實際施工人能夠從自身的非法行為中獲益,有違誠實信用原則,也損害了發包方其他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其次,就實際施工人借用資質與發包人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這種情形而言,應當就發包方是否知情進行區分。如果發包方知情,那么該借用資質的實際施工人本質上就是該項建設工程的承包人,其與發包人之間的合同為有效合同,因此應當享有優先受償權。在發包方不知情的情況下,出于公平原則及保障發包方其他債權人利益的角度出發,實際施工人不應當享有優先受償權。
五、實際施工人法律保護現狀及建議
《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釋(一)》出臺以來,對于實際施工人的法律保護有了較為明確的依據,目的是保護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雖然存在前文所述的問題存在,但不可否認該項制度對于建筑市場的繁榮發展、弱勢群體的保護起到了重要的幫助作用。隨著《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等規范文件的出臺,農民工討薪難的問題日益弱化的當下,對于弱勢群體的保護是否還要以突破合同相對性的實際施工人制度加以支撐,越來越多的人提出了質疑。有觀點認為完全可以采用債的代位權制度對于實際施工人群體的利益進行保護以維持法律體系的完整。也有觀點認為,實際施工人的優勢是靈活、運營成本低。這種經營模式存在于建筑市場中,有其客觀原因,與我國當前經濟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有關,不會因為法律的禁止或者法院不予保護而消失[8]。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及反復,多地的房地產行業受到了巨大影響。停工導致的資金鏈斷裂,進而影響到了整個行業鏈條內各主體的利益。上游發包人主體利益受損,導致中游承包人墊資后資金鏈斷裂,進而無力支付下游農民工群體工資的現象激增。據統計,2020年南昌市線下受理欠薪投訴1000余件,同比增加20%。雖然行政機關有權對欠薪單位進行行政處罰,也存在相應的工資保證金制度,但對于發包人等建設單位而言的震懾力度還遠遠不夠,弱勢群體維護自身利益的最終手段往往還是司法途徑。因此現階段對于實際施工人的特別保護依然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