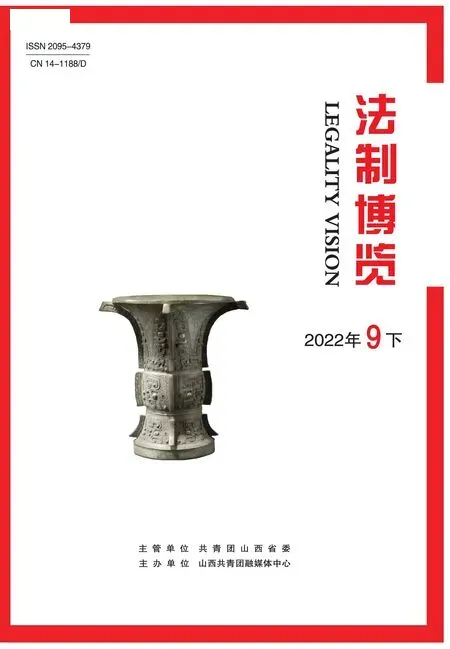電子證據在應用中存在的問題
于 存
上海海事大學,上海 201306
一、電子證據時代
隨著社會信息化浪潮的逐步高漲,信息科技的革命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千變萬化,我們邁入了一個被信息主導的時代,人們的生活越來越依賴于虛擬網絡。同時人與人之間的生活交往、商業交易也由書信、紙質合同轉變為了QQ、微信、電子郵件、電子合同等。人們的各種活動只要和網絡有關都會在電子空間留下自己的痕跡,電子證據也高度滲入各種糾紛中,作為法定證據種類之一被高頻率運用。
證據法領域的專家何家弘教授說:“司法證明的歷史經歷了‘神證’‘人證’和‘物證’三個時代,現在將走向更高層級的電子證據時代。”司法證明方法的歷史演變,表明了法律制度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也在不斷發展和進步。電子證據相對于傳統證據來說,具有虛擬性、復雜性、科技性、易篡改、系統性等特點,而且其無論是在深度還是廣度方面,電子證據的科技含量都不是傳統類型的證據能比的。也正因為如此,電子證據加入三大訴訟法,推動了司法證明觀念的改變,也使得司法證明制度不斷變革和完善,同時,因為其本身的高科技性,電子證據對于司法人員的科學素養和法律素養要求也更高。
二、我國電子證據立法的發展
我國對于電子證據的規定散布在不同位階的法律中。從1999年的原《合同法》初步承認電子合同的合法性,到2004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確交通監控資料可以作為道路交通糾紛的證據之一;以及2004年出臺的《電子簽名法》對電子證據的概念、可采性及證明力作了初步的規定;2013年后,我國的三大訴訟法相繼把電子數據確立為法定證據種類,至此,電子證據開始廣泛應用到訴訟中。在司法解釋層面,最高法、最高檢也出臺了如何適用和認定電子證據的司法解釋。在部門規章層面,2010年最高檢、最高法、司法部、國家安全部和公安部等五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從電子證據進入我國法律的歷程來看,對我們來說電子證據是一種相對陌生的證據形式,它確立的時間并不長,各個層面的法律規范對電子證據的規定都是“各家各論”,就目前為止,也沒有一個協調統一的關于電子證據如何運用的規則。如何收集、保全電子證據,如何認定其證明力,如何對其進行審查和判斷,這些問題都沒有明確的法律規范對其進行規定,這也導致了在司法實踐中對電子證據的運用出現了不確定性和不統一的現象。
三、電子證據在應用中存在的問題
(一)法官對電子證據的認識不統一影響著法律的確定性
1.案例一
原告陳某向法院起訴被告郭某,陳某主張郭某尚未歸還借款1620元。在本案中,陳某只提供了兩頁微信聊天記錄作為證據,該聊天記錄的內容顯示被告郭某曾借陳某3000元,尚有1620元未歸還。但是被告郭某不認可該聊天記錄的真實性。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原告主張被告于2016年8月8日向其借款3000元,截至2017年5月12日,尚欠原告借款1620元,未能提供充實證據予以證實。原告提供的聊天記錄不足以證明欠款尚未歸還,不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①陳某與郭詔某民間借貸糾紛案,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銀海區人民法院(2017)桂0503民初560號。
2.案例二
李某和楊某交往1年后分手。李某將楊某起訴至法庭,要求其返還戀愛期間其贈送給楊某的財物。在法庭上,兩人對聊天記錄的真實性產生了爭議。李某提供了兩人分手后的微信聊天記錄,微信聊天內容顯示了李某在分手后曾向楊某主張要其歸還財物,楊某承諾說錢湊夠了就還,但是后來又回復沒有錢不會歸還。在庭審中,楊某不認可聊天記錄的真實性,楊某辯稱李某知道她的微信賬戶和密碼,李某是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登錄了她的微信賬戶發送的承諾還錢的內容。
該案經過了兩審法院,一審和二審法院對該聊天記錄真實性采取了不同的態度。一審法院認為微信賬號沒有經過實名認證,不是實名制的,賬戶不是專屬于某個人的,知道賬戶密碼即可在別的設備上登錄,從而與通信錄中的聯系人進行聊天。鑒于該特征,法庭不認可該聊天記錄的真實性,故一審沒有支持李某要求楊某歸還財物的訴訟請求。而二審法院則認為,李某提供的聊天記錄是兩人分手后的完整真實的聊天記錄,楊某所辯稱的聊天記錄是李某用其自己手機發出的,沒有出示相關的證據,故楊某要對此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1]
從上述兩個案例來看,在與日常生活聯系最為緊密的民事訴訟領域,并沒有形成統一的對電子證據的認定規則,民事訴訟中對證據的采信要靠法官的自由心證。鑒于電子證據是一種新的證據形式,加上其本身的復雜性,電子數據的易篡改等特性,在大多數民事訴訟中,法官對電子證據的采信持有很謹慎的態度。通過查閱民事訴訟中涉及電子證據的相關判決,發現有相當一部分的電子證據未被采納,不被采信的原因集中在“易篡改、沒有經過公證或者鑒定、沒有其他證據相佐證”等。而采納了電子證據的判決中,法官也避免了對電子證據采信的原因進行正面說理,而是像案例二中的二審法院一樣,從反面說明采信電子證據的原因,即因為反駁方舉證不能,因此采信電子證據。沒有完整統一的電子證據認定規則,必然會導致電子證據在應用中出現“同案不同判”現象,而“同案不同判”的現象又會反過來影響電子證據應用的確定性。法律如果不具有確定性,人們便無法對自身的行為后果有所預期,進而無法據此設定或約束自身的行為。
在我國目前的司法環境中,人們對電子證據的認識水平依然不高,電子證據在司法實踐中的應用尚未形成完整成熟的機制。尤其是在民事訴訟中,訴訟雙方都不是專業的電子證據研究人員,雙方不了解電子證據,也沒有在司法實踐中運用電子證據的經驗,這導致了法庭上關于電子證據的許多交鋒都是走過場,同時審判人員是專業的法律人員,但不是研究電子證據的專家,他們也缺少審查認定電子證據的成熟經驗,對電子證據的采信信心不足。[2]
(二)電子證據的書面轉化現象嚴重
雖然電子證據已經在三大訴訟中取得了獨立的地位,但是在司法實踐中,人們傾向于把它轉化為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證據形式,也就是電子證據的書證化。這種思維模式的產生基礎就是對虛擬數字信息的真實性抱有懷疑的態度。[3]
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尤其是在民事訴訟中,每個法官每年要處理的案件眾多,考慮到審限以及出于盡快解決糾紛的目的,也為了法庭審理中證據展示的便利,訴訟雙方或司法工作人員常常會將電子證據轉變為其他的證據類型,例如,將電子證據以書面化,包括打印書面化、公證書化、鑒定意見書化等形態存在。如民事訴訟中最常用的,將電子聊天記錄證據打印下來轉化書證。但是電子證據作為一種獨立的證據類型,其形成過程、驗證方式以及證據本身攜帶的信息量都與書證存在著明顯的區別,同時電子證據所包含的信息也不是轉化后的書證所能比的。把電子證據書面化的做法雖然可以提高司法效率,但是隨之而來的電子證據的真實性和關聯性問題并未在技術層面得以解決,同時也忽視了電子證據本身蘊含的巨大信息。[4]一些缺乏電子證據專業知識的司法人員,不敢用、不會用電子證據,使得電子證據面臨著被架空的風險。[5]
電子證據書面化轉化的重要成因之一就是傳統觀念認為電子證據是人們肉眼無法識別的信號,人們對它的運行機制也不清楚,所以當然地認為電子證據很容易造假,很容易被篡改。然而,電子證據是一個系統,且具有系統穩定性,也正因為如此,電子證據的每一個微小的變化都會留下痕跡。電子證據的系統性是指電子證據的產生、改變都不是孤立發生的,而是系統性的。電子證據是由若干個元素組成的系統整體,是由一系列命令或程序遵循一定技術規則組成的海量電子數據的融合物,這一現象就反映了電子證據的系統性原理。[6]由于電子證據系統不僅能夠表明電子證據形成的結果,而且能夠表明電子證據在形成的過程中留下的痕跡。雖然破壞部分證據相對比較容易,但要破壞全部證據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破壞證據本身又必然留下了破壞證據的證據。電子證據這種內容本身與附屬信息之間“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系,使得對電子證據的任何操作,都會造成電子證據內容本身及其關聯信息的相應變化,一方面使得任何操作都變得可追蹤;另一方面也肯定了電子證據的“不易毀滅性”,如電子證據并不會因為簡單的刪除甚至格式化操作而被清除。
(三)普通當事人提取電子證據的需求與現實之間存在著矛盾
普通當事人具有電子證據收集的需求以及主體資格。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公訴案件中,公檢法等公權力機關有權向單位和個人收集證據。在自訴案件中,自訴人獨立承擔控訴職能并且要承擔舉證不力的責任,因此自訴人也享有收集相關證據的權利。公訴案中的被告人,雖然不負有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但仍然可以提出關于輕罪、無罪的辯護,因此也享有提出相關證據證明自己無罪的權利。可以看到,不光作為取證主體的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享有法律所賦予的取證權利,被告人、自訴人也同樣享有取證的權利。[7]
而在民事訴訟中,除了法律規定的職權調查外,法院原則上沒有調查和收集證據的義務,通常情況下,證據的收集和提出都是訴訟雙方自己負責。基于民事訴訟的“不告不理”和“法官中立”,在民事訴訟中法官一般不主動幫助當事人調查證據。對于專業性較強的電子證據,普通民事訴訟的當事人不具備相應的能力,此種證據收集制度對于電子證據的收集和提取缺乏現實可操作性,實踐中難以執行。[8]當然,在民事訴訟中,弱化并規范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職能,強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是我國民事審判的要求。但由于電子證據科技含量較高,當取證主體不是專業偵查人員和計算機專家,而是普通大眾時,其證據收集能力是缺乏保障的。此外,普通民眾可以依據怎樣的規范對電子證據進行事先的保全和事后的收集,從而保護自身合法利益,則暫時缺乏配套的可操作性強的法律規范供普通公民參照。
2017年最新出臺了《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律師辦理電子數據證據業務操作指引》,由此,律師在辦理涉及電子證據案件過程中,在取證、舉證環節可獲得一定的操作指引。民事主體和律師雖然擁有了電子證據收集的資格,但是在電子證據應用的大部分環節,尤其是取證環節,當事人或者律師進行電子證據收集取證的可操作性較弱,表現在司法實踐中,民事案件中電子證據遭到質疑的比例和最終法官對電子證據未予采信的數目遠大于刑事案件。
當然,還有一些關于證據的收集和提取的例外規定。例如為了避免證據毀損滅失導致以后難以取得而建立的證據保全制度,但是這種保全需要由當事人主動提出申請,而且從當事人提出申請到法院實施保全行為必然有一個很大的時間跨度,在電子證據可能隨時滅失的情況下,這種取證方式則可能因貽誤時機而難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3]
四、結語:大數據時代需要更加深入認識電子證據
電子證據時代,個人活動越來越多地在電子空間留下直接或者間接的痕跡,電子證據在訴訟中成為獨立的證據形式、是發現線索的來源,并已經為人們所接受,且將會成為主流。但是電子證據在司法應用中存在的問題也是不可忽視的,這些問題甚至已經影響了司法判決的科學性。電子證據在適用中的問題,值得人們去研究、思考。不管是立法規范的缺失、技術規則的過時,還是認識的不統一、思想觀念的禁錮,抑或普通當事人的需求與現實之間的矛盾等,歸根結底,原因在于人們對電子證據的產生、運行機制不了解。在完全不了解某個事情的情況下,又何談基于該事物的運用、審查、判斷甚至立法呢。因此,要不斷加深對電子證據的認識,以在司法實踐中對其更好地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