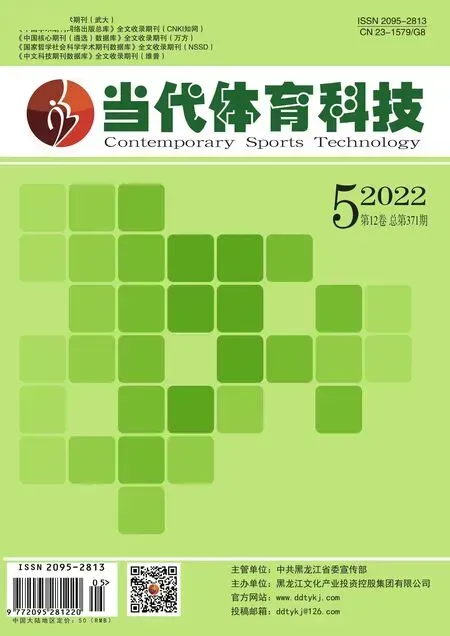武術社會功能變遷及開發研究
楊應威
(鄭州大學體育學院 河南鄭州 450044)
武術是我國民族適應自然、適應社會發展而不斷發展創制的一系列器械、技術與養生的文化綜合體,隨著中國歷史和文明發展,從遠古時期的狩獵技術、防御技術、武舞禮樂、戈術、射禮、養生等多元一體的身體活動符號,逐漸演變成當代具有教化方式的客觀載體。武術在歷史發展變化過程中,依附于不同的載體,給養著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也充分發揮著自身功能,以頑強的生命力得以繼承和延續。然而從不同歷史時期來看,武術的“社會功能”是指,隨著認知自然、社會客觀規律,不同的操作主體借助不同領域活動所獲得的不同社會效應[1],正是由于其社會功能維系著民族生存與發展的魂,才承載中華兒女基因構成的魄。但是,隨著武術的發展,一些不具有文明特征的行為出現,如欺行霸市、魚肉百姓、打家劫舍、自我防衛、人際交往、警務保安等,使武術難以形成統一的“社會功能體系”。但就其超越的層面來說,人們操作時適應自然、適應社會、規訓制己的安然自勝的實力,也是應物自如、改變定勢。這種“勢”以及自我改造、適應和進化,正是武術所具有的社會價值的法寶。武術的發展起源于生活技能的各類形式,如狩獵的方式、動物的模仿等,既展現了人們適應各類威脅的聰明智慧,也體現了不同階段人類的審美觀念和審美情趣,體現著向往自然、自我保全、自我規訓、安然自勝的價值追求。從客觀上來說,這也是一種生態平衡,它促使人們與大自然和睦共處,并產生熱愛自然、保護自然和感恩自然的向善、向美的正能量[2]。
1 武術的社會功能
1.1 武術具有治理功能
武術自古以來就有“強勢”的象征,客觀地獲取食物和配偶之需要,以及社會人際沖突現實,引發出最初的武術技術,其原始基因是動物生存競爭的攻擊自衛本能。其中,一些不成文的規矩,如民間信仰等具有很強的約束性,特別是習武之人在社會上具有較高的地位,有時也需要“武術人”來維持區域的社會秩序。通過這些勢力群體,在某些時間段內化解產生的分歧、差異和矛盾,使群體團結和睦,最終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
1.2 武術具有軍事功能
自古武術一直是多家爭鳴,特別是從軍事功能脫離以后,武術成為維系家族和區域勢力的重要工具,后來也成為朝代專政的工具。中國歷史社會中,由于政府統治能力和手段的不完善,家族爭斗和勢力派系的爭斗較為常見,血統關系與血緣情感在家族內部締結了一種強大的凝聚力和共存亡的使命感,“家族至上”成為武術傳承和當時社會治理功能的邏輯起點。這與武術群體“鼻祖”“門師”“武圣”等圖騰式的人物,鞏固習武者之間的“擬家族式”有連帶關系。
1.3 武術與山林文化的傳播功能
武術本身多帶有的“強勢”的優勢,也是歷代勢力所排擠的對象,這也造成了武術與山林及武術與宗教的結緣,如嵩山、武當山、峨眉山等都成為優秀武術文化發展中心。也可以看出,武術往往是在夾縫中生存,但是武術發展也顯現了擇勝地發展,山林文化也因武術而名響天下,擇山而居,營造神秘、幽靜、閉塞的良好習武環境,給士子帶來隱士的環境體驗,這也是武術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所獨有的社會功能形態。這種擇山傍水的武術文化形態,顯示了武術神秘、磨煉的價值追求,對提升人生境界、習武質量、養生價值培養有著積極的作用與意義。
1.4 武術具有祭祀功能
武術文化的傳承,除了武術家族傳授的途徑之外,武術文化的巫術儀式與圖騰崇拜等祭祀儀式相關。如興盛于先秦且延續至清朝的祭祀射禮,作為國家祭祀的形式——武舞。舞時手執斧盾,郊廟祭祀及朝賀、宴享等大典。其形式為歌頌統治者顯赫地位,對外也顯示統治實力,武舞是祭祀的最高形式之一,但是其發展歷程也是隨著人類認知自然的規律而形成的,其形態也依附于祭禮文化涵蓋下的狩獵技術、武舞禮樂、射禮、戰爭訓練等多元一體的身體符號。祭祀中的武術,顯示了具有以祭禮文化主導下的多符號身體運動參與的歷史印記。武舞誕生于搏殺技術的訓練方式,武舞演練方式,增強軍隊的士氣,武舞也是武術套路形態。但由于社會生產力低下以及對自然和社會發展形態的淺顯認知,武術的祭祀形式也出現了功夫的神秘化,甚至巫術化等文化示范現象。
1.5 武術具有表演功能
武術的表演功能是古代武術的重要功能,包括武術的祭祀、武術在百戲、武術在軍事武舞表演中都一定程度依附于武術的表演功能。由于武術技術動作肢體動作的學習模擬、操作經驗的歷史積累,包括模擬動作、動作經驗等。武術在大型百戲和民間藝人表演中得到廣泛運用,宋人孟元老記述北宋“諸軍呈百戲”時云:“有花妝輕健軍士百余,前列旗幟,各執雉尾、蠻牌、木刀、初成行列,拜舞互變開門、奪橋等陣,然后列成偃月陣。樂部復動蠻牌令,數內兩人出陣對舞,如擊刺之狀,一人作奮擊之勢,一人作僵仆。出場凡五、七對,或以槍對牌,劍對牌之類。”百戲中“如擊刺之狀”的武戲或武打表演;民間藝人表演中出現了花刀、花槍、滾杈、套棍之類成套動作練習,如何繼承和發揮武術的表演功能,是今后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之一。
1.6 武術具有養生功能
在中國文化體系中,武術將保存、保養和體認生命三大功能有機地融為一體而別具中國“系統思維”之特色。武術的健身功能不斷得到人們的重視并不斷強化,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已認識到習武的“拳勇”與“股肱之力”“筋骨”的關系,即使到了軍事武術中也重視武術的強身健體功能,提出“練為戰”,強調實戰應敵是其主要的功能體現。到了近代,“體育救國”的呼聲高漲,當時西方體育項目影響力不大,武術的健身功能被提到新的高度。到了現代,隨著生活節奏加快和生活壓力增大,武術的養生健身功能被進一步挖掘,在武術其他功能弱化的今天,健身養生功能成為武術發展和傳承最好的功能之一。但是武術被并入體育項目以后,武術的健身功能與體育運動形成了競爭的局面。
2 當代武術功能弱化的因素
到了當代,隨著體育的經濟功能、休閑娛樂功能、教育功能、政治功能和社會功能得到體現,武術作為體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功能的地位也逐漸凸顯。然而,武術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隨著時代的變遷,武術的功能也逐漸發生變化,武術的祭祀功能、治理功能、軍事功能等部分功能弱化。隨著西方體育項目的滲入,武術的教育功能、表演功能和養生功能都不同程度地發生了變化,學習武術不再是家族傳承的專利,武術逐漸推行學校教育;武術的養生功能與以往發生了巨大變化,養生價值開發與武術發展的初衷相違背。武術的表演變成團體,單獨的武術技藝魅力被掩蓋[3]。隨著社會生活方式的轉變,武術功能在武術文化傳承中部分弱化,導致武術文化發展不規范,動力不足。
2.1 武術祭祀、治理、軍事功能的淡化
武術的原生和衍生功能,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催化作用,經過長時期歷史變遷,在一定歷史階段,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一系列社會功能。隨著人類探索自然、適應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武術的軍事、社會治理以及祭祀功能逐漸被時代淹沒。武術意識決定武術行為,武術觀也帶動武術功能的演變,武術原生的功能,篤行“生命至上”的觀念,武術正被“競藝”賦予的創新理念、蘊含多類文化元素的優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所改造,繼而轉變成社會經濟、文化教育與體育的發展工具,形成新的功能載體。
2.2 武術套路的“運用”功能弱化
武術套路作為武術結構表層的運動形式,被現代社會所接受,標志著古代武術從整體上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歷程。武術套路也繼承了古代人體文化中的文化現象和武化現象,古代武術訓練目的決定其抵御的功能,其訓練目的為“練著不練套”[4]。武術套路將技術動作組合、串聯,而且飽含攻守進退、動靜疾徐、剛柔虛實等矛盾運動的變化規律,一招一式都蘊含著技擊和攻防的雙層含義。當時,軍旅武術和民間武術強調實用,也就是實戰中的應用,其差別僅在于軍旅武術是用于“開大陣,對大敵”的軍陣群斗,民間武術是用于“私斗”和“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之類個對個的格斗。而到了明清時期,武術的武斗功能逐漸弱化,表現形式轉變擂臺中格斗運動,這就意味著武術進入了戲斗階段。清朝初葉出現的游戲性格斗練習法“太極推手”,技法原則是“舍己從人”[5]。古代武術格斗運動循著由蠻斗、經巧斗、向戲斗發展的歷程中,直接對抗性質日趨淡化,文斗色彩日益濃厚。器械格斗運動始終未能形成穩定的技術體系和比試方法,徒手格斗運動則從走上擂臺而又離開擂臺[5]。
2.3 古代養生功能需求旺盛
以《易筋經》為代表,采用“以血氣之驅,易為金石之體”的價值追求,“并其指可貫牛腹,側其掌可斷牛頭”。養生功法被賦予了延年益壽的時代內涵。如《莊子·刻意》中所謂“吹口句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采用吐納導引術式,獲得身體和心理的優越體驗,傾向于對修養身心價值的追求。在當下,強調和尊重“以人為本”的社會價值觀背景下,滿足個體需要是武術功能傳承和創新應當堅守的基本規約,武術養生功能的提升,也反映了武術文化功能的社會適應性發展,亦是實現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延伸的形態之一。
3 武術功能變遷的動力
3.1 武術生存競爭中打斗求生的“零和博弈”
武本身含蘊武技之意,是應對沖突的操作,需要雙方共同參與,因此操作主體不同的社會需要和環境條件的多種約束,技術內涵可以歸結為對抗、施展技能、保存自己、制服對手、分出勝負條件下的肢體沖突應對操作,其歸屬于生存競爭中的“零和博弈”。武術是用身體或者生命去抗爭,并施以攻防含義的技術操作,克敵制勝,以攻防技術為手段,以攻為目的,以防為措施,保存自我的打斗博弈,這是武術生存的基礎,也是其魅力所在。
3.2 武術飽含著中華民族朝代的更迭,精神追求,價值情懷,文化需要
社會變革能夠不斷生根發芽,彰顯其頑強的生命力和社會價值。從早期的生產勞動中和部落、種族的沖突等方面演變總結出來,后來發展成為人們喜愛的體育活動,其產生和發展見證了不斷變化的歷史過程,武術文化功能的開發有利社會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更有利于滿足當前人民群眾對武術功能價值的需求。武術植根于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中,在人類社會歷史中演繹著獨特的魅力,他又是文化的載體,在不同社會階段顯示著強大的生命活力,即使到了當代,武術攻擊的含義被弱化,但是其技藝、技理、技法仍在不斷演變,其變化無窮的操作,正是吸引武術愛好者的價值情懷和精神追求。
3.3 武術文化展現旺盛的社會功能價值
從歷史的角度看,中華民族的歷史源遠流長,武術作為文化的一種載體,其具有文化所具有的典型特性,武術技法、武術習練者、武術器械等在不同歷史時期展示出不同的社會功能,甚至從不同層面影響著生活、家庭、社會以及思維方式、信仰、審美、社會習慣、生活方式、行為規范等方面。武術文化既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也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特征[7]。武術是中華民族勤勞智慧的結晶,其不但具有獨特的文化特征和社會功能,而且蘊涵著社會發展變遷的歷史文化,從古代的軍事形式發展為今天的養生手段,其文化發展的形式對不同社會階段產生不同的社會功能,而且正逐步展現其旺盛的發展動能,被現代人所接受[8]。
3 結語
中華武術博大精深,歷史悠久,其作為獨立的社會文化現象,是與中華民族文明的產生和發展同步的。武術雖因地域環境、社會環境、社會生產水平等方面,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其都是在生活實踐過程中產生的,從古至今,由于不同社會價值觀的存在,其社會功能也有不同的表現。中華大地疆域遼闊,民族眾多,人文多元,造就了武術的不同地域特征和表現形式,在兩千多年的發展演變過程中與多種文化形態相互滲透交融。雖然歷史背景、政治以及經濟發生著根本性的演變,但武術正以不同的文化形態展現在世人面前,其社會功能取向也發生著相應的轉變。總體來說,武術的作用與價值功能都是相通且互為依存、互為補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