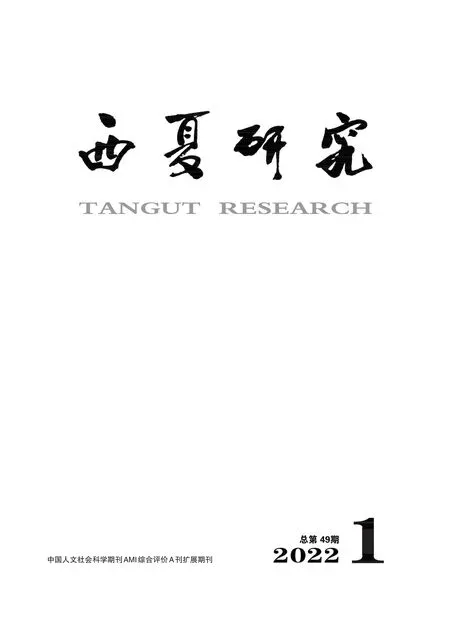西夏醫藥用具考
□黃超群
在現存的西夏醫療材料中,有一部分關于醫藥用具的內容。結合出土文物來看,西夏的醫藥用具可分為醫用工具和藥用工具兩大類,細分則有度量衡器、制藥器、貯盛器、服藥器和治療器五類。醫藥用具是醫藥水平發展的重要標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夏醫學發展的實際水平。因此,通過研究醫療器具的種類和使用狀況,我們可以更為深入具體地了解西夏醫學的發展程度及其特點。
一、出土西夏文獻和文物中的藥用工具
藥用工具即在藥物加工、服用、貯盛以及丹藥煉制等過程中所使用到的器具,數量大,品種較多,實用性也較強,是醫藥用具之大宗。從其功能來看,西夏時期的藥用工具主要有度量衡器、制藥器、貯盛器、服藥器四大類別,分別應用于藥物稱量、加工、貯盛及服用諸環節。
(一)度量衡器
度量衡器主要用于測量物質的長度、體積和重量。西夏的度量衡制度和中原地區一脈相承,是以尺寸、升斗、斤兩來計算的。西夏文蒙書《新集碎金置掌文》中就有“斛斗衡升斗,鈺俞鐵稱斤兩。褐絹量尺寸,大數占算得”[1]8-16的記載。西夏尺寸接近唐、宋制[2]9。《文海》記載:“抄者十粟一圭,十圭一撮,十撮一抄,十抄一勺,十勺一合,十合一升,算計起處是也。”[3]424圭、撮、抄、勺、合、升、斗、斛是容量單位,與中原一致,皆十進位制。“銖者稱算用也,十黍一鎰,十鎰一銖,六銖一錢,四錢一兩,十六兩算一斤。”[3]205鎰、銖、錢、兩、斤是衡量單位,衡制是一斤十六兩,也與唐、宋相近[2]9。
兩、錢、升、斗是西夏在制藥過程中常用的計量單位,經常出現于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醫藥文獻諸藥方中。如“荊芥湯”載:“白茯苓、川椒、荊芥穗各一兩數。”[4]88“豆蔻香連丸”載:“黃連三錢。”[4]107“治熱病要論”第二十九方載:“治孩童小頭疥者,柳葉一升、松子仁一升等為粉,二斗水中煨如血汁時,洗頭疥。”[4]377此外,撮、抄、勺等在其他方面不常用到的較小的計量單位,在西夏制藥過程中也時常用到。如“耳內出血方”載:“搗為細粉,清洗先前淤血,在耳內撒□撮藥粉,撒五至七次則愈。”[4]181“治熱病要論”第十二方載:“治女人生后渴不止者,益母草為干粉,一次一勺端。”[4]340
長度單位在出土西夏文醫方中出現得比較少,主要見于針灸類文獻之中。如《明堂灸經》第一中載“凡下火點灸,欲令灸艾炷根下廣三分”[4]426、“今定患人兩眉中心直上三寸為發際,后取大椎直上三寸為發際”[4]427等,用于確定穴位及針灸位置。
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醫藥文獻諸藥方中,藥物用量上也夾雜著非計量單位。這些非計量單位可分為擬量單位、數量單位、估量單位三種類型。
擬量即以實物比擬的質量或容積單位。在出土的西夏文藥方中,擬量多是用于比擬藥丸的大小,常見的有紅豆大小、梧桐子大小、如小豆許、如豆大、豆粒大、指頭大小等。
數量即以數定量的一種計量方式。在出土的西夏文藥方中,數量單位常用來計量一些體積比較均勻的藥材。此類數量單位有根、粒、副等。
估量單位多以錢幣、勺、盞、碗等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器具,來對藥物容量進行估算。出土西夏文藥方中常見的估量單位有碗、盞、甑、瓢等,也有用手估量的。
進入隋唐以后,藥物計量單位中占主流的明顯是衡量單位,不精準的擬量、數量、估量單位和不適用的長度單位逐漸被淘汰,容量的單位也逐漸減少,藥用計量單位漸趨科學、精確、標準、實用[5]2136。從現存的西夏醫方來看,非計量單位多數是用于藥物毒性小、藥效不猛烈的藥物或者藥方中對應的水、醋的計量,在藥方中并不占主導地位。宋代醫藥中出現了非計量單位向計量單位的過渡[6]2574,深受中原醫藥影響的西夏醫藥對此也有所繼承。
“凡度制、量制、衡制,均有法名與器名二種。”[7]81也就是說,“升”“斗”“撮”“勺”“尺”等,既是度量衡的單位名稱,同時又是度量衡器的名稱。因此,見于出土文獻及文物的西夏藥物計量工具有測量容積的撮、勺、升、斗,測量重量的戥稱和測量長度的尺等。
撮,直柄有勺,是一種小型量器。《說文解字》:“撮,四圭也。”[8]605歷代衡量制度多有變換,由此造成了量制和量器在實際使用中的混亂。鑒于此,唐朝孫思邈曾對小劑量藥物的衡量標準重新作出了規定:“一撮者,四刀圭也,十撮為一勺,兩勺為一合。”[9]25此舉改善了藥物稱量中的亂象。撮作為中國古代常用的量器,在考古過程中也常有出土。1956年,河南省陜縣隋墓曾出土一件新莽時期始建國銅撮,圓口,平底,有長柄,通長11.5厘米,高1.2厘米,口徑2厘米,計算容積2.07立方厘米[10]224。出土西夏文醫方“耳內出血方”中有載:“搗為細粉,清洗先前淤血,在耳內撒□撮藥粉,撒五至七次則愈。”[4]181其中的“撮”,可能是估量單位,即以三指撮取的藥量,也可能是以撮所取之量。遺憾的是西夏目前尚未見有撮這一量器出土。
勺是一種直柄有小杯的量器。《說文解字》:“勺,挹取也,象形中有實,與包同意。”[8]299勺最初是舀酒的盛器,后也被作為量器使用。銀川市曾發現兩把西夏時期的鐵勺。編號N01024·030[NCL:913]鐵勺口徑14厘米,高6.2厘米;柄長23厘米,寬2.1 厘米;流長7.5 厘米,寬5 厘米;重1315.4 克。勺口內斂,弧腹下垂,下腹漸收,大平底,口沿橫出寬長流,腹部附長柄。編號N01024·031[NCL:914]鐵勺高7.7 厘米,口徑14 厘米;柄長20厘米,寬2.8厘米;流長8.7厘米,寬4.5厘米;重2210 克。 半球形勺,短流,勺口附長柄。[11]2626-2627“治熱病要論”第十二方載:“治女人生后渴不止者,益母草為干粉,一次一勺端。”[4]340在醫療過程中,勺主要用于量取液體或粉劑。
升、斗也是古代常用的量器,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在具體容量上,歷代又有所變遷。根據文獻考察,西夏的升、斗在容量上與宋是相近的,但目前尚未有西夏升、斗的考古實物出現,其形制是否與中原一致尚未可知。
戥稱,一作戥子,一名等子,是一種精細小稱量的系盤小型桿秤。其制可考者,唐有大兩小兩之分,《唐六典》謂合湯藥用小兩,是即戥稱之制作,而無其名。宋時始有等子之名。[7]84-85戥子源起于特定稱量的需要,比如醫藥用稱。一個處方往往要列出十幾味、幾十味藥,一般都是稱幾“兩”和“兩”以下的幾銖,所以要求把日常用桿秤改進,精細制作成小型桿秤[12]380。雖然目前尚未見有西夏時期的戥子實物出土,但西夏文辭書中收有“戥子”[13]323一詞,《文海》則釋“稱”為“此者論計也,量用也,令分輕重也,稱星之亦謂”[3]522,說明戥稱在西夏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廣泛的應用。
此外,如前所述,西夏醫方中還有一部分估量單位。如“荊芥湯”:“加水一碗,開八九沸,熱含冷吐,勿咽。”[4]88“人參半夏散”載:“右搗為粗粉,一次三錢,一瓢水中與生姜末同煮,各分盞澄清,熱服時顯效。”[4]90因此,在制藥過程中,還常用到勺、盞、碗、瓢、甑等日常用具作為估量工具。
(二)制藥器
制藥器是指在藥物炮制、研磨、制劑、煎煮等過程中所使用到的工具。西夏的制藥器包括了粉碎器、蒸煮器、過濾器三類。
粉碎器主要是杵臼。杵臼是一對配套使用的研磨工具。《說文解字》:“臼,舂也。古者掘地為臼,其后穿木石。”[8]337“杵,舂柄也。”[8]262杵臼出現的時間比較早,先秦時期已被廣泛使用。杵臼起初用于舂搗糧食,經改造后衍生出了專門研磨藥物的藥杵臼。張籍《臥疾》詩云:“僮仆各憂愁,杵臼無停聲。”[14]6《太平御覽》引杜預《奏事》云:“藥杵臼、澡槃、熨斗、釜、甕、銚、槃、鐵鳥鐵育,皆民閑之急用也。”[15]3360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在其所著《千金方》中多次提及對杵臼的應用,有時還會根據藥物性質的不同選取不同材質的杵臼,其中包括鐵臼、木臼、玉杵以及搗衣石制成的杵等。如“服茯苓方”載:“數數攪不停,候蜜竭,出,以鐵臼搗三萬杵。”[16]662“大補氣方”載:“及熱,木臼合搗。”[9]289
在出土的西夏醫方中,常見將各種藥物混合,“碾為粉”“搗為細粉”“前藥為粉”,再制成丸藥的制藥過程。因而,藥碾和杵臼也是西夏醫人的常用工具。寧夏境內出土過西夏時期的杵臼,包括鐵臼、瓷臼、石杵、鐵杵、瓷杵。其中編號為N01024·027[NCL:910]的鐵杵臼,臼口徑11 厘米,腹徑14.4厘米,高17.6厘米;杵長25.6厘米,直徑2.2 厘米;重7.6 千克。鐵臼直口微斂,溜肩,弧腹,下腹漸收,五蹼足底座。鐵杵為圓柱體,兩頭略粗,中部略細。保存完整。[11]2620此杵臼體積較小,是藥用杵臼的可能性比較大。由于文獻的闕如,西夏醫人在制藥過程中是否也像中原地區一樣,根據藥物的藥性選擇不同材質的杵臼,尚不得而知。
藥物在制劑之前,通常要經過蒸、煮、炒、炙、熬等加工過程。西夏在制藥過程所使用到的蒸煮器有甑、鍋、釜、鐺、銚、鏊、坩堝等。
甑是古代常用的一種炊具,底部有許多透氣的孔格,置于鬲上蒸煮,類似現代的蒸鍋。出土西夏文醫方中反映出很多藥的制作需要蒸制,如“醫肚瀉不止方”載“搗為細粉,水浸蒸餅為丸”[4]98。因此,甑在制藥過程中是十分常用的器具。
鍋也是制藥過程中常用的工具,以鐵質居多,主要用于藥物的熬制和烘焙等。如“五補丸”載:“前列諸藥各一兩,□(鍋?)內為粉,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4]2932013 年,銀川西夏陵區管理處于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征集到一口六鋬耳鐵鍋,編號為N03024·013[YXB:006506],口徑56厘米,壁厚1.8 厘米,重19218 克。呈半球狀。直口微斂,方唇,圓鼓腹,環腹對稱鑄有6只方形鋬耳。鋬耳殘長3 厘米,寬5 厘米。圓底,底面尚存3 條范線。器身布滿鐵銹。保存完整,被定為三級文物。[11]2590西夏文辭書中出現了“藥鍋”[17]243一詞,說明西夏也有專門用于熬藥的藥鍋。
釜即無腳之鍋,可安于灶上烹飪。在新石器時代,釜作為蒸煮器已經被普遍使用,后來還出現過專作衡量體積之用的量器釜。釜在制藥過程中主要用于煎藥。《千金方》就曾記載過銅釜、鐵釜和土釜等不同材質的釜,用于煎煮不同的藥物。“蜜餌”載:“上四味,合和,以銅器重釜煎,令可丸之。”[16]659“太一神精丹”載:“內土釜中,以六一泥固際,勿令泄氣。”[9]216寧夏也出土過西夏時期的鐵釜。其中編號N01024·010[NCL:817]的鐵釜,口徑36 厘米,高24 厘米。口微斂,口沿與腹部間出寬平沿,沿下曲腹漸收,圓底。保存完整。[11]2584
鐺屬于釜的一種。《太平御覽》卷七五七引《通俗文》:“鬴有足曰鐺。”[15]3360在制藥過程中,鐺與釜皆用于煎藥。《千金方》中有金鐺、銀鐺、銅鐺、鐵鐺之別。如“澡豆方”:“取銅鐺于炭火上。”[16]127“豆紫湯”:“上二味,以鐵鐺猛火熬豆。”[9]50西夏辭書中也收錄了“鼎鐺”[17]458一詞,可作鐺曾在西夏普遍使用之證。
銚是一種煎藥、煎茶或者燒水用的器具。《說文》:“銚,溫器也。”[8]711《眾經音義》:“銚,似鬲,上有镮。……銚形似槍而無腳,上加踞龍為襻也。”[18]564白居易《村居寄張殷衡》詩云:“藥銚夜傾殘酒暖,竹床寒取舊氈鋪。”[19]1120可見銚在制藥過程中的實際應用。西夏文辭書中也出現過“茶銚”[17]363,說明銚子在西夏人的日常生活中有廣泛的應用,也應會用于醫療領域。
鏊,俗稱鏊子或鏊盤,是一種平底圓形的炊具,主要用于食物和藥物等的烙制、烘焙等過程。“痢疾神效丸”:“蜀黍子一種多數,鏊中油焙焦。”[4]98
坩堝是一種可移動、耐高溫的容器,是古代冶金活動中的重要工具,可進行多種的金屬的物理和化學反應。文獻記載中的坩堝,最早用于煉丹,宋以后多用于金銀冶煉。[20]358-359西夏制藥中涉及丹藥冶煉過程的,或會用到坩堝。1985 年,寧夏回族自治區海原縣西安州故城遺址出土的編號為N09031·003[0445 F399]的紅陶坩堝,口徑10厘米,底徑7.5厘米,高21.5厘米。夾砂紅陶。方唇,侈口,深弧腹,通體燒成硫狀。平底微外凸。器表凹凸,粗糙不平,有煙炱痕。小氣孔滿壁,內壁較光,殘損。[11]2718
火爐在制藥過程中的作用是給藥物加熱。如“固金丹”載:“前列兩種金丸、麻團丸共三種,火爐上焙熟紅。”[4]251
在藥物烘焙的過程中,有時還用紙張作包裹之用。如“敕賜紫苑方”中,“大黃用濕紙裹火內焙,切作片子”[4]402。
過濾器有漏斗、篩子等。漏斗用于過濾、分離和灌注藥液。1987年,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寧東鎮靈武窯址出土編號為N01032·303[NKIV:445]的黑釉瓷漏斗,口徑11 厘米,斗嘴徑1.4 厘米,殘高9.7 厘米。圓形棱口,曲腹下收,圓錐狀流。通體施黑釉。外壁窯粘青瓷片。[11]3347
(三)貯盛器和服藥器
貯盛器和服藥器之間的界限比較模糊,有一部分貯盛器同時也是服藥器。此類器具主要有缽、甕、瓶、盤、罐、碟、壺、瓢、碗、杯、盞等。
西夏文醫方“經效散方”載:“石搗為細粉,一次一錢,瓢中攪服時,顯效。”[4]205規定此藥粉要在瓢中攪拌后服用,藥效才能得到充分發揮。“治熱病要論”第五方載:“治女陰內出血……又當歸、樸消、白花馬藺等份為粉,一盞水中二錢,煨七分時,熱食則愈。”[4]218藥粉和水的比例以盞數來計算,便捷直觀。此外,西夏文辭書中也保留了很多可作貯存和服藥之用的器具之名目。
這些貯盛器和服藥器均是日用品,用途廣泛,材質多樣,有銀、銅、鐵、陶、瓷等數種。比如,出土的缽就有銀缽、銅缽、陶缽、瓷缽四種,碗有銀碗、陶碗和瓷碗等。從總體來看,陶瓷材質在其中占大多數。其中緣由,除了陶瓷制品在日用品中的廣泛使用之外,也與其自身的性能和特點有關。“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用陶瓷器貯存藥物和煎蒸藥物的良好習慣。陶瓷器性能穩定,不易變質,因而貯煎藥物,明顯優于銅、鐵器皿。”[21]238
二、出土西夏文獻和文物中的醫用工具
醫用工具主要指用于行醫治療的器具及與醫家有關的物品,可分為早期醫療工具、手術用具、手術輔助用具、上藥器等四類。西夏醫療中所使用的早期治療工具有針灸用具和拔罐用具。
針灸是中原醫學中的一種獨特的治療方法,起源于新石器時代,晉唐時期被廣泛應用,后來也為北方各少數民族醫學所借鑒。至遲于春秋戰國時期,“九針”已經成為針灸的專門工具。在西夏,針灸在治療風熱病、皮膚病方面的應用尤其廣泛。黑水城出土過西夏文針灸類醫書《明堂灸經》,出土西夏文醫方中也記載有針灸治病的內容。灸法、針刺法和放血療法這幾種針灸術在西夏都有實際應用,其中尤以放血療法為主。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醫方“治熱病要論”第二十一方載:“治身長黑瘡,劇痛難忍者,針扎小孔,撒松膠,膿流盡,則愈。”[4]355可見放血療法在西夏醫學中的實際運用。因此,雖然目前尚未有西夏時期的針刺工具實物出土,我們還是能夠推測,西夏在針灸過程中,至少是會使用到刺血用的鋒針和放血用的三棱針。《文海》將“扎針”釋作“病左刺右;此者病患處鐵針穿刺使出血之謂也”[3]523。可見西夏針灸所用的針一般為鐵質。
拔罐療法,又稱“火罐療法”,古代多以獸角為拔罐器具,因此又稱“角法”。到了唐代,拔罐療法已經獨立成科,有了較為完善的理論體系,規范的操作步驟和廣泛的臨床適應癥[22]59。敦煌曾出土過兩件涉及拔罐療法的藏文文獻,其中詳細記載了運用拔罐療法治療流血不止和肝腹水的方法。西夏和敦煌毗鄰,又同處絲綢之路上,交往頻繁,加之這一時期北方各民族醫學的廣泛交流與融合,因此西夏也可能掌握了拔罐療法,使用到治療專用角罐。
刀、匕首、剪刀、鑷子、藥鎞、紗布是常見手術用具和手術輔助用具,用于外傷的清理和包扎。其中,鎞是一種治療眼病用的工具,形如箭頭,用以刮眼膜,可除眼翳。杜甫詩云:“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23]西夏文辭書中也出現了“藥鎞”[3]442一詞,可見這一醫療用具在西夏有實際的運用。
上藥器有噴藥器、小竹管、小紙管等。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醫方記載了西夏地區對于點眼法的運用。點眼是眼科常用的外治法,即將粉狀藥物點入眼角,用以消炎退腫除翳,因此需要用到點眼工具。西夏又有吹耳法和吹鼻法,是一種用小竹管或小紙管、噴藥器將藥散吹入耳內或鼻內的治療方法。因此,小竹管、小紙管和噴藥器也是在耳鼻疾病治療時必不可少的工具。
三、西夏醫療用具的特點和價值
以上是對出土西夏文獻和文物中的醫藥用具的歸納和考證。從中我們可以總結出西夏藥用工具在選擇和使用上的幾個特征。
其一,材質多樣,應用廣泛。這些用具有金、銀、銅、鐵、陶、瓷、石、竹、紙、紡織品等,西夏早期日用品多木質,因此,西夏的醫藥用具中應該還有一部分木制品。從醫學考古的角度來分析,又包括稱藥器、制藥器、貯盛器、服藥器等藥用工具,早期醫療工具、手術輔助器械、上藥器等醫用工具。西夏的醫藥用具材質多樣,運用廣泛,囊括了制藥、儲藥、服藥以及外科手術諸環節。
其二,多由其他器具兼用。西夏的醫藥用具,尤其是藥用工具多非單純的醫療用具,而是由度量衡器、食器、炊器、貯盛器以及其他生活用品兼用。這也是中古時期醫藥用具發展的共同特征。在這一時期,中國醫藥用具較多地借用了其他用具如食器、兵器、樂器、飾品等,沒有自己獨立的系統和專門的制造業。[24]3
其三,藥用工具數量明顯多于醫用工具。目前可知的醫用工具只有針灸用具,拔罐用具,刀、剪等手術輔助器械,以及藥鎞等上藥器數種,而藥用工具則在種類和數量上均占大多數。其中原因,一是因為黑水城出土涉醫文獻以藥方居多,因此保留下來了較多制藥和服藥過程中器具使用的實際情況。二是與西夏對中原醫學的吸收具有偏向性有關。結合出土醫方、辭書等材料分析,西夏對于不同體系的醫學理論與知識的吸收具有主動性,也存在偏重性。相比解剖學等不能直接對癥的學科,西夏更側重于對藥物學與方劑學等實用醫學知識的學習。三是與中國古代醫療發展的普遍現象相契合。中國傳統醫學沒有給大型外科術提供生存的土壤,湯藥針灸占據了主流地位。[25]82-95因此,藥學得以持續發展,藥用工具自然就多,而以手術器械和手術輔助器械等為代表的醫用工具則失去了長足發展的動力,形成不了自己獨立的系統和專門的制造業。四是與同時期的宋朝相比,西夏的醫藥用具更加單調、簡陋。宋朝的醫藥用具雖然依舊沒有形成自己獨立的系統和專門的制造業,但始終朝著精美繁復的趨勢發展。宋代藥枕、香爐、瓷質儲水器等的制作達到了很高的制造水平,還首創了中國醫學史上最為精巧名貴的醫學模型針灸銅人[21]238-253。西夏制造的醫藥用具與宋代醫藥用具的精致程度仍有差距,在工具的選用上也更為原始。比如,在治療外傷時,有時直接用樹葉、菜葉等作包裹敷貼之用。
由以上對于西夏醫藥用具在制造和選用上的特點的歸納,我們可以看出西夏醫療的一些實際狀況。西夏的醫藥用具材質多樣,運用廣泛,多由其他器具兼用,這些特征都與同時期的中原一致,體現了西夏對于中原醫學的吸收和運用。西夏的藥用工具數量明顯多于醫用工具,可見其對不同體系的醫學理論與知識的吸收的偏重性以及對于藥學的重視。西夏對醫療器械的使用雖多與宋同,但從品質、數量、種類來看,其與中原地域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夏醫療水平相對落后的實際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