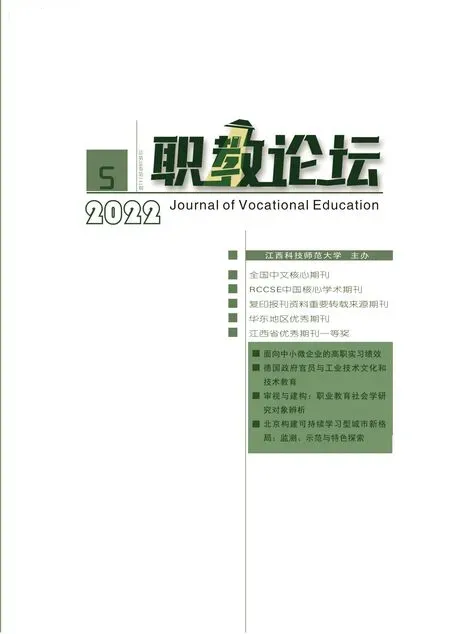工業技術文化視野中的德國科學資助者協會
□咸佩心 李琦琦
德國科學資助者協會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以下簡稱資助者協會)是德國頗具特色的組織,它是由3000 多家企業、基金會和個人組成的協會,是工商界基金會的聯合體,通過管理基金、 募捐以民間資助的途徑為德國的科學、教育和創新提供資助,是德國科教創新體系最重要的推動者之一。依據其章程,其任務第一是“促進科學和研究事業”,第二是“依據協會的目標促進教育和人才培養”。自成立以來這個協會把來自企業界的經費源源不斷地用于教育革新、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為德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在德國的科研體系和人才培養體系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舒爾茨指出:“協會并非在一般意義上單純支持科學的發展,而是將國家科學發展視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來給予特別的支持”,并且將“科學視為工業的基礎,贊助科學也就是促進工業和企業,旨在從產業界的角度來影響國家科學技術的政策”[1]13。那么,作為一個由企業家組成的組織為什么要關心科學和教育的發展?為什么要自愿資助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事業?
如果僅僅從資助者協會本身出發,單純探究其與德國科學技術的關系,是很難回答以上問題的。我們不妨從工業技術文化的視角來審視資助者協會,可更好地理解其行為邏輯。這種以促進經濟發展為宗旨來推進科學教育的發展,并進而影響國家的科學技術政策的行為模式,清楚地彰顯了工業技術文化的底層邏輯。所謂工業技術文化,是指在工業化進程中,圍繞著技術與機器、企業與生產而形成的一整套行為規范和價值觀念[2]。現代工業社會的生產、經濟以及勞動無不以科學和技術為基礎,而基于科學與技術而形成的工業技術文化,就成為科學與技術發展乃至企業發展的精神基礎。工業技術文化可以被視為科學技術和現代工業企業的共同的文化基礎,將看似隸屬不同范疇的兩個領域緊密地聯系起來。德國作為西方工業強國之一,在其工業化進程中形成了獨特的工業技術文化,為工業發展和技術進步提供了文化保障。德國工業的大發展以及工業技術文化的建構,得益于社會的各種力量:包括各行各類的大中小型企業,他們是工業經濟發展和工業技術文化的執行者; 各相關政府部門,他們是經濟發展工業運作的政策制定框架保障者;各種行業組織以及許多以企業和經濟界為背景的社會組織,他們是企業與企業、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協調者;各類高校、應用科學大學以及職業教育,他們是培養工業社會中的經濟運營單位所需要的人才的人才培養科學傳播者。現代工業社會的生產、經濟以及勞動無不受到工業技術文化的影響,社會各個階層各個團體包括現代教育也被納入了工業技術文化的范疇,服從技術和生產的內在需求。這些基于產業和企業而形成的上述各種利益群體,通過各種經濟的、政治的、法律的、社會的手段參與和工業與企業相關的立法及政策制定,維護工業和企業的利益,通過各種手段來為企業的發展提供支持與服務,不僅是德國工業技術文化的主要代表和支撐力量,也是工業技術文化的建構者、促進者和守護者。而本文關注的德國科學資助者協會自成立以來不僅為德國的科學發展、人才培養和科技創新提供了經費支持,而且在德國的科學和教育政策制定以及科技與人才培養制度創新方面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無疑是德國工業技術文化的一個重要行動者,是溝通產業界和科學技術領域的一個橋梁。本文基于工業技術文化的視角,以德國科學資助者協會的活動為線索,通過研究德國工業技術文化行動者的章程和目的以及行為、活動來分析其作為工業技術文化的建構者和推進者的角色和影響,理解工業技術價值觀念、行為規范及運作邏輯。
一、德國科學資助者協會的歷史演變
德國科學資助者協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西方盟國當時抵制德國科學,給德國的科學發展帶來了多方面的挑戰:一是科研活動受限;二是科研人才流失嚴重;三是科學物資缺乏。在此背景下,“德國仍未放棄科技與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3],在普魯士前教育和文化部部長弗里德里希·施密特-奧特(Friedrich Schmidt-Ott)的倡議下,一批科學家和企業家于1920年10月30日聯合成立了德國科學拯救會 (Notgemeinschaf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這就是當今德意志研究聯合會(DFG)的前身。德國科學拯救會集中科學界的利益,并代表科學界向各州和帝國發聲。
與此同時,一批工商業界和銀行的代表于同年12月14日成立了德國科學拯救會資助者協會(Stifterverband der Notgemeinschaf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西門子公司的卡爾·弗里德里希·馮·西門子(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被選為第一屆主席。協會設有兩個管理委員會,負責協會運營的監督和指導,為主席團提供建議,對協會的重要決議進行把關和審批。第一個委員會由來自銀行業、技術行業、德國工業和貿易委員會、零售業、批發業和帝國工業聯合會的代表組成。第二個委員會則由德國經濟巨頭組成,如化學家和工業家卡爾·杜伊斯貝格(Carl Duisberg)、發明家和工程師羅伯特·博世(Robert Bosch)以及當時的聯合鋼鐵公司(Vereinigte Stahlwerke,蒂森克虜伯集團的前身)的董事會主席阿爾伯特·沃格勒(Albert V?gler)①[4]。科學拯救會資助者協會對口工商業界和銀行,對接業界為科學目的籌集資金。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科學拯救會資助者協會每年從私人來源籌集大約30 萬馬克,主要用于支持技術類高校和給青年科研后備軍提供獎學金[5]。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德國科學界再次陷入困境。當年的德國科學拯救會于1949年在西方占領區得以重建,新名稱為德意志研究聯合會(DFG)。同年,在德國金屬集團(Metallgesellschaft AG)董事長莫頓(Richard Merton)的推動下,德國科學拯救會資助者協會以德國科學資助者協會的名稱得以重建②,并定下規則,聯邦德國總統擔任其榮譽主席,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二、資助者協會的任務
資助者協會來自工業界、代表工業界、依托工業界資金而存在,其宗旨是通過發展科學技術來促進經濟和工業發展,為此他們采用的手段就是通過參與教育實現對科學的支持和影響。資助者協會總秘書長施呂特(Andreas Schlüter)說“沒有教育,就沒有科學,而沒有科學就不可能有創新”[6]。自資助者協會成立以來,依據章程,資助者協會的雙重任務為:第一,“促進科學和研究事業,用經濟方面的資金幫助科學,以促進維護或改善德國科學工作的條件,以此來獲得本國工業在與其他國家工業競爭中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1]13。第二,依據協會的目標促進教育和培養人才,“確保工業界對科學的發展及其政治框架有直接影響。因此,該協會的存在本身就證明了20世紀德國歷史上商業、 科學和國家秩序之間的密切聯系”[1]13。
德國科學資助者協會的核心任務是為德國的科學、教育和創新領域提供資金支持、建立聯絡交流平臺和提供咨詢服務,以民間資助的途徑參與德國科學、教育、創新體系的發展。資助者協會是非盈利組織,經費來自于會員的會費、錢物和遺產捐贈等,目前管理著670 家子基金會③,并擁有來自經濟界和學術界的500 多人的團隊,每年資助金額約1.5 億歐元,其中300 萬歐元用于支持大型的學術機構,近75%的德國高校在過去的五年中都受惠于資助者協會的項目,平均每年有20 多萬青少年參與其比賽和教育活動,資助者協會與合作伙伴共同為鼓勵杰出的高校教師教學設立和頒發8 個獎項,自1986年以來,資助者協會在大學資助設立了480 個基金教授職位,主要分布在經濟學、工程學、生物學等學科,總資助金額達2.2 億歐元。除此之外,資助者協會每兩年還對25000 家企業的科研活動開支進行問卷調查[7]。
按照《德國科學資助者協會章程》第二條規定,協會的目的首先是資助科學和研究,其次是資助教育④[8]。資助者協會之所以熱心資助教育和科學,是因為他們把教育與科學視為生產和經濟的一部分,是技術進步和提高生產效率的基礎。正如協會前主席杜伊斯貝格(Carl Duisberg)所說:”剩下的每一分錢都必須捐獻予科學。這是我們擁有的最好的投資資本“[4]。由此可以看出,資助者協會從促進工業和技術發展的立場出發,用工業和企業的資金來促進學術發展、教育發展和科技創新,保障經濟的發展動力。
在資助者協會看來,促進科學研究并不只是政府的事情[9],經濟界本身也應該通過自己的經費投入對科學研究發揮影響。資助者協會前主席(1993—1998年)卡爾海因茨·卡斯克(Karlheinz Kaske)曾說: “在一個總體上科學發達的文明社會中,科學的培養不可能也不應該僅僅是國家的任務,這是一項共同的任務”[10]。工業界和企業參與科學發展與研究創新,有其便利之處,可以及時、靈活地向學術界提出其需求。來自私人的經費支持,有利于使科學研究不完全依靠公共資金支持,從而保持科研的多樣性,保障學界對工業以及經濟需求回應的靈敏性,尊重科學技術發展的自然規律,不預設科研目標從而真正達到科技創新。資助者協會的資助有利于科學工作不受政府行政管理的限制,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以便做出有創造性的成果。
三、資助者協會與工業技術文化
資助者協會是一個代表工業界和經濟界利益的組織,同時,它是德國獨一無二的由商業,科學技術,政治和民間社會組成的聯合會。資助者協會不僅僅是資助者,更是一個用提出倡議并啟動和推動倡議來解決問題的組織,是一個為社會參與者提供共同制定解決方案平臺的組織。它是德國科技系統的資助者、促進者,是關鍵的伙伴和靈感的來源。從德國科學資助者協會的緣起及宗旨可以看出,這個”經濟資助科學”機構離不開德國各界精英的參與和大工業家們的慷慨支持。那么,為什么德國的大工業家們愿意捐助科技研究和教育發展?資助者協會為什么愿意資助本該由國家支持的科學和教育事業?
現代企業的發展離不開技術的創新,而技術的創新離不開科學。自工業革命以來,大量新技術的使用促進了經濟的飛速發展,工業界的大工業家們開始渴望對新技術有更深入的理解,并大量投資科學的創新和發明。德國的大學雖然從洪堡開始注重純科學的研究,但進入19世紀下半葉之后,德國的大學也開始關注科學的應用和技術的開發。科學與技術的結合、科學與經濟的結合為德國工業化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大大提升了德國的經濟實力。在此背景下,在德國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工業技術文化,為科學與技術的結合、科學與企業的結合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基礎。正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德國工業界會主動地積極參與到推動科學技術進步、推動技術人才培養當中,將科學和技術的發展視為自己的事情。正如資助者協會前主席奧特克(Arend Oetker)所說,只有當科學技術發展得好的時候,經濟也會得到發展。經濟將從中受益[11]。而資助者協會促進科學的主要手段和方法就是參與并影響教育,通過教育影響科研、影響科技人才培養、影響教育科技政策。資助者協會的存在本身就很好地解釋了德國社會對“商業經濟與科技和教育”之間的關系的理解,即商業經濟和科學教育是相互依賴的。如果沒有科學研究創新和教育體系輸出的合格的社會人才,現代經濟體系將無法在全球市場上保持自己的地位。因此,科學的任務是為高效經濟創造重要的基礎,經濟有責任促進科學[1]15。
資助者協會緊貼產業界、代表經濟界可持續發展利益的特點,讓資助者協會能夠通過促進教育、科學和創新,在時代的變遷中成功地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定位自己,始終保持與時俱進,共同塑造科教變革。其一,協會用一系列直接和間接參與教育科研的活動影響德國科教界,從本源上直接促成教育界圍繞工業來培養工業人才、學術界圍繞業界需求進行科技創新,科研成果轉化為業界產品本就是自然而然。通過工業界的力量保證學術研究的靈活自由度以及緊貼工業界的靈敏度,也對國家計劃的科研戰略主線進行補充。其二,打通資本市場與科研學術的互動通道,縮短科研成果轉化為產品的路徑和周期,加速經濟依托新科技求發展的進程。其三,同時他們也在政策層面推動科技政策和人才政策的改革,為科學和教育的創新創造良好的環境。因此,這個最初即由工業界經濟界領袖發起的協會,能夠快速獲得企業家們的資金支持,堅定不移地通過資助教育來影響科技發展、促進技術創新,以謀求社會發展和經濟繁榮。這樣的意識和傳統是符合工業技術社會運作要求的,順應了工業技術時代之需。應時應運而生的科學資助者協會因此幾經風雨依然不倒且至今依舊發揮重要作用,并通過組織一系列活動反過來繼續加強在科學技術研究以及教育等社會各界的影響力。其四,資助者協會不僅獨立地資助各種科學和教育活動,而且也與政府保持密切聯系,支持政府的有關科學和教育活動。資助者協會主席是德國國家研究機構德意志研究聯合會(DFG)主席團的成員之一,在最初的15年里,它所募集資金的60%至70%都捐贈給德意志研究聯合會[12]。德意志研究聯合會是德國政府的科研資助機構,是德國科研體系的主要資金來源。
四、資助者協會資助的項目與活動
資助者協會的資助重點是德國科研和高等教育領域,具體資助對象包括科學技術研發創新實踐者(科學人才)、科學技術傳播教授者(教師)、從事科研和人才培養的機構(學校和研究機構)。同時,資助者協會還直接參與有關的科學和社會活動,比如改善科創社會環境、 為科學發展進行分析研判,為政府部門提供咨詢,為學術界科學創新與業界技術發展建立連接,促使產業與科研的互動結合。以下對其主要的項目進行簡要梳理。
(一)資助與獎掖科學人才
資助者協會作為一個科學資助者的聯合體,首先是通過各種途徑實現對科研人才培養的獎學金資助和獎項獎勵,來促進科技進步和拔尖人才培養,引導教育和科研學術發展。
第一,設立獎學金。在20世紀70年代,資助者協會主要支持國家基礎戰略沒有重點支持的科研項目,發展創新的、與業界和實用聯系緊密的科研項目,資助優秀的青年科研人員緊跟工業界的需求進行研發。他們通過企業界的捐贈,以新的視角豐富德國學術界,直接資助科研后備軍及其研究項目,“對德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切實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取得了很好的效益”[13]。比如謝爾基金會/德國腫瘤研究基金會在生物醫藥領域促進對腫瘤的研究,為科研人員出國進行腫瘤研究合作提供獎學金,資助腫瘤研究及國際合作。建于1972年的科學與教育基金會主要資助自然科學和工科的科研項目及社會科學。1963年成立的艾里西米勒基金會主要為來自物理、電工、采礦、能源技術和宇航學的學生提供獎學金[13-14]。
第二,舉辦科學競賽。資助者協會在事關經濟和技術發展的關鍵領域,通過組辦全國性的大型比賽來激勵青年人學習培養關鍵技能,關注獎勵年輕拔尖人才,比如數學。數學技能無論是在證券交易所,還是在軟件編程中或者在理工類的科學研究中都極為關鍵。為了促進青少年的數學學習,以及對數學資優者的早期發現和培養,資助者協會從1970年開始組織全國性數學大賽。競賽活動成功地舉辦不僅促進了公眾對于數學重要性的理解,鼓勵年輕人掌握數學能力,有報告顯示,通過這個競賽資助者協會還將商業、科學、公眾和政治的各種利益理想地結合起來,贏得了商界和政界的高級合作伙伴[1,15]。1985年,資助者協會與聯邦政府、各州和商界一起成立了教育和天才協會 (Bildung & Begabung),專門進行各個學科競賽的運作管理,并制定關于如何盡早發現青年人才并更好地促進其發展的建議,進一步系統地解決支持高天賦人才的問題,持續地、系統性地激勵和支持那些在校外也有挑戰數學的愿望的年輕拔尖人才。
第三,設立杰出科學人才獎項。資助者協會還與其他基金會一起設立不少與經濟科技發展實際相關度高的獎項,獎勵科學拔尖人才。至2017年,資助者協會與其伙伴機構一起設立的獎項共有108 項。其中包括著名的與聯邦總統共同頒發的“德國未來獎——聯邦總統技術和創新獎”,表彰科技、工程和自然科學領域的卓越成就;以及與各大科學機構一起頒發6 項科學獎項:與利奧波第那科學院每兩年共同頒發”魏茨澤克獎(科學與社會)”,與萊布尼茨協會頒發“科學獎:社會需要科學”,表彰那些對科學處理重要社會問題領域做出貢獻的科學家或研究團隊,與馬克斯·普朗克協會合作每兩年頒發“科學獎:基礎與應用研究”,與弗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頒發“科學獎:聯合研究”,與亥姆霍茲協會一起每年頒發“埃爾溫-薛定諤跨學科研究獎”,以及與德意志研究聯合會(DFG)每年共同一起頒發“傳播者獎”;除此之外,還和學科專業協會以及大型基金會合作頒發7 項教學相關獎項,例如,與大眾汽車基金會共同頒發卓越教學天才獎(Genius Loci),每年表彰在教學領域樹立榜樣的一所應用科學大學和一所綜合性大學各20000歐元,用于邀請一名高等教育訪問學者;并且還分別與不同的大小基金會頒發94 項獎勵不同學科學生的獎項,例如與米娜·詹姆斯·海勒曼基金會(Minna-James-Heineman-Stiftung)一起從1961年開始每兩年給杰出的年輕科學人才頒發的丹尼·海曼獎,鼓勵其在新的科學領域的工作[10,16]。
(二)培養科學傳播者
在工業技術時代,經濟發展離不開科學,科學發展離不開技術,技術的傳播與發展離不開教育和教師。因此,支持教育、培養教師、優化教學方法、促進教學理論聯系實踐成為資助者協會的工作重點之一。資助者協會發現師范教育在許多大學仍然處于邊緣地位,師范生經常被視為二等學生。盡管許多大學試圖通過各種措施改善師范教育專業的地位,然而,這些單獨的措施無法整合成一個大學范圍內的戰略,為大學的整體發展提供動力。所以,德國教育界面臨著學校未來教師的培訓發展緩慢問題。另外,大學教學方案也缺乏與實踐的結合以及應對未來多樣化挑戰的準備。在這樣的背景下資助者協會發起了加強教師培訓的倡議。
第一,提升高校師資素養。資助者協會與海因斯·利多基金會(Heinz Nixdorf Stiftung)聯合資助師范學科發展。2013年他們分別為漢堡大學,呂訥堡大學以及慕尼黑工業大學提供了50 萬歐元的資助用于加強大學教師培訓,增加教師職業的吸引力。其一,在漢堡大學規劃六個試點項目,促進學科理論和學科教學更加緊密結合;其二,呂訥堡大學將師范教育嵌入大學的使命宣言和任務,以及與學校合作的創新設計中;其三,慕尼黑工業大學通過創建TUM 教育學院,提高教師教育在大學中的地位。除此之外,資助者協會還與這三所獲獎大學簽訂目標協議,分別設定具體的基準和里程碑。
此項目的基本目標是將師范教育帶回大學的中心,并使其成為各自大學結構中的基本要素。例如,在學術教育的職業領域,通過可持續的初始和繼續培訓計劃,提高教師培訓的檔次,并使其立足于大學;積極招募優秀的大一學生,對他們進行咨詢和能力測試,注重研究跨學科的復雜社會問題;構建一個超越學科的組織結構,與學校和其他非大學機構進行可持續合作,從而使得教師教育成為教育發展的動力[17]。
第二,促進教學改革。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仰仗于教育的創新,教育的最前線就是教師教學。所以,資助者協會一直資助面向實踐的教學示范項目,倡導良好的教學須以就業市場的需求為導向,要求大學和應用科學大學培養產業就業市場需要的畢業生。資助者協會支持教師教學改革,將促進教學列入其議程,主張重新評估教學、研發新的教學形式以及重新定位課程內容,為德國高等教育系統制定了一條重要路線[6],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標準,促使2011年至2020年聯邦教育和研究部投入20 億歐元啟動《教學質量公約》⑤,在教育系統發展路徑規劃中有效影響了高等教育部門的決策。截至2017年,資助者協會為鼓勵高質量的高校教學設立了多項教學創新獎項⑥。并在2013年發起“創造未來”的教育倡議,重點關注德國教育需要優化的六個行動領域:教育平等、職業教育和學術教育、第四階段教育、教育國際化、教師培訓和理工學科教育,對教育系統進行評估并給出行動建議,提高德國高等教育機構學習課程的現代化和國際化,促進與實踐結合,目標在2020年前決定性地推進德國高等教育系統發展。
(三)打造科教發展平臺
第一,設立大學教席,引領科研方向。為了助推對于工業發展至關重要的學科為大學帶來急需的研究新風和新課題、新思維,資助者協會推行一種新型的基金會教授職位,這一方案得到了政府和高校的廣泛認可。1985年,資助者協會收到了來自42 所大學的首批104 份申請。1986年,資助者協會首次批準了16 所大學的20 個基金會教授職位。許多新的研究學科和研究重點也因此被建立起來⑦,如今基金會教授職位成為德國高等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所設基金會教席中,90%的職位集中在生物(34.5%)、經濟學(29.6%)以及工程學(26.2%)[1,18]。
第二,支持職業教育,引領職業教育的改革。資助者協會注重加強職業教育和學術教育的溝通和聯系,拓寬學術教育和職業教育的互通渠道。眾所周知,職業教育和大學教育一直是兩種不同導向的教育,一個以應用和實踐為導向,而另一個則側重理論和反思。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伴隨著應用科學大學的建立以及雙元制教育的實施,帶有職業培養的學術教育讓學術和職業實踐產生了互聯,也很好地滿足了德國人才市場需求。為了確保德國制造的穩定正向發展,資助者協會對職業教育的發展也十分關注,并在德國職業教育面臨挑戰的時候及時推出促進其改善和改革的項目:
自2013年開始,德國第一次出現更多的(高)中學畢業生選擇了學術型大學的學習,而不是雙元制教育,且此趨勢自此保持不變。為了改變這一現狀,自2016年起,資助者協會一直在資助實施試點項目,旨在幫助拓展職業教育和學術教育之間的新過渡路徑,開發學術教育和職業教育之間可能的新合作模式。努力解決如何更好地讓德國職業教育和學術教育互相滲透的問題。
近十年,由于該教育模式的數量快速增長,出現了多種多樣的雙元制學習課程,這讓各界對雙元制課程的質量產生了質疑,因此,在2013年資助者協會在巴魯夫公司、柏林人民銀行、保時捷公司和德累斯頓技術中心有限公司等二十家企業的共同參與資助下建立了一個雙元制教育的質量聯絡網,與十所應用科學大學、綜合性大學和雙元制大學以及教育機構,如柏林經濟和法律學院、比勒費爾德應用科學大學、勃蘭登堡應用科學大學、巴登-符騰堡州雙元制大學、米特海森應用科學大學、慕尼黑應用科學大學等進行為期兩年的合作,共同為雙元制職業教育的質量發展和前景制定建議。
與此同時,雙元制教育的質量正受到職業學校合格教師短缺的威脅,特別是在機械工程、電氣工程、機電一體化這樣的工業技術專業,每年大約有500 名合格專業教師的空缺。資助者協會從2016年開始倡議加強職業學校的教師培訓,幫助高校開發職業教育和學術教育之間的新過渡路徑,提高職業學校教師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學生加入職業學校的教師隊伍[19-20]。
(四)從事科學發展統計與分析
工業技術時代科學創新技術迭代有其自身規律,業界和學界的鏈接及影響隨著時代變化而互相影響,需要對科學發展進行調查統計和分析,才能做出未來發展趨勢的研判和當下決策。資助者協會不僅支持科研人才、培養科技傳播者、打造科研平臺、創造科學氛圍,而且對科學發展進行跟蹤、調查、分析和報告,通過評估當前形勢,在早期階段研判發展趨勢,推導行動建議。資助者協會早在1951年就建立一個“科學捐贈歷史存檔服務”(Archivdienst für Wissenschaftsspenden),專門記錄經濟界的科學資助活動,后來這項工作發展為資助者協會一個專門的工作領域“科學統計”(Wissenschaftsstatistik),并于1984年在艾森(Essen)成立了專門的研究和咨詢機構,科學統計公司 (SV Gemeinnützige Gesellschaft für Wissenschaftsstatistik mbH) 專門收集、分析和解釋關于德國創新體系的數據。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聯邦教育與研究部(BMBF)一直委托資助者協會的科學統計公司對德國商業企業部門的研究與開發(R&D)活動信息進行收集和數據整合,該調查也是歐盟官方統計的一部分,并流向國家和國際報告系統。
科學統計的成果主要調查分析新的科學知識和創新是如何產生的,收集和分析關于研究過程和創新系統的數據,并與客戶和合作伙伴一起制定資助戰略計劃。數據每年收集一次,奇數年對德國所有研究公司和聯合研究機構(IfG)進行全面調查,偶數年則進行抽樣調查。調查核心指標有以下幾方面:一是按資金用途和資金來源劃分的企業內部和外部用于研發的支出,二是相關研發人員,并按所從事活動類型和性別進行分類,三是研發機構場地的區域分布,四是企業的創新活動和關鍵商業指數。科學統計公司作為科學界的一部分,與企業界、政界和民間社會人士保持密切交流,并與咨詢公司和大學合作,快速吸收來自不同部門的知識和信息,并將各方聯系起來,形成新的見解,進一步為政府各部委、基金會、協會和企業提供咨詢[21]。
(五)營造工業技術文化的社會環境
資助者協會深知,工業、科學要發展,離不開社會的支持,所以不遺余力地為工業和科學營造一種有利的社會環境,力爭讓整個社會來關心工業和科學界的訴求。所以,資助者協會除了資助各種科學和教育項目之外,在社會的各個層面進行社會性活動,讓社會更加關心、理解和參與科學技術事業。以下舉兩例。
第一,胡格山莊論壇。為了促進高等教育與研究、工業界、政治與社會之間的對話與連結,1956年起,資助者協會開展了“經濟與科學”的論壇活動,成為德國討論科學和教育政策問題的重要論壇,是現在胡格山莊論壇(Villa-Hügel-Gespr?che,VHG)的前身。資助者協會每兩年舉辦一次VHG,邀請來來自科學、 商業和政治屆的30 位決策者針對與未來相關的科學創新問題進行討論。1981年的VHG主題為“促進卓越科學——原因和途徑”,來自政界、商界和學術界的代表討論了高等教育部門的擴張,以及學生數量的明顯增加所帶來的挑戰。會議尤其關注大學教師的平均質量下降、合格的年輕科學家缺乏機會和激勵措施以及大學的行動范圍受到官僚主義的限制等問題,呼吁政治家和科學管理者給予大學更多的自主權,增加競爭機制,以提高大學的科研創新能力和培養優秀人才的能力,鼓勵私人贊助者將資金集中在國際頂尖研究領域上。1983年VHG 主題為“大學研究和工業創新——我們是否為未來做好準備”,論壇將注意力轉向由國家直接或間接決定的高校研究和工業合作的框架條件上,鑒于其他工業化國家帶來的挑戰,討論首先強調了高校學術研究和工業創新兩個領域之間的通暢交流,要達到科研和工業之間的通暢交流,首先二者要有一個基本共識,那就是促進技術和社會發展進步,在此基礎之上還必須擴大高校科研和工業創新之間流暢過渡的制度性框架條件。資助者協會呼吁學界加強與工業界的合作,這完全符合工業技術文化的基本價值。1988年的VHG 討論“超負荷的大學——研究的新機遇”問題,呼吁大學集中關注基礎研究和培養年輕科學家,并考慮擴大應用科學大學的規模。多年來,VHG 的許多討論對政治決策過程產生了影響,同時也為資助者協會的資助計劃指明方向,確定其優先事項的資助計劃[1]286。
另外,為了進一步發展德國創新體系,推動德國重大科技戰略與政策的形成,資助者協會從2015年開始舉辦研究峰會(Forschungsgipfel)。每年來自科學、商業、政治和民間社會的約400 名專家對德國研究和創新政策的核心議題進行討論,比如,創新(2015)、數字化(2016)、新的創新和風險文化(2017)、人工智能——推動新一代的創新(2019)等。這些重要會議論壇澄清了以商業為導向的科學和研究發展觀的核心要素,為高等教育和研究政策領域的新問題提供交流平臺和決策參考,旨在通過發展科學研究和創新為德國作為經濟發展重地創造更好的軟環境和前景[22]。
第二,種種科普項目。社會對科學的理解決定了科學發展的資金來源和國際競爭力。資助者協會認為“20世紀在很大程度上被自然科學和技術的快速發展所塑造,然而,科學和技術的成就往往不被視為文化成就”[23]。為了使科學技術的社會價值清晰化,需要使公眾了解科學,要塑造科學技術文化,于是,促進公眾與科學的對話和理解成為資助者協會的工作重心[11,23]。從20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資助者協會就開始資助發布最新科學研究信息的新聞門戶網站“科學信息服務網”(Informationsdienst Wissenschaft,idw)。1999年,在資助者協會的倡議下,主要的科學組織聯合發布了“公眾對科學和人文的理解(PUSH)”宣言。PUSH 宣言是科學傳播的一個里程碑,旨在促進科學與公眾之間的對話。2000年5月12日,資助者協會和科學組織聯合成立了科學對話公司(Wissenschaft im Dialog gGmbH,WiD),該公司專門組織公眾與科學對話活動、科學展覽或競賽,開發科學交流的新形式。例如,2000年它成為聯邦教育和研究部的合作伙伴,共同組織”科學之年“激發人們對科學的興趣。同年,它參與組織了第一屆“科學長夜”,至今仍有許多城市還在繼續組織這一活動。除此之外,資助者協會還自2000年起與DFG 共同頒發“年度傳播者獎”,表彰那些以特別生動易懂的方式向公眾進行科普的研究人員[11][24]。此外,為了通過科學推進城市發展,刺激政治、文化、商業和科學在城市發展問題上進行戰略合作,資助者協會發起 “科學之城”(Stadt der Wissenschaft)競賽,通過參加競賽和活動將科學家、政治家和公民代表等所有行動者聯系起來,建立交流平臺,共同為科學城市本地化以及科學推動城市發展交流想法,推進科學與城市的連結[25-26]。
五、結論
綜上所述,資助者協會是一個工業界根據自身的需求發起的民間促進科學的商業界聯合機構,既不是政府公共部門,也不是營利機構,是一種民間的科學教育資助機構,對于促進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推動科技創新和人才教育培養領域互動,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從工業技術文化的角度看,資助者協會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工業技術文化的行動者。其影響范圍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引領科研新方向。自19世紀末以來,德國工業企業一直愿意投資建立和擴大科學基礎設施和平臺,與政府一道進行科研學術體系的建構,支持對提高生產技術至關重要的自然科學研究或工程研究創新。其著眼點不僅是為了直接促進企業等單個經濟體的利益,同時也是著眼于宏觀的社會整體經濟,為了保證德國整個國民經濟的競爭力,以便使科學工作的水準能夠配合國家發展所需甚至高于國家期待的水平[12]597。資助科學是德國經濟界的優良傳統,特別是德國的大型工業企業非常熱衷于對科研學術進行資助。資助者協會繼承了這一傳統,把支持科學事業和技術創新看作自己的職責。但是,資助者協會對科研的支持,有其自身的特點。資助者協會特別關注科研領域的創新項目和活動,直接為其提供科研資金或者獎金,創造創新的平臺。所以,資助者協會對科研的資助,往往具有前沿性和引領方向的特點。
第二,推動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資助者協會不僅僅是德國科學技術研發創新領域的資助者,同時也是德國科學技術與人才培養的參與者和推動者,直接參與到了科學研究、技術創新和人才培養的教育實踐當中。在大學教學改革、尖子人才的選拔等方面都提出了獨特的資助項目,同時也關注教師的發展和成長,比如,在大學設立基金會教授教席。另外,也為職業教育發展提供支持。資助者協會通過這些人才培養項目,為人才培養模式和教學方法創新提供了支持,將經濟和科技發展的最新需要帶到了教育領域,為溝通兩個體系做出了顯著的貢獻。
第三,推進科教政策新方向。資助者協會不僅設立各種項目,直接資助有關的科研和人才培養活動,而且利用自己的優勢為科研和教育決策提供支持,引領新的方向。首先,資助者協會是一個重要的科技和教育政策的智囊,參與了種種相關政策的制定。正如德國國家電臺DLF 評價:“資助者協會是德國高等教育政策中最重要的游說組織之一。它總是在教育系統改革受到威脅時進行及時的干預。資助者協會不僅關心內容,而且更多的是關心科學系統的結構框架。”[27]其次,資助者協會還利用自己的優勢,從事科研事業的數據搜集和分析,為政府提供咨詢,為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據和基礎。多年來,資助者協會的科學統計公司是聯邦政府官方委托的數據收集統計機構。資助者協會作為一個民間組織,由于其經濟實力和理念的先進性,獲得學術界和政治界的高度認可。德國總統一直擔任協會的榮譽主席,德國國家領導人也經常參加資助者協會的重大活動,高度贊揚其對德國科學和教育的貢獻。在資助者協會的百年慶典上聯邦總統施泰因邁爾充分肯定了資助者協會的貢獻:“我們需要科學之光:德意志研究聯合會和德國科學資助者協會就是我們科學的強大支柱。”這印證了資助者協會在政界、科教界和民間社會的聲譽,以及對聯邦政府的強大影響力,資助者協會的聲音勢必影響諸多政策的制定和走向。
第四,營造科學創新環境。資助者協會很清楚,科技創新、人才培養不僅僅是企業、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的事情,在全社會營造一種有利于科技創新的工業技術文化,是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的關鍵所在。基于這種理念,資助者協會聯合政府機構、大小基金會以及媒體,在科研核心區域之外營造社會的工業技術文化氛圍,引導國民尊崇科學技術,提高科研人員在社會中的身份認同感和社會地位,側面促進科研人員的科創熱情,是社會公共領域推動工業技術文化的重要推手。比如“研究峰會”公開討論科學、技術的進步與創新,拉近公眾與科學的距離;從1970年開始組織全國性數學大賽并成為德國傳統經典賽事之一,吸引公眾廣泛關注、參與和推崇科學創新;金額為25 萬歐元的德國未來獎自1997年至今仍在表彰科技、工程和自然科學領域優秀人才的卓越成就,并作為節目在電視上播放,通過媒體進行宣傳,促進科學與公眾對話,加強對社會公眾的工業技術文化熏陶,這些都是工業與技術發展的有利條件。我們從德國科學資助者協會的社會公共領域的活動軌跡可以看出,這個經濟資助科學機構的背后,離不開德國各行各界精英的參與和支持。這樣的意識和傳統是工業技術文化里孵化和哺育出來的,其初衷符合了工業技術文化的要求,順應工業技術時代之需,這也是資助者協會在德國一戰二戰歷史曲折中得以再建續存發展的關鍵所在,其后來的各種行動也反過來繼續加強了工業技術文化在政界、科研教育界等社會各界的影響力。
資助者協會是一個民間的機構,但是卻擔負起了促進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與人才培養的教育任務。其角色具有特殊意義,它所資助的科學技術研究或人才培養項目,均具有引領性的創新意義。他們不做常規的事情,而是資助具有創新和探索性的研究和人才培養模式。那么,資助者協會為什么能夠永遠處于科研和人才培養的前沿,能夠引領方向? 資助者協會特別關注企業發展的需要和科學技術的最新進展,能夠及時把握技術進步和科學發展的趨勢,并采用資金支持和政策建議的方式參與到科技進步和人才培養創新的進程中。從其發展的歷程和結構也可以看出,這是一個代表廣大企業的機構,它要用這些來自企業的資金進行符合企業利益的活動,而企業對于科學和技術的創新、對于人才培養模式的創新有一種天然的追求;企業在工業生產和技術創新的前沿,也能夠最早地抓住科學和技術發展的方向。資助者協會正是代表了企業的利益,不斷地促進科學技術創新和教育發展,綜上所述資助者協會是工業技術文化的行動者之一,而且是一個具有特殊地位的行動者。
注釋:
①阿爾伯特·沃格勒(Albert V?gler)是當時德國最有影響力的工業巨頭之一。1926年成為聯合鋼鐵的董事會主席,后被帝國教育部長任命擔任威廉皇帝促進科學協會(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 zur F?rderung der Wissenschaften)會長(1941—1945)參見:Albert V?gler.[EB/OL].[2022-01-24].https://www.mpg.de/8235512/albert-voegler.
②資助者協會從一開始就與經濟界工業界緊密相連,是工商業界在科學界的代言人。其董事會成員包括例如魯爾燃氣公司(Ruhrgas AG)董事會發言人弗里茨·古默特(Fritz Gummert)、伍珀塔爾人造纖維制造廠(Wuppertaler Glanzstoff-Fabriken)總經理恩斯特·赫爾穆特·維茨 (Ernst Hellmut Vits)、GHH 公司(Gutehoffnungshütte AG)董事長赫爾曼·羅伊斯(Hermann Reusch)和AEG 公司董事會主席赫爾曼·布徹(Hermann Bücher)。參見:Stifterverband.1920—1945:Eine Gemeinschaft in der Not[EB/OL].[2022-01-15].https://stifterverband2020.de/geschichte/1920-1945.
③自成立以來,資助者協會作為工商界在科研學術領域的代言人,從業界和民間社會籌集資金。1956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Stiftungsverwaltung GmbH)建立,任務是募捐,向捐贈者提出建議,讓他們了解德國科學資助者協會在托管基礎上的管理方式。每年都會有的新的基金會加入德國科學資助者協會。這項事務從2002年開始由德國基金會中心(DSZ)正式接手。參見:Stifterverband.Jahresbericht des Stifterverbandes [EB/OL].[2022-01 -15].https://www.stifterverband.org/download/file/fid/4000.
④科學資助者協會章程第二部分第二條Zweck des Stifterverbandes ist vorrangig die F?rderung von Wissenschaft und Forschung.Daneben ist auch die F?rderung von Bildung und Erziehung Zweck des Stifterverbandes.
⑤教學質量公約(Qualit?tspakt Lehre)是BMBF 發起的關于改善大學教學質量的文件。資助者協會在其發布之前就進行了各種準備和游說推動。并且在2018年12月,資助者協會舉行了關于該教學質量公約結束后該如何進行下一步的辯論討論,教師、高等教育機構代表、學生和政治家在這場四方辯論會討論得出的結論是:教學的進一步發展必須得到長期的、有針對性的額外資源支持,并且需要成立一個獨立的組織開展此項工作,讓教學有自己的聲音。根據聯邦和州的協議,高等教育教學創新基金會于2020年底成立,該項目每年的資金總額為1.5 億歐元,到2023年由聯邦政府單獨出資,從2024年開始,各州每年出資4000 萬歐元。基金會的目的是確保大學教學能夠得到更新。參見:Qualit?tspakt Lehre [EB/OL].[2022-01-15].https://www.bmbf.de/bmbf/de/bildung/studium/qualitaetspakt-lehre/qualitaetspakt-lehre.html.
⑥具體獎項有:一是卓越教學天才獎,獎勵那些擁有教學戰略,將教學理解為實驗和創新領域的大學和應用科學大學;二是阿爾斯·雷根蒂優秀大學教學獎,獎勵使用創新的方式方法傳授知識的優秀大學教師,旨在強調大學教學對青年學者教育的特殊重要性,激勵更多人致力于教學;三是阿爾斯·雷根蒂學院獎,主要獎勵在工程科學、計算機、數學、醫學、生物、化學、物理、法學和體育學等方面培養相應學科青年后備人才做出突出貢獻的學院。在數字化教學發展方面,資助者協會也緊跟時代需求,比如,設立“數字高等教育創新獎學金”計劃,資助大學教師探索符合創新理念的數字化教學實踐,從而為全國推進大學教學數字化樹立典范。
⑦例如1987年資助者協會在不來梅提供了一個環境工程的教授職位。1985年至1989年期間,基金會教授職位的數量從25 個增加到90 個,其中50 個是由資助者協會及其管理的基金會設立的,其余的由其他基金會(如大眾汽車公司基金會)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