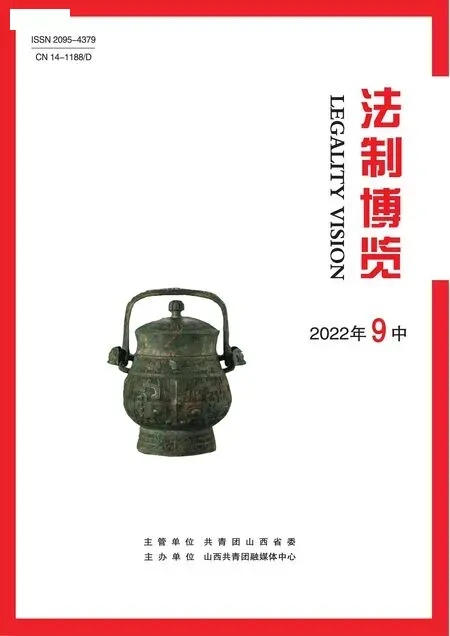網絡傳銷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的分析與解讀
張風虎 張德旭
1.山東昌平律師事務所,山東 濟南 250010;2.山東國曜琴島律師事務所,山東 濟南 250000
隨著互聯網平臺和電商平臺的不斷涌現,新型的網絡傳銷犯罪數量顯著增加,很多傳銷組織“與時俱進”,通過網絡平臺大肆發布“投資理財”“電子商務”“網上創業”等虛假廣告,對網民進行欺詐。一場又一場規模龐大的網絡傳銷犯罪案件層出不窮,涉及的人員數量和數額都讓人瞠目結舌。這種猖獗的犯罪行為不但擾亂了經濟秩序,而且詐騙了大批人民財產,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危害。我國現行法律對網絡傳銷犯罪的適用也遇到了一些難題,例如在確定下線人數時存在以他人名義自行出資的情形、組織、領導者的定義不夠明確等。對這些問題的不同認識,將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結論。
一、網絡傳銷犯罪的基本特點
(一)高度的隱蔽性
新的網絡傳銷犯罪比傳統的傳銷更加隱蔽。首先,傳銷組織一般都是以“電子商務”“虛擬貨幣”為主要業務,或者以慈善、公益為幌子,讓人很難將其與傳銷組織聯系起來。其次,與傳統傳銷人員進行面對面的溝通和“宣傳、教育”是完全不同的,網絡傳銷犯罪是利用網絡虛擬特性,利用現代化的QQ、微信、網站等聊天工具進行高頻率、高強度的“洗腦”,成本低、傳播速度快、不易察覺。傳銷組織成員都是用網絡賬號或者化名,很難核實他們的真實身份[1]。此外網絡傳銷犯罪通常采用在線支付平臺、POS機等手段來收取會費、發放返利等,而且經常會在不同的地區設立不同的結算地點,進行資金的流動。
(二)高度虛擬性
傳統的傳銷活動中,即使只是作為一種廉價的保健品、化妝品等,也會有實物或服務,以獲取會員的信任。而近年來出現的新型傳銷標的物,也逐漸從實體到“虛擬物品”,包括“虛擬貨幣”“等離子體”“納米科技產品”“網絡通信服務”等概念產品。這些商品也僅僅是為了博取眼球,企圖掩飾他們發展下線和非法賺錢的目的。網絡傳銷犯罪組織和領導者往往具有經濟學、營銷學、心理學和計算機技術等方面的知識。他們以概念產品為幌子,從經濟學中斷章取義,制造出各種具有傳奇色彩的金融神話,讓人難以分辨。同時,受過網絡傳銷犯罪的民眾也由原來的欠發達地區的文化程度偏低的民眾擴大到了各區域文化程度相對高的大學生、白領等高學歷群體。
(三)遠程管理運作
互聯網具有高效、便捷、快速傳播、低交易成本等特性,具有很強的區域性和跨越區域界限的能力。網絡傳銷犯罪的主要活動,如策劃、宣傳、資金清算等,經常發生在跨省乃至跨界。服務器的存放、網站的維護、辦公地點,都是按照不同的區域來進行的。傳銷骨干人員頻繁出沒,極大地改變了以往大規模集中培訓、大團隊運作的運作方式。而且,網絡傳銷犯罪的傳播速度遠超傳統傳銷,參與人數成倍增長。這不僅使我國在行政上存在著一定的爭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對網絡傳銷犯罪的打擊力度。通過對新的網絡傳銷犯罪的法律應用困境以及網絡傳銷犯罪的類型與特點的剖析,不難看出,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傳銷的各個要素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由于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標準不統一、存在滯后性等問題,致使我國對于網絡傳銷犯罪的規制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存在著諸多的爭議。
二、網絡傳銷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的分析
(一)網絡傳銷犯罪的層級與數量認定
在組織、領導傳銷犯罪中,以傳銷組織的內部結構、人員結構為依據,以確定其層級、數量[2]。從20世紀90年代大量出現的傳銷到現在已經發展了30多年,從傳統的“五級三等制”到“六級四晉制”“獎金累積制”“級差制”等,逐步形成了不同的層級結構,因此《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中對“30人+3層”的規定明顯太過僵化。在統計新的網絡傳銷犯罪組織的下線數量時,往往會有一個空號或者一個成員注冊了很多的成員的現象,而且,一個網上傳銷組織,其后臺所展示的成員數目,往往比真實的人數還要多出一倍。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是因為傳銷分子利用了網絡的虛擬性,通過自己偽裝的下線來擴大自己的下線數量,從而在傳銷中提升自己的地位,賺取更多的利潤。
(二)網絡傳銷犯罪計酬方式的確定
團隊計酬型傳銷是一種新型的傳銷組織,其性質與處置一直是理論界和實務界的一個熱點問題。團隊薪酬僅是基于銷售人員的銷售表現來計算和支付薪酬的一種方法。但這樣的收費模式,很容易被傳銷人員利用,成為傳銷組織的上上下下的回扣。特別是《刑法修正案(七)》將集體計酬型傳銷進行了非刑事化處理后,幾乎每一個被檢舉的傳銷組織,都會提出“其運作方式是以團隊工資為主,而不是以發展人數為基礎的傳銷”。實際上,在新的網絡傳銷犯罪組織中,組織、策劃人員在制定相關的組織體系時,往往會對其薪酬進行各種修飾和掩飾,從而使得其具有以集體為單位的形式存在的犯罪行為。團體工資,看起來就像是給傳銷組織提供了一個保護傘。這就需要在處理網絡傳銷犯罪的時候,對傳銷的收費方式有很深的了解,準確地辨認出“團隊計酬”的形式,實際上是一種以發展人數為基礎的傳銷犯罪。
(三)網絡傳銷犯罪組織和領導者的界定
傳銷屬于典型的涉眾類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僅處罰組織、領導者,而不包括其他成員。在此,組織、領導者與其他人的界限是非常關鍵的。關于原始組織、領導者的認定是沒有問題的,但爭論的焦點是那些后來加入的組織、領導者,以及在傳銷組織中的活躍程度。那么,對于傳銷組織的實施、組織的成立、發展等,又該如何判斷?根據其具體的行為,或者其在傳銷中的影響,或者發展了多少的下線,獲得了多少非法的金額,這些都不清楚。在認定組織、領導傳銷犯罪時,存在著一個爭論性的問題,即“團隊計酬”傳銷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組織、領導傳銷犯罪的客觀要件有二:一是“以銷售商品、服務等名義,以支付會費、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取會員資格,并按一定的先后次序構成組織,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組織形式,是組織、領導者獲取高額報酬的前提”;二是“以員工人數為單位”,這是傳銷的本質要求,是區別傳銷與合法直銷的主要標準。根據該條款,我國《刑法》僅將組織、領導傳銷(“拉人頭”“入門費”)的組織、領導行為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并沒有明確管理傳銷(團隊計酬型傳銷)的組織、領導行為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3]。那么是否意味著管理型的傳銷并不構成犯罪?針對這一問題,我國《刑法》理論界的一般觀點是,盡管不能按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來處罰,但仍然可以按照非法經營罪等犯罪來處理。我國的司法實踐一般都同意這種看法。2013年,最高檢、最高法、公安部印發的《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傳銷解釋》)第五條關于“團隊計酬”行為的處理問題中明確規定:一是傳銷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利用發展人員,誘導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成員,建立上下級關系,以銷售業績為基礎,計算和支付上線報酬,屬于“團隊計酬”;二是純粹以銷售商品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報酬的純粹“團隊計酬”型傳銷行為,不能視為刑事犯罪。從表面上來看,該司法解釋對“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進行了非法性的處理。實際上,在我國的刑法理論界,許多學者都同意該司法解釋反映了《禁止傳銷條例》與《刑法》關于傳銷活動的一個重大差異,即“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在《行政訴訟法》中是被明令禁止的,而在《刑法》中,進行“團隊計酬”模式的組織、領導行為卻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對《傳銷解釋》進行深入研究,就會發現,該司法解釋并沒有將“團隊計酬”作為一種傳銷行為進行非刑事化,而是僅僅將“團隊計酬”的銷售行為作為一種違法行為,因為在《傳銷解釋》中“以銷售商品、銷售業績作為報酬基礎”,而傳銷的實質就是以銷售商品、提供服務為幌子,以新加入者的錢支付先加入者的利益。如果說“以銷售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報酬”,那就不屬于傳銷,也就不能構成犯罪。所以,《傳銷解釋》僅僅是一種提示,并不意味著組織、領導“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是無罪的。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我國司法解釋的起草者混淆了“團隊計酬”型的直銷與“團隊計酬”型的傳銷,使我們錯誤地認為“團隊計酬”是一種不違法的行為。事實上,按照《傳銷解釋》第五條第二款的后半句,可以認定犯罪人是以“團隊計酬”的形式進行的組織活動,但其本質上是以發展人員的人數為單位進行工資返還的,應當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論處。這就意味著“以團體計酬”的傳銷組織和領導行為,應當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罪名論處,而不能以“組織、領導傳銷”的罪名論處。當然,這也就意味著,在“以團隊計報酬”的傳銷活動中,組織、領導行為不能被認定為“非法經營”。從實踐上講,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發生常常伴隨著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其他形式的發生。此外,組織、領導傳銷活動也可能與其他罪行相競合。《傳銷解釋》第六條第一款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同時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和集資詐騙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第二款規定: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并實施故意傷害、非法拘禁、敲詐勒索、妨害公務、聚眾擾亂國家機關、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等,構成犯罪的,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處罰。但在實踐中,《傳銷解釋》第六條第一款的適用問題卻存在著一定的爭議。在傳銷活動中,介紹別人參加傳銷活動,必然會出現捏造謊言的行為,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人,其目的并非直接非法占有參加傳銷活動的人員的財產,而是為了擴大傳銷活動的規模,從而達到非法牟利的目的。對于集資詐騙犯罪,犯罪人有直接非法占有受害人財產的意圖。在此情形下,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不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條件。換句話說,組織、領導傳銷犯罪和集資詐騙犯罪并非競爭關系,而是一種相互排斥的關系[4]。
三、網絡傳銷犯罪預防措施與對策
(一)防范網絡傳銷犯罪的措施
我國應當加速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使法院和檢察院的執法人員能夠依法處理這些問題。在社會層面,要大力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轉變人們對成功的認識誤區,防止人們因為參與網絡傳銷行為而走向更嚴重的違法犯罪,從而形成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通過加強宣傳,運用新聞媒介等手段,改變群眾的思想觀念,從而阻礙網絡傳銷犯罪的發展。民眾個人也要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不能因為一點小的好處而失去正確的判斷力,不能盲目跟風,堅決不做違法的事情,應該運用各種手段和方法了解法律知識,避免因對網絡傳銷犯罪認識不足而為網絡傳銷犯罪組織所惑。
(二)聯合各部門加大治理力度
在處理網絡傳銷犯罪的各種困境時,各方都應該竭盡全力,包括如下幾種方法:首先,應建立相關的政府機構,主動利用“大數據”將相關的信息篩選出來,然后通過蛛絲馬跡,揪出背后的傳銷組織,并將網絡上的類似廣告進行清除。其次,加強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和合作,法院、檢察院等部門應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合力,共同打擊犯罪。對于網絡傳銷發現晚、擴散快、涉及范圍廣的問題,各個部門都要充分利用各自的職責,各司其職,把問題一一解決,從而消除規制網絡傳銷犯罪的滯后現象[5]。最后,要對網絡監測技術進行深入的探索,降低取證的困難。網監部門要加大對網絡監測技術的研究力度,運用“大數據”對網絡上的傳銷活動進行有效的篩選,幫助相關單位進行對傳銷網站的取證,做好相關的證據保護。為了在不著痕跡的情況下收集到網絡傳銷犯罪人員在傳銷網站上的犯罪證據,保存犯罪的數量、規模、發展路線等電子證據,并通過IP地址確定服務器的位置,與警方取得聯系,查獲其作案工具。
四、結束語
當前網絡傳銷犯罪日趨復雜,對我國現有的刑事法律制度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相關立法機關必須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在刑法解釋已經窮盡的情況下,通過立法方式將那些具有社會危害性的網絡傳銷行為予以犯罪化。在新時代要高度重視對網絡傳銷犯罪危害性的宣傳與推廣,通過“國家反詐APP”等工具讓廣大群眾正確識別違法犯罪行為,并且自覺抵制網絡傳銷,從而確保網絡傳銷犯罪治理水平全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