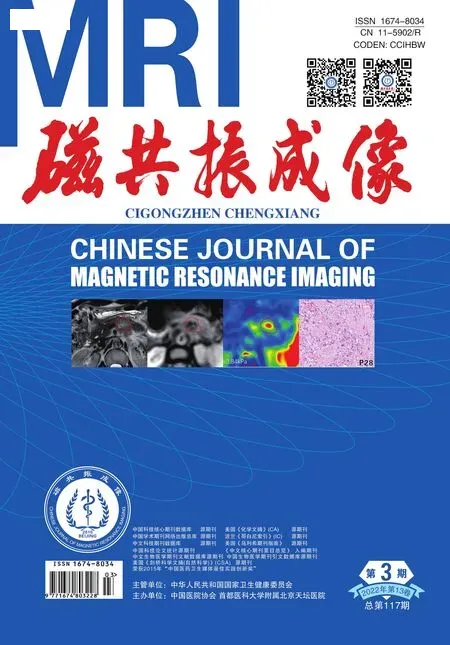蒽環類藥物所致心臟毒性的磁共振研究進展
田瑤天,王翠艷
作者單位:1.山東大學附屬省立醫院醫學影像科,濟南250021;2.山東第一醫科大學附屬省立醫院醫學影像科,濟南250021
蒽環類藥物(anthracycline, ATC)自1962 年從鏈霉菌屬中分離出來后被廣泛應用于多種實體瘤及惡性血液系統腫瘤的治療中,但突出的心臟毒性增加了人們的使用顧慮。最初的研究報道,蒽環類藥物所致心臟毒性(anthracycline-induced cardiotoxicity,AIC)的發生率為16%~23%,通過后續的不斷研究及改進,這一概率有所降低,但仍可達到6%~18%[1]。近年來隨著癌癥治療方法的不斷進步,癌癥患者的無病生存期大大延長,心血管疾病已經成為癌癥存活者遠期發病率和死亡率的第二主要因素,僅次于癌癥本身[2]。因此,早期檢測并正確評估AIC 對于臨床決策具有重要意義。心臟磁共振(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CMR)具有空間分辨率高,診斷一致性強,可重復性好等優點,CMR新技術還可以實現功能成像、應變分析、血流測速及心肌組織特性定量分析等功能,在AIC 的早期檢測、基線評估及跟蹤隨訪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將對CMR 在檢測和評估AIC 方面的技術優勢、應用及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1 AIC的損傷機制
ATC可誘導具有劑量依賴性、漸進性及累積性的細胞層面上不可逆的心功能障礙,其原因可能和ATC 導致的細胞壞死、凋亡有關[3]。AIC 在ATC 治療后幾分鐘至1 周內即可發生,主要表現為短暫的電生理異常,包括ST 段和T 波異常、Q-T 間期延長和QRS 低電壓等;也可表現為急性短暫的心肌收縮功能下降[4]。由于心肌廣泛的代償機制,只有在心功能儲備耗盡之后,這種損傷才可能轉化為臨床表現,因此臨床表現可以在數年或者數十年之后才出現[3,5]。如果AIC表現為明顯的慢性心力衰竭則預后很差,大多數患者在兩年內死亡[6];而如果在檢測到左室功能障礙的征象時立即開始心衰治療,左室功能則部分可逆[3,5]。已有大量基礎研究對AIC的損傷機制進行了探討,盡管具體機制仍不清楚,但氧化應激、脂質過氧化、細胞凋亡和自噬的失調都參與其中[7]。除此之外,AIC 的損傷機制還包括拓撲異構酶Ⅱ的參與。ATC 可以與心肌細胞表達的拓撲異構酶Ⅱβ結合,誘導心肌細胞DNA雙鏈的斷裂與凋亡[3,8]。
2 CMR常規技術在檢測AIC中的應用
常規CMR 技術,包括電影序列及延遲釓強化(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LGE),可以從形態、功能和組織特征等多個方面為檢測AIC 提供信息,最常用的指標是左心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 LVEF)。2014 年的一份專家共識中,AIC 被定義為LVEF 下降幅度>10%,并最終<53%,且在初次異常后2~3 周進行影像學復查結果依然異常[3]。CMR 評估LVEF 具有良好的組間和組內可重復性[9],因而被視作金標準[10]。應用LVEF對AIC進行評估較為便捷直觀,缺點是不能反映AIC 早期心功能的細微變化。諸多研究顯示,在應用ATC 后的早期,LVEF 往往并無明顯的變化,或雖然存在變化,但仍在正常范圍內(>53%)[11-16]。一旦檢測到LVEF 急劇下降,則心功能的改變無法逆轉,影響患者預后[5]。因此,有必要使用更靈敏的指標來及早地檢測AIC。
除了LVEF,左室質量的降低也是AIC 的表現之一。大量研究顯示接受ATC治療后,患者的左室質量降低,此時LVEF可表現為下降或無明顯變化[12,17-19]。對ATC 治療后出現LVEF 下降的患者進行研究發現,左室質量和ATC 劑量成反比,且左室質量的減少和ATC 劑量的增加都與心血管不良事件的高發生率有關[19]。另一項研究認為左室質量的降低可能與ATC 治療后心肌細胞的萎縮有關[12]。此外,部分研究顯示,在接受ATC治療后,患者會出現右心室射血分數(righ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RVEF)的降低及左心房容積的增大[17,20]。總的來說,對ATC治療后右心室和左心房結構及功能的CMR研究目前相對較少,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為我們提供更多的信息。
除了對常規形態及功能的評估外,CMR還可以評估心肌纖維化及瘢痕。LGE 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評估局灶性纖維化的技術,其位置及分布模式有助于鑒別缺血性及非缺血性心肌病。在接受ATC治療的患者中,研究報道的LGE發生率并不一致,為0%~30%。在所有接受癌癥治療(無論是ATC 還是非ATC)的患者中,LGE 存在與否、位置及分布模式都不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差異[21]。因此,目前認為LGE 與AIC 并不具有相關性,但LGE可能有助于鑒別AIC與其他心肌疾病。
3 CMR新技術在檢測AIC中的應用
盡管常規MRI檢查為AIC的檢測和評估提供了諸多信息,但對AIC 的早期改變不夠敏感,無法檢測到亞臨床AIC 的存在。近年隨著CMR 新技術的發展,包括心肌應變、mapping 技術等逐步應用于臨床后均表現出特有的優勢,為檢測亞臨床AIC的存在提供了更多的選擇。
3.1 磁共振網格標記(tigging) 技術及特征追蹤(feature-tracking,FT)技術
心肌力學研究的相關量化參數,如應變和應變率,被認為可以用來檢測早期AIC 的存在。常用的指標包括整體周向應變(global circumferential strain,GCS)、整體縱向應變(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 及 整 體 徑 向 應 變(global radial strain,GRS),其中GLS 較GCS 及GRS 更穩定,具有更好的可重復性[22]。這些參數可以通過tigging 技術及FT 技術獲得。tigging 技術被認為是非侵入性測量心肌應變及相關參數的金標準,所測得的參數準確性高,但需要特定的掃描序列,繁雜的后處理也限制了其臨床應用[23]。FT 技術則是通過算法,在常規電影序列上跟蹤和測量心肌組織的位移,獲取相關量化參數。FT 技術簡化了掃描流程,但無法很好地識別心肌內部均勻組織的運動特征,所獲取的心內膜參數有效性也遠遠高于心外膜[24]。
在接受ATC 治療的患者中,GCS、GLS 及GRS 的變化與患者AIC 的發生風險相關[25]。相較于GLS 正常的患者,GLS 受損的患者發生AIC 的風險增加4.9 倍[26]。Lunning 等[27]研究發現,在ATC 治療后早期(3 個月),患者的GCS 及GLS 即發生顯著降低,此時患者的LVEF并無顯著性變化。對ATC治療后早期AIC的研究普遍證實GLS的降低會先于LVEF,且認為GLS可以預測AIC 的未來發展[3,13,25-26,28-29]。一項系統評價表明,在ATC 治療期間或之后,GLS 會出現9%~19%的下降,其中早期GLS 降低10%~15%被認為是預測癌癥化療患者心臟毒性的最有用參數[29]。因此,在2014 年的專家共識及2016 年歐洲心臟病學會的指南中認為GLS 較治療前基線下降>15%提示了AIC 的存在[3,28]。
3.2 mapping技術
在電鏡下,AIC的組織病理學變化首先表現為心肌細胞變性和炎性細胞浸潤,隨后出現水腫和彌漫性心肌纖維化[30]。這些病理變化會引起心肌組織T1、T2 及細胞外容積(extracellular volume,ECV)的改變。mapping 序列可以基于T1、T2 及ECV 的變化對心肌組織特性的變化進行像素級別的量化及可視化,為在體檢測這些變化提供了解決方案[31]。
3.2.1 Native T1 mapping及ECV
Native T1 mapping 反映的是心肌細胞和細胞外間質水的組成或局部分子環境,可以量化組織的T1 弛豫信號。心肌組織水腫、纖維化、鐵沉積及細胞外異常物質的積聚都會導致心肌組織Native T1 的變化。這些病理變化也會導致強化后T1 的變化,但強化后T1 容易受到對比劑劑量、對比后圖像采集時間、腎功能和紅細胞壓積的干擾,因而較少應用于臨床實踐中[31]。ECV 反映了細胞外間質容積占整個心肌容積的百分比,相較于Native T1 及強化后T1,ECV 與心肌纖維化相關性最強,在沒有浸潤性心肌病及細胞外水腫的狀況下,可作為心肌纖維化的生物標記物[32]。
研究顯示,Native T1 及ECV 對AIC 的檢測往往早于LVEF的變化,并可以預測損傷的恢復情況及AIC 的遠期不良結果[11-12,18,20,33]。在接受ATC 治療時或治療后,患者的Native T1 及ECV 顯著性增高,此時LVEF 往往仍保持在正常范圍內[11,16,18,20,33]。這種升高與LVEF 及左室質量的降低相一致,獨立于癌癥本身及因年齡、性別導致的潛在心血管風險[18]。Muehlberg等[20]對30位接受ATC治療的肉瘤患者進行了研究,發現在ATC初次應用后的48 h內,Native T1的顯著升高可以預測化療結束后AIC 的發展。Ferreira 等[12]的研究則表明,ATC 治療結束后3 個月,ECV 的顯著升高與AIC 所致的心肌細胞萎縮有關。
3.2.2 T2 mapping
心肌水腫及鐵沉積導致的局部磁敏感效應會引起組織T2弛豫時間的改變,引起組織T2的變化。常規T2WI可以監測心肌水腫,但線圈引起的信號強度變化、運動偽影、快心律/心律失常時的信號丟失以及慢血流區域的不完全血液抑制會干擾圖像的最終成像質量[34]。T2 mapping序列具有很好的可重復性,可以快速、準確地量化心肌細胞內及細胞外水腫,因而被應用于多種心臟疾病的水腫檢測及評估中。
多項研究證實,在ATC治療后的早期,心肌T2會出現顯著性升高[11,14,15,35]。心肌T2 的顯著性增高在初次用藥后的48 h內即可發生[15],但在ATC 治療后一年以上的患者中,僅觀察到心 肌Native T1 及ECV 的 增 高,T2 并 無 顯 著 性 變 化[14,16,20]。Haslbauer 等[14]的研究說明了這一點,他們發現ATC 治療后的早期階段(1 個月)心肌T2 顯著性增高,但隨著時間的推移,T2 值出現穩步下降。這可能是由于在ATC 治療早期,炎性浸潤導致的心肌水腫引起心肌T2 增高,隨著治療結束水腫逐漸消退,T2 值開始下降,而由于細胞壞死、凋亡導致的間質纖維化及細胞外容積擴大,Native T1及ECV升高。
3.2.3 聯合Native T1 mapping、ECV 及T2 mapping 對AIC 進行評估
最新的關于AIC 的動物模型研究,聯合應用了Native T1 mapping、ECV 及T2 mapping 序列,將ATC 治療后心肌病理生理學變化與CMR 圖像表現結合起來[35-36]。Farhad 等[36]對45 只小鼠AIC 模型進行了研究,發現心肌T2 及ECV 的增加分別與心肌水腫及纖維化具有顯著相關性,并可以預測AIC 導致的小鼠遠期死亡率;而LVEF 則沒有這個功能。Galan-Arriola 等[35]對構建的豬AIC 模型進行每兩周一次的CMR 檢查,隨訪至16 周并與組織病理學變化相對照。他們發現,最早發生的變化是T2 的增高,隨后才是Native T1 及ECV的增高和LVEF的下降;最初T2的顯著性增高僅與細胞內水腫相關;如果在T2顯著升高時立刻停止ATC的使用,T2及心肌組織學的變化可以恢復。
總之,CMR 在監測及評估AIC 方面具有獨特的價值。部分CMR 新技術,如FT 技術及mapping 技術為監測和評估早期AIC的存在提供了新的選擇。目前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以確定mapping技術檢測AIC的閾值,并解決其在不同機器中存在標準化差異的問題。相信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可以找到臨床干預及治療AIC 的最佳靶點,從而大大降低癌癥存活者心血管不良事件的發生風險。
作者利益沖突聲明:全體作者均聲明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