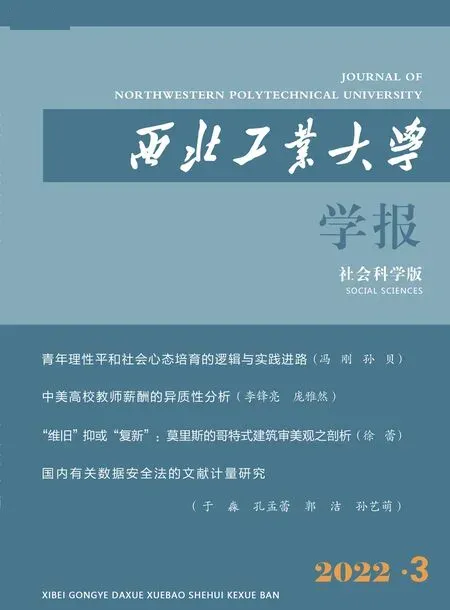風(fēng)險語境下哲學(xué)觀念的反思與重構(gòu)
張云龍 康旭博
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讓全世界的每個人都陷入不可逃避的風(fēng)險之中。德國社會學(xué)家烏爾里希·貝克所謂的“風(fēng)險社會”不再是純粹的學(xué)術(shù)概念,而成了每個人深入骨髓的切身感受。面對疫情,整個社會產(chǎn)生了諸多情緒:國家偉大動員力量激發(fā)的激動與自豪,廣大醫(yī)護人員和志愿者的犧牲與奉獻帶來的感動和憂傷,因疫情擴散和蔓延而產(chǎn)生的不安與憂慮,還有長期居家的煩躁與郁悶,如此等等,都是這一載入歷史的重大事件帶給每個人的切身感受。然而,面對如此重大的疫情,僅僅停留在情緒的層次上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再強烈的情緒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步消退。只有進行哲學(xué)反思,才能真正理解重大疫情和風(fēng)險帶給個人、社會、國家乃至全人類的影響和挑戰(zhàn);也只有理性的觀照,才能使科學(xué)家和工程師反思已有的成見與觀念,真正意識到自身所肩負(fù)的責(zé)任和義務(wù)。
一、風(fēng)險是人類遭遇的不確定性
恩格斯指出:“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xué)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1]而理論思維的發(fā)展和培養(yǎng),“除了學(xué)習(xí)以往的哲學(xué),直到現(xiàn)在還沒有別的辦法”。[2]根據(jù)恩格斯的觀點,理論思維的培養(yǎng)和提高,顯然需要學(xué)習(xí)哲學(xué)。如果說,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哲學(xué)是“科學(xué)之科學(xué)”,是無產(chǎn)階級解放自身所必須具備的思想武器,那么,在功利主義大道流行的當(dāng)代社會,效率和功用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哲學(xué)這一亞里士多德所謂的“無用之學(xué)”,已經(jīng)完全淪為“貧困”的代名詞。與傳統(tǒng)時代“知識即美德”不同,現(xiàn)代社會相信“知識就是力量”,社會進步與發(fā)展的發(fā)動機就是獲得“最好的效益”,應(yīng)該遵循以下原理——客觀、效率、標(biāo)準(zhǔn)化、計量。[3]隨著這一觀念的強化,人類社會發(fā)展到“科技壟斷”的時代,宗教、藝術(shù)、家庭、政治、歷史、真理、隱私的意義必須受到科技的重新界定,進而形成了一個基本的理念:“凡是阻礙技術(shù)革新的東西都不那么值得保存”。[4]這在今天的工科院校表現(xiàn)得非常鮮明,因為工科最大的特征就是“創(chuàng)新”、就是“行動”,就是“設(shè)計”,就是“制造”,傳統(tǒng)哲學(xué)的旁觀與思辨根本無法和充滿質(zhì)感的材料、導(dǎo)彈、航天飛機、人工智能等相提并論。面對科學(xué)技術(shù)的步步緊逼,哲學(xué)的地位和領(lǐng)地不斷降低和陷落,面對如此窘境,哲學(xué)界自我解嘲道:科學(xué)家沖鋒陷陣,哲學(xué)家打掃戰(zhàn)場。
然而,雖然哲學(xué)的任務(wù)是“打掃戰(zhàn)場”,但作為最古老的學(xué)科,它自有其意義與功能。哲學(xué)家采用的旁觀態(tài)度,實質(zhì)上就是理性的態(tài)度,理性旁觀,意味著哲學(xué)對于眼前的現(xiàn)象抱有懷疑,因為這些東西不可靠,不確定。正如古希臘哲學(xué)家赫拉克利特所指出的:一切皆流,無物常駐,人一次也不能踏進同一條河流。永遠的變動和不安定帶給人內(nèi)心深處強烈的不安全感,也就是風(fēng)險。身處風(fēng)險的人如同脆弱的蘆葦一樣隨風(fēng)飄蕩、不能自主,但正如帕斯卡所言,人是一根會思考的蘆葦,人會因為思想而強大,人通過理性的方式在紛繁復(fù)雜的現(xiàn)象背后去發(fā)現(xiàn)一種永恒不變的東西,從而最大可能地避免人類所遭遇的不確定性。人類歷史和現(xiàn)實已經(jīng)充分證明,面對充滿偶然性和意外的世界,人們少有先見之明而不乏事后諸葛,哲學(xué)通過理性把握存在的方式就是未雨綢繆,就是對一切可能威脅人類生存的風(fēng)險和不確定性最大程度地進行規(guī)避。或許,哲學(xué)永遠不可能找到終極性的答案,真理永遠處于遮蔽狀態(tài),但哲學(xué)不會放棄探索,哲學(xué)永遠在途中,永遠不會放棄追問和反思——這是哲學(xué)的精神和特質(zhì),也就是“愛智慧”。從這個意義上講,哲學(xué)的態(tài)度本身就來自于對于人類生存風(fēng)險的深切關(guān)注。當(dāng)然,對于風(fēng)險的關(guān)注和研究,哲學(xué)與其他學(xué)科在方式上是不一樣的,它不是單純從經(jīng)濟風(fēng)險、金融風(fēng)險、技術(shù)風(fēng)險、環(huán)境風(fēng)險、醫(yī)療風(fēng)險、政治風(fēng)險等具體的角度來分析,而是探討風(fēng)險本身。
故而,哲學(xué)意義上的所謂風(fēng)險,就是人類生存必然遭遇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既包括風(fēng)險的種類,也包括風(fēng)險發(fā)生的概率。風(fēng)險與危險不同,危險是確定的,當(dāng)下的,在場的,已經(jīng)被意識到的,從而可以通過種種方式加以預(yù)防與克服;風(fēng)險則是潛在的,不在場的,朝向未來的,只能通過反事實的推理提供相應(yīng)的防控機制,英國社會學(xué)家吉登斯因此指出:“風(fēng)險既與當(dāng)下的實踐相關(guān),也涉及未來發(fā)生的事情,因此,對未來的殖民造成了新的風(fēng)險環(huán)境,其中一些以制度化的形式被組織起來。”[5]從人類歷史和現(xiàn)實來看,風(fēng)險具有客觀性和偶然性,人們無法精準(zhǔn)預(yù)測何種風(fēng)險會在何時何地發(fā)生,當(dāng)風(fēng)險來臨時,也不能完全規(guī)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風(fēng)險是人類生存必定要遭遇的、無法逃避的可能性,人類生活總是處處充滿危險與風(fēng)險。根據(jù)德國哲學(xué)家海德格爾的觀點,人是所謂的“此在”,也就是人“在世之在”,人沒有辦法選擇和把握自己的出生,當(dāng)其身不由己地被拋入世界之后,就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世界中的各種事物,要與世界中的不同東西打交道。“此在”不僅要面對自然界的種種變化、危險乃至災(zāi)難,而且要面對他人帶來的情感、利益方面的煩惱、困惑以及沖突,更要獨自品嘗自我精神世界的紛擾與不安,一言以蔽之,“此在”總是面臨著無法控制的風(fēng)險和意外。因此,完全有理由說,風(fēng)險是人面臨的最大的麻煩,也是最大的課題,其偶然性和不確定性讓人老是處于操心、焦慮的狀態(tài)。
如果說操心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得以克服的話,那么,還有一種感受則是“此在”無法克服而又不得不承受的情緒:那就是“畏”。操心有明確的對象,可以克服,“畏”則恰恰相反,它沒有明確的對象,“大象無形”,個人自己根本沒有辦法克服,但又必須承受,“畏”本質(zhì)上就是對死亡無能為力的結(jié)果。的確,對于生命來說,人們會遭受許多不可確定的風(fēng)險,然而,生命中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無疑的發(fā)生而無法避免——那就是死亡。海德格爾認(rèn)為,“死作為此在的終結(jié)乃是此在最本己的、無所關(guān)聯(lián)的、確知的、而作為其本身則不確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6]“此在”注定要走向死亡。無論一個人生前怎樣神通廣大,最后都不過一個“鐵饅頭”,死亡對于每個人都是平等的。生命給人太多的虛無感,尤其對于生命力充盈的年輕人來說,似乎太過消極,令人沮喪。然而,每個人雖然必定遭遇種種難以確定的風(fēng)險,又必然走向死亡,但人類還是繁衍至今,而且以一種“向死而生”的大無畏精神,直面慘淡的人生,為了滿足生存和發(fā)展的種種需要,不斷認(rèn)識和改造著世界。這正是人之為人最為可貴的特質(zhì)。人生,就像古希臘神話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一樣,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綻放過程。
這意味著,人類是理性的存在者,是“自為”的存在而非“自在”的存在者,人不同于動物,動物只能被動地忍受周遭環(huán)境的傷害,人不會順天知命,而是積極地對自身的生存活動進行籌劃。生活給人類拋出了種種難以確定的問題,有些人或許會以逆來順受的麻木態(tài)度去回避問這些問題,而更多的人則以勇氣和決心,“選擇以更為積極的態(tài)度去抓住那些伴隨問題而來的新機遇并進而改變其自身”。[7]故而,誠如海德格爾所言,盡管死亡是“此在”無法逃避的終結(jié),但“作為領(lǐng)會的此在向著可能性籌劃它的存在。由于可能性作為展開的可能性反沖到此在之中,這種領(lǐng)會著的、向著可能性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能在。領(lǐng)會的籌劃活動本身具有使自身成形的可能性。”[8]海德格爾認(rèn)為領(lǐng)會著的“此在”具有自我造就的可能性,這恰恰表明了:生死之間,人是自由的。人不是既定的本質(zhì)的存在,人是不可定義的,人不是“什么”,人永遠有待于“去—是”“去—存在”。作為不斷生成的、展開的、自為的存在,人能夠自強不息地改變自己所面對的風(fēng)險和危機,進而化危為機。由令人不安的環(huán)境產(chǎn)生的威脅而造成的焦慮與操心,有助于人類形成適應(yīng)性的反應(yīng)機制和創(chuàng)新精神,重新安排和設(shè)計社會組織和行為模式,以讓其“產(chǎn)生個人的福祉安康”。[9]
美國哲學(xué)家杜威明確指出,人生活在危險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尋求安全、尋求可靠的確定性。尋求確定性的路徑有兩種,一種是與影響其命運和安全的各種力量和解,比如通過祈禱、獻祭、禮儀和巫祀等活動;另外一種則是通過科技認(rèn)識和改造世界的方式。[10]隨著人類理性的發(fā)展與成熟,人類意識到,通過思維人們似乎可以逃避不確定的危險,“完全確定性的尋求只能在純認(rèn)知活動中才得實現(xiàn)”。[11]理性和科技因此成了人類最可信賴的方式。面對變化多端、危險重重的世界,他們力圖通過理性尋求絕對永恒、絕對穩(wěn)定的存在。他們認(rèn)為,外部世界就像一團永恒燃燒的活火,有生有滅,無法把握。然而,運用人類的理性,就會發(fā)現(xiàn)看似無常的世界一定存在著某種永恒的規(guī)則,只要真正認(rèn)識并且把握世界運行的規(guī)則和發(fā)展演化的內(nèi)在機制,就可以使人類擺脫不確定性和風(fēng)險。通過理性認(rèn)識世界就是科學(xué)活動,經(jīng)過中世紀(jì)的短暫停滯不前之后,肇始于古希臘的“知識論”傳統(tǒng)在文藝復(fù)興的解放運動中得到了恢復(fù),并且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fā)揚,理性和科學(xué)為人類走上現(xiàn)代化之路揭開了序幕。
二、科技帶來新風(fēng)險
如上所述,人類之所以需要知識,需要科學(xué),并不單純是為了所謂的“仰望星空”,還有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為了找到某種確定的方式,以便應(yīng)對與控制自身所面臨的風(fēng)險,擺脫外在自然界的傷害和內(nèi)心的恐懼。從文藝復(fù)興開始,人的沉寂狀態(tài)逐漸被打破,人文主義者開始思考人本身,他們極力探求人性的奧秘、尊嚴(yán)和力量。人們不再仰望天國,祈求來世幸福,轉(zhuǎn)而開始享受塵世的歡愉,同時將目光投向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界,肇始于古希臘的知識論傳統(tǒng)在這一時期得到復(fù)興。自此,人類的理性光芒一掃中世紀(jì)神學(xué)的陰霾,人不再是聽命于上帝安排、需要被照管和監(jiān)護的沉默的羔羊,而是以絕對的自信確立起光輝而豐滿的主體形象。隨之而來的宗教改革全面開啟了對教會統(tǒng)治的質(zhì)疑和批判,強有力地打破了長期以來人們對權(quán)威和傳統(tǒng)的信仰。人們不再盲目輕信,徹底的懷疑精神成為新的思想潮流。新的時代精神造就了嶄新的社會景觀,現(xiàn)代科學(xué)就誕生于這一時期。從哥白尼開始,中間經(jīng)過開普勒、伽利略和牛頓,科學(xué)向教義發(fā)起了一輪又一輪猛烈的攻擊。最終,現(xiàn)代科學(xué)的形態(tài)得以確立。全新的科學(xué)范式取代了萬物有靈論和有機論的觀念,自然不再是無序的、不可理解的神秘對象,而是充滿有序性從而其每一部分行為具有可預(yù)見性的機器。從此,人的理性取代了上帝神意成為絕對的權(quán)威。自然,在現(xiàn)代科學(xué)技術(shù)的解蔽之下被對象化為人類征服和改造的僵死機器,科技這一人類本質(zhì)力量推翻了自然對人壓迫與統(tǒng)治,人翻身一躍成為操縱自然機器的主人!
進一步說,經(jīng)過文藝復(fù)興、宗教改革和科學(xué)革命的三重洗禮,人一方面擺脫了宗教神學(xué)的束縛,另一方面從自然法則的統(tǒng)治下解放出來。在這一過程中,理性成為人類擺脫危機、獲得確定性最可信賴的力量。“知識就是力量”,培根這句名言宣告了新時代的到來。在培根那里,知識開始作為巨大的工具性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對整個人類社會和自然界進行徹底改造。“技術(shù)是知識的本質(zhì),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圖景,也不是偶然的認(rèn)識,而是方法……知識并不滿足于向人們展示真理,只有‘操作’,‘去行之有效的解決問題’,才是它的‘真正目標(biāo)’”。[12]工具理性的雛形由此鑄就。從此,科學(xué)取代了上帝的地位,而成為新的主義,新的信仰。“知性為自然立法”,科學(xué)作為一種新的認(rèn)知方式成為人類征服、駕馭、和改造自然最可靠最有效的手段。培根和笛卡爾推動了近代哲學(xué)的興起,這種哲學(xué)本質(zhì)上是一種意識哲學(xué)或主體哲學(xué),主張認(rèn)識論上的二元主義,即主體—客體關(guān)系。在這種主體—客體對立模式中,世界被當(dāng)作認(rèn)識的對象,人作為認(rèn)識的主體,知識的可靠來源是人類自身的理性。在培根和笛卡爾那里,自然被視作僵死的無生命的卑微客體,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服務(wù)于人類社會的持續(xù)進步,并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質(zhì)資料。人作為絕對的力量主體站在自然的對立面,對其發(fā)號施令。人們樂觀地相信,只要充分發(fā)揮人類的理性,只要知識發(fā)展了,只要科學(xué)進步了,風(fēng)險就可以被防控,人類就會安全,就會獲得確定性,其原因在于,人類的所有行動,“在理論上都是‘可依據(jù)其風(fēng)險進行估算的’。就某些特殊結(jié)果而言,幾乎所有人類習(xí)慣和行動都可以就其可能性風(fēng)險進行整體性評估”。[13]通過科學(xué)模型的精準(zhǔn)預(yù)測和估算,人類活動的所有領(lǐng)域會讓傳統(tǒng)社會所依賴的“幸運女神靠邊站”。黑格爾因此提出了“歷史終結(jié)”的理論構(gòu)想,在他看來,人類所面臨的饑餓、疾病、災(zāi)難和戰(zhàn)爭等風(fēng)險,都在理性和科學(xué)的照耀下一掃而光,只要堅持理性精神,人類社會必將進入安全、和平、富裕的理想王國,歷史會因為統(tǒng)一于無差別的理性模式而“終結(jié)”。
的確,近現(xiàn)代以來,由于理性的昌明和科學(xué)的發(fā)展,人類樹立起這樣的信心:風(fēng)險是可以防控的,科學(xué)就是最有效的手段和方式。理性主義、科學(xué)主義以及樂觀主義因此成為這一時代的主要情調(diào),即使有盧梭、休謨這樣的不同意見者,但充其量不過是科學(xué)晴朗天空上一點小小的烏云。然而,資本主義世界的多次經(jīng)濟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zhàn)以及不斷出現(xiàn)的各種風(fēng)險和危機,都對啟蒙的理想提出了嚴(yán)重的挑戰(zhàn)和質(zhì)疑。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現(xiàn)代技術(shù)造就的工具理性進行了深刻反思,提出技術(shù)操控下的啟蒙已經(jīng)倒退為一種新的神話,不斷進行自我毀滅。馬爾庫塞揭露和抨擊了發(fā)達工業(yè)社會技術(shù)理性的極權(quán)統(tǒng)治。根據(jù)馬爾庫塞的看法,在發(fā)達工業(yè)社會,技術(shù)日益具有合理性并成為壓倒一切的統(tǒng)治力量,“發(fā)達工業(yè)社會和發(fā)展中工業(yè)社會的政府,只有當(dāng)它們能夠成功地動員、組織和利用工業(yè)文明現(xiàn)有的技術(shù)、科學(xué)和機械生產(chǎn)率時,才能維持并鞏固自己。”[14]技術(shù)的合理性最終轉(zhuǎn)變?yōu)檎蔚暮侠硇裕茖W(xué)技術(shù)不過是意識形態(tài)的另一個稱謂罷了。不可否認(rèn),近代以來科學(xué)技術(shù)和知識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但人類的生存境遇似乎并沒有因此而更加安全;相反,各種危機較之以前似乎更加的突出,危機的解決伴隨著新的危機的產(chǎn)生,作為解決危機的科技本身帶來了新的難題。德國社會學(xué)家貝克指出,人類社會以前面臨財富短缺的風(fēng)險,因此希望通過科技生產(chǎn)來解決財富的問題,科技確實在一定范圍內(nèi)解決了財富問題;但是,科技發(fā)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風(fēng)險和挑戰(zhàn),比如核泄漏、隱私問題、基因編輯、人工智能、生態(tài)危機等等,這些由技術(shù)帶來的風(fēng)險,完全不同于自然界的風(fēng)險,人類由此面臨著自己制造的巨大風(fēng)險。[15]何為人造風(fēng)險?吉登斯指出:“人造風(fēng)險是由人類的發(fā)展,特別是由科學(xué)與技術(shù)的進步所造成的。人造風(fēng)險所指的是歷史沒有為我們提供前車之鑒的新的風(fēng)險環(huán)境。我們實際上往往并不知道這些風(fēng)險是什么,就更甭說從概率表的角度來對它們加以精確計算了。”[16]或許,對于科技專家來說,這似乎是科學(xué)技術(shù)還不夠先進、不夠發(fā)達的原因,還需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發(fā)展技術(shù)。但從哲學(xué)的角度看,除了發(fā)展科技之外,還應(yīng)該審視一下科技的限度,看看是否還有其他的可能性。
毫無疑問,現(xiàn)代科技中所蘊含著的巨大生產(chǎn)力是人類打破自然必然性束縛,進而走上現(xiàn)代化事業(yè)快車道的最有力的推動和保障。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早有論斷:“資產(chǎn)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tǒng)治中所創(chuàng)造的生產(chǎn)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chuàng)造的全部生產(chǎn)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xué)在工業(yè)和農(nóng)業(yè)中的應(yīng)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shù)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jì)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chǎn)力呢?”[17]可以說,正是現(xiàn)代科學(xué)技術(shù)的興起和持續(xù)的進步促使我們與傳統(tǒng)相分離,使我們與前現(xiàn)代的那種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物質(zhì)貧乏的生活方式漸行漸遠,使我們可以有效預(yù)防和應(yīng)對自然的傷害。技術(shù)已然成為我們當(dāng)下生活的背景。毫不夸張地說,沒有科學(xué)技術(shù)的支撐,現(xiàn)代社會將難以為繼,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的自然承載力根本無法滿足60億人口的生存需要。然而,科技在為人類的現(xiàn)代化進程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為人類社會的穩(wěn)定和安全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現(xiàn)代科技所帶來的風(fēng)險和不確定性遠遠高于傳統(tǒng)社會中的自然風(fēng)險。貝克明確指出,“在此處于中心的是現(xiàn)代化的風(fēng)險和后果,這反映在動植物和人類生命所遭受的那些不可逆轉(zhuǎn)的威脅上。風(fēng)險不同于19世紀(jì)到20世紀(jì)上半葉的工廠或職業(yè)危機。風(fēng)險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團體,而是呈現(xiàn)出全球化趨勢。它不僅跨越民族國家的邊界,也模糊了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的界線。”[18]在這種意義上,危險成為超國界的存在,成為帶有一種新型社會和政治動力的全球性危機。與前現(xiàn)代社會風(fēng)險的地域性不同,科技風(fēng)險已經(jīng)成為全球性的危機,成為不同國家、不同地區(qū)不得不面對的共同問題。
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再一次將全人類拉進了巨大的風(fēng)險之中,在災(zāi)難面前,每個人都感受到了生命如風(fēng)中的蘆葦一樣脆弱,聯(lián)系歷史上的黑死病、瘧疾、鼠疫、大流感、核泄漏以及21世紀(jì)的非典、汶川地震等重大災(zāi)難,不得不承認(rèn):人們對風(fēng)險從來都不可能達至完全徹底的估算!其原因在于,“即便是在相對限定的風(fēng)險環(huán)境中,也總是會出現(xiàn)出乎人們預(yù)料和想象不到的后果”。[19]以至于哈貝馬斯面對這次全球性的危機,發(fā)出了這樣的感嘆和警告:“除了病毒之外,我們大家現(xiàn)在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一時半刻沒有任何專家能推測這場疫情的后果是什么。經(jīng)濟學(xué)和社會科學(xué)的專家都應(yīng)該要克制自己,不要魯莽地提出診斷。可以說,我們知道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我們什么也不知道,而我們卻又不得不在不確定的情況下行動與生活。這是前所未有的。”①這位經(jīng)歷過大風(fēng)大浪的活化石級別的哲學(xué)家充滿悲觀的語調(diào),讓人不免想起了兩千多年蘇格拉底的忠告:自知自己無知!科學(xué)的進步,理性的泛濫,已經(jīng)讓人類變得前所未有的自負(fù);面對如此之大的疫情風(fēng)險,是該反思了!
風(fēng)險是永恒的,科技不是萬能的,因此,必須反思以往的觀念,摒棄理性的自負(fù),告別理性主義的迷夢。今天是知識的時代,是依靠專家的時代。貝克指出,現(xiàn)代社會已經(jīng)成為傳統(tǒng)對個人的信任轉(zhuǎn)向?qū)ι鐣w系的信任,主要“表現(xiàn)在對各行各業(yè)的‘專家體系’的充分信任,因為這些專家所掌握的專業(yè)知識成為人們從他們身上獲得安全感的重要基礎(chǔ)”。[20]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專家在今天已經(jīng)成為實際上的控制者,他們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權(quán)力,專家管理、精英主義已經(jīng)成為這個時代最明顯的特征。美國的法學(xué)家德沃金曾經(jīng)提出過著名的“赫拉克勒斯法官”的設(shè)想,也就是為了維護法律的確定性和司法的合理性,只要有一位全知全能的法官就行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一方面,人類不可能完全理性行事,歷史進程總是充滿偶然性和復(fù)雜性,人總是要在多種可能性中進行抉擇,“此外,有許多實際情境中的風(fēng)險是無法得到充分評估的,還有一些實際情境中,相關(guān)專家對某些具體行動過程中的風(fēng)險則完全無法達成一致意見。”[21]因此犯錯是必然的,類似于超人的法官在現(xiàn)實中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法官乃至任何技術(shù)專家在今天,都已經(jīng)具有了非常大的權(quán)力,這使他們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自負(fù)的心理,會覺得一切盡在把握之中。然而,任何個人和群體都有自己的“洞穴”,必然存在認(rèn)識上的不足與缺失。在現(xiàn)代性的條件下,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的不斷發(fā)展,專業(yè)領(lǐng)域勢必進一步細(xì)化,而“專業(yè)化愈加細(xì)分和濃縮,人們在其中能宣稱為專家的領(lǐng)域就越來越小;在生活的其他領(lǐng)域,這位專家則將處于和他人一樣的境地。即便是專家能達成共識的領(lǐng)域,由于現(xiàn)在知識的更替性和發(fā)展性,加之外行思維和實踐之上的‘濾回效應(yīng)’(filter-back effect)也會變得十分模糊和復(fù)雜”。[22]因此,風(fēng)險是難以避免的。法國哲學(xué)家讓-呂克·南希在疫情中告誡人們:“我們在確切的意義上、在絕對意義上、在無限意義上都是極為有限而非全能的:這就是理解我們存在的唯一方式。”②
因此,無論是科學(xué)家還是工程師,完全的科學(xué)主義與專家至上難免產(chǎn)生種種風(fēng)險。世界如同一片叢林,身處其中的人根本不知道如何走出,忽然依靠技術(shù)發(fā)現(xiàn)了走出迷途的路徑,技術(shù)就成了人們最可依靠的方式。然而,澄明即遮蔽,當(dāng)技術(shù)發(fā)展到極致的時候,也意味著它已經(jīng)成為唯一的道路或者選擇,除此之外,已經(jīng)別無選擇,其他的可能性就被完全遮蔽了。這當(dāng)然是非常危險的。因此,在訴諸技術(shù)方案的同時,還應(yīng)該看看其他的可能性。美國技術(shù)哲學(xué)家芬伯格指出,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過去奉行的技術(shù)主義,就是專家路線,但這個路線今天已經(jīng)顯示出了不小的弊端和風(fēng)險。因此,他主張合理的技術(shù)代碼(technical code)應(yīng)該是技術(shù)功能和社會功能的聚合,從而既可以解決技術(shù)難題,又可以滿足社會需要。也就是說,技術(shù)不僅僅是工具,而且是文化體系,蘊含著社會價值。如果說,技術(shù)功能的設(shè)計屬于技術(shù)專家的任務(wù),那么,社會功能顯然需要征求公眾的意見。因而,技術(shù)專家認(rèn)識自己是不完全理性者,需要謙卑,需要合作,需要聽取公眾的意見,交流協(xié)商,走出自己的洞穴,尋求更合理的方案。與此同時,社會也應(yīng)該改變完全聽命于專家的做法,通過制度性的設(shè)計,建立商談的程序,讓技術(shù)的相關(guān)者都參與商談,敞開心扉地從各自的立場和角度進行探討,找到更為健康合理的路線,以便最大可能地避開風(fēng)險。
三、風(fēng)險時代專家的倫理觀念與責(zé)任
當(dāng)然,風(fēng)險不會因為人類的反思而完全消失,但如果沒有反思的精神,就會重復(fù)過往的錯誤,只會使情況越來越糟。反思是一種難以取代的力量,對于個體而言,反思是個體的價值、尊嚴(yán)和能力的充分體現(xiàn);對于群體來說,無論民族、還是國家,只有保持反思的精神,才會總結(jié)過往,開陳出新,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因此,誠如貝克所說:“沒有社會理性的科學(xué)理性是空洞的,沒有科學(xué)理性的社會理性是盲目的。”[23]當(dāng)前世界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中風(fēng)險重重,從不同方面給人類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提出了挑戰(zhàn),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給世界的發(fā)展增加了更大的變數(shù)。科學(xué)家和工程師是當(dāng)代世界發(fā)展的主要推動力量,影響甚至決定著人類社會的持續(xù)發(fā)展。能力越大,責(zé)任越大,在科技高速發(fā)展與風(fēng)險頻發(fā)的情境下,專家們該當(dāng)如何?也就是這個群體應(yīng)該如何恪守自己的職業(yè)倫理,實現(xiàn)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tǒng)一呢?
首先,以交往理性的精神,打破專家的話語霸權(quán),在與公眾的交談與協(xié)商中尋求更合理的技術(shù)工程路線。近現(xiàn)代以來,人文科學(xué)與自然科學(xué)之間形成了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出現(xiàn)了英國學(xué)者斯諾所謂的科技與人文“兩種文化”相互割裂和對立的現(xiàn)象。這種畫地為牢的做法明顯損害了各自的發(fā)展。實際上,各個學(xué)科之間之所以老死不相往來,一方面是因為專業(yè)化導(dǎo)致相互不太了解,長期形成了各個專業(yè)的封閉性“洞穴”;另一方面,則因為長期的沉浸于專業(yè)之中,專業(yè)已經(jīng)成為其生命的一部分,從而賦予其不可冒犯的地位和意義,“文人相輕”形象體現(xiàn)了這種習(xí)慣性心理。只要不同領(lǐng)域的專家拋棄成見,稍稍放下姿態(tài)了解一下相關(guān)學(xué)科,就會發(fā)現(xiàn)對方原來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樣,不同學(xué)科之間還是有不少的共同話語,因為無論是數(shù)學(xué)、物理學(xué)、化學(xué)等自然科學(xué),還是土木工程、計算機、生物工程,或者文史哲,固然存在明顯的學(xué)科差異,但由于最終都要面向人本身,因此彼此之間完全可以對話合作。各個領(lǐng)域的專家,只要能以開放包容的心態(tài)走出各自的“洞穴”,相互學(xué)習(xí),加強對話與溝通,那么,無論是社會方案,還是技術(shù)設(shè)計,或者人工產(chǎn)品,都會更加完美,都會更少風(fēng)險。
顯然,在交往理性的視角下,面對共同的問題與風(fēng)險,不同領(lǐng)域的專家必然會遇到“同一個問題,多個學(xué)科和背景”的挑戰(zhàn)。以新冠疫情為例,單獨靠醫(yī)學(xué)顯然無法有效地防控疫情,其他學(xué)科比如環(huán)境科學(xué)、人工智能、管理學(xué)、政治學(xué)、法學(xué)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故而,對于風(fēng)險的治理與防控,不僅需要科學(xué)層面的認(rèn)識、技術(shù)層面的處理,還需要社會政治層面的統(tǒng)籌、倫理層面的觀照、心理層面的疏導(dǎo)。“這就要求研究者從問題導(dǎo)向研究的系統(tǒng)需要出發(fā),在專業(yè)研究的基礎(chǔ)上,注重知識發(fā)現(xiàn)與實踐應(yīng)用的系統(tǒng)協(xié)同性,逐漸形成一種兼顧發(fā)現(xiàn)和分享的系統(tǒng)共享型的研究模式。”[24]唯有如此,不同領(lǐng)域的研究才能突破各自的局限,致力于“實踐拼合”,共創(chuàng)更為有效的技術(shù)方案。
其次,從個體理性走向公共理性,再一次深化人是“類的存在物”這一觀念,打破對立的他者思維,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世界具有開放性和相關(guān)性,“但是,人的本質(zhì)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xiàn)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25]人從來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存在物,人天生就是‘從二’之社會之人,人始終無法逃乎和命中注定地系身于一定的社會關(guān)系之中。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和他人交往,意味著我們必須面對和處理交往過程中可能出現(xiàn)的矛盾、沖突和風(fēng)險。海德格爾向我們詮釋了“共在”是此在的在世方式,共在先于“此在”的自在存在,此在的基本機制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在世界之中意味著此在必然與物、與人遭遇,此在必然與他人共在,此在的世界是共同的世界。近代以來的啟蒙思想家們秉持原子主義的立場,認(rèn)為每個個體都是自由的,也是有理性的,有理性的個人完全可以照顧好自己,都可以按照理性實現(xiàn)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每個人都好了,作為整體的國家也就好了。然而,之后難以避免的周期性經(jīng)濟危機宣告了這一理想的破產(chǎn)。因為啟蒙思想家們沒有充分考慮到個人主義可能產(chǎn)生的“囚徒困境”。按照啟蒙思想建構(gòu)下的資本主義社會由于缺乏普遍有效的公共理性的規(guī)約,個人在私欲的驅(qū)動下再次退回到了霍布斯所謂的一切人與一切人為敵的野蠻戰(zhàn)爭狀態(tài)。個體自由、理性在高唱凱歌的同時也造就了極端個人主義的出現(xiàn),資本主義條件下個人對財富的貪婪欲望造成了整個社會的混亂無序,無休止的競爭和暴力掠奪,壟斷帶來的整個社會的極端貧富分化,以及日益嚴(yán)峻的階級斗爭宣告了啟蒙理想的幻滅。而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再一次證明了個體理性的局限與錯誤,公共理性因此成為當(dāng)代哲學(xué)的基本觀念。
現(xiàn)代社會是全球化的社會,各地區(qū)交往日益密切,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人類全球化進程不斷按下快進鍵的同時也加劇了風(fēng)險的全球性蔓延,“就某些脫域機制的后果而言,全球化意味著無人能‘逃脫’由現(xiàn)代性所導(dǎo)致的轉(zhuǎn)型。例如,核戰(zhàn)爭或生態(tài)災(zāi)難所導(dǎo)致的全球性風(fēng)險便使得無人能躲避其影響。”[26]的確,面對共同的風(fēng)險和挑戰(zhàn),地球上的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世界的和平與穩(wěn)定需要各國共同努力。對此,必須進一步深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切實加強國際間的協(xié)商、溝通與合作。故而,面對人類共同的風(fēng)險,知識分子也應(yīng)堅守普遍主義的精神,用公共理性為命運共同體做出貢獻。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使命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關(guān)學(xué)大儒張載更是提出了傳頌千古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萬世開太平!古希臘著名的“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明確將“為病人謀利益”“謀幸福”作為醫(yī)生的“道德原則”和“唯一的目的”。對于專家來說,在面對風(fēng)險和生命的時候,需要采用“無知之幕”的方式,忘記其服務(wù)對象的身份、地位以及與自己的關(guān)系,恪守中性客觀的立場,用自己的專業(yè)知識解決問題。眾所周知,新冠疫情發(fā)生后,中美關(guān)系出現(xiàn)了波折,但即使如此,鐘南山院士還是多次和美國通電話,他沒有因為中美摩擦而拒絕合作抗疫,始終將病人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以實際行動詮釋著醫(yī)者仁心,這既是大愛,也是專家倫理責(zé)任的充分表現(xiàn)。故而,面臨“百年未有之變局”,專家需要有更大的胸懷,“心底無私天地寬”,只要有大胸懷,才會有大擔(dān)當(dāng),只要有大胸懷,才會有大成就;只要有大胸懷,才能擱置爭議,秉持生命至上、休戚與共的理念,攜手應(yīng)對未知的風(fēng)險挑戰(zhàn)。
最后,打破工具理性至上的觀念,回歸價值理性。工具理性的行為,歸根結(jié)底也就是“目標(biāo)取向的理性行為”,這在當(dāng)代社會所流行的“資本邏輯”中表現(xiàn)得非常明確。所謂“資本邏輯”,也就是資本活動過程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與發(fā)展規(guī)律,逐利性和增值性是其內(nèi)在本性。在資本邏輯大行其道的近現(xiàn)代社會,所有的社會關(guān)系都化約為資本或者利益關(guān)系,人也因此成為完全追求利益的“經(jīng)濟動物”。在這種情況下,一切東西都成為實現(xiàn)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人也不例外地“物化”了。其結(jié)果是,人這種具有最高價值的存在失去了其應(yīng)有的尊嚴(yán)和地位,人不再是自身行動的目的,反而成為了實現(xiàn)利益的手段,金錢、財富、資本則搖身一變成為最高的價值和衡量一切的尺度。人,這一本應(yīng)作為最高目的的存在,在工具理性和資本邏輯的轄制下淪為明碼標(biāo)價的商品。身價、顏值、腦力、才華,人的一切,都可以被精確的計算,待價而沽。可以看到,面對新冠疫情,凡是以工具理性和資本邏輯為決策基礎(chǔ)和出發(fā)點,都毫無例外地導(dǎo)致了疫情的擴大。反之,以價值理性為取向、以人民為中心的決策,則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發(fā)展和蔓延。實際上,人是最最寶貴的,而不是可以隨意丟棄的東西,只有關(guān)心人,時時刻刻意識到任何一個人都是與我們休戚與共的同類,而不是相互利用、互為手段的敵對的他者,我們的決策必然充滿人文主義的關(guān)懷,更少失誤,從而才能贏得最廣大人民的認(rèn)可與擁護。
技術(shù)專家希望腳踏實地地做出東西,但這還遠遠不夠。愛因斯坦警告說,只懂得應(yīng)用科學(xué)是不夠的,還應(yīng)關(guān)心人的本身,以保證我們科學(xué)思想的成果會造福于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失去了人文關(guān)懷的科技,如同汽車失去了剎車,隨時都有翻車的可能;剎車性能良好的汽車,則可以安全地抵達目的地。充滿人文關(guān)懷和價值理性,專家就不會陷入資本邏輯和工具理性的泥淖中,也不會為了利益而犧牲道德。現(xiàn)代社會是專業(yè)化的時代,倡導(dǎo)“知識即力量”;現(xiàn)代社會是“祛魅”的世俗社會,尊重每個人的自由和幸福。因此,科學(xué)家和工程師有用自己的專業(yè)知識為社會服務(wù)的義務(wù),同時也有獲得自己幸福生活的權(quán)利。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幸福是最高的善,人生一世,就是追求幸福。根據(jù)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幸福無非是三個方面:身體健康,靈魂寧靜、無紛擾,物質(zhì)無憂。新時代專家的物質(zhì)生活已經(jīng)不再有什么大問題,在加強身體鍛煉的同時,靈魂寧靜與否,就成為是否幸福的決定性問題。如果專家由于缺乏人文關(guān)懷而造成道德上的缺失,為了利益僭越人性,為了私欲有損公德,即使沒有法律責(zé)任,也會遭受良心的譴責(zé),輾轉(zhuǎn)難眠,痛苦不堪,幸福自然會越來越遠。如果回歸價值理性,充滿人文關(guān)懷,專家就會有照顧周全的責(zé)任感,也會在道德和利益發(fā)生沖突時第一時間做出合理的判斷和選擇。始終堅持技術(shù)的人性關(guān)照,堅守知識分子應(yīng)有的社會良知,專家才能更好地運用自己的專業(yè)知識服務(wù)于社會,實現(xiàn)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統(tǒng)一。
總之,風(fēng)險具有客觀性和偶然性,只要生活在世界之中,無論是誰,都會遭遇諸多風(fēng)險和不確定性。現(xiàn)代性的風(fēng)險癥候令生存于其中的每個人都感到不安,人們不僅要面對來自自然的威脅與傷害,也面臨著現(xiàn)代科技和風(fēng)險的全球化帶來的更大的危險和挑戰(zhàn)。風(fēng)險使得現(xiàn)代人深感無處可逃。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面對風(fēng)險,我們只能被動哀嘆。作為自為的存在,一方面我們可以運用現(xiàn)代知識體系和先進技術(shù)有效防范、化解危機,各行業(yè)專家依靠各自領(lǐng)域的專業(yè)知識,形成防控風(fēng)險的最大合力,同時進一步加強國際間的合作和協(xié)商,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共同應(yīng)對生態(tài)危機、氣候變暖、疫情蔓延等全球性風(fēng)險的挑戰(zhàn)。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對技術(shù)理性進行反思,打破資本邏輯和功利主義的轄制,回歸技術(shù)的價值維度,防止系統(tǒng)對生活世界的殖民。質(zhì)言之,唯有觀念的根本性變革,人類才能在風(fēng)險叢生的現(xiàn)代社會,走出自我的桎梏與科技的局限,攜手合作,共同創(chuàng)造更為美好的新生活!
注釋
①鄭作彧.“我們知道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我們什么也不知道:哈貝馬斯談新冠肺炎危機.社會學(xué)理論大缸”微信公眾號,2020年4月10日,原德文參見:https://www.fr.de/kultur/gesellschaft/juergen-habermas-coronavirus-krise-covid19-interview-13642491.html.
②小烏爾姆.讓-呂克·南希:惡,力量|疫病時期的哲學(xué).“烏爾姆之夜”微信公眾號,2020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