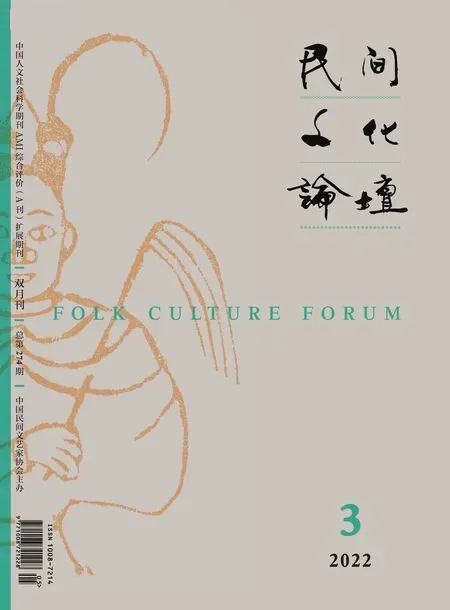亞文本、文本和語境*
[美]阿蘭·鄧迪斯 著 謝亞文 譯
民俗,作為一個學科術語,在其所有不同的文類(genre)或形式被嚴格描述之前,永遠不會被充分定義(define)。試圖用民俗學材料之外的標準來定義民俗注定要失敗。例如,我們不能根據講述者是否相信某個特定的迷信是真實或有效的來準確定義迷信。如果以這種方式定義迷信或民俗的任何其他文類,問題就會隨之產生,例如,如果講述者自己都不相信打破鏡子與壞運氣有關,又該如何解釋“打破鏡子會帶來七年的壞運氣”呢?①從信仰或成因角度定義迷信的民俗學者面臨著不可避免的陷阱,與此相關的更多討論參見Alan Dundes, “Brown County Superstitions,” Midwest Folklore, 11 (1961), pp.26-28.
用來定義民俗的最常見的外部標準大概是其傳播方式。民俗學者經常說,民俗是“口頭傳統”或處于“口頭傳統”之中。②根據多爾森(R. M. Dorson)的觀點,民俗之所以被稱為民俗,是因為其必須“至少在人們的口頭中存活了幾代。”Bloodstoppers and Bear-walkers (Cambridge, 1952), p.7. 雖然多爾森提出“傳統”一詞比“口頭”更為重要,但他基本上將民俗定義為口頭傳統文本。參見 American Folklore (Chicago, 1959), p.2, and Buying the Wind (Chicago, 1964), p.1. 及Francis Lee Utley, “Folk Literature: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J 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74 (1961), p.194.然而,許多形式的民俗根本不是口頭傳播的。一個男孩可能通過觀看其他男孩的游戲來學習打彈珠或用石頭打水漂。非口頭的民俗,如手勢、游戲和民間舞蹈,不能說真正處于口頭傳統之中。事實上,“口頭”和“書面”的二分法標準,經驗上說也是不成立的。書面形式的民俗有很多,主要是書面形式的民俗包括:手寫的留言手冊中的詩句、汽車名稱、扉頁上的手寫韻文(如簿記員所寫)、廁所涂鴉和傳統信件(如連鎖信)等。以傳播方式來定義民俗的一個更大的障礙是,文化的許多方面的傳播方式與“民俗”的傳播方式完全相同。①巴斯科姆(William Bascom)認為:“所有的民俗都是通過口頭傳播的,但并非所有通過口頭傳播的都是民俗。”參見 “Folklore and Anthropology,” JAF, 66 (1953), p.285. (問題是,“所有的民俗都是口頭傳播的”是正確的嗎?)例如,一個農民的兒子可能通過觀察他父親的駕駛或接受言語的(即口頭)的指導,或同時用這兩種方法來學習駕駛拖拉機。然而,是否有民俗學者把駕駛拖拉機這件事作為民俗的例子,這點是值得懷疑的。人們還以相同的方式學習在牙刷上涂抹牙膏和在泊車咪表上投幣。應該清楚的是,民俗的傳播方式不能限定民俗材料,因此,它對界定民俗與其他文化材料的區別幫助有限。由此,人們有理由懷疑,完全依賴“口頭”“傳統”和“傳播”等術語來定義民俗能否有效地向不知道民俗是什么的人解釋民俗。厄特利(Utley)最近試圖解決民俗的定義問題,他的結論是所謂的操作性定義,這一定義主要包括“口頭傳播”的標準。②Francis Lee Utley, “Folk Literature: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JAF, 74 (1961), pp.197, 204.在另一項最近的研究中,馬蘭達(Maranda)認為,“傳播過程是定義什么是民俗的關鍵。”③Elli-Kaija K?ng?s Maranda, “The Concept of Folklore,”Midwest Folklore, 13 (1963), p.85.然而,這兩位民俗學家都意識到,不管是在事實上還是在理論上,形式都應該是定義民俗的決定性標準。必須用內部標準而不是外部標準來定義民俗。當然,注意到民俗像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樣被傳播是沒有壞處的,但應該明白,這并不能對定義民俗、使它區別于以同樣方式傳播的文化的其他方面做出實質性的貢獻。
那么,解決民俗定義問題的關鍵就可以歸結為盡可能詳細地闡明民俗的各種形式。一旦完成了這個任務,就有可能給民俗下一個列舉式的定義。然而,到目前為止,在這一學科的輝煌歷史中,還沒有任何一種文類被充分地定義。④對定義的需求也延伸到了民俗研究中最基本的術語。“版本”(version)和“異文”(variant)之間有什么區別?根據湯普森的說法,“人們習慣把一個民俗事象的各個例子稱為異文”。但是“如果異文這個概念在說話者的腦海中并不重要,那么他更可能使用‘版本’這個詞。”湯普森指出,“除此之外,這兩個術語的使用沒有任何區別。”但是區別僅在于民俗學者的主觀心態嗎?如果研究一個諺語或民間故事的十個文本,人們就能發現版本和異文的區別。和湯普森的說法相反,文本的任何一次重述都是版本,也就是說,如果某個諺語有十個文本,那么它就有十個版本。那些或多或少偏離較典型形式的版本可以被稱為異文。因此,根據上述定義,所有的異文都是版本,但并非所有的版本都是異文。很明顯,困難首先在于“典型形式”的界定,其次是一個版本偏離到什么程度才能被稱為異文。關于湯普森的觀點,參見“variant,” in Maria Leach, ed., The Standard Dictionary of Folklore, Mythology and Legend, Vol. Ⅱ (New York, 1950), pp.1154-1155.如果現在一個初學者問他的民俗學老師什么是諺語或什么是迷信,他往往被告知去讀一本諺語或迷信的書,完成這項任務后他就會知道什么是諺語或迷信。一本關于諺語的權威著作開篇言及:“定義諺語太難了,不值得去做。”學生被告知:“判定一個句子是不是諺語,靠的是某種不可言喻的特性。”由于不可言喻,“沒有任何定義能使我們確定地把一個句子認定為諺語。”⑤Archer Taylor, The Proverb (Hatboro, 1962), p.3. 這種想法與蔡斯(Richard Chase)倡導的神秘主義相似,蔡斯認為判斷民俗是否真實,不需要成為“權威”(=專業的民俗學者),“當歌聲響起,故事被講述,曲調奏響,你可以通過感覺,通過頭皮的刺痛,通過內心深處難以言喻的感受感知到。”American Folk Tales and Songs (New York, 1956), p.19. 人們不禁要問,未來的民俗學家是否會滿足于這種民俗學研究方法?湯普森(Stith Thompson)不僅承認他無法真正回答究竟什么是母題的問題,還辯稱“它們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湯普森對定義問題的態度在他對其專長——民間故事的討論中同樣明顯。在指出“從來沒有人試圖給它下過確切的定義”之后,湯普森在為一本民俗學詞典撰寫民間故事的定義時說,這種缺乏基本定義的情況是“極大的便利……因為它避免了做出決定的必要性,也避免了關于特定故事可能屬于某種敘事文類的冗長辯論。”①Stith Thompson, Narrative Motif-Analysis as a Folklore Method, Folklore Fellows Communications No. 161 (Helsinki, 1955), p.7;“Folktale,” in Maria Leach, ed., The Standard Dictionary of Folklore, Mythology and Legend, Vol. I (New York, 1949), p.408.
在對其他文類的討論中也發現了同樣令人遺憾的情況。盡管有大量關于民謠的學術研究,但要告訴一個從未聽過民謠演唱的人究竟什么是民謠,仍然非常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有的非洲學生想知道,為什么專注于單一事件的非洲敘事歌曲不是民謠。在自然科學中,一些事物可能在有足夠精密的儀器看到它們之前就被定義了,而在民俗學中,材料可能很容易被看到和聽到,卻始終沒有被定義。為了促進對各種形式的民俗進行定義,進而最終定義民俗自身,我想提出三個層次的分析,它們中的每個層次都可以幫助完成定義的任務。②不僅在民間,民俗學界中也有習見的數字。在歐美文化中,民俗學研究和大多數學科一樣,很多標準分類方案都是三分法的。民俗學者熟悉的民間敘事的分類: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民間故事的分類:動物故事,普通民間故事和笑話/軼事;母題分類:角色、事象和單一事件,應該不會被目前的三分法影響。對于任何特定的民俗項目,我們都可以分析其亞文本、文本和語境。只根據其中一個定義某個文類是不可能的,理想的情況是一種文類應根據以上三個方面來定義。
在大多數(包括所有具有口語性質)文類中,亞文本是包含著特殊的音素和語素的話語。因此,在民俗的口頭形式中,亞文本特征就是語言特征。例如,諺語的亞文本特征包括韻律和頭韻。③關于亞文本的更多討論,參見Alan Dundes, “Trends in Content Analysis: A Review Article,”Midwest Folklore, 12 (1962), p.36. 關于特定文類亞文本特征的具體討論,參見Tomas A. Sebeok, “The texture of a Cheremis incantation.”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125 (1962), pp.523-527; Maung Than Sein and Alan Dundes, “Twenty-Three Riddles from Central Burma.” JAF, 77 (1964), pp.72-73.其他常見的亞文本特征包括:重音、音高、語氣助詞、音調和擬聲詞。在特定的民俗文類中,亞文本特征越重要,將該文類的例子翻譯成另一種語言就越困難。因此,固定短語文類(語法和內容都相當固定的文類)的亞文本實際上可能排除了翻譯的可能性。例如,繞口令往往非常依賴亞文本特征,尤其是在相關語言毫無干系的情況下,它們很少從一個語言社區擴散到另一個語言社區。另一方面,不同于繞口令,作為自由短語,民間故事可以更容易地跨越語言的界限。對于民俗的傳播理論來說,固定短語和自由短語形式之間的亞文本區別,可能與馮敘多(C. W von Sydow)對傳統的主動和被動承擔者的區分一樣重要。④C. W. v. Sydow, Selected Papers on Folklore (Copenhagen, 1948), pp.12-13.
由于民俗中的亞文本研究基本上是對語言的研究(雖然在民間舞蹈和民間藝術中也有亞文本的類似物),所以亞文本研究一直是由語言學者而不是民俗學者進行的。此外,由于語言學的許多理論和方法上的進步,在一些語言學者中出現了試圖僅根據亞文本特征定義民俗文類(folklore genre)的傾向。⑤這方面最詳盡的嘗試是斯科特(C. T. Scott)未發表的德州大學博士論文“A Linguistic Study of Persian and Arabic Riddles: A Language-Centered Approach to Genre Definition,” (1963).這種傾向就是我所說的“語言學謬誤”,即把對民俗的分析簡化為對語言的分析。這種方法最明顯的理論弱點之一是,亞文本特征很少(如果有的話),只限于某一種民俗形式。韻律可能是諺語的亞文本特征,但謎語中也有韻律,這意味著韻律在區分諺語和謎語方面的價值有限。然而,當某些亞文本特征與從文本和語境分析中獲得的特征一起使用時,很可能對界定民俗文類有很大的幫助。
一個民俗事象的文本基本上是故事的一個版本或一次講述、一句諺語的引用、一支民歌的演唱。出于分析的目的,文本可以被認為是獨立于其亞文本的。總體而言,亞文本不可翻譯,但文本卻可以被翻譯。諺語文本“咖啡不好煮,煮過滋味無”在理論上可以被翻譯成任何語言,但押韻的亞文本特征被翻譯出來的幾率幾乎為零。正如其亞文本可以進行結構分析一樣,文本也可以進行結構分析。然而,這種分析的結果將是對民俗結構的劃定,而不是基于亞文本分析對語言結構的描述。①關于民俗學結構和語言學結構之間區別的更多討論,參見Robert A. Georges and Alan Dundes, “Toward A Structural Definition of the Riddle,”JAF, 76 (1963), p.117, nn.15, 18.民俗學者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關于文本的,亞文本被留給了感興趣的語言學者,而作為第三層次分析的語境則幾乎完全被忽視了。
一個民俗的語境是該特定事象被實際運用的具體社會情境,這里有必要將語境和功能區分開來。功能本質上是建立在語境基礎上的抽象概念。通常,功能是分析者對(他認為的)某一民間文學文類的用途或目的的陳述。因此,神話的功能之一是為當前的行動提供一個神圣的先例,諺語的功能之一則是為當前的行動提供一個世俗的先例(注意,在非洲司法程序中,引用諺語類似于在我們的文化中引用案例作為法律先例)。這與某一神話或諺語被使用的實際社會情況不同。當我們說一個氏族起源的神話支持了這個氏族的自我意識時,并不是說這個神話在某個特定的場合是在何時何地由何人對誰以何種方式說出的。以謎語為例,可以看出功能的一般性討論和語境的具體詳細描述之間具有重要區別。
長期以來,民俗學者一直滿足于只發表謎語文本,人類學者則以提及謎語的功能為榮。因此,在后者的謎語集序言中,他們可能會列出謎語的各種功能,如在求愛儀式中使用等。然而,他們也很少說明語料庫中哪些謎語是用于何種功能的。②比如Thomas Rhys Williams,“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Rambunan Dusun Riddles,”JAF, 76 (1963), pp.95-110; and John Blacking,“The Social Value of Venda Riddles,”African Studies, 20 (1961), pp.1-32. 即使像這樣優秀的研究,也沒能提供這種具體的語境數據。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提供了語境,卻沒有提及單個的文本,因此他們提及的并不是真正的語境。也許有人會問,為什么在記錄文本(和亞文本)的同時記錄語境是如此重要(請注意,如果未能收集民俗的原初母語,那就意味著亞文本不復存在)。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只有提供了這樣的數據,才有可能去嘗試解釋一個特定的文本為什么會在特定的情況下被使用。讓我用一個關于謎語的假說來說明這一點。
在最近一項關于謎語的結構研究中,一種被稱為對抗性謎語的謎語被區分出來。③Robert A. Georges and Alan Dundes, “Toward A Structural Definition of the Riddle,”JAF, 76 (1963), pp.111-118.在對抗性謎語中,兩個描述性的元素似乎相互矛盾,無法在同一整體中共存,例如,“什么東西有眼卻不能看?”第一個描述性元素“有眼”和第二個描述性元素“不能看”似乎不屬于一個整體,也就是說,似乎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整體或單位。只有在正式宣布答案“土豆”時,這兩個獨立的元素才能被合乎邏輯地聯系起來。回顧謎語在求愛儀式中奇怪而廣泛的使用,人們可能會猜想,這種功能的原因可能是對抗性謎語為婚姻提供了微型結構模型,因為婚姻將兩個不相關的主體聯系起來。事實上,在異族通婚社會的文化中,新娘和新郎正如對抗性謎語中描述性元素那樣并不密切相關。那么,在這里,兩個獨立的個體或者說家庭單位結合在一起的語境(社會狀況)的結構與該語境下使用的文本的結構是一致的。不幸的是,沒有什么證據可以肯定或否定這一假設。在那些在求愛儀式中使用謎語的文化中,沒有跡象表明對抗性謎語比非對抗性謎語使用得多。“年輕人求愛時使用謎語”或“新郎只有和他的伴郎一起解決了針對他的謎語后才有權坐在新娘身邊”的說法也不能對此提供任何參考。①這些典型的說法分別來自Maung Wun, “Burmese Riddles,”Journal of the Burma Research Society, 40 (1957), p.2, and Y. M. Sokolov, Russian Folklore, trans. Catherine Ruth Smith (New York, 1950), p.283.唯一的證據是文學上的例子,例如,在民間故事中,為了考驗未來的新郎,他們被要求解開一個謎語(參見母題 H 551)。此外,還有一些民謠(蔡爾德編號1、46和47)中,解謎是結婚的條件。這些民俗材料里有使用對抗性謎語的證據。在《卡普塔娜·韋德伯恩的求愛之路》(Captaina Wedderburn’s Courtship)中,有一只沒有骨頭的雞,一顆沒有核的櫻桃等等。在民間故事中,婚姻考驗經常包括“不可能的任務”(母題H 1010)或“自相矛盾的任務”(母題H 1050)。矛盾任務的結構通常和對抗性謎語相似:來的時候既非裸體也不穿衣,既帶也不帶禮物,或既不騎行也不走路。任務的完成正如對抗性謎語的答案解決明顯矛盾的描述性元素那樣。
求愛謎語可能的心理學意義似乎支持這里提出的假設。長期以來,對“問題和答案”的關注或對夢中考試的恐懼被解釋為性無能恐懼的傳統表達。因此,強加給民間故事中的英雄的謎語是一種陽痿的威脅。在對抗性謎語中,英雄被要求把兩個不一樣的東西放在一起并使它們保持這種狀態,這兩樣東西(描述性元素)被謎語的提出者放在彼此旁邊,只有主人公給出正確的答案,它們才能正確地結合起來。這里性的象征意義是很明顯的。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點上,僅僅知道求愛儀式中是否使用了對抗性謎語是不夠的,重要的是了解到底使用了哪種類型的對抗性謎語。例如,如果采用的是矛盾的對抗性謎語,那么本假設將得到大大的加強。在這種類型的對抗性謎語中,一對描述性要素中的第二個要素在邏輯或自然屬性上構成了對第一個要素的否定。在英語謎語中,大多數缺省矛盾涉及與人體的比較。沃爾芬斯坦(Wolfenstein)在對這種類型的謎語簡短而精彩的討論中,已經提請注意閹割這一明確的主題。②See Martha Wolfenstein, Children’s Humor (Glencoe, 1954), pp.114-115.在大多數的例子中,身體的一個部分未能發揮作用:眼睛看不到,耳朵聽不到,腿不能走路,等等。如果這種類型的謎語被用于求愛儀式,那么新郎很可能會被期望消除閹割性陽痿的暗示或威脅,即通過給出正確的傳統答案消除身體機能障礙的威脅。
誠然,上述假設具有高度的推測性。然而,不管對最常見的謎語功能之一的假設性解釋是否有效,人們都很容易從中看到記錄語境的好處或必要性。僅僅知道在這樣那樣的文化中謎語被用于求偶儀式是不夠的,重要的是要知道哪些謎語被這樣使用。對抗性謎語是否比非對抗性謎語用得多?如果使用對抗性謎語,哪種類型的對抗性謎語最常見?最常見的類型是缺省矛盾型嗎?應該意識到,即使在沒有對基本亞類型進行結構性劃分的民俗文類中,單個文本的語境仍然可以很容易地被記錄下來。換句話說,即使收集者不知道一種謎語和另一種謎語之間的區別,但作為基本的田野調查方法,他仍然可以記錄語境。
收集語境的重要性在笑話研究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在不記錄語境的情況下,記錄笑話可能對歷史地理學家繪制傳播路徑、確定認知程度和假設亞類型的發展序列有價值,但對社會科學家來說意義不大。語境結構的兩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講笑話的人和聽笑話的人。語境可以影響文本(也可以影響亞文本,比如一個禁忌的詞匯在某種情況下會被使用,但在另一種情況下不會被使用),這是一個常識,但實際發表的關于這種影響的具體例子并不常見,這部分源于民俗學者對未經修飾的、甚至經常是未經注釋的文本的壓倒性偏好。以下是1961年從印第安納州南部一所小學院的男性院長那里收集到的笑話,可以說明觀眾或受眾的影響。
一家精神病院的病人被告知,如果他們能做到三件事就會被釋放。這三件事是用自己的左手拍打自己的右手腕、右手肘和右肩,邊拍邊說:“這是我的手腕,這是我的手肘”和“這是我的肩膀”。三位志愿者中的第一位走到精神醫生面前輕拍自己的手腕,說:“這是我的手腕。”然而,在測試的第二部分,他錯誤地再次敲擊他的手腕,同時說“這是我的手肘”。“很遺憾,”醫生說,“你必須留在這里。”第二個人成功地敲擊了他的手腕和手肘,但是當他說“這是我的肩膀”時,他敲擊了他的手肘而不是肩膀。第三個人拍對了所有三個目標,并正確地識別了它們。“恭喜你,”醫生說,“太好了,你馬上就可以被釋放了。但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得這么好的?”“哦,”那人敲了敲腦袋說,“我只是用了我的屁股。”
這個笑話是在一次海軍后備役會議上,一名成年男子向其他四名男子講述的。這是美國男人試圖通過講帶有性內容的笑話來向其他男人展示他們的陽剛之氣的典型情境。在回答我的問題時,這個講笑話的人說,如果他的聽眾中有女性,他就會隨機應變換個說法,即“哦,我只是用了我的頭”。在這種情況下,講述者拍打他的屁股而不是頭。我的講述人回憶說,有一次在對(男女)混合的觀眾群講這個特別的笑話時,他注意到,在講述期間,一個女性觀眾皺著眉頭,不自覺地扭動身體。很明顯,她知道這個笑點“僅限男性”,而且她對“屁股”這個即將說出的禁忌詞感到很尷尬。講述者中斷了他的笑話,向這位女士保證這個笑話不會有問題(這本身就說明了觀眾的行為,例如面部表情,可以影響故事的講述)。
這里的證據表明,了解語境可以解釋文本和亞文本的變化。另一方面,如果沒有語境信息,民俗學者就會看到笑點交替出現,卻不能確定它們這樣出現的具體原因。語境不可能總是被猜到。
講述者的身份和聽眾的身份一樣關鍵。具體來說,就像觀眾的性別可以影響文本和亞文本一樣,講故事的人的性別也是一個關鍵因素。我們可以通過比較最近收集到的兩個版本的“妻管嚴”故事來理解這一點。①這個故事是母題N13,丈夫們打賭他們能做妻子要求他們做的事。其英文版本參見E. M. Wilson,“Some Humorous English Folk-Tales, Part Two,”Folk-Lore, 49 (1948), pp.282-283. 最近,赫爾(Julia Hull)重印了最初發表于1840年紐約州北部的一家報紙上的版本。Winner in her article, “Wit and Humor A Century Ago,”New York Folklore Quarterly, 19 (1963), pp.56-61. 本文中的文本由貝蒂·安·亨德森夫人(Mrs. Betty Ann Henderson)1963年5月收集于堪薩斯州(Kansas)的勞倫斯(Lawrence)。
三個“妻管嚴”丈夫決定報復他們的妻子。因為怕老婆,他們不能真的反抗妻子,所以他們決定服從他們的妻子并完全按照她們的要求去做。
一個多月后,這三個人在一個酒吧里相聚了。第一個人說:“我們吃晚飯的時候,我不小心把一小點肉汁灑在了桌布上。我妻子說,‘來吧,把肉汁都撒到桌子上吧!’于是我就這樣做了——我把肉汁碗翻過來,把它們弄得滿桌都是。我絕對和我妻子扯平了!”
第二個人說:“我進門的時候,門被風吹了一下,關上了。我的妻子對我喊:‘去吧,把它從合頁上卸下來。’于是我就這么做了。我把那扇該死的門從合頁上扯下來了。我絕對和我妻子扯平了。”
第三個人說:“我們在床上,我想和我妻子做愛,我正在胡鬧,她說,‘切,別鬧了!’我就切了,你們沒見過那東西吧?”①1962年,我在印第安納州布盧明頓聽到的版本略有不同。第一個丈夫開車回家的時候,拐進車道時不小心軋到了一點草坪,他妻子說,“拐的好!把整個花壇都軋了吧。”第二個丈夫在躺椅上打瞌睡,他的煙不小心碰到了躺椅,把躺椅燒了一個洞。他妻子說:“燒的好!把所有的家具都燒了吧。”第三件事與本文相同,只是講述者在講笑話的同時,還做了一個把他的兩個手握在一起的手勢,好像在掩蓋笑話中弄下來的東西。請注意,這個笑話和前面的笑話都很好地驗證了美國笑話中三段式模式。
這個笑話是一個三十歲的男教師講給一個二十二歲的民間文學收集者聽的,這是一位已婚女性。講笑話的時候,講述者的妻子也在場,笑話結束后,她提出了另一種結尾:
“……我正在胡鬧,我妻子說,‘切,別鬧了!’(舉起一只手像鐘擺一樣晃了晃),你怎么把這東西再安回去?”
文本變化與語境關聯的心理學意義應該是顯而易見的。男人的版本除掉了女性的生殖器,而妻子的版本則閹割了男性掠奪者。這些替代的雙關語支持關于西方文化中男性和女性性行為精神分析的幾個假設。然而,這里的重點是,如果沒有最基本的語境信息,即報告人的性別和關系,文本的意義將大打折扣。
前面已經指出,雖然亞文本特征本身不能定義民俗文類,但它們在定義民俗形式時可能具有一定的補充價值,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語境特征。單純的語境并不總能定義一種文類,因為一個特定的社會情景可能適用于許多不同的文類中的任何一個。例如,孩子們之間在爭強斗勝時,一個孩子可能采用謎語、諷刺、笑話、接龍故事或游戲。另一方面,在有些情況下,語境信息對于區分一種文類和另一種文類至關重要。其中一種情況涉及謎語或諺語。謎語和諺語都基于主題-評論的結構,這些結構往往是隱喻性的。然而,在謎語中,所指是需要被猜測的,也就是說,提出謎語的人而不是被問者知道答案。在諺語中,說者和聽者都已經知道所指。沙科洛夫(Sokolov)認為,諺語到謎語的轉變是語調的變化。他說:“有時只通過一個語調的變化,諺語就變成了謎語:‘沒有什么傷害它,但它一直在呻吟’,在諺語中,這句話說的是偽君子和乞丐,但在謎語中,同樣的話指的是豬。”②Russian Folklore, p.285.但應該清楚的是,諺語和謎語的語境不同,不能否認它們之間有亞文本(在該情況中是音調)上的區別,但主要的區別是語境。正是不同的語境造成了語調上的差異。要么是A要求B猜出謎語的所指,即豬,要么是A通過諺語向B評論B認識的某人的行為。語境是至關重要的。請看下面的緬甸語文本。
Ma thi thu kyaw thwar:
Thi thu phaw sar:
不知道的人可能從它上面走過去。
知道它的人就會把它挖出來吃掉。
作為一個謎語,其所指(答案)是馬鈴薯(或任何生長在地下的東西);作為一個諺語,這句話適用于許多不同的某人對不容易發現其價值的東西一無所知的情況。在這些例子里,根據語境,這句話就是一句諺語。我的講述者指出,這段文字作為諺語比作為謎語的作用更大。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如果只給出文本(特別是如果不記錄語調特征),會有多大的誤導性。非緬甸人是否能從文本中猜出這可能是一句諺語,這一點很值得懷疑。
語境的收集對于所有民俗文類來說都是必要的,對于諺語和手勢來說更是不可或缺。然而,大多數的諺語集只提供文本,這就是缺乏語境的民俗收集。諺語作為民俗的固定短語文類的例子,必須用原始母語記錄,這樣亞文本也可以被保留下來。但是語境呢?語境和亞文本一樣重要,但它幾乎從未被記錄。作為收集語境必要性的最后說明,我們來看看另一個緬甸諺語。
Sait ma so: bu:
Kywè mi: to dè
這句諺語可譯為:“我沒生氣,但水牛的尾巴更短了。”在記錄了文本和亞文本之后,我們能明白這句諺語的意思嗎?我們能不能知道這句諺語何時以何種方式被誰使用呢?也許把諺語文本看作類似于水面之上肉眼可見的冰山是有用的。諺語所依據的內容可能是不可見的或在表面之下的,但有經驗的民俗學者知道如何探究其深層內涵。換句話說,諺語可以比作艾略特(T. S. Eliot)的 “客觀對應物”,因為它往往是對能喚起特定情感態度的特定情況或事件鏈的表達。①T. S. Eliot, Selected Essays, New Edition (New York, 1950), pp.124-125.因此,討論諺語而不提及諺語所喚起的東西,就像研究文學典故而不知道典故所暗指的東西一樣,是沒有結果的。如果有口頭文學,就會有口頭或本土的文學評釋(literary criticism)。民俗學者簡單地記錄最為基本的文本,并認為他們自己可以完成需要的所有分析(或文學評釋),這是錯誤的。講述者對材料的意見很少被征求,但他們的意見應該被征求。民俗學者應該詢問講述者,他們認為材料的意義是什么。本土文學評釋的收集并不妨礙民俗學者進行標準類型的分析。但除了雅各布斯(Melville Jacobs)對克拉克默斯奇努克(Clackamas Chinook)口頭文學的精彩分析外,還應該有克拉克默斯奇努克人(Clackamas Chinooks)自己的對其同樣材料的分析。
關于上述緬甸諺語,顯然,沒說的東西比說出來的東西要重要得多。事實上,純文本對另一種文化的成員來說幾乎毫無意義。首先,就亞洲和非洲文化中的許多諺語來說,諺語是故事中的最后一句。
一個農夫到田里去耕種。他從早上一直工作到中午,在饑餓中等待妻子送來午餐。幾個小時后,他不能再等了。他把拉犁的水牛的尾巴切下來,烤熟后吃了。妻子終于帶著他的午餐來了,問他是不是生她的氣了。他回答說:“我沒有生氣,但水牛的尾巴短了。”
現在,我們明白了這句諺語的含義,但是它的用途呢?這句諺語是在人們對某人輕微憤怒時使用的。換句話說即:一個人生氣了,但他做好了原諒的準備。這句諺語最常在夫妻之間使用。理想情況下,收集者本人應該觀察他所記錄的文本的語境。然而,在實踐中,通常有一個人為的語境,即信息提供者面對著收集者和/或錄音機談話。因此,專業的民俗學者有責任設法在那些他不能直接憑經驗觀察到的情況中引出語境。一個有用的技巧是要求講述者創設一個適合引用該諺語的情況。遺憾的是,總體來說,民俗學者傾向于將補充數據限制于“諺語的使用地點、時間和對象”上。換句話說,要在大多數民俗學雜志上發表,只需要提供該諺語的原始文本,并說明它是1962年7月31日在印第安納州布盧明頓從來自緬甸馬圭的芒琛桑(Maung Than Sein)那里收集的。但這能告訴我們這句諺語的含義或用途嗎?記錄講述者的姓名和地址以及收集的地點和日期并無不妥,但不應該自欺欺人地認為這樣做就記錄了語境。這種最低限度的信息數據只是開始,而不是結束。
亞文本、文本和語境都必須被記錄下來。應該注意的是,亞文本、文本和語境都可以進行結構分析。在每個層面上都可以區分非位(etic)和著位(emic)單位①關于“非位”和“著位”的概念辨析和討論,參見本專欄第二篇文章:《民間故事結構研究:從非位單位到著位單位》。——譯者。語境中存在由特定文類的非位例子來填補的著位位置。在一個特定的語境位置中,例如涉及社會抗議的語境,可以采用一些不同的文類,如笑話、諺語、手勢和民歌。另一方面,一個特定的文類,例如謎語,可以填補數個不同的語境位置。這與文本的結構分析完全一致。以民間故事結構為例,文本中的著位位置可以被不同的非位單位填補,也就是說,不同的母題(母題位變體)可被用于給定的母題位上。此外,相同的母題(非位單位)也可以被用于不同的母題位(著位單位)中。②Alan Dundes,“From Etic to Emic Units in the Structural Study of Folktales,”JAF, 75 (1962), p.102.亞文本可以用類似的方式進行分析。
這三個層次之間的相互關系還有待觀察。語境的變化顯然可以影響亞文本的變化(例如,女性敘述者或聽眾可能會導致用委婉語代替禁忌詞)。在對諺語的先行研究中,人們注意到亞文本結構是如何凸顯文本結構的(例如,一個對稱性諺語的兩個部分押韻:咖啡不好煮,煮過滋味無)。③Alan Dundes,“Trends in Content Analysis: A Review Article,”Midwest Folklore, 12 (1962), p.37.在現行研究中,有人認為謎語文本結構可能是謎語語境結構(即求愛儀式中使用的對抗性謎語)的基礎。
關于最初提出的令人困惑的問題,即民俗的定義問題,似乎民俗學者的首要任務應該是分析文本。文本比亞文本和語境的變化要小。就自由短語文類而言,亞文本特征對于定義這些文類可能沒有什么價值。在固定短語文類的情況下,亞文本特征可能相當穩定,但它們的分布很少局限于單一文類。語境標準在定義方面的價值也同樣有限。然而,各種形式的民俗的定義最好是基于所有三個層次的分析標準。因此,民俗學者把亞文本分析留給語言學者,把語境分析留給文化人類學者,可能是一個錯誤。周全的民俗學者應該嘗試分析所有三個層次。一旦所有的文類都在這些方面得到了嚴格的描述,就不再需要依賴那些取決于傳播方式等外部標準的模糊定義了。此外,現在事實上被以文本為導向的民俗學者所忽視的民和俗之間的重要關系,最終可能得到應有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