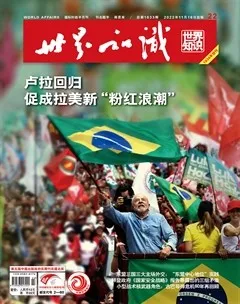預期與現實的落差:韓國年輕人的就業困境
樸光海

2021年11月高考前夕,首爾的家長們為考生祈福。
2022年10月,韓國國家統計廳統計門戶網站(KOSIS)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以今年5月為準,在15~29歲青年群體中,有35.8萬人用三年時間才找到第一份工作,這一數字比一年前(32.3萬人)增加了3.5萬人。此外,連續三年以上終日無所事事的“尼特族”(NEET,不升學、不就業、不培訓)達到了8.4萬人。如果把青年群體的年齡放寬至34歲,那么三年以上的“尼特族”數量達到12.6萬人。韓國年輕人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時間和周期為什么會這么長?為什么會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做“尼特族”?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種情況?
從韓國最近兩三年的經濟發展狀況、就業環境和整體就業形勢、年輕人看待工作的心態等層面來看,韓國年輕人就業難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經濟形勢嚴峻,就業愈加艱難。韓國國家統計廳的“經濟活動人口調查”顯示,2021年韓國青年群體(15~29歲)的就業率僅為44.2%,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38個成員中排名第29位,屬于低位國家。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產業鏈供應鏈不穩定、原材料價格上漲、韓日貿易糾紛等影響,近兩三年,韓國的整體經濟狀況不容樂觀,很多企業為節省成本和開支,都停止了新員工的招聘。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韓國只有40%的企業招聘了新員工。尤其是進入2022年以來,受烏克蘭危機升級及美聯儲持續大幅加息的影響,韓國經濟正遭受著“三高”(高物價、高利率、高匯率)帶來的嚴重沖擊。很多韓國專家預測,今明兩年韓國經濟將陷入低增長、高通脹的滯脹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下,韓國年輕人面臨的就業環境和就業形勢將更加嚴峻和艱難。
二是勞動市場提供的工作崗位及待遇滿足不了年輕人的就業心理預期。韓國勞動市場提供的工作崗位一般分為正式工與非正式工(或臨時工)兩類。二者在薪資、工作條件、福利保障、工作穩定性等方面都有較大差異。例如,非正式工的每小時薪資一般只有正式工的65%,加入社保的比例也只有正式工的一半左右。這種懸殊差異使正式工工作崗位成為一種“身份”象征。韓國國家統計廳的上述調查報告的附加資料顯示,在2021年已就業的青年群體中,非正式工的比例達到了40%以上。為了找到一份相對穩定和待遇好的工作,韓國年輕人會投入大量的金錢、時間和精力來提升自己的學識、學歷和各種能力。然而,他們在求職過程中發現,他們學到的知識和技能與企業的真正需要無法對接和匹配。特別讓他們無法接受的是,現實工作崗位回報給他們的薪資和待遇與他們之前投入的金錢、精力和時間完全不成比例。于是,有很多年輕人寧愿放棄就業或者推遲就業,也不愿意遷就“低質量”就業。尤其是一旦放下身段遷就了“低質量”就業,其經歷會影響到之后的求職。這是韓國年輕人找第一份工作時間相對較長或者成為“尼特族”的主要原因。
三是首都圈對各種資源的吸納和匯聚。韓國面積10萬多平方公里,人口約5200萬。居住在以首爾為中心的首都圈人口大概占韓國總人口的一半左右,首都經濟圈也大約占韓國經濟總量的一半。由于首都圈強大的虹吸效應,人才、資本、技術、資源等都在向首都圈匯聚,由此帶來其他城市和地區的資源逐漸減少、發展受限的結果。為了尋求一份長期穩定、薪資和待遇能夠滿足心理預期的工作,大量年輕人涌向首爾和首都圈。然而,在階層固化、財閥資本已經牢牢控制住韓國經濟命脈的情況下,出身普通、沒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年輕人,即使是大學畢業生,也很難在首爾及首都圈找到理想的工作。
四是與上一代人相比,年輕人看待工作的觀念和意識發生了改變。這些20~30歲的年輕人出生于韓國經濟中速增長期。與上一代人不同,他們從小就生活在物質條件相對較好的環境中,所以不太認同上一代人那種勤勤苦苦、任勞任怨,眼里只有工作、沒有生活、沒有自我的人生狀態。相反,他們非常重視個人的感受和幸福,向往尊重個人喜好和個性多樣化、工作與生活能夠保持一定均衡的人生狀態。另外,韓國社會愈加嚴重的階層不平等、分配不均、貧富兩極分化的結構,也讓年輕人對現實社會充滿了失望,甚至是憤懣。他們覺得自己再努力、再奮斗也不可能跨越階層,對前途失去了信心和勇氣。因此,在他們看來,工作只是謀生的必要手段,通過工作并不能實現人生價值,工作不應該成為人生的全部和重心。這種觀念和心態也延緩了年輕人就業的時間和周期。
韓國年輕人的這種慢就業、緩就業、甚至成為“尼特族”的現象,不僅對他們個人的人生規劃、結婚生子、家庭結構等產生影響,而且對更年輕者的求學就業心態、勞動力結構、經濟消費活動以及經濟發展潛力都將造成重大而深刻的影響。
第一,青年勞動力投入不足,影響后續的經濟發展潛力。韓國20~30歲年輕人的人口數量為1300多萬,占韓國總人口的26%左右。韓國國家統計廳的統計數據顯示,目前韓國共有近180萬左右的青年“尼特族”。有專家預測,如果青年“尼特族”持續增加,將造成韓國勞動力市場青年勞動力的投入不足,對后續的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此外,慢就業、緩就業以及“尼特族”的增多,還將加重父母一代的負擔并造成社會成本的提高。據估算,目前韓國每年為青年“尼特族”所支付的社會成本大約有5000億韓元(約25.5億元)。專家們建議,政府應采取更多的具有針對性和傾斜性的支持政策和措施,來推動和提升青年群體的就業能力和水平。
第二,結婚生育的年輕人越來越少,導致新生人口數量的逐年遞減。早在10年前,在韓國社會就出現了“三拋族”的說法,即指放棄戀愛、結婚以及生育的年輕人群體。后來“三拋族”演變成了“五拋族”“七拋族”甚至“N拋族”。因為難就業、工作不穩定、房價物價高企、生活成本不斷提高,很多年輕人放棄了結婚和生育。韓國的生育率也伴隨不婚不育的年輕人的增加而一路下滑。2001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育齡婦女平均生育數。國際上通常認為,總和生育率為2.1才能使上下兩代人之間人數相等;低于1.5則為“很低生育率”)跌至1.3,2018年則跌破1.0降至0.97,2021年又創新低跌至0.81,成為全球生育水平最低的國家。自2020年起,韓國的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出現了人口自然增長由正轉負的局面。2021年,韓國的出生人口僅有26.05萬人,總人口凈減少了9萬人,從此正式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人口專家預測,隨著結婚人數的持續減少,到2025年,韓國的生育率將跌至0.74的超低水平,低生育率狀態已經形成難以逆轉的趨勢。
第三,對更年輕者的求學就業心態和未來預期造成消極影響。年輕人經過自己的奮斗和努力,走出大學校門并能夠找到理想的工作崗位,將會對更年輕者產生積極正面影響,也會讓更年輕者對求學與就業充滿期待和向往,如此會形成一種良性循環。與之相反,當更年輕者看到前輩和學長們苦苦找不到稱心的工作,甚至成為“尼特族”,將對他們的心理與預期造成嚴重沖擊。他們會質疑自己未來是否也會像前輩們那樣找不到工作,以至于對未來和人生失去信心和勇氣,并過早地放棄努力與進取。這種氛圍一旦形成就不容易褪去,而且會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從20世紀80~90年代開始在日本年輕人當中逐步蔓延的“宅家”現象,就曾對日本年輕人及日本社會造成一系列問題和產生諸多不良影響。
第四,容易被政客利用和煽動,成為黨爭的工具。韓國政治的突出特點是進步陣營和保守陣營的嚴重對立。雙方為在總統選舉、國會議員選舉、地方選舉、補缺選舉等過程中獲得更多選民的支持與選票,經常會挑起地域間、階層間、性別間、代際間的對立與矛盾。近年來,由于進步—保守選民的分化和固化,20~30歲年輕人和中間派選民日漸成為雙方激烈爭奪的對象。例如,2021年大選前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選舉代表30歲男性群體的85后李俊錫為黨首,執政黨共同民主黨推選代表20歲女性群體的96后樸智賢為緊急對策委員會共同委員長。再如,在今年3月舉行的第20屆總統選舉中,代表保守陣營的總統候選人尹錫悅為獲得男性青年的支持,在競選演說中提出要廢除政府中的女性家族部,這一言論遭到了韓國年輕女性群體的強烈反對。除了挑起性別間對立,一些政客還將造成年輕人高失業率、生活成本提升、環境污染嚴重等原因歸咎于外部,并借故煽動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嚴重干擾和破壞了韓國與有關國家的正常關系。
韓國年輕人身上出現的上述現象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且,這些現象在歐洲國家、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向后工業化社會和新自由主義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也都曾出現。韓國政府要想真正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從結構性層面著手,比如改善和調整勞動市場結構、分配結構、教育結構、地區發展不均衡等,并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惟有如此,韓國年輕人才有可能逐步擺脫陷身已久的就業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