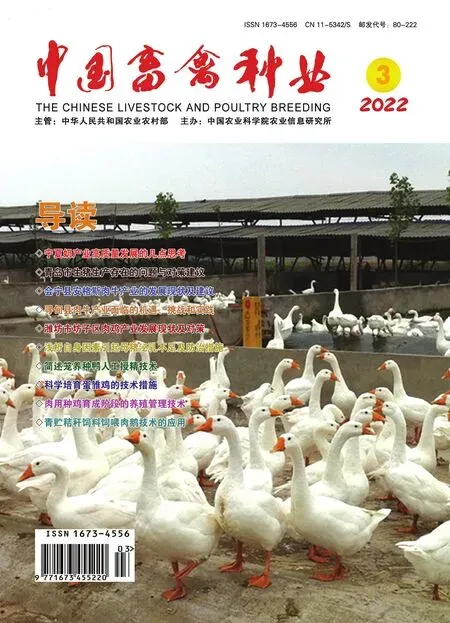論構建非洲豬瘟防控體系的重要性
李洋靜
(江蘇省常熟市畜禽屠宰檢疫和城區動物防疫中心 215500)
當前,非洲豬瘟疫苗尚未研制成功,攻克非洲豬瘟病毒仍是世界性難題,為確保養殖業均衡發展、豬肉市場良性保供、百姓飲食結構穩定,結合國內外對傳染病的防控措施,做好非洲豬瘟防控工作還需構建非洲豬瘟防控體系,建立“早監測、早處理”監管機制,用嚴格的防控措施保障畜牧養殖環境的安全,推動我國盡快凈化、消滅非洲豬瘟病毒。
1 非洲豬瘟病毒監測
據文獻報道,非洲豬瘟病毒的潛伏期為4~19d,感染動物在出現臨床癥狀的前2d 開始傳播病毒,到感染后第7~9d 血清轉陽[1]。由此可見,早期診斷檢測非洲豬瘟抗原比檢測抗體更重要。熒光定量PCR 檢測法是應用于非洲豬瘟病毒早期檢測的一種特異、靈敏、快速的檢測方法,也是日常監測中采用的檢測方法。杜楠楠等[2]建立基于非洲豬瘟病毒p17 蛋白的編碼基因D177L 的TaqMan 實時熒光定量PCR 檢測方法,具有良好的重復性,能有效檢測出陽性核酸樣品,且樣品核酸抽提及熒光定量PCR 檢測最快可在2h 內完成,可推廣用于對非洲豬瘟的快速檢測和早期診斷,有助于早發現疫情、減少經濟損失。
2 國外應對非洲豬瘟疫情的經驗和教訓
2.1 西班牙應對非洲豬瘟疫情的經驗
西班牙非洲豬瘟疫情從爆發到根除用時36 年,第一階段(1960~1984 年)收效甚微,通過加大政策實施力度、補貼強度和廣度、財政支持力度,第二階段(1985~1995 年)實現根除。從根除計劃頒布、實施到根除,西班牙采取了建設流動獸醫臨床團隊網絡體系、對所有豬場進行血清學監測、提高飼養場及飼養設施的衛生水平、主管部門足額補償生產者以剔除所有非洲豬瘟爆發點、嚴格控制豬群移動等重要措施[3],對我國及其他國家徹底消除非洲豬瘟病毒具有參考價值。
2.2 巴西應對非洲豬瘟疫情的經驗
巴西非洲豬瘟疫情爆發后,立即啟動應急預案,在資金大力支持下,僅用了7 年(1978~1984 年)就實現根除。巴西的防控理念與西班牙相似,防控措施比西班牙更加全面、細致、嚴格,如控制國際航運,禁止進口生豬;為降低動物發生相互接觸的可能性,控制國內生豬移動、停止展覽、牲畜市場交易等活動;主動進行血清學監測,對冷凍豬肉進行抽檢;強化豬瘟疫苗免疫;加強動物健康教育與人員培訓,禁止使用餐廚廢棄物飼喂;對豬場的動物衛生援助給予獎勵,通報確診的所有豬病。此外,疫情被撲滅后,要求疫點消毒后4 個月引入并飼喂2 個月哨兵豬,符合要求后才能補欄,而實踐證明,這樣做是出于生物安全考慮但非必要[4]。
2.3 俄羅斯應對非洲豬瘟疫情的教訓
2007 年俄羅斯發生非洲豬瘟疫情后一發不可收拾。官方規定,一旦在某村發現感染非洲豬瘟病毒的生豬,全村所有生豬都要被撲殺,而政府不給予財政補貼,養殖戶自行承擔經濟損失。因處置規定嚴苛、經濟損失慘重,養殖場戶瞞報疫情并私自處理生豬的情況時常發生。同時,俄羅斯還存在豬肉制品(特別是疫區豬肉制品)非法調運、使用未加處理的餐廚廢棄物飼喂生豬、大量非洲豬瘟病死豬未經無害化處理直接私自掩埋或丟棄、大部分養殖場生物安全防護水平低恰好為非洲豬瘟病毒傳播提供便利等風險,從而導致病毒持久存在并擴散,疫情快速蔓延[5]。
3 國內應對非洲豬瘟疫情的做法和難點
3.1 應對非洲豬瘟疫情的做法
2018 年8 月,我國發生非洲豬瘟疫情后,全國上下高度警惕,出臺相關政策意見,嚴格落實有關防控要求,主要從加強動物防疫體系建設、嚴格動物防疫責任落實、加強養殖場(戶)防疫監管、規范生豬產地檢疫管理、嚴控生豬及生豬產品調運管理、加強生豬屠宰監管、加強生豬產品加工經營環節監管、加強餐廚廢棄物管理、加強區域化和進出境管理等方面嚴抓疫情防控工作,力求提升對非洲豬瘟病毒的防控能力[6]。
3.2 應對非洲豬瘟疫情的難點
3.2.1 養殖環節
因目前尚無有效疫苗可預防非洲豬瘟病毒,所以作為防控動物疫病的關鍵防線——生物安全防控系統至關重要。雖然我國養豬業因經濟、生態、文明等驅動力持續向規模化、專業化、集約化的現代養殖轉型,但還有很多中小養殖企業包括散養戶仍然存在生物安全意識淡薄、養殖隔離措施和消毒設施缺乏、生豬調運和屠宰環節及其他情況下人員活動需消毒的意識不夠等生產隱患,這些都是抵御疫病侵襲的重要方面。
3.2.2 運輸環節
由于經濟發展、產業布局、生態建設的需要,我國形成了南豬北養、西豬東調的生豬養殖產業格局,生豬頻繁調運增加了疫情傳播風險。結合生豬運輸監管現狀,有些地方仍然存在生豬運輸車輛備案管理制度不夠健全、生豬運輸車輛建設標準不統一、生豬非法販運監管不嚴、基層動物防疫機構隊伍弱化等問題,對防范非洲豬瘟等疫病非常不利。
3.2.3 處置環節
疫情發生初期,很多養殖場在發生豬群大面積死亡后,為減少經濟損失急于拋售活豬,導致疫情隨著生豬運輸車輛跨區域擴散,引起更大區域的疫病傳染,造成生豬養殖業巨大經濟損失[7]。這從側面反映出有些地方存在政策落實不到位、監管不嚴、補償標準不高導致非法販運屢禁不止的情況,如玉林市博白縣某鄉鎮養殖戶上報疫情時稱存欄生豬1 頭、發病1 頭,但據記者調查了解,該養殖場原存欄生豬超200 頭。
4 展望
隨著我國“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養殖業已從粗放式養殖向集約化、科學化、生態化、可持續化養殖徹底轉變,從最初非洲豬瘟疫情爆發采取撲殺措施到《動物防疫法》第二次修訂并調整動物防疫方針,充分闡釋了我國在動物疫病防控中積累的有效經驗和合理做法,同時也表明了我國著力推動重點動物疫病從有效控制向逐步凈化、消滅轉變的決心。
孫永健[5]從深化畜禽養殖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給出了詳細的政策建議,提出通過政策制定推動畜禽養殖業轉型升級、通過合理引導促進畜禽養殖業提質增效、通過細化管理保障畜禽養殖業健康發展入手,設置畜禽養殖業準入門檻,制定更為嚴格的環保政策,加強基層防疫機構隊伍建設;增加豬肉替代品供應,加大發展規模化養殖力度,引導市場借此契機發展行業新設備、新模式,充分發揮部門聯動作用,探索重大疫情補償專項基金運作機制;縮小疫區及無疫區劃定范圍,不斷加大防控政令貫徹宣傳力度,實行透明、高效、有力的監管舉措。本文根據已發表的文獻資料,系統闡述了非洲豬瘟病毒監測、國外防控經驗和教訓、我國防控難點等內容,希望對我國構建非洲豬瘟防控體系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