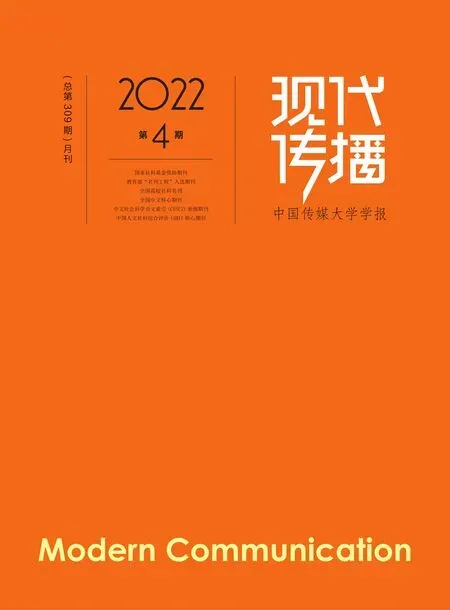傳播史分期法的技術否思與功能導向
趙雪波
迄今為止的傳播史分期法不約而同地采用了一種技術路徑,即把媒介及其技術在歷史上的幾次重大迭代變革作為傳播史或媒介史的分水嶺,用這種技術思維覆蓋傳播史分期的知識判斷,進而宰制人們對傳播史分期的認識。但是一個很明顯的哲學疑問是,我們關于傳播史分期的認識只能徘徊在技術的路徑上嗎?通往傳播史分期的知識殿堂還有沒有別的路徑可以選擇?此外,什么是新媒介?什么是舊媒介?歷史上的每一種“新媒介”出現后,與之相對應的舊媒介并沒有被取而代之,它們或者繼續獨立并旗幟鮮明地存在,或者與“新媒介”共同形成一種融媒介。麥克盧漢已經在他的年代意識到了媒介與媒介之間的銜接性和繼承性:“任何媒介的‘內容’都是另一種媒介。文字的內容是言語,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內容,印刷又是電報的內容一樣。”①那么“新媒介”還能被看作為一種準確的、劃時代的代表嗎?或者說文字、印刷、電子技術和互聯網等各自還能被看作是一個時代的特征嗎?放眼當今時代,媒介及其技術正在日新月異地裂變、迭代,媒介的邊界正在變得越來越模糊,在若干年后,我們又該如何來準確地描述今天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傳播時代?總之,我們能不能換一種思維重新思考傳播史分期問題?能不能設計一種有別于技術路徑的新的傳播史分期路徑或傳播史分期法?為此,我們需要先回顧現有的分期法的基本理路。
一、媒介環境學是傳播史分期技術路徑的底層思維
20世紀40、50年代傳播學創立以后有關傳播史的研究也就正式逐漸展開了。然而最先開展這項工作的并不是施拉姆,也不是他所屬的學派的其他學者,而是其它學科的學者。比較早的是加拿大經濟學者哈羅德·伊尼斯(Harold Innis)。伊尼斯的專業是經濟史,但是“正是在攻克了皮貨、鱈魚等課題后(伊尼斯先后出版了《加拿大皮貨貿易:加拿大經濟史導引》和《鱈魚業:國際經濟史》),試圖轉向加拿大經濟中的另一件重要的大宗商品,即木質紙漿的研究時,他突然打開了思路,一舉轉入傳播史研究”②。這是一種猜測,但是應該是合乎邏輯的猜測。伊尼斯給傳播學界留下了永恒的經典之作《帝國與傳播》和《傳播的偏向》。他在這兩部著作中首次系統地回顧了從蘇美爾、古埃及以降直到19世紀的美國,媒介是如何作用于社會和文化的問題。他按照傳播媒介將世界史分為以下幾個時期:“從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開始到泥版、硬筆和楔形文字時期;從埃及的莎草紙、軟筆、象形文字和僧侶階級到希臘—羅馬時期;從葦管筆和字母表到帝國在西方退卻的時期;從羊皮紙和羽毛筆到10世紀或中世紀時期,在這個時期,羽毛筆和紙的使用相互交疊,隨著印刷術的發明,紙的應用更為重要;印刷術發明之前中國使用紙、毛筆和歐洲使用紙、羽毛筆的時期;從手工方法使用紙和印刷術到19世紀初這個時期,也就是宗教改革到法國啟蒙運動的時期;從19世紀初的機制紙和動力印刷機到19世紀后半葉木漿造紙的時期;電影發展的賽璐珞時期;最后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到現在的電臺廣播時期。”③伊尼斯并不是直接對傳播媒介史進行分期,而是用“傳播媒介”的視野對世界史進行分期,從這個角度說,他所做的工作的性質和過往歷史學家所做的工作的性質是一樣的,只不過換了一個視角而已,或者說給世界史找到了一個新的背景和環境。然而正是因為他的這一新視角,傳播學史上一種獨領風騷的學派——媒介環境學開啟了。因為他是以各個時期的傳播技術——媒介作為分期標準的,這注定傳播史分期法從一開始就要沿著技術路徑走下去。
在傳播史分期(或媒介史分期)一事上,麥克盧漢并沒有在他的著述中專門為傳播史進行分期,他的同事羅伯特·洛根(Robert K.Logan)為他和伊尼斯做了一個總結。洛根認為伊尼斯和麥克盧漢把傳播史分為三個時代:口語傳播時代、書面傳播時代和電力傳播時代。大約對應的時間是5萬到20萬年前獲得言語能力至5000年前文字濫觴、5000年前至1844年電能發現、1844年至他們所處的時代。④洛根在此基礎上又補充了兩個時代:前言語時代即模擬式傳播時代和互動式數字時代。這樣他把“智人”的傳播分為界限分明的5個時代:
(1)非言語的模擬式傳播時代(遠古智人的特征);
(2)口語傳播時代;
(3)書面傳播時代;
(4)大眾電力傳播時代;
(5)互動式數字媒介或“新媒介”時代。⑤
這種分期的技術特征是非常明顯的,第(4)、第(5)完全體現為兩種媒介技術,第(3)的背后其實也是印刷技術。就算是書面文字和口語,在麥克盧漢筆下也都屬于技術。麥克盧漢借用了法國哲學家亨利·伯格森的觀點:“語言被認為是人的技術。”⑥他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強調口語和文字的技術性質:“拼音字母是一種獨特的技術……只有拼音字母表才是創造‘文明人’的技術手段。”⑦事實上,媒介環境學派是把媒介和技術直接劃等號的。因為從麥克盧漢開始這一學派就把媒介泛化了,或者說他們把一切技術和發明都媒介化為人的器官的延伸。衣服是皮膚的延伸,城市是人身體的延伸,輪子是腿和手的延伸,口語是口和耳的延伸,文字是眼睛的延伸,電力是中樞神經的延伸,諸如此類,它們既是媒介的代表,也是技術的體現。
伊尼斯、麥克盧漢這一派明顯受到了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啟發和影響。在芒福德的《技術與文明》中有很多我們似曾相識的概念,“感知的平衡”⑧、“書面語言擺脫了時間和空間的局限”⑨、“回到最初的人與人之間的瞬時反應”、“人所使用的工具和器皿總體說來都是他自身機能的延伸”等。這不就是媒介環境學者們所謂的“感官平衡”“時空偏向”“人性化趨勢”“媒介是人的延伸”的同義詞和同義語嗎?芒福德當然也回顧了技術的歷史,并且也提出了技術史分期理論。他把技術史分為三個時期,分別是“始生代技術時期”“古生代技術時期”和“新生代技術時期”。但是他對技術的理解是狹義性質的,他認為技術開啟于公元10世紀左右,在此之前的人類沒有技術。然而當他把能源和材料作為考察標準,并且把“水能—木材體系”和“始生代技術時期”對應起來以后,我們很容易產生困惑。水能等利用顯然不是10世紀的現象,木材的使用則更早,否則人類如何進入農業文明?農業文明強調的是人類對作物栽培技術的掌握,但是用什么工具呢?當然不是石頭,也不是金屬。利用石頭的時代被人類學家稱作“石器時代”,而那個時代因為打磨石器的技術高低不同還被分為“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新時代得到了陶器的加持)。對金屬的利用肯定是農業文明的一大特征,但絕對不是最早的特征。也許是意識到自己判斷的狹隘,芒福德在幾十年后的另一部著作《機器神話》中從頭回顧了人類早期的技術前身的歷史,他仍然堅持石器等工具不是技術的立場,但是他強調了語言、非理性等人文精神在人類進化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這也許是對媒介環境學派的又一大啟示。不管怎么樣,芒福德的觀點影響了麥克盧漢等人,但他的技術歷史分期對媒介史或傳播史的分期來說,不具有學派上的開創意義,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施拉姆在他的學術生涯的最后階段終于開始觀照傳播學歷史,他的《人類傳播史》第9章明確地把人類傳播史分為了口語時代、文字時代、印刷時代和大眾媒介時代:“人類已歷經了口語、文字和最近的印刷時代。到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時,印刷時代更加入了電子和攝影等新成員,以及一種吾人稱之為大眾媒介的嶄新傳播組織。幾個世紀后的歷史學家或許不會以印刷時代來稱呼我們,而是以這個時代為大眾媒介的時代。”很顯然,施拉姆也是以媒介技術為路徑對傳播史進行了分期。這種分期顯然受到了麥克盧漢等人的影響,正如有人所言,“施拉姆提出的‘人類傳播的發展歷程’的四個對大眾媒介的出現特別重要的時刻,都建立在文字、印刷、電子等某種技術方面的創造發明上的觀點,也沿襲了麥克盧漢人類傳播歷史四階段技術角度的歷史分期邏輯”。
媒介環境學傳播史分期的技術路徑給傳播史分期確定下了一種基調,后來的研究傳播史分期的許多人基本都沿襲了這一路徑。比如美國學者約書亞·梅羅維茨將媒介歷史劃分為口頭文化、手抄文化、印刷文化和電子文化四個階段。羅杰·菲德勒(Roger Fidler)在其著作《媒介形態變化:認識新媒介》中認為人類的媒介形態發生了三次大變化,口頭語言是第一次媒介形態大變化,書面語言是第二次媒介形態大變化,數字語言是第三次媒介形態大變化。加拿大人戴維·克勞利和其他人合著的《傳播的歷史:技術、文化和社會》以“早期文明”“印刷革命”“電流”“影像技術”“無線電時代”“電視時代”和“信息時代”為線索探討了各個時期媒介技術和社會的關系。法國人讓-諾埃爾·讓納內的《西方媒介史》對18世紀前的歷史一帶而過,這使18世紀開始的媒介史散落在各種重大事件和媒介機構之中。即使這樣,各章節也仍然隨處可見各種媒介技術的身影,如“無線電廣播的產生”“1945年以來的書面出版物”“電視的政治解放”“互聯網的闖入”等等。馬歇爾·波(Marshall T.Poe)的《傳播史:從口語到互聯網進化的媒介與社會》是晚近較為全面回顧媒介歷史的著作,他把媒介史分為了言語時代、手稿時代、印刷時代、視聽媒介時代和互聯網時代五個階段,并相應地把各個時期的人稱作語言人(Homo loquens)、手稿人(Homo scriptor)、誦讀人(Homo lector)、視頻人(Homo videns)和智能人(Homo somnians),得出三個重要的結論:(1)媒介技術改善了人類的物質生活;(2)媒介技術給了我們更好的感官體驗;(3)媒介技術對人類的精神世界并沒有帶來太好的影響。
也有一些外國學者對媒介史進行了斷代史性質的分期。比如美國學者沃爾特·翁的著作《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語詞的技術化》回顧了從11世紀以來西方媒介從口語文化到書面文化再到次生口語文化(secondary orality)的發展過程,認為電話、廣播、電視等電子媒介讓人類進入了一個次生口語文化時代,從內容和標題兩方面都明顯地表現了媒介斷代史分期的技術特征。比爾·科瓦里克(Bill Kovarik)的《傳播的革命:從古登堡到數字時代的媒介史》把古登堡以后的媒介史分為了“印刷革命”“視覺革命”“電子革命”和“數字革命”幾個階段,歷史的技術線索一目了然。阿薩·布里格斯(Asa Briggs)等人合著的《媒介社會史:從古登堡到臉書》幾乎復述了科瓦里克的媒介斷代史,沒有什么特別之處,但是他們的結論之一對我們是有啟發的:“書寫歷史的方式并不唯一,沒有一個標準答案,任何一種不同的角度都是可以的。”
中國學者關于傳播史或媒介史的時間敘事邏輯或歷史分期基本上也都沿襲了這種技術路徑。郭慶光的《傳播學教程》把人類傳播發展歷程劃分成“口語傳播時代、文字傳播時代、印刷傳播時代和電子傳播時代”。胡正榮等人編著的《傳播學概論》把傳播史劃分成“符號和信號時代、口語時代、文字時代、印刷時代、大眾傳播時代、網絡傳播時代”。李彬的《全球新聞傳播史》重點在新聞史,但是他也從媒介變遷的角度給人類傳播歷程劃分了階段,他把傳播史劃分成口頭傳播階段、手寫傳播階段、印刷傳播階段和電子傳播階段。新聞業創始于印刷傳播階段,電子傳播階段則囊括了廣播、電視和網絡。
“技術決定論”已經成為傳播史的基因了。在很大程度上,傳播歷史乃至整個人類史的方向或進程無可置疑地受到了技術的影響,至少可以說技術和其他因素共同支配了歷史。這種認識是傳播史分期法采用技術路徑的思想基礎。
二、傳播史分期法技術路徑的否思
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在談論歷史哲學時都普遍地堅持一種觀點,即任何一種歷史分期方法都有其不同歷史的、精神的原因,如果把歷史分期限定為某一種固定的范式或結構,那我們看到的歷史極大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歪曲的。傳播史分期也如此。美國學者邁克爾·舒德森就提出了異議,他認為,傳播媒介的引入及其結果不應該再被當作是傳播史研究的唯一核心問題。如果這樣規定,那就會將研究指向多種多樣的技術。人類現在積累的知識讓自己有理由懷疑這種取向的合理性。特別是如果我們將技術寬泛地定義為口述、印刷和電子通訊技術,傳播史研究就會深陷困境。他引用別人的觀點指出:“我們只能將傳播媒介視為社會實踐和文化供給性,而不僅僅是單純的技術。”舒德森還引用了威廉姆斯的話:“傳播史研究的結構所依據的是技術發明的順序,這導致傳播史研究更青睞某種技術決定論。誠然,在建構傳播史時,研究者很難避免不對新技術新發明出現的重要時刻另眼相待。但同時,我們也應當清楚這種以技術為中心的研究模式的局限性。”這清楚地說明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媒介技術上面睡大覺。
我們都知道“世界歷史”自黑格爾產生以后,世界歷史的分期研究也很快出現了,而且分期方法并沒有局限于某一種固定的模式。黑格爾把世界歷史的“絕對理念”劃分為東方世界、希臘世界、羅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四個地理形態從不成熟到成熟的發展過程;斯賓格勒把歷史看作是文化和文明發展躍升的過程,他把歷史過程分為“前文化階段”“文化或高級文化階段”“文明階段”三個時期,并且用 “埃及文化”“巴比倫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和“墨西哥文化”八大形態總結世界文化和文明;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變遷為線索把世界歷史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幾個時期。世界歷史的分期法還有很多種形式。
歷史分期的結果昭示了若干規律性的結論。歷史分期首先是人的精神性活動,是人對各種有機的和無機的、過去的和現在的、生成的和成長的、物質的和精神的事物的發展過程的普遍性的、整體性的、規律性的認識活動和結果,這個過程和結果彰顯了主客觀的二元結合,并且體現出一種高度的哲學思辨的性質。歷史及其規律固然是客觀存在的,但是人對歷史的認識明白無誤地體現了這一過程的主觀性,這意味著不同的主體對同樣的歷史的認識是不同的,如此也就產生了歷史上各種各樣對歷史分期的認識和結果。歷史的客觀性不僅僅體現在歷史的自在和自為,還體現在這種客觀性所包含的要素的多樣性,這樣一來歷史分期就體現出第二個特點,也就是第二個規律性的結論,即歷史給試圖認識它的人提供了不同的認識角度和判斷標準,可以讓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去認識它,也可以讓同一個人從不同的角度認識它,這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持有的幾種歷史分期法同樣成立、同樣有效的原因。第三種啟示是,任何總結出來的歷史分期法和分期結果,必須能夠反映歷史的最客觀、最普遍、最深刻的規律。強調這一點有助于防止有人對歷史隨意加以解釋,更防止有人隨意對歷史“打扮”、歪曲。但是,歷史規律不止一條,為何強調這一方面而不強調另一方面?除了對歷史進行分期的人在歷史世界面前的有限性——認識是有限的——之外,還因為主體的價值取向——即采取某一種歷史分期法——其實反映了主體的目的,簡單地說就是選擇某一種歷史分期想達到什么目的?這說明了歷史分期的合目的性和方法論性質。馬克思之所以得出“五種社會形態”的結論,一方面是這種結論確實揭示了歷史的客觀規律,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在資本主義的環境下,充分地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給勞苦大眾施加的壓迫和剝削,他希望找到一種能夠替代它、超越它的路徑。最后,歷史分期要有一個標準,一個能夠反應客觀規律的標準,一個能夠保證達成目標的智慧的標準。這個標準可以是歷史的性質和特征,可以是生產力、生產關系狀態,還可以是產生全局性影響的事件,或一段有特點的時間,如“中世紀”。至于歷史分期法的目標則分幾種,一種是歷史的終極目標,即歷史指向哪里,歷史分期就指向哪里;另一種是歷史分期法自身的目標,即每一種歷史分期總是要服務于它預設的目的;最后一種則是技術性的目標,即為了認識歷史的方便。雖然不能說所有的歷史分期都有此屬性,但是“在歷史編纂的實踐中還有對于具體的歷史過程為了敘述的方便而做的分期”。“歷史分期的本質是人們為了使自己的知識得到一種更簡單的從而更有說服力的表述而把連續的歷史內容依照從某種特定的角度選擇的事實和一定的觀念體系分為段落。”
除了哲學層面的思辨,媒介技術的進化和傳播業的發展也在逼問傳播史分期技術路徑的有效性。互聯網出現以后很多人把這一時期開始的媒介史或傳播史稱作互聯網時代,相應地把原來的傳播史分為了口語傳播、文字傳播、印刷傳播、電子傳播和互聯網傳播,最近幾年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又增加了數字傳播時代。這樣的劃分準確嗎?很少有人質疑這些概念的準確性。口語、文字是一種具體的媒介,但是從印刷開始,時代的代表變成了印刷、電子、互聯網和數字技術。媒介形式和媒介技術顯然不能被混淆為一體,兩者代表了兩種標準,用兩種標準同時為傳播史進行分期,其結果必然是兩類事物的拼組,而不是同類事物的整合。也許有人會說印刷傳播一詞是“印刷媒介傳播”的縮寫,電子傳播是“電子媒介傳播”的縮寫,互聯網傳播是“互聯網媒介傳播”的縮寫,數字傳播是“數字媒介傳播”的縮寫,它們都是指稱媒介形式。然而,如果這種理解成立的話,這些概念之間仍然存在著差異,并會引發新的質疑。印刷媒介和電子媒介是一種或一些有形的實體,但是互聯網媒介和數字媒介呢?電腦和手機固然是有形的,可是微信、微博、臉書、推特呢?可能是意識到這種區別了,有人把社交媒體、自媒體等媒介稱為“新媒介”或“新新媒介”,但是這種新媒介和舊媒介的本質區別是什么?“新媒介”和“新新媒介”的界限何在?新概念不僅沒有清晰地指出媒介與媒介之間的差別,而且讓原本存在的界限更加模糊了,關系更加復雜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對傳播史的分期如何能夠準確地描述傳播發展的階段性差異?
隨著全媒體時代“融媒體時代”和“全媒體時代”的出現,新舊媒介的界限不再是模糊的問題,而是消失了。新媒介并沒有完全地取代舊媒介,各種不同時代的媒介實現了交叉、融合或覆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是最早的媒介也能找到和新媒介結合的機會,而再新的媒介也需要以其他媒介為依托,或為內容。正如前文所引用麥克盧漢所指出的:“任何媒介的‘內容’都是另一種媒介。文字的內容是言語,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內容,印刷又是電報的內容一樣。”當我們把各種媒介都擺放到一起的時候,會發現我們根本不能理直氣壯地按照媒介各自出現的時間早晚給它們排序。比如當讀者看到這些文字的時候,它們僅僅是文字嗎?別忘了它們背后隱藏著的電腦顯示器和鍵盤;當我們面對一個電子媒介時,我們看到的僅僅是一臺電腦或一部手機嗎?不是!在它后面還隱藏著電子化的報紙、書籍、紙張等。只要放飛思維,我們會發現由傳統的媒介技術路徑展開的傳播史分期法制造的困惑還有很多。
提出以上質疑并不是要徹底地推翻傳播史分期的技術路徑,也不是說傳播史技術路徑已經窮途末路。而是為了在技術路徑險象環生時能夠另辟蹊徑,哪怕只是一條小路、輔路。也許問題正在于我們越是想用清晰的標準標識出歷史的每一個節點,節點就越是模糊;而當把標準設定得模糊一些時,歷史的節點可能反而會更加清晰一些。
事實上,已經有人在這方面做過一些無意識的改變。美國傳播學者詹姆斯·凱瑞在把傳播技術史分為“口語傳統—印刷媒介—電腦”三個階段的時候,沒有停步于這種簡單的歷史表征。他認為這三個階段是一個時間軸,它們分別有不同的“形式維度”和“內容維度”。“形式維度”表現為“表演—印刷—編程”,或者“演說—印刷—人類行為的編程”,再或者“演說家—印刷術—編程人員”,但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些“形式維度”要看到與之對應的“內容維度”:“談話—文本—模型”或“談話—文本性—結構”,而最關鍵的是在“內容維度”背后還有更深層的哲學隱喻:“實用主義—解釋學—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媒介不再是簡單的技術,更深刻地對標精神產物。按照凱瑞的思維邏輯,“傳播技術研究關注的重點并不在技術本身,而是技術所展現的言說方式、技術背后的話語和權力關系、思想觀念以及這些因素爭斗所形塑的現實世界”。這種理解在沒有主動挑戰傳統技術路徑的情況下為傳播史分期貢獻了一種獨特的哲學思維。
此前,也有過其他學者產生過類似的想法。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學者馬克·波斯特把電子媒介以來的時代分成了“第一媒介時代”和“第二媒介時代”,這個分期算不上歷史分期,只是對電子媒介時代傳播關系的一種“再構型”(波斯特語)。但是,這種思考實際上是運用了一種很特殊的分期標準的結果。他之所以把電影、廣播、電視時期稱作“第一媒介時代”,是因為那個時期的傳播關系表現為“為數不多的制作者將信息傳送給為數甚眾的消費者”。而“第二媒介時代”的特征是在信息“高速公路”和衛星技術與電視、電腦、電話結合的媒介環境下,“制作者、銷售者和消費者這三者概念之間的界限將不再涇渭分明”。很顯然,波斯特是從傳者與受眾之間的傳播關系切入問題的。
總之,舒德森已經提出了質疑,我們需要作出回應。
三、傳播史分期的功能導向
歷史分期的目的之一是方便人們認識歷史,即用一種最少的文字、最直觀的結構統攬歷史。歷史分期既要反映歷史的客觀性,又要體現對歷史分期的主體意識。歷史分期有時需要庖丁解牛,精確細微;有時又需要大刀闊斧,簡約概括。隨著數字媒介技術的誕生,也隨著我們對史前史認識的深入,傳播史分期中的歷史階段比麥克盧漢、施拉姆時期的時段延長了,洛根的分期法是典型的現代分期法,得到了國內外很多人的認可。然而,歷史分期的細化意味著我們在解釋歷史時需要更多的筆墨,但有的時候我們又希望能用更“經濟”的語言來描述歷史。傳播不等于媒介技術,傳播還有內容、功能、效果、受眾以及由自己構成的文化、經濟、政治等等。因此,當我們在沿著技術路徑往下走的時候,我們能否考慮把其它路徑如內容路徑、功能路徑或效果路徑等作為一種備選,說不定新的選擇恰恰是一條捷徑。當我們面對麥克盧漢的河流時,我們可否不順流而下,而是摸著石頭直接跨過這條河,沒準兒對岸就在咫尺之遙。
本文擬以傳播的功能為導向開展一番實驗性認識。
傳播學理論所涉傳播功能指的是傳播的社會功能。最早系統地提出相關理論的是拉斯韋爾,他在1948年的博士論文中提出傳播有三種社會功能:守望環境、協調社會和傳承社會遺產。后來默頓、拉扎斯菲爾德、帕克、賴特等人發展了他的學說,施拉姆將之發展為教科書理論:社會雷達、管理、傳授、娛樂。由于這些功能理論的復雜性,我們似乎無法從其中總結出一種歷史分期的線索。那么還有什么傳播功能理論嗎?如果我們稍微留心就會發現以上的功能理論也罷,功能主義也罷,所強調的是傳播的“社會功能”。這意味著在“社會功能”之外,傳播還有別的功能被我們遺忘掉了。這個被遺忘的功能其實就是傳播本身——傳播本體功能。媒介傳播什么呢?人們會回答說媒介傳播信息,但是在歷史的不同時期,信息是不同的,人們對信息的理解不同,信息的內容不同,信息的功能也不同。我們的出發點就在這里。如果按照傳播的本體功能框架耙梳,那一條不同以往但同樣清晰的傳播史線索就出現了。我們不妨根據傳播本體功能的“理想類型”(韋伯語),再結合媒介形態衍生的傳播形態的差異,借助歷史哲學的抽象思維,把傳播史劃分為記憶/記錄時代、新聞時代和全息時代三個大的歷史階段。
第一個時代是“記憶/記錄時代”。這一時代從神話時代開始,也就是從語言用于集體記憶開始,經過文字發明、書寫(手抄),到15世紀和16世紀的地中海城邦國家占據統治地位時期為止。人類在這一階段相繼發明了語言、圖畫(畫符)、文字、紙張、印刷術(主要是指中國的印刷術)等媒介載體和媒介技術,傳播的內容包含社會交往、官方布告、郵驛傳報、王權階層活動記錄、各種理論著述和知識、涉及軍事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集體記憶等等。圖畫(畫符)和文字是我們窺探那些過去歲月的最主要的表現手段。從本體功能角度看,它們并不強調即時性的信息交流,它們更多追求的是記憶、記錄。各種景物、事件、記憶、知識、歷史等通過崖壁、建筑、器皿、竹簡、紙帛等載體以圖畫、文字等方式保存下來,流傳至后代。這種傳播的目的也許是當時為了告知天地、族人、敵人以及可以到達的“天下”,也許是為了跨越時空傳頌千秋萬代。“記錄”這種傳播方式不追求即時性和廣泛性,它可能甚至只是為了讓記錄者自己銘記這些記錄的內容。當然比圖畫和文字更早的傳播是面對面的口語交流,它所體現的特征和記錄沒有直接的關系,那些傳播內容能夠轉述和傳承靠的是集體的大腦記憶。有關那些交流過程的認識我們后人們只能靠合理的推斷獲得。然而人類是如此的偉大,我們的祖先發明了文字,可以把耗散地存儲在每個個體大腦中千差萬別的“記憶文本”用一種具備一以貫之意義的、能夠為后人辨識的“可視文本”——文字永久地記錄下來。傳播完成了從記憶到記錄的轉變。通過這些記錄,我們得以了解古代的各種神話、史詩,也得以了解過去的一切。只有把歷史看作時光隧道,站在隧道的這端看隧道的那端,我們才會深切地體會到“記錄”的含義,體會到如德布雷等人所強調的“傳遞”(transmission)概念而不是“傳播”(communication)概念在人類傳播歷史中的意義。“傳播是在一個空間完成,是在同一個空間—時間—領域當中的信息運動,是一個長長過程的節點;而傳遞強調時間的緯度,意味著是在不同的空間—時間—領域當中的信息運動。”從時間偏向的意義上講,沒有比“記錄”二字更能概括這一段漫長的歷史,只有依靠記錄,那段時間才構成了整個傳播史的一部分。
15世紀手抄新聞的出現是傳播史上的第二階段“新聞時代”開啟的號角。隨著威尼斯、熱那亞城邦的興起,再加上教宗影響力的加持,意大利成為近代歐洲最早的集政治、經濟、文化為一體的中心。整個歐洲和西亞、北非的貿易、金融中心落戶在了地中海的東北地區,這個地區迅速成為了世界各地貨物的集散地。威尼斯和熱那亞商人們的足跡遍布整個歐洲和北非、西亞、南亞、美洲甚至東亞地區,他們對于有關地區的信息需求也成為第一需求。“消息奇貨可居,價值何止千金。”這就是手抄新聞出現的歷史背景。在那之后,新聞成為了信息傳播的一種更顯性的時代特征。它開始強調即時傳播,因為商人們需要用最快的消息把自己的損失和風險降到最低,還需要用最快速的消息換取更大的收益。在此基礎上還產生了一種新的業態——新聞業,新聞變成一種生產活動,變成有組織、有規律、有目的、有規模的傳播活動。因為印刷業的加盟,傳播不再是街頭巷尾的鄰里互動,而成為規模巨大的大眾行為。總之,在持續兩百多年的印刷業、郵政業、新聞業的推動下,日漸成熟的報紙刊物和大眾化受眾群體以及有目的有組織的傳播活動,帶來了近代報刊業的大發展,逐漸地、最終地讓人類的信息傳播邁入了新的時代——新聞時代。
我們都知道傳播學者和歷史學家更愿意把15世紀中期古登堡的金屬活字印刷術看作傳播史上的歷史性轉折點,幾乎所有的傳播歷史分期都把印刷術作為一個時代的開啟。伊麗莎白·愛森斯坦等人把印刷機(不是印刷術,強調了古登堡的首創)看作是歐洲變革的動因,芒福德把印刷術和鐘表一起看作是技術史的第一階段“始生代技術時期”最主要的創新。這些判斷是可以理解的,它們首先體現了大部分人對技術的重視(我們不隨便指稱別人是技術決定論,因為這個詞還沒有被還以清白)。站在技術主宰生活的今天,沒有人能否認第一種作為現代技術形式出現的媒介的重要性。產生這種判斷的第二種原因是印刷機給歐洲帶來的各種變化,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新教崛起、資本主義萌芽、報紙的大眾化,這么多的重大歷史現象都伴隨印刷機而出現,自然鞏固了人們對它的信任。另外,我們還可能要“妄自揣測”是不是“歐洲中心主義”在其中發揮作用——西方的學者故意放大了印刷機的歷史貢獻。畢竟,最早的印刷術誕生在東方而非西方,除此之外,中國在6世紀還掌握了木板印刷,9世紀掌握了雕版印刷。五代十國的“十朝元老”馮道于932年開始主持刻印的儒家經典《九經》,在他去世前一年的953年全部刻印完成,前后歷時21年。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官方性質的大規模印刷套書,對儒家經典的繼承作出了重大貢獻,我們甚至不能否認它在數千年塑造東亞各國社會結構以及東亞“天下—朝貢體系”中的作用。對于中國的成就,西方學者只是贊嘆“這一行為對于中國印刷業的意義,幾乎相當于后來古登堡印刷圣經對于歐洲的意義”,有意或無意地抵消了中國印刷業對人類傳播史的貢獻意義。不顧中國最早印刷術在世界歷史上的作用,而一味推崇古登堡的金屬印刷,肯定不是因為金屬比木頭先進或者昂貴。那么,如果我們充分肯定中國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的歷史意義的話,把古登堡印刷術作為人類傳播的歷史節點就值得商榷了。我們承認古登堡印刷對歐洲文明進化的重大推動,但這與新聞史的起點和新聞出現的傳播學意義不能劃等號。
李彬曾詰問:“新聞史所關涉的到底是新聞媒介對某些有新聞價值事件的報道呢,還是媒介自身的演進呢?”他的詰問和我們要談論的問題不直接關聯,但他提醒我們在這里提出一個類似的問題:把15世紀開啟的時代稱作“新聞時代”是因為金屬印刷術這種新聞媒介的出現嗎?為什么不是那些由報紙、金屬印刷機等共同構成的、被稱作新聞媒介的媒介開始塑造一種新的信息傳播模式和系統呢?無論如何,從新聞傳播本體的角度看,不把新聞本身作為歷史的起點,而把一種輔助它的技術作為它的起點,要么是一種“燈下黑”的表現,要么就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鑒于此,我們從傳播本體功能出發,從新聞本身出發,把這一時期稱為“新聞時代”。新聞時代不等同于印刷時代的涵義不僅從源頭上得以體現,還從它的結尾處得以見證,我們都是見證者:從傳播內容角度看,電子媒介出現后并沒有對信息傳播的本質形成根本性的改變,主要是沒有撼動新聞在傳播內容方面的主導地位和壟斷地位。即使是互聯網媒介出現初期,新聞在傳播內容中的壟斷地位也沒有被動搖,它的重要性只是從社交媒體和自媒體等“新媒體”出現后才開始被慢慢稀釋。
這個稀釋新聞時代的傳播史第三時代可以稱為“全息時代”。全息時代的源頭可以上溯到20世紀的信息時代,但它不等于信息時代,而是信息傳播進入融媒體、全媒體狀態的一個躍升。“信息時代”概念在20世紀60年代出現并風靡一時。阿爾文·托夫勒提出人類社會經歷了三次產業革命,第一次浪潮是農業革命,第二次浪潮是工業革命,第三次浪潮是信息革命,人類社會從此進入信息時代。這次革命的代表性事物是計算機、太空技術、分子生物、多樣化傳播等,其中信息技術和信息理論是核心。不過托夫勒認為當時還沒有一個國家進入真正的信息社會,盡管第三次浪潮到來了,但是第二次浪潮還沒有退去,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第三次浪潮將和第二次浪潮并存。這正如我們說傳播史的全息時代到來了,但新聞時代并沒有真正地結束。時代的更迭就和媒介融合一樣,新媒介出現了不意味著舊媒介就會徹底退出歷史舞臺,媒介融合更準確地說是新舊媒介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新舊媒介之間的關系是覆蓋的關系,不是替換的關系。傳播史的三個時期之間的關系也如此,在任何一種新時代都會彌漫著濃烈的舊時代的氣息,以至于我們不知道身處何時何處。
今天的移動媒體、社交媒體和自媒體已經成為信息傳播的主要載體,打開各種各樣的媒介界面,每個人都能感覺到信息平臺上除了新聞板塊之外,更多的是和新聞難以區分的各種商業資訊、廣告推薦、短視頻、游戲欄目、百科知識等等。對于受眾或網民來說,新聞內容往往不是第一選擇。很明顯,在新的傳播環境中,傳播主體和客體界限在模糊,新聞信息和非新聞信息的界限在模糊,主流媒體的新聞傳播屬性也在明顯地淡化。所有的社交媒體、主流媒體移動端的信息集散的功能遠遠超越了新聞傳播等功能。媒體不再只屬于新聞,它同時屬于知識、社交、娛樂、商業。一個全信息化、大信息化的傳播時代來到了。這正是“四全媒體”中“全息媒體”的要義。
全息時代的信息傳播看似經過一個輪回,從專業化的、分工協作的、注重即時消息的新聞時代回到了過去那種傳播內容不加區別、包羅萬象的記憶/記錄時代,但這種“回歸”不是簡單的回歸。媒介環境學派的學者萊文森說媒介正在再一次回到部落鼓時代,體現出一種“人性化趨勢”,但他明白這種回歸絕對不是技術上的一種重復,而是媒介和人的關系的重塑。全息時代和記憶/記錄時代的關系也如此,傳播功能打破了新聞時代那種新聞信息占據主導的格局,但新的復合信息格局絕不會是第一個時代那樣雜亂無章的生態環境的復制。全息時代是對包括新聞時代在內的過去一切傳播時代的一種覆蓋式的超越。在全息時代,新聞并沒有被其他信息取代,而是被覆蓋掉了,也就是說在各種互聯網新媒體、自媒體中,新聞最多可以說是海量信息當中有身份、有分量的一種內容,而不是像在新聞時代那樣占據絕對的統治地位。全息時代不是對截止今天的歷史的簡單總結,它更包含著對未來的預判。
注釋:
② 胡翌霖:《媒介史強綱領:媒介環境學的哲學解讀》,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132頁。
③ [加]哈羅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譯者序言第6頁。
④⑤ [加]羅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麥克盧漢》,何道寬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