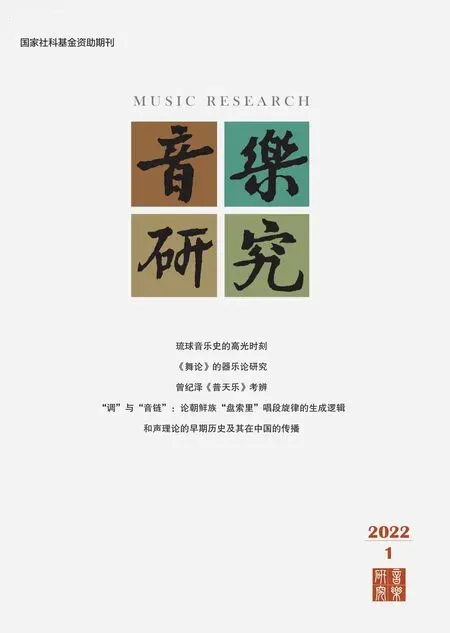中南半島復簧樂器歷史圖文考
文◎劉祥焜
一、樂器名稱的語言學初探:原生與外來
中南半島復簧樂器的名稱,大多由一個泛指管樂器的詞Pi(泰語、老撾語)或Pey(高棉語)后接一個或多個修飾詞而構成。Pi/Pey 這一詞根,在臺-卡岱(Tai-Kadai)語系(又稱壯侗語系)侗臺(Tai)語族中的西南臺(Southwestern Tai)語支諸語言中,均有同源詞,如泰語、老撾語、蘭納語(Lanna,即北部泰語)、傣仂語(Tai Lue)、撣語(Shan)等;中國云南撣傣系族群①楊民康《論云南與東南亞撣傣系族群傳統器樂的社會階層特征》,《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2 年第4 期。的多種管樂器名稱,常帶有“篳”字②參見《云南民族器樂薈萃》,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張興榮主編《云南樂器王國的傳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 年版;吳學源主編《云南少數民族樂器圖錄》,云南美術出版社2015 年版;等等。,均為這一詞源的音譯。該詞的唯一含義,即為管樂器的統稱,并無其他詞根來源;而具體所指何種管樂器,則由其后的修飾詞決定,在口語簡稱無修飾詞時,則指該文化中最常用的一種管樂器。例如,在泰國中部和南部,多指紡錘形復簧樂器Pi nai;在泰國北部和中國西雙版納等古蘭納王國地區,多指自由簧管樂器Pi chum(國內文獻的“篳總”);在老撾,多指自由簧樂器Pi lue(國內文獻的“篳鹿”)。而高棉語屬于南亞(Austroasiatic)語系,Pey 一詞是系自上述各語言中轉借,并不在口語中單用,僅用于后接修飾詞的正式名稱中。
在中南半島復簧樂器的名稱中,Pi/Pey 一詞之后所接修飾詞的含義,可分為如下三類:“指稱材質”“區分使用場合及調高”“暗示民族及歷史淵源”。
“指稱材質”的名稱,有柬埔寨雙簧樂器Pey prabauh。prabauh 為一種蘆葦類的水生植物,因這一樂器早期用這種植物制成。③Sam, Sam-Ang. “Musical instruments of Cambodia.”Senri Ethnological Reports (29).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02, p.34.近代以來,人們多用硬木代替蘆葦來制作該樂器,以使之更加美觀耐用,故也常稱其為Pey bobos 或Pey aw,bobos 是一種硬木的高棉語名稱、而aw 則是這種木材的泰語名稱。④Keo, Narom. Cambodian Music. 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 2005, p.157.
“區分使用場合及調高”的名稱最為普遍,如上述Pey prabauh 的另一個常用名Pey ou。ou 意為“低音”,也用在其他樂器名稱中,如泰國豎笛中粗長音低者稱作Khlui ou。泰國中部的紡錘形復簧樂器Pi nai、Pi klang、Pi nok,其中nai 和nok 意為“內”和“外”,指二者的演奏場合分別為宮內和宮外。據傳,在素可泰時代(1238—1438 年),民間出現了Pi nok 這種樂器,后來宮廷發現這件樂器很好,決定納入宮廷樂隊,但覺得它太高太尖銳,不易與其他樂器合奏,就把它加長、降低,形成了今天的Pi nai,所以從nok 到nai 就是從(宮廷)外到(宮廷)內,在大型的Piphat 宮廷樂隊中,仍使用二者同時演奏。⑤根據與Sugree Charoensook (2017 年10 月31 日,曼谷)、Grit Lekakul (2018 年4 月26 日,清邁)等人的訪談整理。Morton 給出了類似的解釋,但認為該樂器是在拉瑪四世時代(1854—1868 年在位),隨面具舞劇Khon 被引入宮廷的。⑥Morton, David. The Traditional Music of Thailan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79.后來,nai 和nok又成為調式名稱,并加入了klang 等其他幾個名稱,以適合泰國傳統音樂的七個音級,因為一直以來,宮廷樂隊都是以管樂器定調的。⑦緬甸的Hsaing Waing 樂隊,也是以復簧樂器Hne的各音孔作為各調高名稱。此外,柬埔寨里薩湖以西等地區使用的復簧樂器Sralai trai leak,也是得名于它所屬的Trai Leak 樂隊。
“暗示民族及歷史淵源”的名稱亦有許多,如泰國的Pi mon。mon 得名自緬甸南部泰國邊境的孟族人,且Pi mon 專用于其中的葬禮樂隊,也稱作Piphat mon。泰國北部古蘭納王國地區所用的錐形復簧樂器被稱作Pi nae,nae 是蘭納語借用緬甸語的Hne 一詞(下詳),因為這一樂器是緬甸統治蘭納時期(1558—1775 年)由緬甸傳入的。Pi nae 與緬甸Hne 一樣主要分為大小兩種,分別稱作Pi nae noy 和Pi nae luang,其中noy 和luang 即為“小”和“大”之意。泰國宮廷樂隊曾經在行進隊列中經常使用(現在已經罕用)的小型錐形復簧樂器Pi chanai,得名于印度復簧樂器Shehnai,而后者又被認為是得名于其發明者——波斯(今阿富汗)蘇菲派詩人Hakim Senai(1072或1080—1131 年)。⑧Fyzee-Rahamin, Atiya . The Music of India. London:Luzac, 1925, p.59.這一說法很可能只是后世的附會,因為Pi chanai 與Shehnai 兩者的基本形制相差甚遠。對于Shehnai 的歷史,周菁葆指出,印度的“Shehnai 被認為是起源于克什米爾山谷,通過改進Pungi而形成。”傳說在古代波斯禁止使用聲音尖銳的Pungi,“一個出生于音樂世家的理發師,將其改良,創造了Shehnai”。⑨周菁葆《絲綢之路上的雙簧樂器研究(三)》,《樂器》2013 年第4 期,第66—69 頁。Dick亦指出,印度復簧樂器與Pungi 有歷史關聯。⑩Dick, Alastair. “The Earlier History of the Shawm in India”. The Galpin Society Journal, Vol. 37, 1984, p. 82.類似說法也被中南半島傳統音樂家和學者們所證實。Shehnai 近似柱體管身、無喇叭口、無拇指孔的特征,均與Pungi 相符,但Pi chanai 明顯為錐體管身、有喇叭口、有拇指孔,與Shehnai 的相似程度反而不及Pi nai。從樂器基本形制來看,Sachs和Farmer 兩位學者提出的另一學說?Sachs, Curt. Die Musikinstrumente Indiens und Indonesiens. Berlin: Vereinigung Wissenschaftlicher Verleger,1923, pp.154-158;Sachs, Curt. The History of Musical Instruments. New York: Norton, 1940, p.230;Farmer, Henry G.Studies in Oriental Musical Instruments. Glasgow: Civic Press, 1939, pp.76-84.顯得更為可信:chanai 一詞來自梵語sanayi,而sanayi 則是對波斯語surna 的音譯。這暗示了Pi chanai 并非由Pungi 演化而來,而是直接由波斯(經印度或/及緬甸)傳入。然而, 若chanai 一 名 果 真 由Shehnai 而 非surna 而來,則另一種語言學的推論或許解釋了為何Pi chanai 至今仍為泰國皇室所專屬:最早見于13 世紀波斯(今印度)蘇菲派詩人Amir Khusrav(1252—1325)著作中的波斯語詞shah-nai,意為“王者的管樂器”?同注⑩,第91 頁。;而受梵語svara“音、主音、持續音”一詞(如Naga-svaram 一名,見彩版圖8)的影響,sur-na 一詞在印度一般被理解為演奏持續低音,而非旋律的管樂器。?Jairazbhoy, Nazir A.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Oboe in India.” Ethnomusicology, Vol. 14, No. 3, 1970, pp. 382.
另一個“暗示民族及歷史淵源”的名稱是泰國的Pichawa,同柬埔寨的Peychvea。chvea(高棉語)最早見于Sdokkak thom寺廟1052 年的銘文?Higham, Charles. Early Mainland Southeast Asia.Bangkok: River Books Co., Ltd. 2014, pp.353-354.,該銘文記載了阇耶跋摩二世(Jayavarman II,約770—835年),“從Chvea 來 到 皇 城Indrapura 并 在此統治”。較早的史學及語言學研究認為,chawa 和chvea 即爪哇島(Java),因此認為此類樂器源自爪哇。?Miller, Terry E. & Williams, Sean. The Garland Encyclopedia of World Music: Southeast Asia. New York,Routledge, 2013, pp. 173-174, 235-237.但當代史學家們認為,Chvea 這一地名所指并非爪哇島,而是臨近的,位于今日柬埔寨與越南邊境占婆國(Champa)。?Vickery, Michael. 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pre-Angkor Cambodia: the 7th–8th centuries. Toyo Bunko, 1998.佐證這一觀點的是,阇耶跋摩二世的政治生涯開始于今柬埔寨東部磅湛省(Kampong Cham),從其地理位置來看,與占婆國聚居地相符,而若他來自遙遠的爪哇島則顯得并不現實。由蘇利耶跋摩二世(Suryavarman II,1113—1145/1150年在位)始建于12 世紀的吳哥窟浮雕中描繪的復簧樂器,大多具有唇擋片(pirouette),富有伊斯蘭教象征意義;他本人也與占婆國多次往來征戰。?Maspero, G. The Champa Kingdom. Bangkok:White Lotus Co., Ltd. 2002, pp.75-76.據阿拉伯地理學家Al-Dimashqi(1256—1327)的記載?轉引自:Al-Dimashqi. Manuel de la cosmographie du Moyen ?ge. (1325). Translated by A. F. Mehren. Copenhague:C. A. Reitzel, 1874。,自阿凡(Uthman,644—656 年在位)和阿里(Ali,656—661 年在位)哈里發的時代起,一些從倭馬亞王朝(Umayyad Caliphate,今阿拉伯半島及北非等地)被逐出的穆斯林,逃亡至占婆國。歐陽修所撰的《新五代史》稱該地為“占城”。據此,占婆國在11世紀時,其民族與阿拉伯帝國(大食)一樣,已經伊斯蘭化。而爪哇島直至14 世紀仍處于印度教/佛教盛行時期。根據Tomé Pires 于1515 年撰寫的《東方集成》(Suma Oriental)記載,16 世紀初的爪哇人仍對伊斯蘭教充滿敵意。?Ricklefs, M.C.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since c.1300, 2nd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1991.這些史實均表明,與高棉歷代君主關系甚密的Chvea,顯然指占婆國,而非爪哇島。直到今天,在柬埔寨東部越南邊境的占族人聚居區,仍然存在著一個名叫Chvea 的村莊!因此Pey chvea 和Pi chawa 之類名稱,也并不意味著此類樂器來自爪哇島,而很有可能是來自占婆國的占族(Cham)穆斯林——直接來源于阿拉伯半島的移民。
從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出,樂器名稱所暗示的民族及歷史淵源未必可信,需結合相應樂器的使用現狀和相應民族、地區的史實等加以綜合審視和解讀,才有可能更加接近其歷史真相。
除了上述三類外,老撾的紡錘形復簧樂器Pi keo 這一名稱中的修飾詞keo(意為“透明的、優美的”)算是一個例外,并不屬于上面三類。這或許是因為老撾各民族稱作Pi 的樂器幾乎全部為自由簧管樂器。而Pi keo 是老撾唯一使用的復簧樂器,且它本身已經極為罕見,因此并不需要通過名稱與其他樂器加以區分,其命名應是當地人認為它比其他的Pi 更加“優美”。Pi keo 這一表達,雖然在泰語中同樣存在,但并不用作樂器名稱,僅用于贊揚任何簧管樂器的優美演奏。泰國基于傳統音樂近代以來受西方影響、受眾逐漸流失這一背景拍攝的熱播劇《》(Pi keo Nang Hong,直譯為“天鵝小姐的優美的Pi”),劇中用于泰國中部宮廷Piphat 樂隊的Pi nai,?參見 http://www.ch3thailand.com/news/drama/15218(2019 年1 月26 日)。與老撾并無任何關系。
中南半島復簧樂器的名稱,除了Pi/Pey這一基本詞源外,還有緬甸的Hne 和柬埔寨的Sralai 兩個詞源。緬甸語Hne 一詞,很可能轉借自15—16 世紀中古孟語(Middle Mon),據此重構的中古孟語詞形應為*sanay,但這一詞形未見于現存資料;孟語中存在的詞形僅有sanoy,該詞轉借入緬甸語后,根據音變規則應為Hnwe,這一詞形雖未見于標準緬甸語,但存在于與其關系密切的若開邦方言(Arakanese)中。進一步說,孟語的sanoy 一詞,可能同樣是借自梵語sanayi 或其他印度來源的詞如shehnai或surnaya,由此明確指向它與波斯語surna這一詞源的關聯。[21]Okell, Johk. “The Burmese Double-Reed ‘Nhai’.”Asian Music, Vol. 2, No. 1, 1971, pp. 25-26.這一語言學的推論,與Sachs 分析樂器本身得出的觀點[22]同注?,第157 頁。相互佐證,他認為從緬甸Hne 的形制,尤其是其巨大的喇叭口來看,它應該直接自西向東由陸路傳入緬甸,而非經印尼諸群島從海路傳入。此外,有早期記錄表明,現代Hne 的前身是尺寸很長、調高很低的vamsanu[23]同注[21],第25 頁。,這一名稱來自梵語詞vamsa“笛”[24]同注⑩,第85 頁。。這同樣暗示了它直接源于印度,而非源于南島。
高棉語的Sralai 一詞,從其輔音詞干s-r-l 即可直接看出它與波斯語surna (s-r-n)的關系:前兩個輔音相同;第三個鼻音n與邊音l 因發音方式相同,僅氣流除阻方式不同,而在許多語言中被廣泛混淆,[25]李俊生《四川方言中邊音鼻音混淆對英語語音學習負遷移影響的實證研究》,電子科技大學2013 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 頁。且兩者的語音聲學性質也極其近似[26]Ladefoged, Peter. Phonetic Data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fieldwork and instrumental techniques.Oxford: Blackwell, 2003.。結合其他高棉語樂器名稱,這一詞源上的相似,并不暗示Sralai 樂器本身與波斯的surna 有關,因為各種外來樂器均被冠以Pey 這一西南臺語外來詞。如前述來自占族人的Pey chvea,形制近似西亞duduk 或balaban 的Pey prabauh,以及或許來自撣傣系族群的自由簧樂器Pey pok,[27]如前所述,類似的樂器在中國云南與老撾、緬甸和泰國北部的邊境地區十分常見,且名稱大多帶有“篳”這一音節。pok 是制作該樂器所用的一種細竹子名稱。參見注③,第30 頁。但Sralai 卻并未被冠以Pey 之名。鑒于此種紡錘形復簧樂器僅存在于中南半島的柬埔寨、泰國、老撾的部分地區,基本可以推斷它是本地區古代先民發明的,而非外來傳入。
二、書面史料中的中南半島復簧樂器
(一)中國古籍
中國文獻對錐形復簧樂器的記載,始見于明正德年間(1506—1521)王磐《朝天子·詠喇叭》,此后見于戚繼光(1528—1587)的《紀效新書》,因此推論此類樂器傳入中原的時間大致是在元代。[28]陽鶴廬《從Zamr 類樂器的東漸探中國對阿拉伯音樂文化的吸收和改造》,《藝術探索》1991 年第1 期,第19 頁。而建于12 世紀的吳哥窟浮雕上,便已描繪了大量復簧樂器形象,這表明中南半島的復簧樂器并非由中國傳入,甚至可能中國的錐形復簧樂器是從中南半島傳入。[29]〔日〕岸邊成雄著,郎櫻譯《伊斯蘭音樂》,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 年版,第90 頁。這暗示著復簧樂器從西亞及南亞進入中南半島的路徑,主要經由中南半島西南部,而非與中國來往密切的緬甸東北部地區,因此不見于中國史料。
至清朝中期,緬甸音樂也被納入清宮宴饗禮樂之中,中國文獻對其樂器有非常詳細的記述,包括以圖畫描繪。據《清史稿》載:“乾隆五十三年(1788),緬甸國內附,獻其樂,列于宴樂之末,是為緬甸國樂。……聶兜姜,木管銅口,近下漸哆,前七孔,后一孔。管端設銅哨,加蘆哨于上,管與銅口相接處,以銅簽掩之。聶聶兜姜,形如金口角(嗩吶——筆者注)而小,木管木口,馀與聶兜姜同。”[30]《清史稿》卷101“樂八”。這很可能是中國古籍第一次對中南半島復簧樂器做如此細致的描述。“聶兜姜”中的“聶”字,顯然為緬甸語Hne 之音譯,“兜姜”二字的原文無法考證,現存緬甸各種Hne 的名稱中已無類似的發音。《皇朝禮器圖式》(見彩版圖1)對這兩件樂器有更加細致的描述:
燕饗用緬甸國樂聶兜姜。謹按聶兜姜規木為管,范銅為口,如竹節式,近下漸哆,管長一尺三寸二分、徑九分五厘。前七孔,后一孔。銅長六寸八分,口徑五寸九分,管端如盤,有銅哨插入,以象牙盤為飾,加蘆哨于上吹之。上下俱用?紃環系,旁有銅簽一,以彌管與銅連接罅隙之處。……聶聶兜姜形如金口角而小,木管木口,管長八寸六分,口長二寸,徑三寸三分,馀與聶兜姜同。[31]《皇朝禮器圖式》卷9“樂器二”。
類似的文字也見于《欽定大清會典圖》卷四十三“樂器八”,但繪畫略有不同。
從這些記載可以清晰地看到,錐形復簧樂器的形制,有拇指孔和唇擋片,喇叭口寬大,用繩子拴系在管身上。但文獻中認為,“銅簽”的作用是為彌合喇叭口與管身間無法緊密拼插的縫隙,疑有誤。事實上,這一銅制、木質或象牙質細簽的用途,是插在簧片之間,以保持簧片打開至合適的角度,以易于演奏。至今“銅簽”在中南半島及印度的復簧樂器上仍被廣泛使用(見彩版圖2)。此外,因Hne 的喇叭口與管身尺寸大小太過懸殊,前者直徑往往比后者大1 厘米以上,即使插入銅簽也難以“彌其罅隙”(見彩版圖3)。即使演奏者確實將銅簽插入喇叭口與管身間的縫隙,其目的也多在于保護銅簽不損壞、不刺傷人。此外,這些史料中記載的聶兜姜和聶聶兜姜的長度,與現代大小Hne 非常相近,兩者長度分別為44 厘米和28.7 厘米,與現代大Hne(40.6 厘米)與小Hne(27.9 厘米)的尺寸非常近似。[32]見緬甸廣播電視臺(MRTV)紀錄片Myanmar Traditional Instruments - Myanmar Oboe (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7-r4N9AHp8(2019 年1 月14 日)。《皇朝禮器圖式》的聶聶兜姜圖畫中,木質喇叭口兩肩較陡直,四周有條紋“卷邊”,非常類似現代南印度的復簧樂器Nagasvaram(見彩版圖4)。[33]http://collections.nmmusd.org/India/1191Nagaswaram/OttuNagaswaram.html(2019 年2 月1 日)。推測當時的聶聶兜姜的外觀,仍保留著Nagasvaram的影響,或可印證前述觀點,即緬甸Hne經陸路傳入,與印度有直接淵源。
以上幾部清代文獻,也同時記載了多種來自中亞及西亞的復簧樂器,如蘇爾奈等。這暗示中國的嗩吶類復簧樂器,是兼由西域和南洋兩條路徑,而非僅由兩者之一傳入的。
(二)印度古籍
中南半島深受印度文化影響,且印度是中南半島與波斯之間的必經之路,因此,有必要對印度古籍中的復簧樂器加以查考比較。
印度文獻對復簧的明確記述,最早見于中世紀南印度君主娑密室伐羅(Someshvara)三世于1131 年完成的皇室休閑消遣百科全書《心智之娛(Manasollasa)》,其中記載的復簧樂器Muhurika,用在牛奶中煮過軟化的蘆葦制作簧片,形狀類似一種花朵,并通過一段銅制細管連接在管身上。約一個世紀后,北印度音樂學者Sarangadeva于約1202—1212 年間成書的《音樂之海(Sangita-Ratnakara)》中記載的復簧樂器Madhukari(意為“蜜蜂”)的簧片,被稱作Suktika(意為“小貝殼”),同樣用在牛奶中煮過軟化的草葉或蘆葦制成,“形似微開的茉莉花蕾”,并通過一段銅制細管連接在管身上。[34]同注⑩,第86 頁。從以上形制描述看,這顯然是典型的肖姆類(shawm)樂器。根據這兩則文獻的上下文可知,這兩種樂器均為錐形管身,下端有顯著外擴的喇叭口,約53 厘米長,正面七個指孔加背面一個拇指孔,具有唇擋片(pirouette)。[35]唇擋片是置于簧片與管身之間的一個薄片,演奏者的雙唇緊貼其上,有助于提高口腔的氣密性,減輕長時間以較高的口腔氣壓演奏時雙唇的疲勞。這種形制,既不同于現代印度的Shehnai或Nagasvaram(無拇指孔、無唇擋片、長度亦不符),更不同于中南半島紡錘形復簧樂器,而是類似緬甸Hne,尤其與其古制Vamsanu(又作Wum-thar-nu[36]同注[32]。)形制極為接近。vamsa 一詞正是梵語的“笛”。[37]同注⑩,第85 頁。
可見,印度9—13 世紀的文獻中所提及的復簧樂器均為錐形管身,印度現存的復簧樂器管身幾乎為柱形;中南半島的復簧樂器分為錐形和紡錘形兩大類(見彩版圖5)。故可以推定,中南半島的紡錘形復簧樂器并非從印度傳入;錐形復簧樂器不同于近現代印度復簧樂器錐度很小、近似柱形的管身,可能經由占婆及印度分別傳入,并保留了較古老的、更接近波斯的形制。
(三)西方史料
1693 年,一位法國駐暹羅大使寫道:“他們有……非常尖銳的雙簧管,當地人稱作Pi,而西班牙人則稱之為Chirimias(肖姆)。”[38]La Loubère, [Simon]de. A New Historical Relation of the Kingdom of Siam, 1693, Reprinted as The Kingdom of Siam. Translated by A. P. London.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68.這是西方人最早對中南半島復簧樂器的明確記載,表明當時肖姆類錐形復簧樂器已用于暹羅宮廷。1852 年,英國人Neale 對Pi chawa 做了詳細描寫并繪有圖示(見彩版圖6):演奏Pi chawa 的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大多是樂團團長,而樂團團長又常常是職業耍蛇人;Pi chawa 常用波羅蜜樹的木材經拋光制成,有六個指孔,所演奏的旋律悲悲戚戚,令人不忍卒聽,“只有老舊的破風笛能與之相提并論”[39]Neale, Frederick Arthur. Narrative of a Residence at the Capital of the Kingdom of Siam. London: Offices of the National Illustrated Library, 1852, pp. 234-235.。在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1868—1910 年在位)皇室擔任家庭教師的英國人Anna Harriette Léonowens,也證實了Pi chawa 有六個指孔,其演奏者為職業雜耍者和耍蛇人。[40]Léonowens, Anna Harriette. The English Governess at the Siamese Court. Boston: Fields, Osgood, and Co, 1870,p.170.這些記述,證實了前述中南半島的復簧樂器與印度耍蛇管Pungi 間的淵源關系。但六個指孔的記載疑為有誤,因為前述年代更早的中國和印度史料中,均明確記載錐形復簧樂器的指孔為前七后一。暹羅駐英國倫敦公使館秘書Frederick Verney,最早繪制了Pi nai 的圖片,并引用著名學者Alexander J.Ellis 的文字描述:Pi nai 多用象牙、大理石或烏木制成,有六個指孔,不等距地分為四個一組和兩個一組。[41]Verney, Frederick. Notes on Siamese Musical Instruments. London: Wm. Clowes and Sons, 1882, p.17.
西方對柬埔寨復簧樂器Sralai 的提及則要晚得多,直到1907 年德國音樂學家Knosp 才首次提到Sralai,他指出:其簧片為四層經煙熏處理的棕櫚葉制成,通過一段銅制細管與管身相連;管身長度36 厘米,直徑4.5 厘米,有六個指孔;具有“鋸木頭般的可怕聲音”,最低音約為g1,音域約兩個八度。[42]Knosp, Gaston. “über Annamitische Musik.”Sammelb?nde der Internationalen Musikgesellschaft, Vol. 8,No. 2, 1907, p.156.這一記載中的尺寸與音高,介于現存一大一小兩種Sralai 之間。
法國在20 世紀前半葉對高棉音樂有數次考察研究。最早記錄柬埔寨復簧樂器的為法國人Roeské。該學者于1913 年提道:為柬埔寨Bat 和Kalabat(敘事詩演唱)伴奏的大型樂隊,包括十余種樂器,其中有一支Sralai 和一支Sralai khlan khèk(作者原注“馬來雙簧管”,即Pey chvea 的別名[43]同注③,第38 頁。),以及Khloy(豎笛),三種木琴和多種鑼鼓。[44]Roeské, M. “Métrique Khmère, Bat et Kalabat.Troisième Partie.” Anthropos, Vol. 8, No. 6, 1913, p. 1036.然而,柬埔寨現存的各種傳統樂隊中,卻并無這種紡錘形復簧樂器與錐形復簧樂器同時演奏的組合形式,或許這是一種業已失傳的樂隊組合形式,抑或是該作者當年所觀察的樂隊為臨時拼湊,并非傳統制式。據法國遠東學院記錄,1927 西索瓦(Sisowath)國王的火化儀式樂隊中使用了Sralai,但在腳注中解釋為“一種哨笛”[45]L'é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 “CHRONIQU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 Vol.28, No. 3/4, 1928, p. 624.。該學院學者Baradat 于1941 年在對柬埔寨西部派爾人(Pear)的研究中亦提道:“他們的歌唱由Sralai 尖利的笛聲伴奏”[46]Baradat, R. “Les Samrê ou Péar Population Primitive de l'Ouest du Cambodg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 Vol. 41, No. 1, 1641, p. 17.。該兩處稱為“笛”,顯然有誤。
可見,中南半島的復簧樂器自17 世紀后期至今,形制基本沒有發生變化。對錐形復簧樂器的記述,遠遠早于紡錘形復簧樂器,這表明后者進入宮廷音樂的時代更晚;[47]Miller, Terry E. and Jarernchai Chonpairot. “A History of Siamese Music Reconstructed from Western Documents, 1505-1932.” Crossroad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8, No. 2, 1994, p. 71.這或可印證前文對樂器名稱的語言學分析所得到的推論,即錐形復簧樂器自古與王室相關,而紡錘形復簧樂器則經歷了從“宮外”到“宮內”的過程。
三、吳哥城浮雕中的中南半島復簧樂器
(一)吳哥窟浮雕
吳哥窟由蘇利耶跋摩二世(Suryavarman II,1113—約1150 年在位)建造于12 世紀前半葉,其回廊包含超過1200 平方米的浮雕,這些浮雕大多與建筑主體同時完成或不久后完成。據當時的銘文記載,北廊東翼和東廊北翼(見彩版圖7)的浮雕,雕刻于16 世紀中期,比吳哥窟其他浮雕晚300 余年。[48]Knust, Martin. “Urged to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he Iconography of Music on the Reliefs of Angkor Wat.” Music in Art, Vol. 35, No. 1/2, 2010, p. 41.回廊浮雕中共出現近150 件樂器雕刻,因浮雕大多描繪軍樂隊場景,因此所刻樂器主要為管樂器和各類鑼鼓樂器,幾乎沒有弦樂器。管樂器之中,有一部分可明確辨認為復簧樂器、螺號或號角,其余則因細節不全或形制奇特而難以確定其分類。可明確辨認為復簧樂器的浮雕,均出現在年代更晚的北廊東翼,其形制也包括與現代Sralai 近似的管身呈紡錘形、帶有平行環帶、上下兩端稍突出式(見彩版圖8),以及與現代Pey chvea 近似的管身呈錐形、下有喇叭口式(見彩版圖9)。兩種類型大多具有唇擋片,并出現在類似現代Pinnpeat 樂隊的合奏形式之中。其他位置的浮雕中均未出現此類雕刻,這表明與現代形制近似的復簧樂器在高棉帝國廣泛應用的時間應在13—16 世紀之間。
本文以回廊上的各個柱子來標記浮雕所處的位置。各處柱子按逆時針方向依次計數,結合所處回廊位置命名并簡記,如彩版圖7 所示。
類似的典型復簧樂器雕刻也見于NE3、NE9 等處。此外,令人驚訝的是,NE5 與NE25 兩處出現了雙管雕刻(見彩版圖10),兩處雕刻均為兩手各持一管呈“V”字形端吹(豎吹),管身均為錐形,后一處有喇叭口,無唇擋片。由于唇簧樂器需要雙唇振動發音,而雙唇不可能或極難同時產生兩處振動以吹響兩個號角,故可以排除其為唇簧樂器。在中南半島未見任何雙管樂器的實物、文字記載或其他雕刻。中國甘肅、壯族等地的漢族和部分少數民族,有雙簧雙管帶喇叭口的“雙嗩吶”,但其兩根管身平行綁定,并非呈“V”字形。錐形雙管、呈“V”形持奏的樂器,在世界范圍內極為罕見。然而,中國民間常有同時吹奏兩支普通嗩吶,呈“V”形持奏的情形,且往往與其他雜技相結合(如邊吹奏邊頂碗)。這一演奏形式在世界其他文化中也有可能出現,所以此兩處浮雕所刻可能并非描繪某一“V”形雙管樂器,而是同時演奏兩件錐形復簧樂器。
除北廊東翼以外,在其他位置的年代較早浮雕上,最接近復簧樂器形制的是SW28 處的一件錐形管身、下端有喇叭口的樂器雕刻(見彩版圖11)。該樂器管身筆直,不同于其他各處浮雕中的唇簧樂器雕刻(見下);有擋唇片,但或許是演奏者雙唇四周的髭須。筆者以為,將這一雕刻辨認為復簧樂器應該比較合理。
有一種外形頗為奇特的管樂器雕刻常見于吳哥窟浮雕,如NW19(見彩版圖12)、NW23、WN9、WS13,以及西北角樓(見彩版圖13)等處:頂端有唇擋片,中上部膨大,底部略呈魚尾狀向外延伸。這一奇特的外形,與中南半島乃至世界各地現存的樂器都缺乏相似之處,吳哥城東部建于10 世紀初的鷹爪花廟(Prasat Kravan)兩處浮雕雕刻中的毗濕奴(Vishnu)手中所持梵貝(儀式用螺號),具有類似的魚形輪廓(見彩版圖14),因此Kersalé 等學者認為此類樂器為螺號。[49]https://www.soundsofangkor.org/english/ancientinstruments-va/conch-va/ (2019 年1 月27 日)。但天然螺貝并無形似魚尾的下部,各文化中的儀式樂器螺號也并無人工制作魚尾形裝飾的實例;且吳哥窟浮雕中可明確辨認為螺號的雕刻(如彩版圖11、12 等)與此迥異,而此類樂器雕刻往往并無螺紋外觀(如彩版圖13等);因此將其辨認為螺號有些牽強。然而,此類樂器雕刻卻與宋代陳旸《樂書》(1101)卷一百三十中對胡笳的記載頗有類似:“胡笳,似篳篥而無孔,后世鹵簿用之……豈張博望(張騫)所傳《摩訶兜勒》之曲邪”;“篳篥……以竹為管、以蘆為首,狀類胡笳而九竅,所法者角音而已”;“胡角本應胡笳之聲”。這些記載表明,胡笳為類似篳篥的復簧樂器,沒有音孔,只能發出一個音高,與號角聲音相仿,用于皇室儀仗隊。《樂書》中所繪的大小胡笳,亦有唇擋片,上部突起,底部稍有擴大。僅觀吳哥窟浮雕樂器雕刻:有明顯的唇擋片,表明其為復簧樂器;雙手左右并排而非上下持管,表明無音孔;[50]僅塤、陶笛等腔體笛(vessel flutes)類樂器可能出現左右并排的音孔,此處顯然不符。常與號角和螺號同時出現在行進樂隊之中。《樂書》與吳哥窟浮雕均成于12 世紀,且前者記載的雙角、吹鞭、哀笳等,皆可在吳哥窟浮雕中找到類似的樂器雕刻。值得注意的是,其曲目名《摩訶兜勒》中的“摩訶”,為梵語Maha“大”之習慣音譯用字,暗示該樂器并非來自中亞游牧民族,而是來自南亞印度民族,更有可能與中南半島有所聯系。
(二)巴戎寺浮雕
巴戎寺由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1181—約1220 年在位)建造于13 世紀初,經后代君主不斷添加擴建。巴戎寺浮雕總面積超過1000 平方米,獨特之處在于其分布于內外兩圈回廊中,外圈與建筑主體在13 世紀初同時完成,描繪歷史事件和日常生活;內圈則由阇耶跋摩八世(Jayavarman VIII,約1243—1295 年在位)在13 世紀后半葉添加,內容多為印度教神話。內外圈浮雕中共出現近百件樂器雕刻,外圈因大多描繪軍樂隊場景,因此主要為管樂器和各類鑼鼓樂器,罕見弦樂器;內圈則兼有行進樂隊和室內樂舞,因此管弦打擊各類樂器出現較為均等。浮雕的位置標記方式,即用回廊朝向和柱子計數表示。
與吳哥窟南廊西翼類似,巴戎寺外圈東廊南翼浮雕描繪的高棉軍隊簇擁其君主出行的行列,ES10 處出現了僅有的兩處類似復簧樂器的雕刻(見彩版圖15)。出現在中層的這一樂器雕刻為直錐形管身,具有明顯喇叭口,但末端稍內收呈梨形,且其似乎與管身并非一體,而是分立拼插,雙手上下持管,基本可以辨認為復簧樂器。下層出現了一種形似糖葫蘆而稍呈錐形的奇特管樂器雕刻,它在外圈ES5 處又出現一次。其外觀稍有類似中國部分地區的嗩吶或日本的復簧樂器Charumera,其管身上有一條條竹節狀凸起裝飾;而吳哥城地區廣泛分布的大佛肚竹(Bambusa vulgaris)的下部,則更加類似這一外觀,又或許是此種竹筒制成的唇簧樂器。[51]https://www.soundsofangkor.org/english/ancientinstruments-va/trumpet-horns-va/ (2020 年2 月15 日)。這兩種猜測,在柬埔寨當地均無樂器實物或圖文記載佐證,因此無法確定辨認。然而,鄰國越南中部的復簧樂器kèn b?u,卻兼具前者的梨形喇叭口和后者的糖葫蘆形管身,[52]http://hoinhacsi.vn/toan-cau-hoa-va-buoc-chan-daqua (2020 年2 月16 日)。為進一步考證提供了一條可能的線索。
雖然巴戎寺與吳哥窟浮雕總面積相差無幾,但是其樂器雕刻數量及種類均明顯少于后者。這是因為巴戎寺浮雕(尤其是內圈)受建筑空間的制約,大場面尤其是戰爭場面較少,或許也有統治者個人喜好的影響。然而,巴戎寺浮雕中的弦樂器雕刻反而遠多于吳哥窟,表明在吳哥王朝,管樂器大多用于軍樂和行進樂隊中,而弦樂器則與舞蹈和表演藝術關系密切。
結 語
一種或一類樂器出現在某一地區,究竟是來自本地古代先民的發明創造,還是外來傳入該地的,抑或是外來傳入的某種原型被當地民族加以改造的,往往難以明確考據定論。但樂器的出現和使用,主要是由材料與工藝的可獲得性(accessibility)及該樂器的社會功能這兩個要素決定的。本文探討中南半島復簧樂器在語言學、圖像學,以及口述和書面史料中的蛛絲馬跡,梳理其早期歷史源流和脈絡,即是基于這兩個要素。筆者認為,無論是本地發源還是外來傳入,樂器若想實現代際傳承并成為某地音樂傳統的一部分,必定需要不斷生產新的樂器實物;因此,這一地區必須出產制作該樂器的豐富材料或性質近似的代用材料,且加工這些材料所需的工藝水平必須較為成熟。另一方面,某一樂器及其曲目的持續生存,受到其社會功能的影響,包括審美欣賞功能、娛樂功能、交流功能、象征功能、情感表達功能。[53]Merriam, Alan P.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349.或許可以說,某一樂器在某一文化中所參與的社會功能種類越多,它在該文化中的生命力就越旺盛,越不容易消亡或被取代;反之,當某一樂器所參與的社會功能較為單一甚至沒有,則它很容易被其他樂器和曲目所取代或自行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