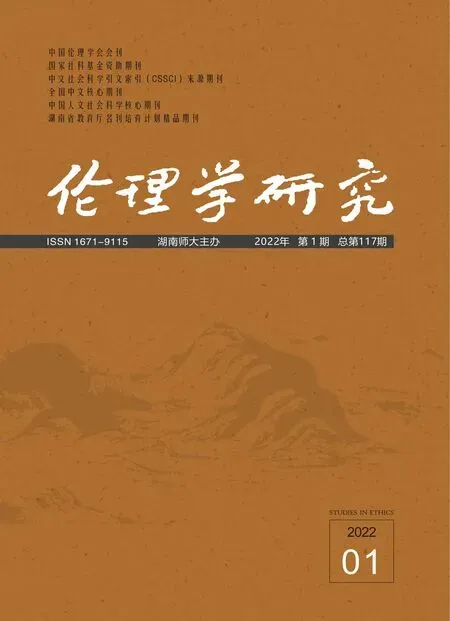論孔子“均、和、安”的公平正義思想
楊 潔
近代以來,詮釋公平正義的話語權一直由西方掌握,這導致我們在分析中國自身問題時也習慣于在西方的公平正義學說中汲取理論依據,以西方的公平正義觀來衡量中國自身問題。“如果我們不能把握中國傳統的公正觀的特征,也就難以把握社會公眾對‘公平正義’訴求的真實內涵,更難以找出解決問題的恰當辦法。”[1](28)所以在關注借鑒西方理論成果的同時,我們更需要結合傳統精神、時代特征與現實需求“反求諸己”,從中國歷史積淀中發掘并汲取傳統公平正義觀的思想資源。孔子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代表,其思想一直為中國傳統文化提供著“源頭活水”。孔子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公平正義”的具體概念,但從其“均、和、安”思想中仍然能夠感受到他對公平正義的考量與重視,探究到他對公平正義的闡釋與發揮,其“均、和、安”思想深具中國傳統公平正義思想的意蘊。
一、孔子“均、和、安”的公平正義思想
孔子在《論語·季氏》中提出“均、和、安”的思想: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于費。今不取,后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于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朱熹如此解釋道: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于貧而和,和則不患于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2](170)
朱熹認為“寡”涉及人口數量,“貧”涉及財富問題,“均”意為“各得其分”,故對原文其更傾向于“貧”與“均”,“寡”與“安”的搭配。俞樾認為“上下兩句互誤例”[3](109):“寡、貧二字,傳寫互易,此本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貧’以財言,‘不均’亦以財言,不均則不如無財矣,故‘不患貧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不安則不如無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可據以訂正。”[3](111)李零表示:“‘均’固對‘貧’,但‘寡’卻并不對‘安’,而是作‘和無寡’‘安無傾’。”[4](290)
我們認為,根據“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三者之間的有機聯系,《論語·季氏》原文可為:“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傾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貧”意為財富貧乏,“均”意為各得其分,“寡”意為人口稀少,“和”意為社會和諧,“傾”意為政權傾覆,“安”意為民安邦寧。孔子認為相比擔心財富貧乏、人口稀少、政權傾覆,更擔心財富分配的不均衡,社會關系的不和諧以及人民生活的不安定。
無論《論語·季氏》是否具有錯漏補綴存疑的問題,結合孔子對冉求說教的背景,其體現出的正是孔子深諳人民對公平正義的訴求。“均”要求財富分配“各得其分”,以此縮小貧富差距,體現社會公平,實現社會之“和”。但孔子認為此時所達到的“和”之深度仍然不夠,進而提出“寡”的問題,即人口數量的問題,但孔子并不擔心人口多寡而威脅到“和”,相比人口數量更擔心人口質量,確切地說,是人的內在道德問題,所以,“和”的要求不能只停留于等級分配正義的經濟社會之“和”,要從經濟社會之“和”上升到道德社會之“和”,即進一步深化到內生道德正義層面。在這個意義上,“和”之高度在于“中庸”,“和”之根基在于“仁性”,以“仁”界定社會秩序的合理性,以“仁”肯定固有人性的平等性。但是,孔子認為具有高尚德行的人民還未達到“安”的程度,想要達到真正的“安”還需要從內生道德需求之“安”落實到外在物質需求之“安”,所以,必須堅持“藏富于民”的民本經濟正義,鼓勵人民自由生產,保障人民利益,增進人民福祉,民富則國富,國富則民安,本固則邦寧。
可見,從孔子“均、和、安”的思想中提煉出“各得其分”的等級分配正義、“崇仁尚中”的內生道德正義和“藏富于民”的民本經濟正義,均內含公平正義的思想意蘊,均是公平正義的具體體現。因此,對孔子“均、和、安”的思想可作進一步解讀:以“均”為基,“和”為貴,“安”為重,將經濟、道德、政治統一起來,形成從“各得其分”的等級分配正義層面,到“崇仁尚中”的內生道德正義層面,再到“藏富于民”的民本經濟正義層面的理論邏輯,建構出一套有機聯系的傳統公平正義思想體系。
二、“均、和、安”公平正義思想的三重意涵
1.以“均”為基:“各得其分”的等級分配正義
孔子強調“各得其分”的等級分配,以處理貧富差距問題。這里的“均”,為均衡、各得其分之意,誠如李澤厚所說:“其實這里的‘均’并非平均,而應作為‘分’解。康有為《論語注》:‘均,各得其分’,即按不同等級、身份而有不同的分配。”[5](285)孔子認為,人與人之間的身份、地位、能力等差別會產生資源利用、財富收入的差距,社會成員之間財富收入“不均”會導致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最終使得社會不和、國家傾危。因此,必須在人民中重視“不均”的貧富差距,因為這可能會導致比整體貧窮更為嚴重的后果。但孔子對于貧富差距問題并不認同“平均”意義上的絕對公平,而更傾向于在“各得其分”意義上的相對公平。
那么,如何把握孔子“各得其分”的分配原則,以緩解貧富差距懸殊的問題呢?
孔子肯定“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論語·學而》),認為國家貧富差距的“度”在于富者不因過富而驕,導致因欲望而缺少敬畏,故肆無忌憚地做殘暴之事。貧者不因過貧而憂,導致因生存而違背本性,被迫做違法之事。一旦社會出現此類情況必須要以“均衡”收入分配的方式來及時止損,防止貧富懸殊導致矛盾激化而影響國家的安定。可見,孔子的分配原則或者“度”的衡量標準是動態的,是靈活地根據社會現實和客觀實踐的分析與要求來確定的。同時,在靈活的調度標準中需要把握一條重要的底線——民本原則,維護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權利。
由于處于等級制時代,孔子的“各得其分”內含等級差別之意。那么,如何理解孔子的“等級差別”?
孔子的分配原則是建立在禮制等級下對社會財富“各得其分”的“均衡”分配。但是,不能因“等級差別”而否定儒家思想中的平等精神,進而否定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公平正義。
其一,保障人民生存、生產、發展等社會公平。“平均分配財富,并非意味著人人均享有同等收入,而是人人均應有獲得同等收入的同等機會。”[6](359)而且,“在他們之中,沒有任何人能獲得任何特殊的有利條件以增加其收入;另一方面,禁止了上層階級為了與庶民競爭而從事任何有利可圖的職業”[6](360)。
其二,孔子的“等級差別”具有開放性和流動性。雖然等級是固定的,但是對于誰處于哪個等級卻是可以憑借能力而取得的,爭取更高等級的機會對每個人仍然是開放的。“絕對沒有把任何人限制在某一類人之中,而是根據他的能力,或者上升為尊貴,或者下降為卑賤”[6](360),甚至“天子”的地位也是可以憑能力爭取的,“元子而常常可以改,則元子與眾子之地位原非絕對的。質言之,則人人皆可以為天子也。此種人類平等的大精神,遂為后世民本主義之總根芽”[7](37-38)。
其三,“仁民愛物”的平等精神和民本原則是“天子政治”的道德根基。所謂“君權天授”,作為宗法等級中最高的“天選之子”也只是“天”的代理人,其權力由“天”賦予,需要對“天”負責,而“天”是人民意志的體現,對天負責即是對民負責,只有敬民、重民、愛民、安民的統治者,才能成為“天子”,否則只是“一夫”。
概言之,孔子等級分配正義體現出的“平等”“民本”精神是公平正義的基本要求。以“富者不驕”與“貧者不憂”的社會狀態來把握貧富差距的“度”,以平等精神與民本原則來守住“相對公平”與“差別共富”的底線。人民擁有生存、生產、發展等相對的社會公平;開放性與流動性的等級設定讓人民具有爭取上層等級的公平機會;“君權天授”的法統奠定了“仁民愛物”的民本政治。
2.以“和”為貴:“崇仁尚中”的內生道德正義
孔子通過“各得其分”的等級分配以縮小貧富差距,但孔子認為貧富均衡不是社會和諧的關鍵,社會和諧不僅表現在經濟公平上,更體現在人的道德正義上,這是價值層次上的“和”。此外,“和”作為一種社會狀態,不僅是“均”的結果,更是“均”的初始條件。
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和”,人口多寡也不是社會和諧的關鍵,人多力量大的前提是人人具備高尚的德行,以德行修養之“和”維持社會關系之“和”,否則人多反而成為維持社會穩定的障礙。而且,孔子的等級分配正義是基于禮制的宗法等級社會背景而建立的,一旦禮崩樂壞以及統治者貪婪腐敗必將導致社會公平正義的削弱,從而民不聊生,財匱力盡,因此,禮制必須基于更高的價值層面,以道德為基;統治者必須具備高尚的德行,以德治化民。
首先,如何理解儒家的“和”①儒家的“和”包含著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天等各個層面上的豐富內涵,此處僅指社會關系層面上的“和諧”之意。?“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劉寶楠將“和”以“中庸”的高度進行詮釋:“有子此章之旨,所以發明夫子中庸之義也。”[8](29-30)然,何為“中庸”?“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2](17)因此,以“中庸”致社會之“和”,需要堅持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恰如其分、合情合理的德行以及具有審時度勢、靈活應變的能力。
“明中庸之為德,皆人所可常用”[8](248),但事實上百姓卻缺失已久,孔子不得不感嘆“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那么,為什么會出現“常用之中庸”而“民鮮久矣”呢?究其原因,是因為百姓未“盡己之性”,未“盡人之性”。
孔子之“性”被思孟學派和宋明理學繼承,認為“天”所賦予的人之本性是仁、義、禮、智。而“仁”又是四德之首。“仁”是人與人相處的大道,這種大道不是外在賦予的,是人性所固有的。孔子之“仁”,自差等之愛始:“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本,基也。基立而后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后仁道可大成。”[8](7)“仁”的實現自對父母之愛發端,從人最初的自然情感出發,擴充至人類普遍的仁愛,達到“仁者愛人”(《論語·學而》)的境界。誠如錢穆所說:“發于仁心,乃有仁道。而此心實為人性所固有。其先發而可見者為孝弟,故培養仁心當自孝弟始。孝弟之道,則貴能推廣而成為通行于人群之大道。”[9](8)
“和”之基在于“性”,“性”以“仁”為首,那么,如何踐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何為“忠恕”?“盡己之心以待人謂之忠,推己之心以及人謂之恕。”[9](72)孔子認為,人心所欲所惡相差無太大懸殊,因此“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作為踐行“仁”的忠恕之道,從自我所欲所惡出發,可以貫通到人人之心,人人盡力便可實現。“恕”表達了不侵害他人利益的底線道德,“忠”表達了和合互利的人生境界,這也正是現代公平正義的體現。
“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此處的文德既可以表示統治者“以民為本”的仁治,也可以表示人民“崇仁向善”的德行,不論是統治者還是人民,修好各自的文德,遠方的人才能歸順。以德服人,這或許正是孔子“和無寡”所表達的深意。
3.以“安”為重:“藏富于民”的民本經濟正義
“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季氏》),孔子認為人民歸順后統治者應提供“富足”之“安”,他強調“藏富于民”的民本經濟正義,民富則國富,國富則民安,民安則邦“無傾”。
第一,孔子承認求富逐利的目標追求,肯定“人之所欲”: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
孔子承認人求富逐利的欲望,但要求在道德本位下進行。同時,他區分了精神追求與物質追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人民以追求財富、促進生產、發展經濟為目的,而君子不應囿于物質利益的滿足,還應在現實生活中以“修齊治平”為政治理想,在人生追求中以“孔顏之樂”為價值目標。
第二,孔子重視民富國安的辯證關系,要求“藏富于民”: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趕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8](529)
孔子認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民富與國安休戚相關,民富須先于國富,社會才能穩定,國家才能安治。所以,統治者要調動人民生產積極性,支持人民去創造財富,發展經濟。那么,如何調動與支持呢?孔子認為“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要求統治者誠實無欺,以保障人民的利益;提倡節用,以減輕人民的負擔;不違農時,以順應生產的規律。他尤其主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認為統治者應對人民的逐利行為采取順應放任的態度,保障生產自由、機會均等的權利。陳煥章認為這是孔子提出的自由放任的經濟原則,“普遍平等、普遍機會以及理財自由,這些均為孔子最重要的教義……即是以自然之道引導民眾進行理財活動的一般政策”[6](144-145)。
第三,孔子強調財富智富的協調發展,主張“先富后教”:
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
孔子對于“民富”不僅強調物質上的“財富”,還重視教育上的“智富”,主張人民富足之后就可以通過教育來開啟民智。他特別強調對人性的道德教化,使人民樹立正確的求富觀,不僅要“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論語·學而》),更要“貧而樂道”“富而好禮”,以維持社會的安定和諧。此外,孔子的公平正義觀還體現在他“有教無類”的思想上,孔子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傳統,使受教育者無關貧富、地位、地域,每個人都能公平地接受教育。在為統治階級提供豐富的人才資源的同時,“針對世卿世祿的制度,孔子主張從民間‘舉賢才’與‘有教無類’,開放教育與政治,此即機會公平與公共權利向民間敞開的大事,也即肯定民眾的受教育權與參與政治的權利。此為最具有正義性、公共性的遺產”[10](147)。當然,這也是最根本的“民富”。
三、“均、和、安”公平正義思想的內在邏輯關系
孔子以“均”為基,以“和”為貴,以“安”為重,建構了從“各得其分”的等級分配正義到“崇仁尚中”的內生道德正義,再到“藏富于民”的民本經濟正義的公平正義思想體系。那么,這個公平正義思想體系的內在邏輯關系是什么?
如果說“分配”只具有工具理性的意義,那么孔子強調的“分配正義”則被賦予了價值理性的內涵。“從實質的層面看,正義問題的核心無疑在于社會資源的合理占有和公正分配。”[11](254)通過“公正”的分配使得人與人、人與群體之間相互讓渡和勻取資源、財富、機會等利益,從而保障公平權利,維持社會和諧,不僅具有社會性,而且也是一種道德實踐,符合儒家合乎普遍利益訴求的“義”。所以,對“分配正義”之“正義”的內涵進一步深化和抽象,便可歸溯至儒家的“義”。“分配正義”,即用“義”的準則來進行利益分配是為公正,正如蒙培元所說,“中國儒家的正義倫理,用一個字表示,就是義”[12](4)。儒家之“義”,是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的標準和原則,是儒家的核心價值之一。“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易傳·乾卦·文言》),“利于他人、利于社會、即促進和實現他人和人民的正當利益者為義”[12](7)。概言之,關于孔子的分配之“義”,其外在表現是縮小貧富差距,內在目的則是保障人民的權利和利益,在這個意義上,它也是“民本”與“平等”的雙重體現。
那么,“分配正義”之“義”作為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的標準,其正當性又從何而來?關于“義”正當性的來源與依據,可以在孔子提出的內生道德正義中得到答案。在孔子的內生道德正義中,“和”之基在于人性,人性以“仁”為首。“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13](3279),“仁”是高于一切道德的“至德”,是“眾善之源”,具有終極性與本源性。也就是說,“義”為本源之“仁”一個方面的表現,“義”通過“仁”來界定,“義”的正當性通過“仁”來確證。因此,“分配正義”必須建立在人的內生道德之上才具有正當性,公平正義的根本最終需要追溯至普遍的本源之“仁”。此外,“仁”之人性還體現出平等的倫理意蘊,“固有之仁”存在于每個人的人性中,因此人性并無優劣等級之分,“人不僅在天性上是平等的,而且可以因為德行或德性而平等”[14](123)。人性平等是“現實”平等的形上根基,因為就實然層面而言,人與人之間必然存在著天賦、能力、地位等差異,但既然人性平等,從價值應然層面來看,每個人都應該得到平等對待和尊重。
概言之,“仁”與“義”的關系,或者說“道德之仁”與“分配正義”的內在關系可以如此來理解。其一,“仁”是“義”的本源,“義是從屬于仁的,儒家的正義原則,是在仁愛這個總原則之下的正義”[12](7)。在這個意義上,“道德之仁”是“分配正義”正當性的根基。其二,孔子對人性之“仁”的提出,是對人價值本質的重視,肯定人在價值應然層面上的“平等”。“對個體來說,人在價值層面的這種平等性,為其平等地獲得和接受發展資源提供了內在根據;從社會的層面看,這種平等性則構成了社會公正地分配個體發展所需資源的前提。”[11](259)
最后,孔子強調從“義”到“仁”的價值層面再回到“利”的工具層面。欲富貴而不欲貧賤,是人之常情,也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但是,“只能在正義原則之下求發展,絕不能以破壞正義原則的方式去發展”[12](7)。那么何為“正義之利”?這涉及儒家的“義利之辨”,簡言之,是在“仁”“義”本位之下的民本經濟之“利”。作為統治者,“以民為本”是利之底線,孔子認為具備內在仁德的統治者要保障人民生產自由、機會均等的權利;以“義”為標準制定合理的分配政策來縮小貧富差距。作為人民,“先義后利”(《論語·陽貨》)是利之原則,當道德與利益產生沖突時,要正確取舍,反對損害他人利益的逐利行為。更為重要的是,孔子要求逐利當以“人”為目的,人的追求不應該只停留在物質利益層面,而更應該追求精神上的“孔顏之樂”。
孔子強調在“仁”“義”道德本位之下追求財富,通過以“仁”為本源的道德正義緩解社會等級固化以保障民之平等,增進民之福祉,實現富國裕民;通過以“義”為內在根據的分配正義約束逐利欲望膨脹,防止“人的異化”,做到見利思義,維護社會和諧。當然,孔子也同樣認為民富之“安”可以進一步促進“仁”“義”道德的提升,化解社會矛盾,實現社會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