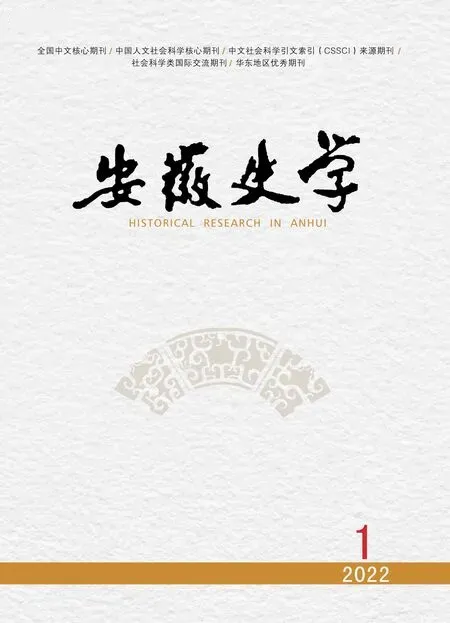辛亥革命后十年間的武漢社會
嚴昌洪
(華中師范大學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漢 430079)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人們在回顧建黨之初,即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時候,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湖北人為這個大會的成功召開作出了比較多的貢獻。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5位湖北籍人士:董必武、陳潭秋、李漢俊、劉仁靜和包惠僧。同時,李漢俊、董必武受大會委托起草了給共產國際的報告,總結了大會討論的主要問題。(1)中共湖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委員會編:《中國共產黨湖北歷史大事記(1919.5—1949.10)》,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頁。而且大會的主要會址就設在李書城、李漢俊兄弟在上海的寓所里,李漢俊還和李達承擔了會議的聯絡、籌備和會務工作。這一情況被視為中共“一大”上的“湖北現象”。
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應該在辛亥革命后十年間武漢地區的社會土壤中尋找。參加中共“一大”的5位湖北人,都是從辛亥革命首義之區走出來的。他們目睹了辛亥革命后十年間武漢地區乃至全國政局的動蕩、民生的凋敝,認識到辛亥革命由于其局限性,未能使國家實現真正的民主共和,更沒有讓廣大人民享受到自由幸福的生活,這些原本就是辛亥志士為之奮斗的、人民群眾為之期盼的革命目標。辛亥革命的經驗教訓,證明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走不通,于是,他們和許多先進的中國人一樣,在對辛亥革命的反思和對各種思潮的抉擇中探索著中國的前途和命運;進行各種各樣的嘗試,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終于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找到了中國的出路,即創立無產階級政黨,進行不同于辛亥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建立一個不同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新中國。
辛亥革命后十年間的武漢社會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縮影,董必武等人是中國早期共產黨人的代表,產生“湖北現象”的原因可以從一個地區、一個側面反映中共建黨的歷史背景。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有學者已經關注到“湖北現象”,并對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進行了簡單的分析;(2)王性初:《中共一大上的5位湖北人》,《黨史天地》2001年第7期。而對辛亥革命后的武漢社會變遷卻缺乏深入探討。筆者不揣淺陋,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辛亥革命后十年間武漢地區的社會演進作一系統考察,以期在深化中共建黨歷史背景的研究方面貢獻一點拙見。
一
1918年,一位作者從民國歷史的角度對民初政局進行了概述:“我國共和七載,變亂三次,時戰時和,循環不已,演成今日遍地荊棘,民不聊生,庫帑耗盡,國將不國之慘狀。”(3)林軒:《永久和平之芻言》,《漢口新聞報》1918年12月30日,劉望齡編著:《辛亥首義與時論思潮詳錄》下卷,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35頁。
武漢地區何嘗不是這樣,辛亥革命后十年間先是投靠了袁世凱的黎元洪當政,黎元洪被召上北京后,袁世凱的親信、皖系將領段祺瑞、段芝貴先后督鄂,然后是直系將領王占元統治湖北八年。在他們的統治下,武漢地區從無寧日。
1912年,武昌首義一周年到來前后,曾參加首義的人士紛紛回首一年來的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狀況,認為:“不圖民國成立,人民竟有‘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之苦。”(4)《時報》1912年4月1日,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頁。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是政治斗爭無有止息,黎元洪統治時期表現為如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黎元洪大失人望。此時的黎元洪已不是一年前被革命黨人擁戴上位的起義軍首領,而是獲得了民國大勛位、副總統、鄂軍都督、上將、參謀部長等崇高職位的權勢人物,其地位得到鞏固后,反動面目和野心終于暴露,為了將來能登上大總統的寶座,他厚植自己的勢力,籠絡順從其旨意者,打擊他眼中的叛逆者。他非革命黨出身,常對革命黨人有一種疑忌的心理。他利用孫武與他人的矛盾,拉一派,打一派,以殺戮敲逐為事。革命黨人慢慢認識了他的真面目,進行各種形式的反抗,他則借機殺人,竭力芟夷“不聽話”的起義有功人員。為鞏固其統治,在鎮壓反對他的首義軍人的同時,還壓制輿論,摧殘報業。不僅走了瑞澂的老路,強加“專取無政府主義,為亂黨秘密機關”的罪名(5)黎元洪:《上大總統并致京外各機關》(中華民國元年八月九日),易國干等編:《黎副總統政書》第13卷,上海古今圖書局1915年版,第5頁。,下令查封復刊的《大江報》,通緝何海鳴,抓捕殺害主筆凌大同,還派人查封國民黨人辦的《漢口民國日報》《震旦民報》。
革命黨人對袁、黎的“武器的批判”被黎元洪殘酷鎮壓,而針對袁、黎的“批判的武器”也被其封禁,武漢出現“萬馬齊喑”的局面。黎元洪擅殺功人的倒行逆施,使首義功臣人人自危,故有人哀嘆:兔死狗烹,鳥盡弓藏,“古今同慨”。曾參加文學社和辛亥革命的李六如1952年借給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一書寫序言的機會,總結教訓說:革命黨人“尤其錯誤的是,在起義時,盲目地臨時推戴僅有軍事聲望,毫無革命關系的黎元洪為都督,而又不抓住自己的革命領導權。因而黎上臺后,敢于起用大批舊軍官,靠攏憲政派,依附袁世凱,調轉頭來壓迫文學社,殺害社員祝制六、滕亞光等及日知會員宋錫全若干人,這都是文學社武昌首義的失敗教訓”。(6)李六如:《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2年版,第2頁。
其次是革命黨人被黎元洪分化,互相殘殺。武昌首義之時,面對清政府這一共同的敵人,為了實現“反滿”的共同目標,革命黨人能夠“有難同當”,“同心協力”,聯合作戰,創建奇功。但推翻了清廷,建立共和以后,他們卻不能“有福同享”,“和衷共濟”了。武漢革命黨人原本就有同盟會、共進會、文學社等團體之分,在組建革命政權時又有先來后到之別。文學社與共進會之間早已存在的芥蒂因內斗再添裂痕。孫武在主持軍務部期間,“攘功怙權,無所不至”,漸漸失去革命同志的支持,頗感處境孤立,遂投靠黎元洪,擁黎自重,黎元洪也希望在革命黨人中找到一個有力人物為己所用,兩者一拍即合。圍繞著反黎與擁黎,“首義三武”(即孫武、張振武、蔣翊武)之間又展開了新的矛盾與糾葛。革命黨人內部的矛盾為黎元洪所利用,他通過種種陰謀手段,挑撥離間,最終導致各個擊破。群英會事件后,迫使孫武去職,并借袁世凱之手殺害張振武,還擠走了蔣翊武,“首義三武”這一黎元洪實行專制統治路上的障礙就這樣被瓦解了。黎元洪擴大鎮壓范圍的倒行逆施,遭到更加激烈的反抗,以暴制暴、以殺止殺的結果是風潮、暴亂、暗殺無有止息,反黎組織“此仆彼繼,愈接愈厲”,社會豈有安寧可言。
第三是退伍軍人被黎元洪逼迫走投無路,頻繁鬧事。武昌首義后,在戰爭中陸續擴軍,增兵至八個鎮,加上各省援鄂部隊尚未撤離的人員,到1912年3月,黎元洪承認:“即以敝省計之,兵力幾逾十萬。”(7)黎元洪:《上大總統》(中華民國元年三月十九日),易國干等編:《黎副總統政書》第8卷,第15頁。大局粗安以后,這么多官兵實在難以安插,又由于帑項支絀,餉械供應難以為繼,只有裁軍了。經過幾次“倒孫(武)”“倒黎”風潮,黎元洪認識到具有反抗精神的軍人是對自己的威脅,于是借裁軍為名,對軍隊進行清洗,有危險性的首義老兵被強迫退伍,僅給“恩餉”一月,使得他們生活無著,人人自危,成為不安定因素,對黎元洪仇恨加深,對軍政府亦極其不滿。軍隊嘩變,時有發生。他們或者參與“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或者組織同志乞丐團,“擇因革命而致暴富者與前清貪污官吏之家,善求調劑衣食”。(8)《時報》1913年2月10日,《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第670頁。為了遏止軍隊反叛,黎元洪要求退伍士兵“速回鄉里”,“各歸本業”,否則予以相當之罪。但退伍軍人并不買賬,仍然日日鬧事,夜夜放槍,攪得社會不得安寧,人民無法休養生息。
可見,武昌起義后,雖說武漢三鎮所受戰爭創傷逐漸平復,但政治局勢動蕩不息,經濟生活每況愈下,社會秩序長期不寧,人民群眾所期盼的革命后的民主、共和、幸福、自由終未實現,其切膚感受是起義“周年以來,無一善政”,就是二年、三年以后,仍無改善。
黎元洪懾于湖北倒黎風潮,大量裁撤首義軍人,保留下來的人員也覺得不可靠,“殊不足恃”。如此一來,他想在武漢戒嚴,軍隊顯得不足分布,希望袁世凱派兵前來鎮懾革命黨人。而袁世凱面臨南方革命黨人將欲興師問罪,也急于派兵南下,“未雨綢繆”。于是,兩人在利用北洋軍對付南方革命勢力上取得一致,黎元洪電請袁世凱派兵來武漢“震懾”,袁世凱便命駐扎信陽的李純部聽候黎元洪節制調遣。此后,北洋軍浩浩蕩蕩地向湖北開來。
“二次革命”爆發后,根據袁世凱的命令,黎元洪派兵參與攻打江西李烈鈞革命軍,大肆鎮壓湖北革命黨人的討袁軍事行動,使得“二次革命”在辛亥革命的發源地湖北、武漢,未能像江西、江蘇、安徽、湖南、重慶等地那樣上演有聲有色的活劇。相反地,袁世凱乘鎮壓“二次革命”之機,調派大批北洋軍進入湖北,在首義之地建立起北洋軍閥的統治。待到鎮壓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凱再次敦促黎元洪到京,以便分擔政府違法操作的責任。1913年12月8日,派陸軍總長段祺瑞親自來鄂迎接,黎元洪再也不能遲遲其行了,只得離鄂北上。12月10日,袁世凱發布大總統令:“兼領湖北都督事黎元洪呈請因公來京,請派員代理等語。著段祺瑞暫兼代領湖北都督事,此令。”(9)《時報》1913年12月12日,《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第715頁。
段祺瑞以陸軍總長兼任湖北都督后,安插親信十余人在府辦公。自民政長至各觀察使,均加以更換。12月12日,袁世凱準黎元洪親信、署湖北民政長饒漢祥辭職,以段祺瑞之舊友、袁世凱之姻婭呂調元繼任。呂接任后,延攬前清官員,無論科甲捐班出身,均蒙任用。舊官僚聞信趕至者日漸增加。而呂調元又由直、皖、汴調來數員,均系前清科甲出身并曾與呂調元有寅年鄉友之誼者。而昔日革命有功人員多被擯棄于公門之外。于是,一切政治似乎盡復前清之舊。如,民政長出署,仍乘綠呢大轎。拜會投刺,一律照舊,用大紅手本。出則頂馬在前,跟隨在后,幾如前清儀制。舊官僚則紛紛來鄂,希圖起用,大事運動,攀同鄉,認門生,絡繹不絕。因軍民兩政長皆系皖籍,所有撤換改派人員,又以安徽人居多,故當時有改湖北省為安徽省之譏,竟有好事者,寫出打油詩,分貼軍民兩府照壁之上。其一云:“二黃(黎公黃陂、饒公黃梅)唱罷又徽腔,果是官場即戲場。又是一翻新角色,軍民兩府拜同鄉。”其二云:“半赴燕京半赴湘(指武昌起義人),前途各自覓同鄉。偉人從此無消息,到處紛紛鬧出洋”云云。(10)姜泣群:《朝野新譚己編·官署壁上打油詩》,宋傳銀編:《筆記小說武漢資料輯錄》第1冊,武漢出版社2018年版,第167頁。
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歷來如此。更讓時人不能接受的是,將“起義門”又改回原名“中和門”。武漢為首義之區,革命精神、共和觀念深入人心。段祺瑞來鄂時,袁世凱密授方略,要改變湖北人革命心理。因為袁世凱自己有一潛在心理,即最惡人談“武昌起義”四字,常謂起義即是“造反”,如人人以造反為起義,則天下將無寧日。另一心理,謂共和系其誘獲于清室,鄂人何功之有?常對人說:“華甫(馮國璋字)攻下漢陽,宋卿(黎元洪字)已逃往洪山,我如不密電阻攻武昌,黎已被俘,都督何來?若云贊助共和,則菊人(徐世昌號)方足以云有功,我亦不敢自居。”(11)吳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6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7頁。意即說武昌起義不值得紀念。段祺瑞來鄂后,面飭警察廳長將武昌起義、聚義二門仍改為中和、通湘門。教育司長時象晉質問改城門理由時,段祺瑞答稱:“辛亥武昌起義,為歷史上所不可滅。……惟以中和門、通湘門改名為起義門、聚義門,竊以為不妥。查通湘門無非因起義諸君居其附近而改名,中和門則因炮隊由此入城而改名。實起義之功不僅由于居近通湘門之二三子及斬關而入之炮隊也。今以二城門為標榜,致軍民腦筋易起浮動觀念,所以南湖馬隊之亂、改進團之亂,均系攻撲此二門以求勝利。而年來功人之放縱,軍隊之驕蹇,令鄂中時呈亂象,亦未始非旌獎過甚有以致之。”(12)《時報》1913年11月26日,《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第718頁。翌年接任都督的段芝貴,更下令將起義門城樓建筑拆毀,僅剩下城門拱洞與斷壁。“二段”改掉起義門名字,就是要否定武昌首義之功,消泯黨人的革命精神。有學者說得好:“這兩座城門名字的改過來又改回去,形象地標志著辛亥革命在湖北的勝利和失敗。”(13)吳劍杰:《辛亥革命在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頁。
段芝貴來鄂,下車伊始即對輿論示威,凡稍帶民黨色彩的報紙,即予封禁。1914年3月14日,他首拿辛亥革命中創辦的以敢言著稱的《大漢報》開刀,派軍警圍抄,并逮捕經理胡石庵等14人,押于軍法局。胡石庵受迫害最重,因為他不止牽涉“黨人”問題,而且因在報上揭發段的隱私,為段所忌。先是,袁世凱之子袁克定來漢,在漢口怡園觀劇,喜慕名伶王克琴的才藝姿色,段芝貴知道后兩次私訪王克琴,欲重演其清末在天津買歌妓楊翠喜獻與貝子載振謀官的故伎,獻于袁克定。事為《大漢報》揭露,段芝貴遂惱羞成怒,對胡石庵刑訊慘毒,時人莫不為之喊冤。而《大漢報》編輯余慈舫,“筆鋒甚健,而性極剛烈,嫉惡如仇,言論犀利”,也被段芝貴逮入軍獄,于8月14日殺害于漢口滿春園。凌大同之后,報人被殺,此為第二次。
王占元統治湖北八年,更是臭名昭著,引起湖北人民的驅王運動。王占元向袁世凱表示“忠誠”,袁世凱稱帝期間,王占元等北洋將領通電討伐唐繼堯,王被袁世凱改封“襄武將軍”,督理湖北軍務。1916年1月10日,王占元等借宜昌在神龕山洞發現龍骨化石之機,編造離奇神話,向袁世凱獻媚說:“當此一德龍興之日,肇造萬里磐石之機”,“天眷民佑,感應昭然”,正是稱帝開國的祥瑞,電請袁世凱早登大寶。(14)涂文學主編:《武漢通史·中華民國卷(上)》,武漢出版社2006版,第25頁。洪憲帝制失敗后,黎元洪任命王占元為湖北督軍。王上任后操縱湖北省政,以圖長期控制湖北的軍政大權,先保薦督署參謀長何佩瑢為湖北省長,后又保薦其親家孫振家接任省長。遭到反對后,北京方面任命夏壽康為湖北省長,王占元竟以武力威脅,使夏壽康不安于位。他還玩弄軍權,仇視革命,將鄂軍大量裁撤,只留下劉佐龍一個混成協。他嗜財好貨,貪得無厭,用擁兵敲詐、克扣軍餉、搜刮民財、擾亂金融等手段,搜刮了近4000萬銀元入自己私囊,在北方各大城市購置房地產,投資紗廠、煤礦、面粉廠、電力公司等,成為北洋軍閥中最大的富翁。(15)吳自強:《北洋軍閥把持下的湖北政局》,《武漢文史資料》1990年第3、4輯合刊,第80—81頁。
王占元裁軍而克扣軍餉引起兵變。1921年的“五·二兵變” 給武昌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公私財產損失5000萬元以上,打死57人,300余戶房屋被焚。次日,王占元竟下令將嘩變官兵大部誘殺。武漢兵變前后,還有宜昌、沙市兵變。消息傳出,國際、國內輿論一片嘩然,武漢人民深感荼毒之痛,甚至有“不仰托于外人之保護,則愿舉族投江以求死所為樂”(16)彭洪鑄:《湘鄂川鄂戰爭紀略》,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7輯,第89頁。之語。武昌兵變的結局,再次證實了王占元之“殘暴貪鄙”。
王占元在湖北的殘暴統治,鄂人苦之,屢求北京政府罷免王占元。驅王運動迅猛高漲,驅王人士宣布王占元“吞沒軍餉,激成變亂”“摧殘教育,戮辱學生”等十七條罪狀。驅王民軍紛紛組織起來,通電驅王,實行獨立。而政府恃有武力而以全力保王,驅王人士不得已赴湘請兵協助驅王。1921年7月20日,在“倒王運動”主持人李書城等聯絡下,湖南督軍趙恒惕任援鄂總司令,以湘軍兩個師由岳州進攻湖北。吳佩孚表面應王占元之請令第二十五師師長蕭耀南為援鄂總司令率兵入湘。然蕭耀南“援鄂不援王”,率軍抵漢口后,不再前進,坐山觀斗,準備鵲巢鳩占,聯合湘軍趕王占元下臺。在此情形下,至8月初,王占元所屬兵力已消滅殆盡,遂通電辭職。蕭耀南部立即入駐武昌。王占元攜帶他在湖北搜刮的大批財物逃往天津。
縱觀辛亥革命后十年的武漢社會,辛亥志士拋頭顱、灑熱血所追求的國家民主共和,人民自由幸福終成泡影,誠如胡石庵在1917年所言:
因循歲月,至于今日,政局之敷衍如故,仕途之淆雜如故,疆吏之跋扈如故,南北之水火如故。所謂共和之偉人,多亡清之庸臣,執政之巨子,半帝制之元兇。議會也而贅旒視之,志士也而籠鳥畜之。極目各界奔競于要津者,非奴隸犬馬吮癰舐痔之徒,即長奸逢惡小信偽忠之輩,以革命為謀利之幟,借黨派為終南之徑。一三賢俊之士,不甘比周自污,相率高蹈遠引,入山已深,且復去國。嗚呼,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循是不變,必至氣節日頹,廉恥日喪,豺狼當道,狐鼠憑陵。人心既壞,人格愈卑,四維不張,九法盡斁,欲求終免傾覆,蓋萬難矣。(17)胡石庵:《上黎大總統書》,劉望齡編著:《辛亥首義與時論思潮詳錄》下卷,第723頁。
為了挽救時局,為了尋求中國的出路,有識之士遂開始了探索的征程。
二
南北戰爭和隨后無止境的政治爭斗,使民國初年武漢經濟受到巨大創傷。馮國璋一把火燒了三天三夜,把繁華的漢口市場化為一堆瓦礫。南北戰事平息后,省內局勢又因政府的腐敗和內斗而持續動蕩不安,資本家均不敢卷土重來,以致漢口商業一蹶不振。據1913年1月10日《時報》報道,由于金融業無大資本,影響所及,“百業停滯,商務衰敗”,“市房住宅,關空累累”。(18)《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第605頁。省城文武官員、在公人等,為了維持大局,紛紛參與種種經營,而一些民國新貴則乘機插手戲院、客棧、番菜館等營業,甚至明目張膽開設花酒樓等不正當行業。
黎元洪當政時期,實業司一再換人,被媒體稱為“尸位素餐,罔知振作”。該司附屬機關二十余處,月支經費十余萬元,但均不能為湖北開辟財源。該司所經營的工礦業,均是虧損。工礦業虧折,商業蕭條,造成的后果是國家稅和地方稅兩種稅收都不夠旺。軍政府只好加印紙幣,紙幣又大多用于“維穩”,即鎮壓各種“叛亂”,于是市面通貨膨脹,兌換基金空虛,造成銅元紙幣和洋銀折合的價值日益低落,物價飛速上漲,人民生活困難;工商業受紙幣低落的影響,大多無法維持下去,金融愈見紊亂,市場愈見蕭條,官錢局也弄得無所措手,連政府的辦公經費也難以照常支給。最后只得學清政府搞橫征暴斂。武昌起義后本來宣布鏟除前清一切惡稅、陋規,后來許多地方陋規不收了,但將陋規變成了正稅,“于滿清薄稅之名亦不能保存”(19)《時報》1913年5月23日,《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第607頁。,故媒體報道稱:“鄂省政權近年為黨人所把持,橫征暴斂有甚于前清官僚。”(20)《時報》1913年12月20日,《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第716頁。
經濟不景氣帶來的另一后果是謀生機會減少,失業者增多。從前居民失業,還可以通過投軍找到衣食來源,因為每月有幾元錢的餉金,尚不覺得困頓,后來軍隊裁汰大半,擴大了失業隊伍,“武漢失業者,至此遂陷絕地”。失業軍人沒有辦法,組織同志乞丐團,去民國新貴家強索衣食,而街衢之中老少乞丐則到處追逐行人,哀求施舍。革命后,“幸福未見絲毫,惟睹滿目餓殍”。
李四光有鑒于受戰爭破壞和政局動蕩嚴重影響的武漢地區之慘景,于1912年6月在《湖北農林會報發刊詞》中指出了當時全國的亂象:“試問民國今日,其危險現象,果視滿清時代有減分毫乎?人民猶是其顓頑,社會猶是其腐敗,且各省繁富之區,萃數十百年來之精華,焚掠以盡,市井蕭條,流亡載道,農輟象耕,婦休蠶織……嗟我農夫,胼手胝足而猶窮困,靡知所屆不已,大可哀乎!”(21)李四光:《湖北農林會報發刊詞》,劉望齡編著:《辛亥首義與時論思潮詳錄》下卷,第449頁。
黎元洪統治下的湖北是如此,“二段”督鄂時湖北財政亦極其支絀。當道遵照中央政策,于舊稅則力圖規復,新稅則切實進行。媒體報道,自呂調元任省長、王茂卿任廳長以來,“各處厘捐局卡之于起義后認為重征繁苛裁撤蠲免者,現皆逐漸復設。而新稅之中,驗契稅、印花稅、房稅辦理亦有成效,較前本省人柄政時代每月約增進款十余萬元。無如月須認解中央政費至三四十萬之多,以致財用視上年尤為不足。而襄河各屬近又受匪黨影響,于稅收大有妨礙。當道籌思至再,無可如何。遂擬獨加重漢口商民負擔,將各項捐稅盡施之于漢口。”(22)《時報》1914年5月1日,《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第608頁。他們在漢口增加的捐稅有革命時裁撤而現時重又規復的鋪捐、房捐、妓捐、屠宰捐等等,還準備開辦“九九商捐”。
王占元的貪婪比前任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蹂躪湖北八年,“喝兵血”“貪公款”“調售銅元”“壟斷軍服”、設立“信城公司(售皮貨)”“霸占良田”等,無所不用其極,“而鄂省財政則完全陷入危機”,所有實業、教育、行政、司法各業皆停頓。這引起了鄂省紳商的極度不滿,鄂人對王切齒痛恨。(23)郭劍林主編:《北洋政府簡史》(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46頁。以致武昌總商會在致政府的電文中憤怒指出:“王所部軍隊,搶劫我財產,殺戮我人民,我人民希望官吏保護之心至此已絕。”(24)《武昌劫后之官民兩面觀》,《晨報》1921年6月13日,郭劍林主編:《北洋政府簡史》(下),第749頁。
造成武漢民生凋敝的還有列強的經濟侵略。1917年2月28日湖北旅京學會在北京創辦的《楚寶》雜志,刊載《外人在湖北內地通商勢力最近調查表》,并加按語指出,通商實為一種手腕最辣,效力最強,結果最慘的“滅國新法”之指南針、導火線,著實“可畏”。(25)劉望齡編著:《辛亥首義與時論思潮詳錄》下卷,第484、730頁。正是這種 “滅國新法”,破壞了武漢的經濟活動,對民眾無聲的盤剝,加劇了民生的艱辛。所以,要改變人民的苦難,在鏟除軍閥的同時,還要打倒列強。
為了喚醒民眾,引導民眾從苦難深淵中走出來,仁人志士開始了艱難的探尋之路。
三
辛亥革命后的十年,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階段。雖然政局動蕩不已,民生凋敝不堪,但由于社會的緩慢進步,各種社會思潮得以在此傳播,并不斷演進著,而這些思潮多半是以報刊為載體,以學校為傳播源的,而有些學校甚至成為傳播新文化、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據點和與反動勢力作斗爭的重要陣地。
這一時期武漢地區報刊與教育的發展迅猛。筆者根據各種資料做了一個不完全的統計,1912—1921年,除了在清末和武昌首義期間已創刊的有關報刊外,武漢地區新出版發行的報刊多達120余家。為什么這個時期武漢地區媒體如此發達?
一是民國建立以后,《約法》規定,共和制度下,“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因此報界就成為許多人都想插一腳的地方,不僅革命派大辦革命報刊,商報也越來越多,“甚至販夫走卒亦以辦一日之報為樂,三家村冬烘先生亦欲做一夕主筆以為榮”(26)阿真:《言論界之悲觀》,《天聲報》1916年10月17日,劉望齡編著:《辛亥首義與時論思潮詳錄》下卷,第675頁。,各種休閑小報和短命報刊也不在少數。新式學堂的學生將辦報作為一種就業渠道,也使報人與報紙與日俱增,言論機關發達的狀態猶如雨后春筍,不斷從武漢社會破土而出,數量之多,令人矚目。
二是民國初年的所謂“政黨政治”,造就了政團、黨派林立的局面,多數政黨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宣傳自己的學說主張,批駁政敵對自己的攻訐,往往要創辦本黨的言論機關,有的甚至不止一家,以便牢牢地把握話語權。黨派斗爭催生了報界的“熱鬧”。雖然黎元洪和“二段”為了鞏固獨裁統治,都干過封報館、捕記者的勾當,使輿論消沉于一時,“二次革命”失敗和袁世凱專制獨裁時期,武漢報刊甚至出現“閉館風潮”(27)唐惠虎、朱英主編:《武漢近代新聞史》上卷,武漢出版社2012年版,第300頁。,但是,由于革命報人堅忍不拔的斗爭精神,在袁氏倒臺后,乘北京政府逐步改變言論控制政策之機(28)1916年6月17日《盛京時報》稱:黎大總統尊重言論,對于報館“取寬大主義,除其最極端激烈、妨害治安者外,毫不加以干涉,以示尊重言論自由”。轉引自唐惠虎、朱英主編:《武漢近代新聞史》上卷,第316頁。,把被查封的報紙重新復刊,而且新辦的報刊也越來越多,武漢地區報刊漸呈復興之勢,報刊數量增加不少。
三是武漢作為首義名區,九省通衢的大都會,這里的一舉一動,足以聳動中外視聽。連湖南人想把輿論宣傳做大做強,也選擇武漢為辦報之地。湖南歸國留學生曾毅、楊端六、周覽、李劍農等為了發揮平民政治之真精神,造成健全輿論,從長沙攜款到武漢籌辦《漢口民國日報》。他們在出版廣告中解釋說:“我國報紙向集中于上海,然滬瀆僻處東海,以地勢論實不及漢口之適中,將來各處干線告成,漢口為全國交通之中心點,必成為第二之倫敦、紐約。不有大報,文明曷由灌輸。本報之出現,冀借漢口為舞臺,以樹言論界之重鎮。”(29)劉望齡編著:《辛亥首義與時論思潮詳錄》下卷,第436頁。這就是說,他們看到漢口不僅有區位優勢,而且市面大,適合于報紙的發展。無獨有偶,湖南都督譚延闿也曾委派湘人在漢發刊《共和日報》,期與《大漢報》《大江報》結為一“聯合壁壘”,作為革命派的言論機關,也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可見當時人們認為,要想在行動上做一番大事業,在言論上產生大影響,在武漢辦報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四是漢口有五國租界,租界當局除了允許本國僑民辦商業報刊和傳教刊物外,對于華人在租界辦報也本著“言論自由”觀念而持寬容態度,加上中國政府的權力難以到達租界,因此許多反政府報刊的報館多設在租界內。誠然,租界當局有時會應中國政府的要求協同查封報館,但這種情況比較少,多數時候是報館借租界的庇護而倡言無忌。所以武漢報人常常到租界辦報。
此外,民國初年,新的政府機構各自辦有出版物;由于教育的發展,部分高校甚至中學辦有校刊、學報或專業刊物。這么多報刊,既是辛亥革命后十年間各種社會思潮的載體,同時也為社會思潮的傳播與演進推波助瀾。
至于教育方面,這一時期武漢地區的學校教育在艱難中有所發展。1912年和1919年的教育改革促進傳統教育向近代教育轉型,為學校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因此,辛亥革命后十年間,在晚清張之洞主持創辦的新式學堂和教會學校的基礎上,小學、中學數量有所增加,一時私立中學勃興。
1912年起,新建了湖北省立第一中學和省立二中、三中。1917年,又設省立一女中。1918年,接管了德國人辦的德華學校,改為省立漢口中學。1920年,董必武開辦私立武漢中學,陳潭秋、錢亦石開辦私立共進中學。吳德峰建立了崇實中學。1921年,武漢三鎮中學增至35所(公立6所,私立23所,教會6所)。
高等教育也有所發展。1912年黃陂人陳宣愷、陳時父子捐家貲創辦的中華大學,被視為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黃興、宋教仁則創建了江漢大學,“借江漢之炳靈,留中華之紀念”;(30)宋教仁:《江漢大學之前途》,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31頁。1913年,北洋政府以方言學堂為基礎,建立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女子師范學校等;教會大學文華大學在1911—1912年辛亥革命期間關閉數月,復課后也有所發展,到1915年已可頒授碩士學位了。1920年,韋棣華、沈祖榮創辦了文華大學圖書科(又稱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開中國圖書館學高等教育之先河。
這些學校,在辛亥革命開啟的思想解放潮流里,辦學理念有所提升,辦學條件有所改善,課程設置更兼中西,尤其是采取開門辦學模式,即聘請有新思想、新知識的學者來校任教,延請中外名流到校講學,如,陳獨秀、杜威等先后到武漢高校演講。他們精彩的演講開闊了教師們的視野,充實了學生們的頭腦。武漢的中學和高校,傳承著中國傳統文化,也傳播了西方的近代文化,新舊文化、東西文化在此交匯,如,1915年5月1日創刊的中華大學《光華學報》,是長江中下游鼓吹新文化的重要陣地,中華大學和華中大學則是武漢學生運動的重要據點。新文化運動各種新的思潮以及馬克思主義得以廣泛傳播,并通過學生傳播到社會,為武漢地區早期共產黨組織的建立提供了思想理論基礎。
四
辛亥革命后十年間,革命帶來了民族資產階級地位的提高,“實業救國”思潮也盛行一時,加以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列強無暇東顧,對華商品輸出和資本投入減少,于是,中國民族工商業得到一次短暫的發展機遇。在中國民族工商業重鎮之一的武漢,一批愛國的工商界人士,致力于辦廠興業,在一批老、舊企業發展壯大的同時,一批新興的近代企業應運而生,大量手工作坊也轉化為近代工廠。這些民族工業加上外資企業、官辦企業,武漢工商業發展形成一定規模,導致的結果,一是民族資產階級人數增加,社會地位進一步提高;二是無產階級隊伍逐漸壯大,并開始了自發的斗爭。
清末,武漢三鎮的工廠“使用職工數不下三萬人。特別是百貨集中地的漢口……苦力據說達九、十萬人”。(31)《清國事情》第1輯,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2頁。到1912年,僅紡織工人就達10827人。到1920年,全省工礦企業達1000處以上,武漢即達600余家,全省近代產業工人接近30萬,其中武漢地區就有10余萬,位居全國第二。(32)③《中國共產黨湖北歷史大事記(1919.5—1949.10)》,第2、9頁。
這么多工人,在軍閥、官僚和資本家的壓迫剝削下,過著牛馬般的生活。《少年世界》第1卷第6期發表了王崇植撰寫的《武漢工廠紀略》,記述漢陽鐵廠、大冶礦廠、大冶鋼鐵廠、漢口揚子機器有限公司、諶家磯造紙廠、湖北兵工廠、湖北水泥廠、武昌電話局、武昌無線電臺的設備和生產情形,同時也反映了工人工資和勞動的一些情況,披露了工人所處的“處處足以喪人性命”的勞動環境和如陷“人世間的三十六層地獄”的悲慘生活。(33)③《中國共產黨湖北歷史大事記(1919.5—1949.10)》,第2、9頁。
于是,為了增加工資,反對剝削的自發斗爭,在辛亥革命后十年間,此起彼伏。如,1913年6月,漢陽兵工廠工人反對總辦劉慶恩在發工資時以貶值的銀元紙幣與銅元官票對成搭發,要求全發官票,黎元洪借口“共體時艱”加以拒絕,于是全廠工人舉行罷工,以作抗議。其他工廠工人準備以同盟罷工予以支援,“工人聯合聲勢日甚”的情況迫使黎元洪將劉慶恩撤職,工人才開始復工。經過這次斗爭,工人們進一步團結起來,組織工業同盟會,準備迎接新的斗爭。1919年2月25日,漢口揚子機器廠工人罷工,反對廠方制定工人必須繳納50兩銀元作保的規定,并搗毀部分廠房、設備。王占元遣兵鎮壓,雙方發生激烈沖突。工人、兵士均有死傷。3月5日,業主與工人經協商,恢復生產。
五四運動中,工人的斗爭顯示出他們也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武漢學生響應北京五四運動,向反動政府發起挑戰,王占元竟實行武力鎮壓,造成“六·一”慘案。6月11日,武漢各輪船公司和武漢造幣廠、武昌五局、模范大工廠等廠的工人也醞釀舉行同盟罷工,人力車工人六七千人也商議舉行罷工。盡管在湖北當局和資本家的嚴密監控下,同盟罷工未能發動起來,但各行業工人的罷工斗爭還是不斷發生。這些斗爭使工人階級受到鍛煉,并引起正在向馬克思主義轉變的先進知識分子的注意。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武昌工學互助團發起人之一梁空撰寫的《武漢工廠調查》一文在《少年世界》第1卷第2期(1920年)發表,介紹了一些工廠的沿革和工人罷工情形,為武漢地區五四運動后先進知識分子初步了解工人階級狀況的首次調查報告。惲代英、施洋、李書渠、包惠僧等發起組織的湖北平民教育社和董必武、陳學渭、宛希儼等組織的進步學生讀書團體人社,以及稍后建立的湖北職業教育研究社,都開展社會教育,開辦多處平民學校或工讀學校,以工人、農民、城市貧民及其子女為主要對象進行義務教育,幫助工人和其他勞動群眾學習自身求解放的道理,使馬克思主義開始同湖北工人運動結合起來。文華大學校工鄭凱卿在陳獨秀指導下,組織文華大學學生對武昌工人狀況進行調查,他們編制的《武昌五局工人狀況表》由陳獨秀發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1號上。該刊同期所載劉云生《漢口苦力狀況》一文,詳細敘述了漢口碼頭搬運工人的來源、苦難生活狀況和致死原因,指出他們“若異類之不如”,“所受之痛苦,實人生之最難堪者”。這些調查活動和社會教育活動,使學生運動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組織在湖北的創建奠定了階級基礎。
五
近代以來,仁人志士為了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現狀,探索著各種救亡之路,做著各種強國之夢,進行了多次奮斗,然而都失敗了,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也很不徹底,封建文化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并未清除,民國初年不僅出現袁世凱帝制自為、張勛擁遜帝復辟、軍閥割據與混戰的短暫歷史倒退,而且封建文化的幽靈再度游蕩,尊孔讀經、祀孔祭天、鬼神迷信、宗法禮教、節烈觀念、復行大人老爺名稱……一時搞得烏煙瘴氣。辛亥革命后十年間武漢的社會現實,從一個地區反映了國家的情況一天比一天壞,動蕩的政局和凋敝的民生,使得人們生活不下去了,刺激著先進的人們從西方思想武庫中搬來各種兵器,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到激進民主主義,從無政府主義到空想社會主義,從新村主義到工讀互助主義,從地方主義到聯邦主義……都進行實驗,各種思潮此消彼長,互相激蕩,但都未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曾經留戀過別的東西的人們,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覺悟過來了,有些人正在換腦筋。”(34)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61頁。
為了尋找到改造中國的道路,先進的人們進行了艱難的探索。在探索過程中,五四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給了探索者很重要啟發。
武漢高校師生初步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是在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應邀來漢演講后。1920年2月上旬,陳獨秀應邀在文華大學、武漢高等師范學校等講演社會改良方法,宣傳馬克思主義。其演講受到聽眾熱烈歡迎,卻嚇著了湖北官廳,他們以為中國最高學校之文科學長,乃有此鼓吹社會共產主義之論調,應予取締,迫使漢口青年會取消此前約定的陳獨秀講演會,令其速離武漢。(35)《陳獨秀在鄂演講之經過》,《申報》1920年2月15日。
通過對俄國革命的了解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通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武漢地區一批先進青年李漢俊、董必武、惲代英、林育南、陳潭秋、施洋、黃負生、蕭楚女等逐步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成為中共早期黨員。
筆者比較了董必武等創立的湖北早期共產黨組織和惲代英等創立的共存社的名單,發現兩個名單并不重合。1920年9月成立的中共湖北早期組織成員是董必武、劉伯垂、包惠僧、陳潭秋、張國恩、鄭凱卿、趙子健、趙子俊8人。1921年7月16日從漢口到黃岡浚新小學開會成立的具有共產主義小組性質的共存社的人員有吳景鐘、唐際盛、李求實、盧斌(陸沉)、林育南、林育英、漢儒、浚孫、鄭遵芳、鄭興煥、龔士希、易禮容、克友、鎮山、惲代英、李書渠(李伯剛)、冼百言(冼震)、行健、沈光耀、林洛甫、劉光起、劉茂祥、盧春山、廖煥星。(36)于麗、田子渝:《共存社:創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最早團體》,《湖北文史》2021年第1期。2020年10月20日在武漢召開的紀念中國共產黨湖北早期組織成立10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與會專家認為,在湖北地區先后建立的兩個共產主義組織,“路徑不同,殊途同歸”(37)周志兵等:《湖北是中國共產黨組織的重要發祥地》,《湖北日報》2020年10月21日,第2版。,筆者認為這一看法是實事求是的。
路徑怎樣不同?
董必武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路程并不平坦。他參加過辛亥革命,在辛亥以后仍堅持民主主義,并為尋找救國之路而四處奔波。1919年2月,他與原同盟會員張國恩為鄂西靖國軍總司令蔡濟民伸冤事來到上海,通過詹大悲認識了由日本回國的湖北潛江人李漢俊,李漢俊向他們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和蘇俄的情況,并推薦一些馬克思主義書籍和進步雜志給他們看。受到啟發的董必武對辛亥革命進行了反思,“逐漸了解到俄國革命中列寧黨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與孫中山先生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國民黨一套舊的搞軍事政變的革命方法,行不通了,應該改為一種能喚醒群眾,接近群眾的方法”。(38)董必武:《私立武漢中學簡記》,《董必武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3頁。李漢俊還與他們在一起分析、比較俄中兩國革命成敗的經驗教訓,董必武初步作出了信仰馬克思主義、走俄國十月革命道路的抉擇。以后董必武一直稱李漢俊為“我的馬克思主義的老師”。返漢后,他即開始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組織工作。(39)中共武漢市委黨史研究室等編:《中國共產黨武漢歷史圖志》,武漢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頁。
董必武等人認識到中國革命要采取能喚醒群眾、接近群眾的方法,即辦報紙和辦學校。辦報紙因故未果,他們便從辦中學開始,然后徐圖擴充。1920年4月,私立武漢中學正式開學,學生男女兼收,提倡白話文。董必武主持校務,親自定校訓為“樸、誠、勇、毅”。工作有了一些起色后,早期共產黨組織從幾個渠道聯系他們,動員他們創建武漢的共產黨組織。陳獨秀也發展了湖北人劉伯垂為共產黨員,并委托他回武漢找到鄭凱卿和包惠僧,讓他們共同參與武漢黨組織的籌建工作。他還聯系上董必武,并與李漢俊介紹董必武入黨。這年秋季,董必武、劉伯垂、包惠僧、陳潭秋、張國恩、鄭凱卿、趙子健等聚集在董必武、張國恩寓所,大家對組黨問題取得一致意見后,正式成立了武漢早期共產黨組織,包惠僧為負責人,陳潭秋分管組織工作,張國恩分管財務。
他們為什么沒有吸收惲代英和利群書社成員參加武漢早期共產黨組織呢?當時,各地的早期黨組織成立不久,對于吸收黨員非常慎重。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曾寫信給包惠僧,要他們吸收惲代英及他領導的利群書店的分子。包惠僧在回憶錄里稱:“我去訪問過他們,也同惲代英談過,李書渠、廖煥星、蘆斌(陸沉)、林育南等,我和劉伯垂、陳潭秋都直接同他們接觸過。但他們此刻熱中搞新農村運動、辦書店,注意個人進修,一個一個都像清教徒似地不容易使人接近。我們認為惲代英及利群書店的分子是小心小眼、小手小腳、不滿意現狀,又怕革命,沒有出息,就放棄了。李漢俊來武昌,也到利群書店談過,馬邁耶夫來武昌也到利群書店參觀過,終沒有同他們聯系上。”(40)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后》,《一大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頁。其實,這里有包惠僧的偏見在作祟。據陳潭秋的回憶,在一大上有一種極“左”的觀點,以劉仁靜為首,認為一切知識分子都為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表者,應該拒絕知識分子入黨,“同情他的觀點的有包惠僧”。(41)陳潭秋:《回憶黨的一大》,《一大回憶錄》,第9頁。可見,包惠僧是以“左”的眼光看待惲代英們的所作所為,從心里排斥他們,而不是團結他們。好在惲代英們自己從實踐中覺悟了,放棄了空想社會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
惲代英曾經將無政府主義視為救國救民的真理而進行過“細心的研究”。1913年他進入中華大學預科,開始接觸無政府主義。后來,通過鉆研國外“安那其主義”理論,對無政府主義的前途十分樂觀,認為經過持久不懈的教育,改變謬誤之學說和一般人道德心的薄弱,發明真理,培養民德,就能不待革命即可推翻代表富人、貴人階級的政府,破壞天下事攘之泉源,且為不合自然法則的階級界限。1917年,他結合了一批同樣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同道,組織互助社,實驗新村主義和工讀互助主義等空想社會主義。他曾和互助社成員一起討論過新村的設想,并籌備在林育南的家鄉黃岡回龍山八斗灣恢復浚新學校,作為新村的基地,試圖“以鄉村的共同生活為我們解決自己問題的重要一步……我們盼望這樣便可以全然共產,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而且靠這種共同生活的擴張,把全世界變為社會主義的天國”。(42)惲代英:《未來之夢》,《惲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頁。1919年11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文章,批評惲代英在《未來之夢》中的觀點,指出:“在全社會底一種經濟組織、生產制度未推翻以前,一個人或一團體決沒有單獨改造底余地,試問福利耶以來的新村運動,像北京工讀互助團及惲君的《未來之夢》等類,是否真是癡人說夢?”(43)陳獨秀:《獨秀復東蓀先生底信》(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4號。陳獨秀的尖銳批評使惲代英及利群書社社員受到極大震動。惲代英們的空想社會主義實驗雖然都失敗了,但它是這些先進青年走上科學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
1920年2月1日惲代英和林育南等以互助社等團體為基礎創辦了利群書社,經銷各種新思潮書刊,并先后同新青年雜志社、長沙文化書社建立了密切聯系,成為《新青年》在武漢的代派處。他們如饑似渴地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乃有所覺悟,逐漸拋棄社會達爾文主義、新村主義、工讀互助主義等西方思潮的影響。惲代英也對辛亥革命進行反思,對辛亥革命后軍閥當政的現實非常不滿,認為拯救國家,不能靠軍閥政客野心家,因為他們“擁兵自重,使國家法紀蕩然”,“廉恥蕩喪,綱紀無存”,所以他在1920年中華民國九年的國慶紀念日(也是辛亥革命9周年紀念)發表文章宣稱:中國現在仍需要革命。并且他在馬克思主義初步傳播到中國之后,接受其影響,走上了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就在這年秋天,陳獨秀委托惲代英翻譯考茨基的《階級斗爭》一書,翌年1月由新青年社作為新青年叢書第8種正式出版。此書對惲代英和利群書社的成員從空想社會主義向科學社會主義轉變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44)李良明、鐘德濤主編:《惲代英年譜》,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頁。此后,惲代英開始逐步改變無政府主義立場,終于在1921年7月召集受利群書社影響的林育南、林育英、唐際盛等進步青年在黃岡浚新小學成立革命團體共存社。其宗旨是:“以積極切實的預備,企求階級斗爭、勞農政治的實現,以達到圓滿的人類共存為目的。”(45)《浚新大會記略》,《我們的》第7期,李良明、鐘德濤主編:《惲代英年譜》,第195頁。這與隨后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第一個綱領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共存社的成立,是惲代英等一批先進青年由空想社會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的轉折點。中共一大召開后不久,惲代英獲悉了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的消息,立即宣布解散共存社,與林育南、林育英、李求實、蕭云翥、李書渠、廖煥星等先后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們從此為共產主義理想不懈奮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以上史實說明,湖北早期的兩個共產主義組織,在辛亥革命后十年間武漢社會局勢動蕩、民生凋敝的環境下,探索著救國救民之路,并通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雖然走的“路徑不同”,但“殊途同歸”,都走向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征途。因此,湖北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創立的六個地區之一和重要發祥地,在中國共產黨宣布正式成立的“一大”上出現“湖北現象”,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