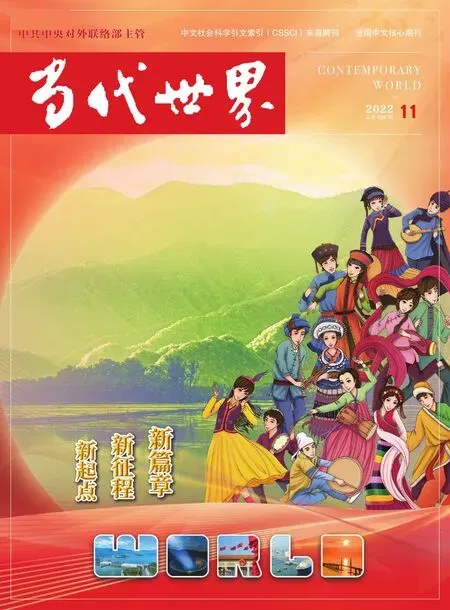區域合作新趨勢與政治戰略博弈
張蘊嶺
區域合作是當前國際關系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潮流。區域合作有多種形式,包括建立區域組織、簽署合作協議、實施靈活的合作項目和倡議等。在全球多邊合作進程遇阻的情況下,區域合作則呈現出加速發展的趨勢,成為各國對外關系的重點選擇。從各國的政策取向看,區域合作大體分為三類:一是雙邊選擇,主要基于雙方利益的認同;二是近地緣選擇,這類安排最多;三是戰略利益選擇,這類安排不限于某一單一地緣區域。一個國家往往同時參與不同的區域合作安排。因此,從全球范圍看,區域合作機制有著復雜的相互交叉性,不同的安排和規則交互并存。區域合作不是對國際多邊合作的替代,二者相互支持、相輔相成,共同構成全球合作的體系。
區域合作的新趨勢與新特點
現代意義上的區域合作,主要起源于二戰后,并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加速發展。當前,區域合作出現了許多新的趨勢和特點,深刻影響國際合作的未來發展方向和區域國家的政策選擇。
一是經濟合作不斷向深度和廣度拓展。一方面,自貿區的構建逐漸由“淺層協議”(Shallow Agreement)轉向“深層安排”(Deep Agreement)。前者著眼于市場準入,主要包括降低關稅和降低交易成本;后者著眼于規則制定,涉及競爭政策、政府采購、勞工標準、環保、知識產權等諸多所謂“邊界內”(Behind Border)領域。比如,美國推動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
不僅市場開放度高,而且包含諸多嚴格的“邊界內”準入標準。在美國退出后,日本領銜簽署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保留了原協議中絕大部分內容。東盟發起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雖然在市場開放和規則制定方面的標準較低,但也在數字經濟等領域制定了許多新規則。而在《美墨加貿易協定》中,甚至包含了有關在墨西哥生產產品數量的具體規定和工資標準等。另一方面,經濟合作所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多,形式多樣,從綜合性合作到功能性合作都得到長足發展。在功能性合作方面,現在的區域經濟合作重點是推動包括公路鐵路、通信、數字等基礎設施網絡的建設;在綜合性合作方面,現在的區域經濟合作更加注重綜合發展環境與發展方式轉變。例如,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建設方式推動新型發展合作,旨在改善區域發展環境,提升區域經濟發展活力,從而實現共同發展。

(澎湃影像/IC photo圖片)
二是安全因素越來越受到重視。傳統上,區域經濟合作更加看重開放水平和效率。如今,受到發展不平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及世界經濟下行等影響,區域合作中的安全因素增強。安全因素涉及很多方面,在微觀層面,包括個人就業、生活安全,公司經營安全,特別是供應鏈安全等;在宏觀層面,包括國家總體安全、發展安全、社會安全等。在開放競爭環境下,一方面市場空間擴大,促進了貿易和投資,從而推動經濟發展;另一方面資本對社會控制力加強,經濟安全甚至國家安全可能受到威脅。在此情況下,無論是政府,還是社會、企業以及個人都強化了安全意識。在當下的區域經濟合作中,各方更加關注和強調安全問題,并且體現在政府政策、公司經營策略和個人行為上。例如,政府在開放安排上加入安全條款,在政策上加強對本國市場、企業和個人的保護。特別是在信息化、數字化和網絡化飛速發展的情況下,網絡安全的重要性更為突出。值得關注的是,在強調安全的同時,需要避免“安全泛化”,即把許多不相關的問題都與安全掛鉤,以安全為借口制定單邊規則,重拾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對他者進行限制甚至制裁,這將對區域經濟合作造成不利影響。

2022年9月20日,第七屆中國—亞歐博覽會在烏魯木齊舉行。(新華社圖片)
三是“價值觀政治”嵌入合作議程。現代區域經濟合作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政治包容性,即把有不同價值觀、政治制度的成員納入共同參與的合作機制中,共同制定規則與合作議程,實現共同利益。以亞太經合組織(APEC)為例,盡管美國與中國、東盟一些成員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和政治制度,各方還是走到了一起。為了規避政治敏感問題,APEC把參與成員稱為“經濟體”,把領導人會議稱之為“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以提高參與上的靈活性,共同的目標是推動形成區域開放的大市場,實現經濟的共同發展。但是,美國打破了“開放的地區主義”的合作原則,先后推動構建了TPP、“印太經濟框架”(IPEF)以及半導體和供應鏈聯盟,旨在排斥與遏制中國。目前,出于不同考慮,部分亞太國家加入了這些機制,使得亞太地區經濟合作陷入一種“結構性分離”狀態,以APEC為主軸的區域經濟合作制度安排面臨著失去聚合力的風險。
區域合作中的戰略博弈
區域合作都有著鮮明的政治驅動,主要是出于區域整合的政治考慮,通過把區域成員吸納到區域合作平臺,建立區域合作機制、制定區域規則與合作議程,實現區域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同時,不同的區域合作也都有著清晰的戰略博弈考慮和設計,其動因和目標較為復雜。
美國在推動區域合作上向來有著強烈的戰略博弈動機和目標設計。比如,面對歐洲統一大市場的構建,美國曾推出兩大區域戰略,一是1993年推動召開APEC領導人會議,提出構建亞太共同體,通過與東亞地區建立緊密的經濟關系,構建亞太大市場來確立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對沖歐洲統一大市場的影響。彼時,美國歡迎中國加入APEC。但面對中國綜合競爭力大幅提升的現實,美國減少了對APEC的投入,摒棄了“開放的地區主義”原則,轉而推動構建排斥中國的TPP,后又推出旨在遏制中國的“印太戰略”。事實上,“印太戰略”不是著眼于區域合作構建,而是著眼于對抗性的戰略博弈,通過強調價值觀和戰略認同,與中國進行全面戰略競爭。二是1994年美國提議構建美洲自貿區,旨在建立包括多數美洲國家的大市場,以此來平衡歐洲統一大市場的影響。美洲自貿區原設想在2005年建成,但由于分歧太大,在經過幾輪談判后就夭折了,美國統合美洲的戰略企圖并沒有實現。
歐洲的區域合作始于西歐,其政治驅動是構建區域合作組織,把包括德國在內的成員吸納到一個區域框架中,制定共同遵守的規則,對區域重要事務進行管理,實現成員間的友好相處和地區的持久和平與發展。西歐國家開展合作的戰略博弈有雙重設計,一是現實的考慮,主要是在冷戰期間以合作求自保;二是長遠的考慮,主要是增強歐洲的自立,逐步擺脫美國對歐洲的控制,重塑歐洲在世界上的強勢地位。冷戰結束后,歐盟加快了吸收中東歐國家入盟的步伐,把大多數歐洲國家吸納到歐盟。盡管英國在2021年脫離歐盟,但歐盟的地區中心地位并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歐洲與美國的戰略博弈雖是以非對抗的思考與設計進行的,主要是通過增強區域的內在凝聚力和能力建設來實現,但美國對歐洲統一大市場建設、歐元的使用以及歐洲聯合軍事力量的構建均懷有高度戰略警惕,并采取措施加以對沖。當前,受俄烏沖突影響,在戰略和安全上歐盟對美國的依賴有所增強,但是歐盟減少對美依賴、改變美國主導的戰略努力并沒有改變。
東南亞國家推動區域合作也有著鮮明的政治與戰略博弈考量。一方面,希望通過成立東盟把東南亞國家納入一個區域合作機制中,實現區域國家間的友好相處與合作發展,改變地區對抗、沖突的歷史。東盟在發展中逐步提升,由構建自貿區到建設共同體,創建了包容、開放與合作的“東盟模式”,成為亞洲區域合作的成功典范。另一方面,東盟的戰略考量主要體現在以區域整合為平臺,維護本地區的自主和主體性,從而在大國地緣戰略博弈中獲得主動,維護其自主和中心地位。東盟的戰略博弈是非對抗性的,在堅持“以東盟為中心”的基礎上,創建廣泛對話合作網絡,不陷入大國沖突旋渦,拒阻他國在該地區策動爭斗,特別是戰爭。東盟構建了“東盟 +1”(合作伙伴國)、“東盟 +3”(中日韓)和東亞峰會、亞歐會議、東盟地區論壇等開放性合作框架,引領構建了RCEP,從而獲得戰略博弈上的主動。東盟的非對抗性戰略博弈不僅維護了本地區的和平發展,也對緩沖東亞以及印太地區的戰略博弈起到積極作用。

2022年6月23日,歐盟峰會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新華社圖片)
以推動開放合作為驅動的政治戰略博弈與以對抗性競爭為驅動的政治戰略博弈不同,前者利己和利他并行,稱之為良性驅動;后者只是為了利己,稱之為非良性驅動。近年來,排他性的政治與戰略競爭被嵌入區域經濟合作進程中,導致區域合作中的政治化、安全化。在這種導向下,一些區域性議程強調合作伙伴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戰略認同,把認定的對手排斥在外,并且制定歧視性規則,甚至不惜推動所謂“脫鉤”。美國是區域合作戰略化、政治化的始作俑者,目前主要是基于對華戰略競爭的考量,是一種零和戰略博弈,與以包容、開放和互利為主要特征的現代區域合作精神及實踐相背離。
中國的區域合作戰略定位

2022年10月27日,印尼雅加達,東盟各國外長就緬甸問題召開特別會議。(GALIH PRADIPTA / HANDOUT/澎湃影像/IC photo圖片)
中國一向重視參與和推動區域合作。作為一個區域大國,中國有著清晰的地緣區域定位、戰略與政策。中國把周邊作為對外關系的首要,積極推動多方位的區域合作,參與和推動構建中國—東盟自貿區、中國—韓國自貿區、中國—巴基斯坦自貿區和RCEP;引領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積極參與“東盟+1”“東盟+3”、東亞峰會、亞歐會議等對話合作機制,提出睦鄰、安鄰、富鄰,親誠惠容和周邊命運共同體等重要合作理念。中國推動構建的周邊區域合作機制不是排他性的,更不是對抗性的。以上海合作組織為例,上合組織的建立初衷是為了與俄羅斯和獨立后的中亞國家構建新型合作關系,以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為導向,創建和平、穩定、發展的區域。如今,上合組織已經成為新型區域合作組織,各成員國通過協商與合作創建區域安全與發展環境,實現合作共贏。
作為世界性大國,中國的區域合作定位具有世界視野。除了積極參與和推動近地緣區域合作外,中國還積極參與和推動同其他區域的合作,有些是通過雙邊渠道,有些是通過區域合作機制。例如,中國積極推動與非洲、拉美等區域的合作關系,推動構建了中非合作論壇、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論壇、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等合作機制。中國參與和推動區域合作的重點是發展領域,也有改善對外關系、發揮大國影響力、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政治與戰略考量。中國的區域合作戰略不針對第三方,也不搞選邊站,旨在聚焦共同設定的合作議程實現共同發展。

第十九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在南寧開幕。(新華社圖片)
針對區域合作的新趨勢和新特點,中國將堅持開放、包容的區域合作原則,堅持合作發展、共同發展的方向。一方面主動與現行的區域合作機制對接,比如中國提出申請加入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就是著眼于與新規則對接;另一方面提出符合新時代需求的方案,比如中國在制定《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數據安全法》等自身數字安全規則和法律的同時,倡導共同保護數據安全與數字經濟安全。針對各國對開放中發展安全、社會安全的高度關注,中國應更加重視區域合作中的共同發展、合作發展議程設計和落實,既重視硬件項目合作,也重視“軟件”合作。比如,構建更加安全的資金鏈供應鏈體系,構建基于認同的“友好圈”保障機制。
美國在對華開展全面戰略競爭下,通過推動基于“價值觀認同”的合作圈,排除中國的參與,在關鍵技術和重要供應鏈方面與中國“脫鉤”,參與者既有美國的盟友,也有基于利益考慮的機會尋租者。但對多數國家來說,考慮到與中國關系的重要性,并不會唯美國馬首是瞻,而是進行多方選擇,堅持“不選邊站”原則。針對這種情況,中國在參與和推進區域合作中應采取更為靈活的方式,把推動項目合作和功能性規則制定作為重點。例如,考慮到供應鏈的重要性,中國可積極推動供應鏈安全保障的構建,制定在正常情況下和非正常情況下維護供應鏈的相關規則。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不確定、不安定因素和沖突發生的風險增大。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有賴于穩定的供應鏈體系,因此,要把維護和保證供應鏈的安全平穩運行作為重中之重。供應鏈有著很強的區域性集聚特征。在此背景下,需要制定有針對性的供應鏈安全機制,可將中國—東盟以及中日韓三國的供應鏈安全保障構建作為重點。同時,針對供應鏈的專業分工特征,選擇關鍵性的節點予以重點保障,比如積極推動中德之間的汽車供應鏈、中韓之間的半導體供應鏈、中日之間精密部件供應鏈構建等。
總之,在全力支持多邊體系發揮效能的同時,面對區域化的新形勢和新特點,中國應該把參與和推動區域經濟合作作為對外經濟戰略的重點,根據不同地區的形勢、特點和利益,制定不同的規劃和行動議程,積極應對國際政治經濟形勢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