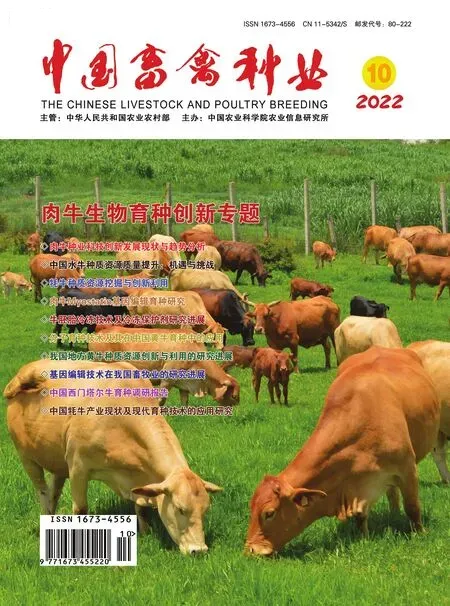牦牛種質資源挖掘與創新利用
鐘金城 王會 柴志欣 馬志杰
(1.西南民族大學青藏高原研究院,四川成都 610041;2.青海省畜牧獸醫科學院畜牧研究所,青海西寧 810016)
牦牛(Bos grunniens)是分布在海拔3000m 以上,以我國青藏高原為中心及其毗鄰的高山、亞高山地區分布的具有獨特種質特性的牛種。它對高寒草地生態環境條件具有極強的適應性,能在空氣稀薄、牧草生長期短、氣候寒冷的惡劣環境條件下生活自如并繁衍后代。牦牛可為當地牧民提供肉、奶、毛、役力、燃料等生產和生活必需品,是一種“全能” 家畜,在當地畜牧業發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遺傳上是一個極為寶貴的基因庫。
牦牛種質特性的研究一直是牦牛科學研究的重點和熱點之一。20 世紀70 年代末,隨著全國牦牛品種資源的調查研究,利用形態遺傳標記對牦牛的種質特征特性進行了分析,并結合牦牛產區的生態環境條件將中國牦牛分為青藏高原型和橫斷高山型2 個類型,這一分類結果列入了《中國牛品種志》。從20 世紀80年代末至2000 年的10 多年中,人們又利用生化遺傳標記、細胞遺傳標記系統全面地研究了牦牛的種質特性和品種分類。但關于牦牛種質分子特性的研究,在2000 年以前報道的很少,僅見西南民族大學對九龍牦牛和麥洼牦牛mtDNA 的多態性分析(1992 年)、西藏自治區農業科學院畜牧獸醫研究所對牦牛生長激素(GH)基因的克隆分析(1994 年)、四川大學和西南民族大學對牦牛Sry 基因的克隆分析(1994 年)、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對幾個牦牛品種的mtDNA 多態性分析等一些零星的研究。進入21 世紀后,特別是近10年來國內外學者對牦牛基因組及功能基因開展了較為系統的分析研究,這為牦牛種質資源的開發利用提供了基礎。本文以作者近年來的研究成果為主線,綜合分析牦牛資源的現狀與特點、牦牛分子遺傳標記和功能基因的研究進展以及牦牛種質分子特性研究和開發利用中存在的問題,探討了其對策和措施,以便為今后合理開發利用牦牛種質資源提供理論依據。
1 牦牛種質資源的現狀及其特點
1.1 牦牛的數量與分布
牦牛是牛屬動物中能適應高寒氣候條件而延續至今的珍稀畜種資源,是世界上地理分布范圍十分有限的少數家畜之一。中國是牦牛的發源地,主要分布于以中國青藏高原為中心及其毗鄰的高山、亞高山地區。除中國外,在與我國毗鄰的蒙古、原蘇聯中亞地區以及印度、不丹、錫金、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國家或地區均有少量分布[1]。
目前,全世界現有牦牛約1753.5 萬頭,其中中國有1655.6 萬頭,是世界上擁有牦牛數量和品種(類群)最多的國家,占世界牦牛總數的94%以上。在中國的省區中,青海580.0 萬頭,占全國牦牛總數的35%,居全國第一;西藏492.3 萬頭,占26%,居全國第二;四川400.0 萬頭,占24%,居全國第三;其次甘肅145.0 萬頭,占8.7%;新疆25.0 萬頭,占1.51%;云南9.0 萬頭,占0.54%(表1)。

表1 牦牛的數量與分布
此外,歐美等國也引入牦牛飼養,但數量未見其報道[2]。英國在1785 年由圖爾勤氏首次帶入一頭牦牛。1854 年法國國外動物馴養協會得到法國駐上海領事館蒙蒂尼氏由中國北部運去的12 頭牦牛,這批牦牛分別飼養在法國的馬爾科特、汝拉、阿里埃、阿爾卑斯地區。加拿大在1909 年得到英國彼德福爾公爵贈送的6 頭牦牛,飼養在加拿大西部的阿爾伯達省石山公園。美國阿拉斯加在1919 年從加拿大引入3 頭牦牛,1923 年和1932 年又引入6 頭牦牛,均在阿拉斯加進行飼養試驗。
1.2 中國牦牛的品種資源
中國牦牛遺傳資源十分豐富,由于分布區的自然生態環境條件、人們的選育方式、品種形成歷史等的不同,形成了體型外貌、生產性能和生態適應性各異的牦牛品種。目前,青海、西藏、四川、甘肅、新疆、云南等我國牦牛的6 個主產區共有20 個優良地方品種或遺傳資源和2 個培育品種,即青海高原牦牛(青海)、環湖牦牛(青海)、玉樹牦牛(青海)、雪多牦牛(青海)、西藏高山牦牛(西藏)、斯布牦牛(西藏)、帕里牦牛(西藏)、娘亞牦牛(西藏)、查吾拉牦牛(西藏)、類烏齊牦牛(西藏)、九龍牦牛(四川)、麥洼牦牛(四川)、木里牦牛(四川)、金川牦牛(四川)、昌臺牦牛(四川)、天祝白牦牛(甘肅)、甘南牦牛(甘肅)、巴州牦牛(新疆)、帕米爾牦牛(新疆)、中甸牦牛(香格里拉牦牛,云南)、大通牦牛(青海,培育品種)、阿什旦牦牛(青海,培育品種),其中列入《中國牛品種志》 的有九龍牦牛、麥洼牦牛、青海高原牦牛、西藏高山牦牛、天祝白牦牛共5個品種。
家畜品種資源同其他資源一樣,正確的分類和認識意味著有可能合理利用和創造財富,對長遠的經濟發展有不可忽視的巨大作用。牦牛品種的正確分類和鑒定對牦牛產業的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一直是牦牛科學研究的熱點之一。我國自20 世紀70 年代中期以來對中國牦牛遺傳資源進行了廣泛深入地調查、鑒定和分類研究,提出了多種分類方法,主要的有3種:①蔡立等[1]依據牦牛的形態、毛色特征、生產性能并結合產區的地形地貌、水熱條件、草地類型、牧草種類以及經濟結構、飼養水平、選育程度等自然和社會生態環境的不同,將中國牦牛分為橫斷高山型(谷地型)和青藏高原型(草地型)兩大生態類型,橫斷高山型牦牛主要包括九龍牦牛、西藏高山牦牛、中甸牦牛等;青藏高原型牦牛主要包括麥洼牦牛、青海高原牦牛、巴州牦牛、天祝牦牛等。②陸仲璽[3]引用蘇聯學者考萊斯尼“動物地區差異的標志不是動物的絕對大小,而是動物的體型” 的原理,對中國25個地區牦牛群體的體尺、生產性能、毛色、角的有無等進行綜合、歸納后按產地生態條件將牦牛分為3 大類型,即西南高山峽谷型(主要包括九龍牦牛、中甸牦牛、西藏牦牛等)、青藏高原型(主要包括麥洼牦牛、果洛和玉樹牦牛、甘南牦牛等)、祁連山型(主要包括天祝牦牛、青海北部牦牛和山丹牦牛等)。③在《中國牦牛學》 一書中,根據牦牛產區的地形地貌特點劃分為:青藏高原型、橫斷高山型和羌塘型3 個類型[4]。近年來,作者根據RFLP、RAPD、AFLP、微衛星DNA、mtDNA 和多個功能基因的多態性等分子遺傳標記以及染色體特征、血液蛋白多態性進行了牦牛品種分類研究[5],結果與蔡立等將中國牦牛劃分為橫斷高山型和青藏高原型的分類基本一致,表明中國牦牛分為兩大類型是比較合理的。
1.3 野牦牛種質資源
野牦牛(Bos grunniens mutus)是青藏高原珍貴的野生畜種資源,是家牦牛的近緣種,屬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對青藏高原惡劣生態環境條件具有極強的適應能力,是家牦牛改良復壯的重要遺傳資源之一。
歷史上野牦牛曾廣泛分布于中國至亞洲北部,由于自然地理和氣候變化以及人類活動的影響,目前,野牦牛的分布僅限于中國,主要分布于南自西藏的岡底斯山、北至與新疆接壤的昆侖山(包括支脈阿爾金山和可可西里山)和甘肅西北的祁連山、東達青海境內遠離青藏公路的海拔4000m 以上的山間盆地、湖盆四周以及山麓緩坡區,總面積不足40 萬km2(其中西藏約30 萬km2,青海、新疆和甘肅等地約10 萬km2),估計世界上現有野牦牛總數40000 頭左右(西藏約20000 頭,青海約17000 頭,新疆、甘肅等地約3000 頭)。國外僅見于印度和尼泊爾,但20 世紀80年代后已見不到野牦牛的蹤跡。盡管在俄羅斯東部發現了更新世的野牦牛化石,但是幾乎沒有證據表明那里的野牦牛不是家養的。
野牦牛身軀高大碩壯,體型比家牦牛大2~3 倍,體長l.6~2.2m,肩高2.0m 左右,尾長35~45cm,體重可達600~1200kg;肩部中央有顯著凸起的隆肉,站立時略顯前高后低;全身被毛密長,呈黑色或烏褐色,鼻臉部及背線的毛色稍淡,似灰白色,成年野牦牛的脊背往往有金黃色或微紅色的背線,體側下部、肩部、胸腹部及腿部均披長達40cm 以上的長毛,尾端長毛形成簇狀;性情兇猛,野性十足,體態魁壯,雌雄均有角,角形相似,但公野牦牛的角比母野牦牛大。
1.4 牦牛種質資源的特點
牦牛是我國的主要牛種之一,僅次于黃牛、水牛而居第三位,占我國牛只總數的1/6,從古至今都是青藏高原牧區的優勢種家畜和當家畜種,可以說沒有牦牛就沒有青藏高原的畜牧業。牦牛種質資源具有不同于其他畜種資源的特點:①牦牛對高寒草地的生態環境具有極強的適應性,能把人類無法直接利用的自然資源轉化成人類需要的畜產品。②牦牛主要分布在我國西部300 萬km2的人口稀少地區,不與人爭地、爭糧、爭奪自然資源和生存空間,牦牛業是典型的節糧型畜牧業。③我國的牦牛主要分布在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牦牛業對加強民族團結,穩定民族地區具有重要意義。④牦牛是一種人工選育程度不高或者說是半野生的家畜,在長期的自然選擇中,形成了在暖季強生長和育肥的能力,是發展季節性畜牧業的最佳畜種之一。⑤牦牛品種均未經過系統的選育提高,缺少詳細的系譜和生產性能記錄,生產性能仍處于較低水平,多數性狀還不夠整齊。⑥牦牛未補飼任何添加劑和飼料,完全在未施過化肥和農藥的天然牧場上放牧育肥,其產品是名副其實的綠色食品。牦牛奶、肉、血液、骨等中含有一些其他畜種中沒有或含量較低的成分,可以作為醫藥和食品工業的重要原料開發利用。
綜上所述,牦牛種質資源是任何其他畜種資源無法代替的特殊畜種資源。但由于無法利用在其他畜種中普遍采用的常規育種方法來進行選育提高其生產性能,加之受所處自然環境條件的影響和限制,以及牦牛服務的人口相對較少,與豬、雞等畜種相比,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相對較低。因此,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牦牛品種至今仍為生產性能遠低于其他牛種的原始品種,主要表現為生長速度慢,成熟期晚,產肉、產乳量低等。中國雖然是一個牦牛數量和品種的大國,但牦牛業仍然是一個較落后的畜牧產業,急需進一步做大、做強。
作者認為,今后在開發利用牦牛種質資源的過程中,不能把牦牛作為普通家畜來對待,要把牦牛放在稀有動物資源的角度來考慮。牦牛產品可分為畜牧產品和非畜牧產品兩大類,在畜牧產品中,牦牛肉、奶等應視為野味、綠色、保健食品。牦牛全身是寶,有很多可開發利用的非畜牧產品,如牦牛胎盤素、奶中的食品保鮮成分、乳脂中的護發護膚成分、血液中的生物活性因子等。但目前開發利用的程度和數量極為有限,其產品在牦牛產品中所占的比例極小,進一步開發利用的潛力很大。此外,牦牛還可作為旅游業中的一種工具,開發旅游產品,如牦牛尾、角、骨等可作為裝飾品利用,牦牛調教后可供人們乘騎娛樂等。
2 牦牛種質分子特性的研究現狀
2.1 牦牛種質資源的挖掘
從線粒體基因組和核基因組兩個方面對四川、西藏、青海、甘肅、新疆、云南等省(區)的牦牛種質資源開展了系統全面研究。發現除了已經列入《中國牛品種志》 的九龍牦牛、麥洼牦牛、西藏高山牦牛、青海高原牦牛和天祝白牦牛具有各自的種質特征外,國內外研究者還研究挖掘出了木里牦牛、金川牦牛、昌臺牦牛、斯布牦牛、帕里牦牛、娘亞牦牛、查吾拉牦牛、類烏齊牦牛、環湖牦牛、玉樹牦牛、雪多牦牛、甘南牦牛、帕米爾牦牛、錯那牦牛、申扎牦牛等具有獨特種質特征特性的牦牛類群。
2.2 牦牛種質資源庫的建立
采集了包括20 個優良地方品種或遺傳資源和2個培育品種在內的共32 個牦牛品種(類群)的1783頭牦牛的組織樣品,建立了牦牛種質資源的組織庫和細胞庫。
運用高通量測序手段,利用bionano、二代和三代測序等新技術,測序研究了32 個牦牛品種(類群)各6 頭牦牛,共192 頭牦牛的全基因組。通過生物信息學手段進行組裝、注釋完善牦牛基因組信息,將牦牛全基因組的DNA 序列組裝到30 條(29 條常染色體和X 染色體)染色體上,構建了牦牛全基因組的精細物理圖譜和泛基因組圖譜,獲得了32 個牦牛品種(類群)獨有的DNA 序列和功能基因[6]。建立了牦牛全基因組數據庫和牦牛功能基因數據庫。這豐富了牦牛種質資源的遺傳信息,為挖掘與牦牛重要經濟性狀相關的功能基因、研究牦牛功能基因的作用和網絡關系、牦牛基因定位和分子標記育種奠定了堅實基礎。
2.3 牦牛種質資源的遺傳多樣性研究
從牦牛核基因組(ISSR 遺傳多樣性、SRAP 遺傳多樣性、微衛星遺傳多樣性和全基因組測序的序列多樣性)和核外線粒體基因組(12SrRNA、16SrRNA、mtDNA COⅠ、mtDNA COⅡ、mtDNA COⅢ、mtDNA ND5、mtDNA ND6、mtDNA D-loop、mtDNA ATP8、mtDNA ATP6 等的遺傳多樣性和整個線粒體基因組的遺傳多樣性)兩個方面系統深入地研究了32個牦牛品種(類群)的種質資源遺傳多樣性。在國內外首次發現牦牛具有豐富的遺傳多樣性,改變了以前認為牦牛遺傳多樣性貧乏的觀點;搞清楚了牦牛品種或類群間的親緣關系;還發現牦牛有兩個起源,可分為明顯的兩大類,青藏高原東部是家牦牛的主要馴化起源地。這為牦牛良種選育、雜交改良利用提供了理論依據。
2.4 牦牛經濟性狀功能基因和分子標記的挖掘與鑒定
在牦牛基因組研究的基礎上,挖掘鑒定出了600余個與牦牛經濟性狀相關的功能基因和分子標記,其中進行了初步功能驗證的功能基因和分子標記有48個。這些基因和分子標記主要包括以下幾大類:
(1)牦牛的GH、GHR、POMC、MC4R、CHR、TG、CPE、PRKAG、Hal、CTGF、EGR、FIGF、Gprin、Hbegf、IGF、NGF、NGFR、OGFR、ATGL等與牦牛的肉質和生長性狀相關的基因和分子標記。
(2)牦牛的EPAS1、EGLN1、HYOU1、HMBS、HIF 等與牦牛高原適應性相關的功能基因和分子標記。
(3)牦牛染色體的BTA3、BTA4、BTA6、BTA9、BTA14、BTA28 等與牦牛產乳量和乳脂肪合成相關的功能基因和分子標記。
(4)牦牛的EIF1AY、USP9Y、ZRSR2Y、UTY、DDX3Y、ZFY、EIF2S3Y、SRY、GDF-9、ZP3、BLG、IFN-tau、FSHβ、LHB、TRO、PRLR 等與牦牛繁殖和犏牛雄性不育相關的基因和分子標記。
這些研究結果為開展牦牛的分子標記輔助選擇和分子育種提供了重要依據,對牦牛良種選育、雜交改良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5 牦牛卵母細胞成熟與早期胚胎發育轉錄組學特性
首次采用轉錄組測序(RNA-Seq)技術和單細胞轉錄組測序等現代生物技術對牦牛卵母細胞成熟前后以及牦牛和犏牛2-、4-、8-細胞、桑椹胚和囊胚的轉錄組進行了系統分析,結果發現:牦牛卵母細胞成熟前后有4767 個差異表達基因(DEG);牦牛2-~4-細胞、4-~8-細胞、8-細胞~桑椹胚及桑椹胚~囊胚4個發育階段分別有6922、7601、8071 和10555 個差異表達基因(DEG);犏牛2-~4-細胞、4-~8-細胞、8-細胞~桑椹胚及桑椹胚~囊胚4 個發育階段分別有3690、6332、8965 和10298 個DEG;牦牛與犏牛在2-、4-、8-細胞、桑椹胚和囊胚中分別有2960、7287、6420、7724 和10417 個DEG;對DEG 進行了系統GO 分析和KEGG 分析。這些成果首次從轉錄組學的角度系統揭示了牦牛卵母細胞成熟機制、牦牛與犏牛胚胎早期發育調控機制。
2.6 犏牛雄性不育機理的新發現
犏牛是牦牛與普通牛的雜交后代,其雄性不育是牦牛雜交改良中的一大難題。國內學者對牦牛、普通牛及其犏牛開展了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組織學、免疫化學、比較組學等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
首次在犏牛、牦牛睪丸組織文庫中分別鑒定出17784 和18529 個表達基因。發現在犏牛睪丸組織中的高表達基因大多參與減數分裂前期和非生精細胞增殖及蛋白合成活動,而參與精子生成的基因低表達或不表達。比較分析了睪丸細胞特異標記基因在兩文庫間的表達差異,結果發現犏牛睪丸組織中精原干細胞、支持細胞、間質細胞和肌樣細胞等的標記基因表達上調,而已分化精原細胞及其后期生精細胞的標記物表達量較低甚至幾乎不表達。這些基因表達下調可能受到激素合成、精原干細胞自我分化及更新、減數分裂和細胞等過程相關基因表達下降影響。進一步分析表明,犏牛精子發生阻滯可能由激素分泌失衡或不足、RA 信號相關通路受抑制和Syce3、Fkbp6、Dmrt7、Spo11、Dmc1、survivin、Bcl-2 等基因表達下降所導致的。GRTH/DDX25、Crem 和Crem 下游調控基因分別顯著表達下調和極顯著表達下調或不表達可能導致了F1 代犏牛生精細胞只能分化至圓形細胞期。這些結果有助于人們進一步了解犏牛雄性不育的機理和精子發生機制。
在牦牛、普通牛和犏牛Y 染色體的比較研究中發現,牦牛的Y 染色體兩端含有大量的重復序列,并且重復序列分布在基因間區和內含子區,這些重復序列是Y 染色體進化的結果,可能在X、Y 從常染色體分化的過程中起到了阻止染色體重組的作用,同時對保護牛Y 染色體兩端重要的單拷貝基因起著重要的作用。
發現牦牛的EIF1AY、USP9Y、ZRSR2Y、UTY、DDX3Y、ZFY、EIF2S3Y、SRY 基因除SRY 基因外,均有大量的重復序列,在犏牛與牦牛間有3219 個SNPs,其中有8 個非同義SNPs,并得到了一些可能與犏牛雄性不育相關的SNP。
在國內外首次利用體外受精(IVF)研究發現牦牛與普通牛之間受精率和卵裂率正常,說明種間雜交受精過程正常;首次發現牦牛與普通牛種間雜交存在免疫難孕現象,即用奶牛精子人工授精母牦牛后母牦牛對奶牛精子產生免疫應答,用精子抗體對母牦牛進行免疫,可顯著提高母牦牛人工授精(AI)的受胎率;同時發現牦牛、普通牛和犏牛早期胚胎發育轉錄組有明顯差異,表明犏牛早期胚胎發育分子調控機制與牦牛有差異。
2.7 牦牛胚胎工程技術體系的建立
國內學者建立了牦牛組織細胞冷凍保存技術,獲得了牦牛成纖維細胞、乳腺細胞、顆粒細胞等體細胞系,建立了牦牛卵母細胞、胚胎的冷凍保存技術體系;開展牦牛體細胞克隆相關研究,建立了牦牛體細胞同種和異種核移植技術體系,提高牦牛與普通牛異種克隆胚胎發育效率,開展異種克隆的表觀重編程研究,提高異種克隆核質互作,將異種克隆效率從10%左右提高到20%~30%;在國內外首次建立了卵裂球用量少、速度快、結果準確的牦牛與犏牛早期胚胎性別鑒定技術體系;首次建立包括牦牛卵母細胞體外成熟、精子體外獲能、體外受精及早期胚胎體外培養等關鍵技術的一整套牦牛與犏牛胚胎的高效體外生產技術。為牦牛種質資源保護和高效利用提供了技術保障。
2.8 試管犏牛繁殖技術的創新與利用
研究了促卵泡激素(FSH)、促黃體素(LH)、蛋白酶體抑制劑(MG132)、褪黑素(MLT)、半胱氨酸(Cys)、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IGF-1)、上皮生長因子(EGF)等10 余種激素、抗氧化劑和生長因子對牦牛卵母細胞體外成熟和胚胎發育的影響;優化了牦牛和犏牛胚胎體外生產技術;研究建立了犏牛同期發情技術與胚胎移植技術。
采集屠宰母牦牛的卵巢,通過對牦牛卵母細胞體外成熟(In vitro maturation,IVM)、黃牛精子體外獲能(Capacitation)、體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早期胚胎體外培養(In vitro culture,IVC)和胚胎冷凍(Embryo cryopreservation)等犏牛胚胎體外生產(In vitro production,IVP)技術在體外獲得犏牛胚胎,再利用犏牛誘導發情、同期發情、胚胎移植等技術,實現了在自然條件下無法實現的犏牛生產犏牛,獲得了世界上第一批試管犏牛后代。
這一技術成果,不僅可以在體外大量生產犏牛胚胎,還可充分利用母犏牛的繁殖性能,把母犏牛作為犏牛胚胎移植的理想受體,生產高經濟價值的后代。相對于傳統的犏牛生產方式是重大的技術變革,可顯著提高牦牛生產效益,具有極其明顯的優勢與很好的應用前景。
3 牦牛種質資源的利用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青藏高原的牦牛業在全國乃至亞洲的畜牧業生產和生態安全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近幾十年來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但對牦牛種質資源的保護和開發利用均存在著較多的問題,是低水平的,明顯地落后于其他畜種,今后提高發展的潛力巨大。
3.1 牦牛種質資源的利用現狀
牦牛業的發展現狀是青藏高原畜牧業發展現狀的一個縮影,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3.1.1 青藏高原的主要畜牧業
中國是世界上擁有牦牛數量和品種(類群)最多的國家,有1655.6 萬頭牦牛和22 個品種或遺傳資源,占世界牦牛總數的94%以上。我國的牦牛數量僅次于黃牛、水牛而居第三位,占我國牛只總數的1/6,牦牛分布于我國西部約300 萬km2的地區,是青藏高原牧區的優勢種家畜和當家畜種,沒有牦牛就沒有青藏高原的畜牧業。
3.1.2 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牦牛業歷史悠久,是青藏高原的農牧民賴以生存的傳統產業,也是一個常講常新的話題,但更是一個“沉重” 的話題。所謂常講常新,就是在近60 多年的牦牛業發展歷史進程中,無論是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集體經營或實行雙層承包經營責任制,還是牦牛承包到戶等形式,每一個階段中都有大量的資金投入,并運用許多新的品種改良和選育提高技術、飼養管理方式和方法、牦牛產品營銷理念和措施來推進牦牛業發展。所謂“沉重”,是由于雖然在牦牛業的發展過程中,實施新的品種改良和選育提高技術、飼養管理方式和方法、產品營銷理念和措施以及在每個階段力所能及的資金投入,雖然取得了階段性的發展,但牦牛業未能從根本上擺脫靠天養牛的現狀:“逐水草而居” 依然是牦牛業的主要經營形式;牦牛業的可持續發展和牦牛種質資源的高效利用依然是青藏高原畜牧業發展中最大的難題;為徹底改變牦牛業現狀而實施的一系列工程措施所做的努力和實際效果與初衷相距甚遠,牦牛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3.2 牦牛種質資源利用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對牦牛種質資源的開發利用,總的來說,一方面是不充分,另一方面是具有盲目性和不合理性。
3.2.1 管理粗放,牦牛品種生產性能低
由于多年來粗放的掠奪式經營管理和良種體系不健全、商品意識淡薄、畜群結構不合理、以自然交配為主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嚴重影響著牦牛群體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牦牛品種至今仍為生產性能較低的原始品種,甚至使部分地區的牦牛表現出體格變小、體重下降、繁殖率低、抗病力弱、死亡率高等“退化” 征候。
3.2.2 牦牛數量增長過快,草畜矛盾突出
近10 多年來,牦牛數量發展較快,加之牦牛生長所處的生境,氣候惡劣,牧草生長季節短,枯草期長,牧草單產低,飼草匱乏,更加速了草場的退化。若全年放牧,僅靠質量不高、數量不足的高寒草場獲取生存、生長、繁殖所需要的營養物質遠遠不夠。牦牛營養需要的均衡性和牧草生長供應的季節性矛盾十分突出,冷季牦牛處于半饑餓狀態,牦牛生產存在夏壯、秋肥、冬瘦、春死的自然循環,牦牛業處于粗放經營的生產模式。
3.2.3 牧民科學文化水平較低,新技術推廣緩慢
牦牛產區的多數牧民受牲畜越多越富有的傳統觀念影響較深,養長命畜現象較為普遍,致使適齡繁殖母牦牛比例偏低,相應地增加了老弱等非生產牦牛的比例。這既增加了草場資源的浪費,又增大了冬季掉膘和冬春季的死亡率。牦牛與荷斯坦牛、西門塔爾牛等普通牛品種的種間雜交,雜種一代具有顯著的雜種優勢,但由于雜交改良實施過程中的技術復雜,牧民掌握應用較困難,加之雜種一代雄性不育,使這一技術無法較大面積的推廣應用。其他提高牦牛生產性能、繁殖率和出欄率的新技術也因受當地自然環境條件和牧民接受程度的影響,無法有效地在青藏高原上推廣應用。因此,如何集成、示范現有的提高牦牛生產性能的有效技術和方法,以及提高牧民科學文化水平,盡快改變牦牛這一低產出系統,使之轉化為高效畜牧業,是國家加快提升牧民生活水平的重大需求之一,也是我國發展西部畜牧業的戰略決策之一。
3.2.4 牦牛產品精深加工落后,商品率低
牦牛生產性能低,各種產品又是牧民的主要生活資料,加之牧民的商品意識淡漠,因而牦牛產品多半是自用,供出售的不多,商品率低。即使出售部分產品也多是未加工,而是將牦牛、牦牛肉、牦牛奶等直接出售,粗加工少,基本處于出賣初級產品階段。缺乏牦牛系列產品深加工體系,產品結構單一,有老產品、老面孔、小規模等特點。牦牛產品的精細加工業薄弱,優質綠色的牦牛產品急需高、精、尖新技術加工業的支撐,才能提高產品的價值。
3.2.5 牦牛業抗災害能力差
新中國建立以來,盡管國家對牦牛產區加強了基礎設施建設,但還不足以滿足抗災保畜要求,牦牛業抵御自然災害能力差。飼草生產體系、良種繁育體系、疫病防控體系等技術體系不健全、不完善,草畜生產機械化缺乏,科研推廣力量薄弱,草原建設和草原監理力度小等諸多問題,使我國有特色的牦牛業未形成優勢產業走向世界。
4 牦牛種質資源開發利用的對策與措施
牦牛是一個“全能” 的畜種,具有深度開發價值。牦牛可為人類提供肉、乳、毛、絨等用途廣泛的畜產品。牦牛還是牧民的交通和使役工具,它可馱、可駕、可騎、可犁;牦牛糞曬干后,還是牧民生火做飯取暖的燃料。同時,牦牛也是青藏高原獨特的景觀動物。所以如何將其原料產品進行深加工,多層次利用,開發功能性和特色產品,是提高牦牛產值及經濟效益的重要課題。
4.1 立草為業,以草定畜
牧草是牦牛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目前,草場退化,產草量下降,草畜矛盾突出,牦牛夏飽、秋肥、冬瘦、春乏的惡性循環日趨加劇,在這種情況下,應因地制宜地立草為業,加強草地建設,以草定畜。首先應進一步加強草場使用、建設和管理的承包責任制,草場承包到戶后應推行草場有償使用、建設和管理,繼續改變草場使用無償、放牧無界、建設無責的“大鍋飯” 制度;二是推行草場季節性牦牛業生產,制定科學合理的冷、暖季節草場載畜量,實行以草定畜,草畜平衡,防止草地的超載退化;三是加強人工草地建設,改良天然草場,開展草原補播、種草、施肥、灌溉以及防治草原病、蟲、鼠、毒草侵害,進行圍欄、水利建設等。加強草原監理,依法治草,劃區輪牧,以草定畜,實現畜草平衡,遏制草場退化。
4.2 加強牦牛品種的選育提高和優良品種的快速繁育
牦牛雖然對高寒草地的生態環境條件具有極強的適應性和抗逆性,但由于牦牛品種都未經過系統地選育提高,其生產性能還處于較低水平,多數性狀還不夠整齊,加之近親繁殖、飼養粗放等原因,品質退化較嚴重。因此,應在牦牛品種產區,劃定品種選育基地,建好各種類型的牦牛養殖場,組建選育群和核心群,按照育種方案進行嚴格的選種選配和培育,開展品系繁育和雜交改良的有機結合,不斷提高牦牛品種的質量。
4.3 合理雜交改良,充分利用雜種優勢
通過雜交改良可以豐富和擴大牦牛品種的遺傳基礎,提高生活力和生產性能。科學研究證明,牦牛品種間、家野牦牛間、牦牛同普通牛間雜交均可獲得程度不同的雜種優勢,可顯著提高乳、肉等生產性能,尤其是牦牛與普通牛雜交,其雜種的產乳量、產肉量可比牦牛高1 倍以上。蔡立教授提出的“一代奶用,二代肉用” 的雜交繁育體系,綜合了三個親本品種的優良基因,能最大限度地產生雜種優勢,同時用母犏牛繁殖后代,可充分利用母犏牛在繁殖性能方面的雜種優勢,又可繞過公犏牛不育的問題而使雜交繼續進行,且方法簡單,在牦牛生產中的應用取得了理想效果。因此,在雜種優勢利用中,可推廣這一雜交體系。
由于野牦牛是改良家牦牛的天然基因庫,通過加強家野牦牛間雜交產生雜種優勢的機理、野牦牛遺傳資源保護、家野牦牛間雜交技術等方面的研究,進而充分利用野牦牛遺傳資源來提高牦牛品種的生產性能,也是發展牦牛業的有效途徑之一。
4.4 加快發展現代牦牛產業
牦牛奶、肉不僅營養價值高,而且是天然的綠色食品,符合世界食品潮流。積極研發牦牛奶、牦牛肉、保健品、生化醫藥、皮衣系列及牦牛工藝品等系列產品,進一步擴大牦牛畜產品市場,加強政策、資金、科技投入力量,出臺優惠政策,扶持優勢企業,打造國內、國際品牌,實現產業化道路,加快產業升級,積極探索發展新模式,使牦牛生產方式由重量的粗放型向重質的集約型轉變,促進牦牛業的發展壯大。
4.5 利用生物高新技術,加快牦牛遺傳資源的開發與利用
人類基因組計劃、動物基因組計劃的實施和完成,為開展不同物種間比較基因組學研究提供了契機。充分利用人、牛、豬、羊等物種的科研成果,進一步開展牦牛基因組學研究以及與其他物種特別是近緣種間的比較基因組學研究,加快牦牛科學研究的步伐,不失為一條有效的途徑。在牦牛與其他物種的比較基因組學研究上,目前已用多個牦牛經濟性狀功能基因開展了與其他物種的比較基因組分析和分子進化研究,表明大多數核內功能基因能夠用于牦牛與其他物種的分子進化分析,同時證明比較基因組學研究是提高牦牛基因組研究和利用的一條有效捷徑。這充分說明利用生物高新技術可加快牦牛遺傳資源的開發、利用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