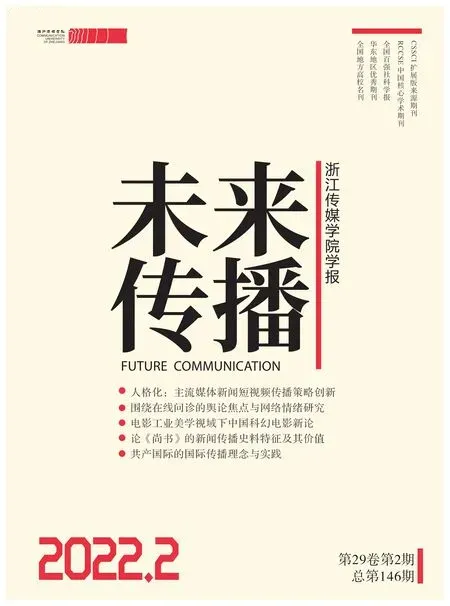想象力消費:電影工業美學的延伸
李玥陽
(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北京100024)
2019年,在電影《流浪地球》上映之后,陳旭光在《中國電影藍皮書2019》和《類型拓展、“工業美學”分層與“想象力消費”的廣闊空間——論〈流浪地球〉的“電影工業美學”兼與〈瘋狂外星人〉比較》等文章中提出,科幻電影一直是中國電影的軟肋,但是以“《流浪地球》為標志,一個新時代已經來臨。時間,開始了。”[1]這種新時代不僅在于《流浪地球》開啟了電影高度工業化的新前景,并且賦予電影工業一種難得的硬科幻的想象力。與此同時,《瘋狂外星人》拒絕復制好萊塢,致力于走一條本土科幻之路。在這里,電影工業美學發生了“分層”,進入到想象力消費的新時代,這種想象力包括科幻、恐怖冒險等多個層面。此后,陳旭光等人又在更多面向展開對“想象力消費”這一概念的理論思考。在《論互聯網時代電影的“想象力消費”》一文中,陳旭光梳理了西方文藝理論中關于“想象力”的論述,并提到中國“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家思想,以及1949年以后借鑒蘇聯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一種非現實主義的想象力的發生。文章特別提到了互聯網時代“想象力”的特別之處:“互聯網時代的后想象力大多表現為‘擬像’的仿造(counterfeit)、生產(production)之后的仿真(simulation)階段,成為完全沒有現實摹本的超現實擬像。也就是說,同樣是‘想象力’這個術語,后人類、后假定性、擬像時代的想象力,其內涵特征與現實主義甚至浪漫主義的想象力均有很大的不同”[2]。而受眾對于這種想象力的接受也將具有時代特征,是一種復雜的消費行為:“我們也可以說,‘想象力消費’既是一種藝術審美消費,又是一種經濟消費,因而是一種重要的國民文化經濟消費。”[2]
應當說,“想象力消費”提示出中國影視正在浮現的重要現象,即舊有的以現實主義為主要訴求的文藝范式正在發生的轉型與巨變,當下在文學藝術等諸多層面占據主導地位的并不是現實主義,而是另一種非現實主義的思潮。就電影而言,對于這種新范式進行理論思考與闡釋,將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在另一個層面上,這種新美學形態的浮現,與媒介技術的變革息息相關,中國電影在多年來提高工業化水平的急切召喚之下,全新的電影形態是媒介變革、工業化水平的提升,以及中外文化交流與互動的結果。這與“電影工業美學”的發展一脈相承,一如陳旭光的分析,是電影工業美學進一步發展、分層的結果。換言之,“想象力消費”概念的提出,是電影工業美學在新時代的全新延伸,對于這次文藝形態的轉型的成敗與未來影響,還需要更多時間來觀望、考察與分析。
一、“想象力”:現實主義的超越
“想象力消費”這一概念在最顯在的層面上,是對中國電影現實主義范式之“轉型”的回應。這種反思基于一個事實,很長時間以來,中國電影的“想象力”是以現實主義來加以限定的,即使是無法以現實主義來闡釋的現象,也會在現實主義中謀求存在的合理性。例如,1949年以后對“鬼”的接受,曾經歷了長時間的論爭與重構。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人們便展開了對《紅梅記》“鬼戲”改編本的探討,基本上是在現實主義反映論中展開。支持者大都認為,鬼戲和神話屬于同一個性質。鬼魂形象仍然“是人和人世間現實斗爭的反映”,[3]對于那些宣揚迷信的,應該批判繼承。這是將鬼戲作為現實斗爭的反映。80年代《紅梅記》的改編戲曲《李慧娘》重新上演,支持者的論述基于同樣的邏輯:“鬼戲……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宣揚封建迷信,因果報應,愚弄人民,恐嚇人民,這樣的鬼戲是糟粕,應該消亡。……還有一種鬼戲,為受壓迫者鳴不平,鼓舞人們的斗志,說出人民的愿望,在善與惡的斗爭中,站在善的一方面,在美與丑的斗爭中,站在美的一方面,這樣的鬼戲,在在社會主義舞臺上,應該有一席之地。”[3]也就是說,鬼戲可以是現實生活中被壓迫者和人民愿望的反映,并因此擁有存在的合法性。
與之類似,既往帶有幻想傾向的電影都帶有強烈的現實訴求。1958年著名電影《十三陵水庫暢想曲》是20世紀5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幻想類電影。但與其說這是一部“科幻”電影,不如說這是一部烏托邦式的暢想社會主義未來的電影,它基于幻想,卻落腳于現實。影片中對于天氣的控制,結尾處長滿瓜果梨桃的大樹,都是對社會主義技術進步前景的良好預期。彼時現實中創造的奇跡,如在雪山上試驗種青稞,使雪山有了植物,都可以在現實中找到注腳。這種現實主義范疇中的幻想來源于“現實主義”這一概念的多重性。雷蒙德·威廉斯在《漫長的革命》中梳理了“現實主義”的不同含義。在通常的意義上,現實主義的題材是“平凡的、當代的、日常的”,與英雄和浪漫傳奇相對。而恩格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定義,給現實主義帶來了根本性影響,“典型”不能混同于常見的人物,現實主義也不再是對現實的直接復制,而是變成了“有原則、有組織的選擇”,這就包含了“未來社會發展的規律和前景的理解”。[4]也就是說,在現實主義這一能指之上,既包含著反對浪漫傳奇的“當代的、日常的”的現實主義,又包含著充滿浪漫想象的“未來社會發展規律”的現實主義,它們在不同層面構成對立的關系。50年代末期“科學文藝”最活躍的時期,也是現實主義討論最激烈的時期。1957年,蘇聯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中國不由驚嘆,對未來的幻想已經變成了眼前的現實。繼而,中國文藝界展開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激烈論爭,這一論爭以《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為導火線,核心問題在于社會主義和現實主義是否能彼此脫離。[5]1958年,毛澤東在討論新詩時,提出了另一種說法,即“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即“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6]可以看出,在新中國現實主義的探討中,始終包含著超越現實主義的沖動與可能性。
這種在現實主義范疇中,嘗試超越現實主義的傾向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彼時帶有幻想元素的電影仍然沒有跳出現實主義的限定,如《珊瑚島上的死光》(1980)以及更晚近的《霹靂貝貝》(1988)等。《珊瑚島上的死光》在發達現代科技,乃至科幻的外表下,卻只是講述了一個極富現實感的可怕未來——劇中神奇的“激光器”像是核武器的復制品,電影所講述的正是核武器被壞人利用所引發的恐慌。更晚近的“第一部兒童科幻片”《霹靂貝貝》則講述了一個有特異功能的帶電的孩子,他是外星人與地球人的結晶。這部電影在很大程度上具備了科幻電影的元素,超能力、外星人等。但外星人只在片頭序幕一閃而過,貝貝的超能力也與日常生活中的“特異功能”十分相似,整部電影并沒有脫離現實主義的軌跡。
以上述事實為前提,“想象力消費”向我們昭示出現實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斷裂”。新世紀的文化藝術發生了不同既往的轉變,有了全新的趨向。首先是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媒介變革,VCD機橫空出世,一系列電影作品通過全新的媒介進入中國,如《午夜兇鈴》《奪寶奇兵》《古墓麗影》。這些電影所攜帶的盜墓、恐怖題材不同于中國本土的現實主義傳統,而是帶有傳奇或羅曼司的特征。受到這些作品的影響,中國也掀起了恐怖盜墓影視熱潮。此次恐怖盜墓影視劇的敘事方式已經跳出現實主義,與本土神怪武俠傳統相結合,形成不同以往的影視潮流。同時,以2019年的《流浪地球》為明確的標識,國產硬科幻電影也被創造出來,接下來的一系列電影《瘋狂外星人》《重啟地球》《平行森林》等,更是對國產科幻影片進行了不同層面的推進。總體而言,無論是科幻題材,還是玄幻、盜墓、恐怖推理題材,新世紀的影視劇都發生了結構性轉型。這些作品不僅是傳奇式的、幻想的,同時也是帶有賽博格傾向的,它們無法再以“發展規律和前景”來闡釋,既往的現實主義不能囊括這些作品。在這個意義上,需要一種全新的理論視野來賦予其意義,而“想象力消費”則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闡釋的維度。
二、“想象力消費”與外來影響:羅曼司、虛構文學與黑色電影
從上述20世紀90年代末期進入中國的電影來看,無論是《古墓麗影》《奪寶奇兵》還是《閃靈》都在更大的范疇內傾向于幻想、虛構類的電影。一如陳旭光所說,所謂的“幻想”不只包括科幻,還包括更廣闊的面向。陳旭光將其概括為“想象力消費”的四種形態,包括“超現實的、假定性美學和寓言性電影”“玄幻、魔幻類電影”“科幻類電影”和“影游融合類電影”。[2]這一判斷無疑是敏銳的。在90年代外來電影的影響下,中國電影出現了較早的恐怖片習得之作,如阿甘導演的《兇宅幽靈》(2002)《閃靈兇猛》(2001),文學領域也出現了周德東、蔡駿等模仿痕跡較重的早期恐怖小說,此后涌現的盜墓題材小說和影視劇也受到這一脈絡的影響。
這一電影文化可以上溯到中世紀羅曼司傳統。董雯婷曾在《西方文論關鍵詞:羅曼司》一文中進行概念的追溯,認為羅曼司作為一個中世紀的文化現象,更傾向于指代一種口頭流傳的故事,內容包括神話、歷史、武功歌、基督教文學、民間故事、童話等作品。這種故事與歷史寫作相對,董雯婷引用了格倫(D.H.Green)在《中世紀羅曼司的開始:事實與虛構,1150—1220》中的論斷:“中世紀早期的七十年“歐洲文學傳統呈現出一個轉向,從明顯傾向于歷史寫作,到傾向于虛構敘事,最充分的例證就是羅曼司的模式。”[7]這也正是在區分“寫真實”的歷史寫作與虛構故事的不同思路,即一種“有意識的虛構”。董雯婷繼而梳理了羅曼司此后的發展和轉變過程,指出羅曼司超越現實的特征,在18世紀以后慢慢轉化成虛構小說(Fiction),包括此后影響深遠的哥特小說等。[7]對于這一問題,著名的“克蘇魯神話體系”創世人,美國哥特(恐怖)小說家H.P.洛夫克拉夫特在其西方哥特小說簡史的研究中做了更具體的論述。洛夫克拉夫特認為,這一傳統在中世紀末和文藝復興時期,是“對神學可怕的顛覆和對魔鬼撒旦的崇拜”,此后恐怖幻想文藝中常見的意象,如“那些要求入土為安的尸骨、將他活著的至愛帶走的魔鬼情人、死亡惡魔……緊閉的臥室、不死的巫婆等等,所有這些都可以在神秘的中世紀遺產里找到影子。”[8]更為重要的是,這一傳統不斷拓展,并催生了“描寫恐怖和異想天開的散文——哥特派的誕生”[8](123)。在哥特小說的末期,出現了經濟學家威廉·歌德溫的恐怖作品,如《圣·里昂》。而歌德溫的女兒,詩人雪萊的妻子瑪麗·雪萊則完成了從哥特小說到科幻小說的重要轉變。她在哥特小說的余韻中,寫出了那部被命名為文學史首部科幻小說的《弗雷肯斯坦》,成為此后不斷被重拍的科幻電影重要題材。應當說,諸多后來在新世紀中國電影中出現的主題,已經在歐美從羅曼司到哥特、科幻小說的發展過程中,具備了本土的原初形態,如《奧特朗圖城堡》《烏爾多夫城堡的秘密》中的哥特式古堡,《鬼船》中永遠不會停航的鬼船,霍桑《農牧神的大理石雕像》《七堵山墻的房子》、愛倫·坡《鄂榭府的倒塌》中那些鬧鬼的、被陰霾籠罩的古老別墅或宅院,以及瑪麗·雪萊《弗雷肯斯坦》中耳熟能詳的科學怪人。這些意象在20世紀初期好萊塢類型片形成的過程中被電影化,在20世紀20年代環球影業公司建構的恐怖世界中,僵尸、古墓、吸血鬼、狼人,都是上述文化的電影形態。這一外來影視文化在90年代中后期以院線或碟片等方式進入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中國舊有的現實主義格局,轉變為中國電影中的鬼宅、荒村、孤島,并經過中國科幻電影的艱難醞釀,在2019年催生出《流浪地球》等中國科幻大制作電影。
在哥特文化之外,同樣在新世紀影響中國電影文化的是介于“哥特式恐怖片和敵托邦科幻片之間”[9]的另一種電影類型——黑色電影。而黑色電影同樣來源于哥特文化,在通常意義上,黑色電影被認為是發生在美國的、“硬派小說和德國表現主義綜合的結果”。[9]無論是以錢德勒為代表的硬漢派推理小說,還是深受哥特文化影響的德國表現主義電影,都可以看到以推理、驚悚懸疑為主要特征的黑色電影,與哥特文化之間的緊密關聯。而當下影視劇中帶有“黑色”色彩的不在少數,刁亦男《白日焰火》、愛奇藝“迷霧劇場”《無證之罪》等,都與這一脈絡有關。
在這個意義上,新世紀已經發生,并在當下中國形成獨具特征的影視形態的這種新趨向,確乎是一種“想象力的轉型”,這一轉型并不能在中國本土的文化中被闡釋,而是外來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此輪影視文化中“想象力”的發生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也極大改寫了中國影視文化的舊有形態。陳旭光“想象力消費”的論述,及這一概念所嘗試囊括的較廣泛的范圍,都成為進一步探討的可能起點。值得關注的是,隨著外來文化和中國本土文化的融合,中國“幻想”影視劇并非亦步亦趨模仿外來電影,而是與中國本土文化融合,漸趨形成基于自身文化的本土特征。這些本土特征還造成中外觀眾在相同電影文本上的不同接受過程。凡此種種,都使得“想象力消費”的提出更像是一種全新探討的開端,其包含的不同層面和廣闊范疇都需要在進一步探討中不斷細化。
三、“想象力消費”:媒介變革與電影工業美學
陳旭光對于“想象力消費”的思考是建立在電影工業美學的基礎之上的。陳旭光對于“電影工業美學”的討論是在“電影產業化”多年歷程之后,對“電影工業”這一命題的再度回歸與重申。如果說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電影產業化進程,將電影放置在“第三產業”,以凸顯電影娛樂產品的功能,那么“電影工業美學”(也包括饒曙光重工業電影美學)則再度強調了電影作為工業產品的層面,強調了電影作為“重工業”的可能性,以及工業向數字化轉型的新趨向——凡此種種,都涉及“媒介”問題。2018年,陳旭光在闡述電影工業美學概念時,一方面將電影視為拒絕精英主義的“常人的美”,同時又拒絕僅僅以產業和市場等非藝術的觀點看待電影。這種美學強調一種調和式的美學建構,“從切實的現實問題出發,在日新月異、風云變幻的中國電影場域內發現問題、聯動產研、溝通上下,進行一種‘中間層面的研究’。”[10]彼時的討論更多在工業和商業化的層面上。而此后的“想象力消費”則囊括了“工業”這一概念所無法覆蓋的部分,它更多著眼于后工業時代的數字和虛擬經濟及新媒介的涌現。在此,媒介的更替與融合成為想象力消費的重要面向,這也正是陳旭光在影游融合、VR、擬像等問題的探討中試圖傳達的。
事實上,上文所探討的世界范圍內的“想象力轉型”,盡管以羅曼司與哥特傳統的再度勃興為表象,但其深層驅動力還是要回到媒介變革這里。例如,被譽為“賽博朋克”科幻小說奠基人的美國作家威廉·吉布森,1984年開始創作對電影《黑客帝國》影響深遠的賽博格三部曲,第一部便以“新羅曼司”為名(Neuromancer)。[11]這部小說講述了一群“電腦牛仔”放棄軀體,進入賽博空間的故事。此處的“新羅曼司”強調的不僅僅是羅曼司的復制,而是強調全新媒介的登場,以及由此引發的全新想象方式。在中國發生的轉型同樣如此。20世紀90年代末期進入中國、并引發中國“想象力轉型”的電影《古墓麗影》,本身便是游戲改編之作,同樣包含著媒介變革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想象力消費”較之于“電影工業美學”已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海外學者試圖思考新媒體與虛擬技術誕生后的美學,如建構一種新型的“數字美學”,[12]陳旭光之“想象力消費”也正是在中國電影的“后工業時代”,探索新美學方案的嘗試。
因此,“想象力消費”勢必包含著電影本體論的再思考,需要直面電影本體論重構的問題。應當說,電影的“想象力”與媒介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早在世界電影史發端處,喬治·梅里愛在《月球旅行記》《魔術》等電影的制作中,便不斷探索電影制片技術的各種可能性。但梅里愛的技術創造,如疊映、停機再拍,仍然基于膠片攝影機的技術限定。也就是說,無論電影中的想象有多么奇妙,膠片攝影機仍然遵循自身的記錄特性,攝影機需要現實參照物,膠片感光后形成的影像是不可修改的。因此,梅里愛的“月球旅行”只能在固定鏡頭中切換或疊映不同的布景。正是在膠片攝影機這種“機械復制”的基礎上,電影發展出了巴贊的現實主義美學以及克拉考爾的“物質世界的復原”理論。但在“想象力消費”的時代,電影已經越來越多地借助數字攝錄設備制作,電腦數字技術可以隨時加入到電影制作之中,某些電影甚至完全由電腦制作完成。電影的發行也依靠數字技術完成,無論是互聯網還是院線的數字放映設備。電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計算機軟件可以“將攝像機的設定、狀態和攝像機拍攝的相關信息集合成數據庫,方便后面的數字非線性編輯”。[13]這也就是說,數字的成像技術已經不同以往,它不再依賴于現實中的參照物,并且數字生成的圖像也不再是不可修改的,人為介入可以出現在影片制作的任何階段。而當電影技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電影藝術和電影觀念也將隨之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嘗試在數字電影階段重新闡釋巴贊等人的理論,尋找此前忽視的理論面向。但無論怎樣鉤沉那些被壓抑的層面,都只是將膠片攝影機時代的電影觀念搬到數字電影時代。它們能夠給非現實的“幻想”提供理論資源,卻始終不能回應數字時代的幻想與膠片時代的巨大差異。
陳旭光在不只一篇文章中,強調了“想象力消費”之“擬像”的層面,這無疑是具有洞察力的。鮑德里亞談到復制品媒介發展的三個階段,并強調了最感興趣的第三個階段,即仿真階段,將這一階段描述為:“一個你不再談論復制的階段——因為復制仍然提示著存在一種訊息——也是現實的一切參照物都銷聲匿跡的階段。在這種情況下,媒介不再是復制現實的一種工具,而是使現實消失的一種形式。”[12](98)鮑德里亞的擬像理論提示出數字電影時代電影觀和世界觀層面正在發生的斷裂——數字電影的“想象力”不僅僅關乎虛構性,不只是幻想或超現實的問題,而是一種更深遠的整體性轉變。它所涉及的問題將是“后人類”“后人文主義”或者“后電影”。現實已經消失,人文主義最重要的三維空間已經被賽博格的無限時空所取代。攝影機背后的眼睛可以是任何一種人類或非人類的觀看。不僅如此,一種沒有現實參照物的電影將可能與任何一種媒介融合,在融合過程中,重要的不是現實參照,而是媒介之間的互文性。例如,游戲改編電影已經是常見的現象,但一如約斯·德·穆爾在《賽博空間的奧德賽》中指出的,游戲與電影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游戲缺少電影敘事的時間層面,游戲玩家處在“永恒的現在”。“你可以用本·拉登或布什總統的形象來代替太空飛船,但是根本不會對游戲產生任何改變。”因此,游戲常常無關敘事或與敘事相脫離,“在大多數冒險游戲中,敘事通常是與游戲本身相抵牾的。”[12](75-77)就此而言,當游戲改編成電影,重要的問題便不是電影與現實參照物的關系,而是與敘事沖突的游戲與作為敘事的電影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垂直的深度模式被取消了,被代之以橫向的指涉關系。(這也正是張明浩、陳旭光在《影游融合的“合”與“不合”——論動畫電影〈姜子牙〉中的游戲影響》一文中試圖探討的。[14])在這個意義上,不僅是既往的電影現實主義理論需要重新思考,電影的幻想理論乃至本體論都需要進行顛覆性的重構。“想象力消費”所提供的也正是這樣一種可能的探索。全新的想象力是怎樣被生產并被消費的,這種生產和消費與80年代以來人文主義時代的生產和消費有何不同?這些都是“想象力消費”涉及的面向。
總體而言,作為當下最重要的課題之一,“想象力消費”包含著諸多亟待思考和解答的疑問。這個植根于電影,卻又超越電影的概念,以電影為起點,同時指向更宏大的層面。與電影相關的首先是“電影是什么”,繼而是“我是誰”,以及如何建構我們的身份等等。這個相互遞進的追問,需要在層層剝離和反思中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