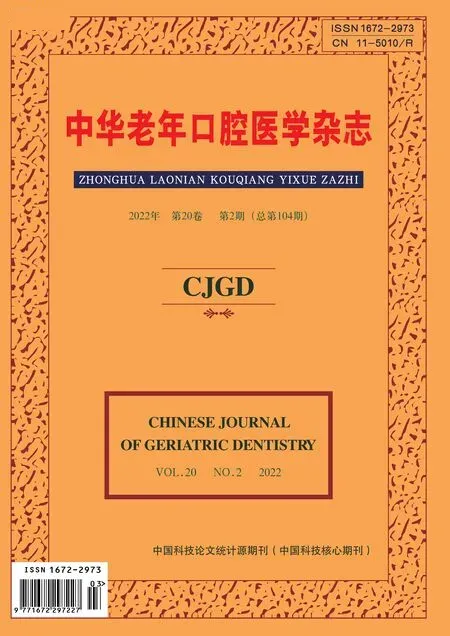慢性牙周炎與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相關性的研究進展*
胡穎哲 徐全臣
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NDD)在老年人中發病率逐年提高。NDD 的具體發病機制尚不明確,目前無有效的預防和治療措施[1]。研究表明,全身免疫系統的持續性炎癥會對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產生有害影響,繼而引發神經炎癥,加速衰老過程中神經功能的惡化[2]。慢性牙周炎(Chronic periodontitis,CP)作為一種局部感染性疾病可通過多種途徑引發全身炎癥反應,從而影響CNS 的穩態平衡[3]。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CP 和神經系統退行性變之間存在著某些緊密的聯系,預防或控制CP 的發生發展或許是預防或改變NDD 進程的潛在策略。本文就CP 與常見NDD 之間的相關性及其影響神經系統的可能方式作一綜述。
1.NDD
NDD 是由于機體特定神經元結構或功能逐漸喪失,進而導致認知和運動功能障礙的一類不可逆轉的神經系統疾病,主要包括阿爾茨海默癥(Alzheimer’s disease,AD)、帕金森癥(Parkinson’s disease,PD)和多發性硬化癥(Multiply sclerosis,MS)等。此類疾病以蛋白的錯誤折疊和沉積、突觸功能障礙、自噬異常與缺失以及炎癥為共同病理特征,臨床主要表現為認知功能降低、癡呆及運動功能喪失,多發于老年人[4]。
2.CP
CP 是一類以牙齦炎癥、牙周袋形成、牙槽骨吸收、牙齒松動為主要臨床特征的慢性感染性疾病,是成年人失牙的首要原因[5]。2017 年第四次全國口腔健康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各年齡組人群的牙周患病率居高,中年和老年人群中牙周健康者分別僅為9.1%和9.3%。醫學的迅速發展使人們逐漸意識到牙周病不再是單純的口腔疾病,而與各種全身系統性疾病緊密相關[1]。
菌斑微生物是CP 的始動因子。牙周袋內的細菌成分和結構復雜,牙齦卟啉單胞菌(Porphyromonasgingivalis,Pg)是CP 的優勢致病菌。CP 的發生發展過程中,細菌及其毒性產物和牙周局部組織產生的炎性介質可直接通過牙周袋內壁進入循環系統,導致菌血癥或內毒素血癥從而進一步加重全身系統性疾病;或是間接調節宿主免疫功能從而引起全身炎癥反應[6]。
3.CP 與常見NDD的相關性
3.1 AD 2020 年一項Meta 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牙周炎患者更易發生癡呆癥,預防和治療牙周炎有助于控制全球癡呆癥的流行[7]。一項包含27963 名50 歲中老年人的回顧性隊列研究發現,與牙周健康組相比,具有10 年牙周病史的受試者患AD 的風險大大增加[8]。有學者調查了各年齡組受試者中癡呆癥的發病率[9,10],發現30 歲以上的牙周病患者更易于患癡呆癥,且70 歲以上年齡組癡呆癥發病率最高,但在20~29 歲年齡組中未發現癡呆癥患者。以上結果提示牙周炎是導致癡呆和認知障礙的潛在危險因素之一,老年牙周炎患者更易出現認知功能降低。
AD 以神經細胞外β-淀粉樣蛋白(Amyloid β-protein,Aβ)的異常沉積為典型病理特征。2018 年的一項研究首次證明,成年小鼠在反復口服Pg 后導致神經變性和神經細胞外Aβ 的形成,提示低度慢性牙周病原體感染可導致與AD 一致的神經病理學發展[11]。研究人員用二維差分凝膠電泳分析CP 患者和對照組的血清樣品,發現AD 和CP 之間存在直接血清蛋白聯系,為兩者之間的相關性提供了直接證據[12]。
牙周治療干預后,AD 患者的記憶力得到改善,更好地管理牙周細菌能夠預防AD 發生[13]。最新研究發現,在口服感染Pg 的小鼠大腦及腦脊液中顯示Pg 浸潤,給予其口服牙齦蛋白酶抑制劑可降低其腦部Pg-DNA 的含量、減輕神經毒性作用,抑制牙齦蛋白酶或許能夠成為治療AD 的潛在策略[14,15]。
CP 和AD 之間的聯系已逐漸被學者們所關注,成為研究熱點。二者皆為老年人群高發疾病,究竟是CP 促進了AD 的發展,還是AD 促進CP 的發生,抑或是二者相互影響推動病程發展,仍未得知。且目前研究中并未完全排除年齡及性別因素對這兩種疾病的影響,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來進一步探索這兩種疾病之間的因果關系。由于CP 的發展可以通過牙周系統治療等方式進行有效的控制,因此學者們期望通過治療CP 進而緩解AD 的癥狀,為未來治療AD 探索新道路。
3.2 PD PD 在65 歲以上的人口中發病率達到2%~3%,在常見NDD 中位居第二,以含有α-突觸核蛋白聚集體的細胞內包裹體為典型神經病理學特征[16]。研究人員調查了45例輕度PD 患者和45例同年齡非PD 患者的口腔健康狀況,發現PD組的缺牙數和牙周病的患病率皆顯著高于非PD組[17]。將伴有牙周炎的PD 患者的血液和標準生化指標與無牙周炎的PD 患者進行比較,結果顯示兩組之間白細胞和分葉嗜中性粒細胞的指標存在明顯差異[18],皆提示牙周炎和PD 之間存在潛在聯系。
最新研究表明牙周炎引起的全身性低度炎癥可能在PD 的早期導致神經功能障礙,這為學者們探索兩者間的作用機制提供了新的思路[19]。迄今雖無直接證據證明CP 在PD 的發病機制中起作用,但充分研究表明慢性神經炎癥與PD 的病理生理密切相關[16]。CP 很可能通過局部炎癥-全身炎癥-神經炎癥這一途徑影響PD 的發生發展,而PD 患者的運動功能及認知障礙也同樣妨礙其對于日常口腔衛生的維護,從而增高牙周病患病風險。兩者之間究竟如何相互影響需進一步研究,兩者之間的相關性也需要更加充分的證據證明。
3.3 MS MS 是一種常見的CNS 特發性炎性脫髓鞘疾病,與機體的自身免疫有關,白質周圍T淋巴細胞、巨噬細胞浸潤,并伴發局部脫髓鞘病變,最終引發MS[20,21]。T 淋巴細胞在MS 的發生發展中發揮關鍵作用,其中T 淋巴細胞各亞群功能之間的平衡喪失是導致MS 的直接原因。CD4+T細胞受到激活后分化為Th17 細胞亞群并分泌其特有的細胞因子IL-17,誘導自體免疫反應,引發一系列神經炎癥[22]。在CP 進展過程中,T 淋巴細胞同樣發揮重要作用:受到特異性抗原信號刺激的CD4+T 細胞分化為Thl、Th2、Th17、Tregs 等細胞亞群,并且研究人員發現IL-17 這一細胞因子在Th17 細胞亞群中明顯高表達。活化后的T 淋巴細胞與牙周致病菌、炎癥因子及其他免疫細胞共同介導牙周炎癥反應[23]。
2013 年曾有研究表明CP 與MS 之間存在關聯,但這一結論2 年后被另一項研究所推翻[24,25],直至今日,仍缺乏對于CP 與MS 兩者相關性的研究。但根據上述T 淋巴細胞在這兩種疾病各自發生發展中的作用,CP 與MS 的發病機制可能在機體的某些免疫反應或炎性通路上存在交叉,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有待進一步研究。
4.CP 影響CNS 的可能方式
4.1 血液循環途徑 牙周炎發生發展過程中,牙周致病菌及其毒性產物可通過血液循環影響CNS并損害其功能[3]。
在UAV+RFID技術中,UAV路徑規劃問題是關鍵性技術,合理規劃路徑能夠使UAV在庫存信息采集過程中有效規避障礙物,采集到在制品數據信息,且得到一條最優化的盤點路徑。
4.1.1 直接途徑 感染口腔紅色復合體細菌(牙齦卟啉單胞菌、福賽坦氏菌、齒垢密螺旋體)的小鼠腦中被檢測到Pg-DNA 序列,證實Pg 能夠突破血腦屏障進入大腦[15]。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LPS)是Pg 分泌的一種重要毒力因子,研究發現Pg-LPS 能夠進入腦組織并上調大腦皮層炎癥細胞因子的表達,導致小鼠的記憶和學習障礙[26]。于CP 患者而言,常規的拔牙、牙周手術、刷牙甚至使用牙線,都可能導致口腔致病菌進入全身血液循環,從而對CNS 產生影響。
4.1.2 間接途徑 口腔病原微生物及其代謝產物可誘導全身免疫炎癥反應,循環系統中的炎癥因子水平的上升可激活CNS 炎癥級聯反應,誘導神經膠質細胞分泌大量的促炎細胞因子如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1、6 和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 等,造成腦細胞炎性損傷和壞死[3,27]。最新研究證實革蘭氏陰性細菌能分泌一種直徑20~250nm 的外膜囊泡(outer membrane vesicle,OMV),其含有豐富的細菌LPS 并可調節機體免疫反應[28]。牙周致病菌可能通過這一間接途徑參與CNS 免疫反應。
除上述外,近期研究發現以Pg 為代表的革蘭氏陰性細菌表面存在一種外膜蛋白——孔蛋白,它能夠從細菌胞漿移至細胞膜外,并控制細胞膜上小溶質的通過,影響細胞代謝[29]。學者們由此推測這或許是細菌誘導神經元凋亡的途徑之一。
盡管很多研究證明牙周致病菌可通過血液循環途徑影響CNS,但仍有學者對其存在異議,具體發生機制尚需更深入的研究。
4.2 神經旁路途徑 口腔病原菌可通過與大腦相連的三叉神經、嗅覺神經和面神經等進入大腦,周圍神經在將致病微生物運送至CNS 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30]。螺旋體是一種具有高活動性的革蘭陰性細菌,能夠沿神經纖維移動,具有較強的親神經性。研究人員在AD 患者的大腦中檢測到6 種口腔密螺旋體,由此提出口腔密螺旋體可能通過三叉神經的分支感染大腦[31]。
4.3 軟腦膜細胞介導途徑 學者們發現,軟腦膜細胞在將全身炎癥信號轉移至小膠質細胞(microglia,MG)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由此提出一條由全身炎癥誘導CNS 神經炎癥的新路徑,即軟腦膜細胞介導路徑[32]。
MG 是CNS 駐留免疫細胞,MG 功能紊亂可引起或加重神經元損傷,其介導的神經炎癥是神經退行性變的重要機制之一[33]。Liu 等首次提出巨噬細胞可分泌炎性物質作用于軟腦膜,誘使其釋放出相應的促炎因子,刺激CNS 內的MG[34]。Pg-LPS刺激后的軟腦膜細胞進一步處理MG,與單純用Pg-LPS 處理的MG 相比,前者TNF-α 和IL-1β的mRNA 表達水平顯著增加,說明軟腦膜細胞分泌的細胞因子在MG 活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支持軟腦膜在外周炎癥影響神經系統炎癥過程中發揮信使功能[34]。牙周致病菌及其產物通過刺激軟腦膜細胞釋放炎癥因子,使MG 發生活化并產生TNF-α、IL-1β 等。其中TNF-α 在神經炎癥、血腦屏障破壞、脫髓鞘等病理改變中發揮重要作用,參與了NDD 的發生發展[27,34]。
除神經毒性作用外,軟腦膜細胞還可刺激MG分泌IL-10 等抗炎因子,與促炎因子一同調節CNS內的免疫平衡[35]。
綜上所述,軟腦膜細胞在外周炎癥影響神經炎癥的過程中可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牙周致病菌或許可通過軟腦膜細胞介導路徑影響CNS。雖然目前有關該途徑的研究為數不多,為探索牙周炎與NDD 的相關性開辟了新方向。
4.4 NLRP3 炎癥小體途徑 炎癥小體是先天性免疫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先天性免疫介導的神經炎癥在NDD 的發生發展中發揮關鍵作用。激活的NLRP3 炎癥小體活化MG 并使其分泌IL-1β 和IL-18,進而引發神經炎癥,被認為是NDD 中最具特征的炎癥體[36]。
NLRP3 的激活有助于Aβ 的積累,在AD 的發生發展中發揮關鍵作用。敲除NLRP3 基因的小鼠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空間記憶喪失和其他與AD相關的后遺癥,檢測發現其大腦中IL-1β 的水平降低,Aβ 的清除率提高[37],提示通過抑制NLRP3炎癥體活性或許能有效地干預AD 的進展。另有研究發現抑制NLRP3 激活可減少大腦的MG 焦亡,減輕神經元功能損傷,進而改善大腦認知功能[38]。
Yamaguchi 等首次證明了Pg 通過激活NLRP3引發炎癥反應,促進牙周病的發展[39]。與健康人相比,CP 患者的牙周組織和唾液中NLRP3 及齦溝液中IL-1β 的表達明顯增高[40]。
已有研究發現肺內NLRP3 激活引起的外周炎癥可引發腦內神經炎癥,從而擴大中樞炎癥反應,加重腦內多巴胺能神經元的退化[41]。那是否有這樣的可能:CP 的發生激活牙周組織內NLRP3 小體,引發外周炎癥繼而導致神經炎癥,損害CNS;或是牙周致病菌(如Pg)進入CNS 直接激活腦內NLRP3炎癥小體,活化MG 進而引發神經炎癥,導致神經元的損傷。目前并無相關研究報道,未來仍需要進一步探究。
4.5 微生物-腸-腦軸途徑 微生物-腸-腦軸是將大腦和腸道功能整合的雙向信息交流系統,涉及免疫、內分泌及神經通路機制。腸道菌群結構的改變可能導致機體免疫功能障礙和穩態失衡,從而引發多種系統性疾病。近年來大量對微生物-腸-腦軸的研究表明,腸道微生物參與調節人類行為和認知,其失衡可能導致神經炎癥和認知障礙[42]。
口腔作為消化道的起點,其菌群失衡會誘導腸道微生物群組成、屏障功能和免疫系統發生變化,從而導致以全身低度炎癥為特征的疾病風險增加。有研究發現口內涂布Pg 的小鼠腸道菌群發生變化、腸緊密連接蛋白mRNA 表達降低以及血清內毒素水平升高,由此支持因口腔菌群失調引起的腸道微生物改變介導全身性疾病這一假說[43]。動物實驗發現,在建立小鼠實驗型CP 模型1 年后,CP 組小鼠大腦神經元突觸受到損傷、MG 被激活,并伴有進行性認知障礙,并且其唾液和糞便的微生物多樣性明顯高于正常組,證明CP 影響口腔和腸道菌群的結構。進一步研究發現,CP 組小鼠血清中LPS的濃度顯著增加且血腦屏障受到損傷,這表明CP誘導的腸道菌群失調和引發的全身炎癥能夠損傷血腦屏障,導致神經元損傷[44]。這一發現為微生物-腸-腦軸在CP 與AD 關系中的可能作用提供了直接證據。
目前研究已證明牙周炎與腸道菌群、腸道菌群與神經系統以及牙周炎與神經系統之間各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然而對于這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及作用機制的研究仍處于空白。未來的研究可著重于探索CP、腸道菌群及NDD 之間的關系及可能的相關機制,或許能通過微生物-腸-腦軸這一途徑防治與CP 相關的認知功能障礙。
5.小結與展望
CP 可能通過調節宿主全身免疫反應參與NDD的發生發展,牙周致病菌及細胞因子可通過血液循環、神經旁路等多種途徑影響CNS,造成神經元的損傷。雖然AD、PD 及MS 的臨床表現略有差異,但三者所導致的認知及行為功能障礙皆能影響患者對于日常口腔衛生保健的實施,從而引發或加劇患者牙周疾病。NDD 和CP 皆為老年人群高發疾病,如何完全排除年齡因素對于兩者相關性研究的干擾,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研究難題。由于目前對于NDD 發病和進展機制的認識有限,且缺少研究資料來證實和闡明CP 影響NDD 的具體機制,因此未來研究一方面應著重于為二者是否存在相關性及具體作用機制繼續尋找直接證據;另一方面可嘗試對NDD 患者進行牙周干預治療并觀察其治療效果及預后,從而為NDD 患者的治療方式尋找新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