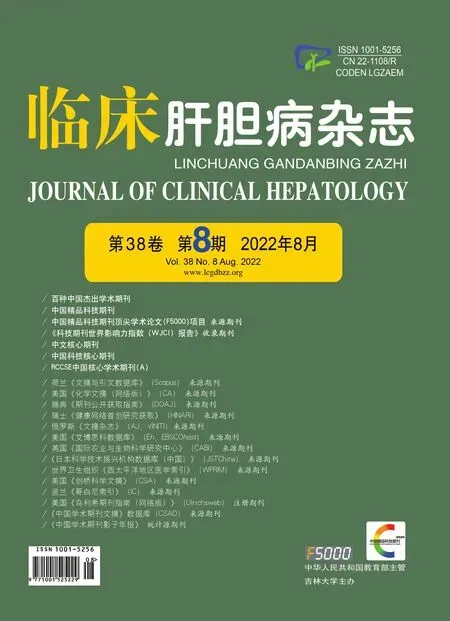肝癌微環境靶向與免疫治療的研究現狀
朱明強, 丁佑銘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 肝膽外科, 武漢 430060
肝癌惡性程度高,預后差,是全球死亡率第三位、發病率第四位的常見惡性腫瘤[1]。目前,肝癌治療的首選治療方法仍是肝切除術和肝移植,但術后的復發率高。肝癌表型和分子異質性使其對常規化療和靶向治療具有高度耐藥性。失去手術機會的肝癌復發患者往往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肝癌細胞與其微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已成為當前研究的熱點。肝癌微環境主要由腫瘤細胞、腫瘤浸潤性淋巴細胞(tumor infiltration lymphocytes,TIL)、腫瘤相關成纖維細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CAF)、肝星狀細胞(HSC)、腫瘤相關中性粒細胞(tumor-associated neutrophils,TAN)、內皮細胞等細胞組分以及細胞外基質(ECM)、細胞因子、趨化因子、蛋白質和蛋白水解酶等非細胞成分構成[2]。TIL包括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T淋巴細胞、B 淋巴細胞、自然殺傷細胞(NK細胞)和髓源性抑制細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和發揮抗原呈遞作用的樹突狀細胞(DC)等,參與腫瘤免疫反應,調控腫瘤生長、轉移[3]。TIL的細胞亞群具有促腫瘤和抗腫瘤的雙向作用,靶向肝癌微環境治療肝癌越發被關注。免疫治療可激發腫瘤特異性免疫,打破免疫耐受來識別并殺傷腫瘤細胞,進而延緩腫瘤進展。本文將闡述肝癌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的特征、TME組分在肝癌進展中的作用以及靶向TME治療的研究進展。
1 肝癌微環境的特征
肝癌微環境的特征包括:(1)缺氧。缺氧是所有實體瘤的共性,缺氧誘導因子(HIF)信號通路參與炎癥反應、免疫抑制、激活多種促癌生物效應。HIF可導致調節性T淋巴細胞(Treg)與巨噬細胞聚集,促進索拉非尼耐藥,是肝癌診斷、預后和復發的潛在生物標志物[4]。(2)免疫抑制。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CTL)、NK細胞和單核細胞發揮抗腫瘤作用。TAM、MDSC和Treg介導了免疫抑制的TME,幫助腫瘤細胞免疫逃逸,促進肝癌的惡性發展。(3)炎癥反應。炎癥環境利于循環腫瘤細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轉移的播種存活和增殖轉移。腫瘤細胞Toll樣受體信號通路上調IL-6的表達和缺氧促進了腫瘤的炎癥反應,促進腫瘤抵抗、增殖和侵襲[5]。(4)血管生成。CAF釋放基質細胞衍生因子、促血管生成因子等,促進腫瘤生長和血管新生,導致肝癌晚期轉移。(5)淋巴管生成。淋巴道是腫瘤轉移的主要途徑之一,淋巴管生成是腫瘤轉移的重要基礎。臨床資料表明,腫瘤源性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A/D誘導局部淋巴管轉移,并與局部淋巴管轉移有關[6]。(6)親器官性。肝癌轉移多見于肝內轉移和肺轉移,這可能與腫瘤來源的炎性因子改變定植部位黏附分子和ECM成分有關。富集不同分子和細胞成分使腫瘤轉移具有不同親器官性。(7)異質性。免疫和藥物等多種刺激使肝癌微環境產生瘤內異質性。當微環境細胞死于凋亡,癌細胞前體發展成肝癌。當周圍細胞死于壞死,前體細胞發展成肝內膽管癌[7]。肝癌微環境在不同空間具有異質性,即形成熱腫瘤和冷腫瘤。單中心起源的多發性肝癌,微環境巨噬細胞多,異質性弱;多中心起源,微環境CD8+T淋巴細胞多,微環境間異質性強[8]。原初腫瘤與次生腫瘤基因與表型也不同。早期復發肝癌表現為Treg細胞減少,DC和CD8+T淋巴細胞增加,CTL處于低細胞毒性和低耗竭狀態[9]。(8)可塑性。上皮-間充質轉化和典型干細胞脫分化狀態等機制參與可塑重編程,這是侵襲性和化療抵抗的驅動因素。癌細胞狀態對TME的反應是可塑的,改變TME可以將腫瘤細胞從一種狀態驅動到另一種狀態,藥物敏感性也隨之改變。
2 TME與肝癌的發生發展
2.1 HSC和CAF HSC緊貼著肝竇內皮細胞和肝細胞,是ECM的主要來源。正常情況下HSC處于靜止狀態,肝損傷時HSC激活為肌成纖維細胞,在肝癌發展過程中,經EMT和TGFβ的作用可有效轉化生成CAF[10]。活化的HSC與免疫細胞相互作用,抑制T淋巴細胞的增殖及促進肝癌發展及肝癌切除術后早期復發[11]。HSC通過PGE2破壞 NK 細胞功能以及抑制HSC誘導的MDSC在腫瘤組織中蓄積從而抑制肝癌的生長[12]。HIF-1α、TGFβ、外泌體等可以誘導CAF細胞FAP和α-SMA的表達[13]。CAF活性受腫瘤細胞分泌的生長因子調控,CAF激活后可以自身分泌趨化因子,誘導ECM各細胞類型的募集,構成ECM成分,促進腫瘤血管生成。Ji等[14]發現手術切除殘存結直腸腫瘤組織可釋放攜帶整合素β亞基樣蛋白1的胞外囊泡,激活NF-κB信號通路促進CAF轉化,進而促進癌細胞的肝轉移。
2.2 腫瘤浸潤性淋巴細胞
2.2.1 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AM) TAM可分為M1經典激活型和M2替代激活型。M1型巨噬細胞抑制腫瘤、促進炎癥及發揮免疫活性作用,M2型巨噬細胞則起到組織修復、免疫逃逸及促進腫瘤進展。有研究[15]發現一種新型的“生化開關”,從糖酵解途徑分支出來,為快速細胞增殖和分化提供原材料,抑制該途徑可抑制M2極化和增殖。同時,SHH-Hedgehog信號軸可促進TAM極化來抑制CD8+T淋巴細胞的增殖[16]。TAM中RIPK3的缺乏通過重編程代謝,促進脂肪酸氧化以及誘導M2極化,地西他濱調節脂肪酸代謝和增強TAM的抗腫瘤免疫來治療肝癌[17]。Sharma等[18]研究表明胚胎肝臟發育與肝癌生態系統之間存在一個共享程序,即胎-瘤重編程。TAM及相關因子能促進肝癌的侵襲和轉移,導致肝癌進展和肝切除術后復發,降低術后生存率和無病生存率[19]。
2.2.2 腫瘤相關淋巴細胞 CTL細胞接受CD4+輔助性T淋巴細胞(Th)的指令來識別異常細胞和激活細胞毒活性。高活化DC能為CTL提供IL-15、CXCL16等生存信號,幫助CTL在TME中聚集,使CTL能夠存活足夠長的時間以有效地消除癌細胞[20]。實體腫瘤內抗腫瘤T淋巴細胞浸潤極少,而浸潤的T淋巴細胞以促腫瘤的Th2和Treg為主。Huang等[21]發現IFN-STAT1通路轉錄上調了RGS1,RGS1抑制了CTL和Th1細胞遷移至腫瘤的能力。在代謝物缺乏等條件下,Treg細胞通過剝奪效應T淋巴細胞的營養、替代代謝物乳酸和增強氧化應激損傷抵抗力幫助腫瘤免疫逃逸。Treg免疫抑制并非傳統的抑制因子的表達,而是通過CD39/73的釋放并將ATP轉化為腺苷,氧化應激引發的Treg細胞凋亡降低了阻斷PD-1介導的抗腫瘤治療效果[22]。B淋巴細胞產生的抗體可通過抗體依賴性細胞毒作用、補體激活和增強DC抗原呈遞等促進抗腫瘤免疫。B淋巴細胞有助于腫瘤相關三級淋巴結構的形成,這支持腫瘤特異性B淋巴細胞的進一步成熟和亞型轉換,以及腫瘤特異性T淋巴細胞反應的發展。腫瘤浸潤性B淋巴細胞發揮促腫瘤和抗腫瘤作用取決于TME的組成、B淋巴細胞表型及其產生的抗體。
2.2.3 NK細胞 NK細胞屬于天然淋巴細胞,通過穿孔素/顆粒酶的胞吐作用、結合FASL/RAILR和分泌IFNγ、TNFα非特異性直接殺傷腫瘤細胞。根據CD56的表達可以將NK細胞分為兩個亞群:CD56dim和CD56bright。CD56dim亞群是成熟的細胞毒性細胞,占血液中的大多數;CD56bright亞群則并不成熟,細胞毒性較小,位于次級淋巴器官,負責免疫調節[23]。NK細胞在TME中浸潤少,細胞功能明顯被抑制。NK細胞亞群的遷移受趨化因子和趨化因子受體表達譜的調控。肝內CD56+NK細胞表達多種趨化因子受體CCR5和CXCR6,其參與NK細胞在肝臟的駐留[24]。TME能夠改變局部趨化環境,優先招募細胞毒性較小的NK細胞。果糖-1,6-二磷酸酶通過抑制NK細胞糖酵解代謝從而削弱NK細胞功能,腺苷可以限制NK細胞的成熟和功能,所以,靈活底物提高細胞毒性免疫細胞的代謝能力是一種有前途的治療策略[25]。
2.2.4 髓源性抑制細胞(MDSC) MDSC是一群由分化狀態各異的不成熟髓源性組成的異質性群體,可發揮免疫抑制功能,包括抑制T淋巴細胞激活、使激活的T淋巴細胞失能、抑制NK細胞的細胞毒性、使巨噬細胞向促進腫瘤生長的表型極化等。MDSC由共同髓系祖細胞發育而來。MDSC可分成兩大亞群:單核MDSC和多核MDSC。MDSC在正常狀態下分化為巨噬細胞、粒細胞和DC細胞,在炎癥、腫瘤等疾病狀態下迅速擴增,分化為免疫抑制性腫瘤相關巨噬細胞[26]。MDSC競爭性消耗微環境半胱氨酸,上調iNOS和ARG-1,使T淋巴細胞生成受阻以及誘導Treg擴增來增強負調控作用,通過產生ROS下調NKG2D的表達,抑制 NK 細胞的功能[27]。在單核MDSC中還發現KRAS突變抑制IRF2,導致CXCL3的抑制被解除,可召集MDSC抑制殺傷性T淋巴細胞[28]。
2.2.5 樹突狀細胞(DC) DC是目前功能最強的抗原呈遞細胞,體內DC多處于非成熟狀態,具有極強的抗原內吞能力。DC除激活T淋巴細胞抗腫瘤外,還能刺激B淋巴細胞成熟和Th細胞、NK細胞活化。DC傳統上分為cDC1和cDC2。cDC1由髓樣干細胞在粒細胞-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的刺激下分化而來,也稱為髓樣DC;cDC2源于淋巴樣干細胞,與T淋巴細胞和NK細胞有共同的前體細胞,也稱為淋巴樣DC;DC經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MHC)-Ⅰ/Ⅱ類途徑呈遞捕獲的抗原,同時誘導共刺激信號B7/CD28等充分活化CTL來發揮抗腫瘤免疫反應[29]。關于DC傳遞抗原的形式,眾說紛紜。有研究[30]認為DC通過外泌體囊泡激活T淋巴細胞。在肝癌中,存在一群表征特殊的LAMP3+DC,主要表達CD80/83、CCR7 等與成熟和細胞遷移有關的基因,具有向肝淋巴結遷移的潛在能力。LAMP3+DC可吸引T淋巴細胞,通過CD86-CD28作用于Treg亞群、CD86-CTLA4作用于耗竭性T淋巴細胞亞群[10]。
2.3 腫瘤相關中性粒細胞(TAN) 腫瘤組織產生趨化因子,中性粒細胞在趨化因子的作用下通過血管壁進入腫瘤組織,這些浸潤的中性粒細胞即TAN。TME可通過釋放趨化因子CXCL1/2/5/6/8、CCL3/5與CXCR1/2結合趨化外周血中的中性粒細胞到達腫瘤局部微環境中[31]。TAN具有雙重作用,通過驅動血管生成、ECM重構和免疫抑制等發揮促瘤生長作用,通過產生ROS、RNS或直接殺死腫瘤細胞等方式介導抗腫瘤反應。在IFNβ、IL-1β等作用下,中性粒細胞向N1極化。N1型為短壽命、成熟型、高毒性,可促進CTL活化。在 TGFβ、IL-6/7/8作用下,中性粒細胞向N2極化,N2型為長壽命,不成熟型,低毒性,促進腫瘤的生長及轉移[32]。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是反應免疫系統功能的一項指標,是影響肝癌患者預后的獨立因素[33]。循環腫瘤細胞-中性粒細胞簇與循環腫瘤細胞相比,細胞周期和DNA復制通路基因明顯上調,細胞增殖加快,循環腫瘤細胞的轉移潛能提升[34]。
2.4 腫瘤血管內皮細胞 腫瘤血管的生成以從頭生成和血管芽生為主。血管生成的過程包括啟動、增殖和遷移、成熟。影響血管生成的因素主要包括:(1) HIF-1。(2)促血管生成因子,如VEGF、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等。(3)抑制血管生成因子,如血管生成抑素、內皮抑素等。(4)ECM,有膠原蛋白,層粘連蛋白等。缺氧使SDF1和CXCR4在血管內皮細胞上調,誘導腫瘤細胞與血管內皮細胞的黏附,刺激腫瘤細胞跨內皮遷移[35]。VEGF是最強的促血管生成因子,可招募TAM間接刺激血管生成。Zhang等[36]發現DLL1可通過激活CD8+T淋巴細胞來誘導長效腫瘤血管正常化,進而創造一個促進抗腫瘤免疫反應的微環境。Zhao等[37]證實CDP-二酰基甘油合成酶-2(CDS2)基因缺失,將VEGFA信號傳導的輸出從促進血管生成切換到誘導血管退化,這其實是取決于特定的內皮代謝狀態和信號傳導的相互交流。
2.5 TME非細胞組成 ECM 由膠原蛋白、蛋白多糖、層粘連蛋白和網絡連接蛋白等組成,為腫瘤細胞提供生化成分和基本結構支持,還負責細胞間通訊、參與細胞增殖和黏附。膠原沉積和成纖維細胞浸潤導致結締組織增生,與患者預后不良密切相關。肝癌細胞通過趨化因子的作用可促進肝癌進展。缺氧條件下的糖酵解活性增強會增加乳酸的積累,乳酸脫氫酶與腫瘤大小和臨床嚴重程度呈正相關。乳酸可通過降低T淋巴細胞增殖、IFNγ的產生來抑制效應T淋巴細胞功能,同時,低pH可顯著促進DC分化,這些細胞減少葡萄糖消耗,上調線粒體呼吸基因和抑制mTORC1活性。低糖誘導FOXP3的表達,增加T淋巴細胞從效應T淋巴細胞向Treg的分化。糖酵解代謝的加速增加了腫瘤源性GM-CSF的產生進而促進MDSC的浸潤。脂質、脂肪因子可促進腫瘤細胞的黏附、遷移和侵襲,影響腫瘤惡性進展[38]。
3 靶向肝癌微環境治療
3.1 靶向TME組分
3.1.1 靶向CAF 靶向CAF方法包括殺傷CAF、抑制CAF活化、干擾CAF功能。以納米載體靶向細胞毒性藥物(吖啶黃、紫杉醇)和腫瘤疫苗可選擇性殺傷CAF[39]。通過阻斷TGFβ/Smad/ROS激活信號、逆轉表型可抑制CAF的活化[40]等。抗纖維化藥物、細胞因子阻滯劑可干擾CAF細胞因子的分泌。有研究[41]以脂質體為載體遞送質粒DNA和siRNA,阻斷CAF與腫瘤細胞Wnt信號和CXCL1的信息交流,抑制了IL-6、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產生,抑制了腫瘤的進展,通過阻斷CAF分泌囊泡是治療肝癌耐藥的一種方法。
3.1.2 靶向慢性炎癥 TAM通常表現出M2樣表型,靶向M2細胞或將M2重編程為M1細胞可抑制肝癌進展。CSF-1是TAM主要調節因子,在腫瘤細胞含量高多提示預后不良。CSF-1R激酶抑制劑BLZ945減少M2型極化,阻止腫瘤進展并改善小鼠的存活率[42]。GM-CSF可刺激TAM和DC的抗原呈遞,進而刺激抗體依賴性細胞毒作用。肝癌細胞TAM增多與血管侵犯、衛星灶、淋巴結轉移呈正相關,術后生存率降低[43]。TAN是不良的預后指標,靶向TAN能抑制腫瘤進展。TGFβ調節TAN的促腫瘤和抗腫瘤雙重表型,因此,TGFβ和趨化因子的阻斷可能是潛在的有效治療策略。細菌外膜囊泡包被納米顆粒形成仿生納米病原體(NPN),攜帶此病原體的中性粒細胞可主動趨化至光熱治療的炎癥腫瘤部位,中性粒細胞胞膜破裂使釋放出的NPN通過其包載的順鉑有效殺死殘存的腫瘤細胞,達到完全清除腫瘤的效果[44]。
3.1.3 靶向腫瘤血管生成 血管生成和抗血管生成分子介導的信號不平衡導致血管異常,使腫瘤逃避免疫系統的攻擊,其中,VGEF和血管生成素-2可見明顯升高。目前有許多的血管生成抑制藥物被批準用于臨床治療。抗VEGF-VEGFR藥物大致包括以下幾類:直接靶向VEGF和VEGFR蛋白的抗體藥物,例如貝伐單抗等;酪氨酸激酶信號通路抑制劑,例如索拉非尼等;還有融合蛋白以及免疫調節劑等類型的藥物。結合臨床可以發現,血管生成抑制劑的臨床效益其實并不明顯,有治療局限性,而原因可能是因為調控血管生成網絡,涉及多個蛋白或信號通路,單靶藥物抑制某一蛋白后,血管生成出現代償性現象以及腫瘤患者體內新生血管結構不完整,通透性較差,一些治療藥物也不能有效地達到病灶部位。
3.1.4 靶向細胞外組分 酸性條件使相關基因表達非正常剪接的蛋白質形式,幫助細胞遷移到血管,針對性降低局部酸度的方法可能干擾腫瘤生長和轉移[45]。基于酸性pH開發選擇性抗體及嵌合抗原受體T淋巴細胞(CAR-T)治療技術更具靶向性,攜帶pH敏感信號的納米成像診治技術將開發出對肝癌更有效的納米診斷和療法。肝癌細胞來源的外泌體(EV)可觸發HGF/c-Met/Akt信號通路,在抑制索拉非尼誘導的細胞凋亡和促進肝癌耐藥方面發揮作用[46]。EV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低免疫原性和低毒性等優點,開發精確設計EV的方法將有助于EV抗腫瘤治療。靶向代謝也為腫瘤治療提供良好的方向。抑制糖酵解調節酶或使用競爭性葡萄糖類似物以及抑制脂肪酸合酶可用于腫瘤治療,間接影響免疫細胞的功能,同時,靶向代謝通信應考慮腫瘤類型、分期、位置和潛在的補償機制[47]。
3.2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腫瘤疫苗 目前上市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主要是CTLA-4抑制劑和PD-1/PD-L1抑制劑。伊匹單抗是首個獲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的CTLA4抑制劑。PD-1抑制劑有納武利尤單抗、帕博利珠單抗、卡瑞麗珠單抗;PD-L1抑制劑有阿替利珠單抗和度伐利尤單抗等;阿替利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在歐美和我國獲批用于治療既往未接受過系統治療的不可切除肝癌患者,是晚期肝癌一線治療的優選治療方案。伊匹木單抗+納武利尤單抗, 帕博利珠單抗已獲批用于肝癌的二線治療。目前,針對肝癌靶點的疫苗主要包括異種重組甲胎疫苗、DC疫苗和溶瘤病毒疫苗。成纖維細胞活化蛋白靶點的DNA疫苗可改變腫瘤間質,協同腫瘤抗原特異性DNA疫苗可提高抗腫瘤作用[48]。DC腫瘤疫苗將體外誘導或構建的可特異性識別腫瘤的DC細胞回輸入腫瘤患者體內,激活T淋巴細胞對腫瘤的免疫反應。盡管DC疫苗在國內被提及的比較少,但國際上已有幾款DC疫苗獲批上市,用于乳腺癌、前列腺癌與肝癌的治療。溶瘤病毒聯合CAR-T療法可彌補CAR-T單獨作戰的缺陷,在實體腫瘤治療方面產生較強的協同效應[49]。
3.3 嵌合抗原受體T淋巴細胞(CAR-T) CAR-T是將能識別某種腫瘤抗原的抗體的抗原結合部與CD3或FcR的胞內部分在體外偶聯為一個嵌合蛋白,通過基因轉導的方法轉染患者T淋巴細胞,使其表達嵌合抗原受體。“重編碼”T淋巴細胞具有腫瘤特異性。肝癌過繼細胞治療常見的靶點包括:甲胎蛋白、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黑色素瘤抗原基因-1/3、人端粒酶逆轉錄酶、VEGF、上皮細胞黏附分子、NK組2成員D配體等,相關靶點的CAR-T治療肝癌的臨床研究有相應的報道。在實體瘤中,過表達BATF轉錄因子可以阻斷CAR-T的耗竭,增強CAR-T的增殖能力和毒性,并形成記憶細胞,提供長期的腫瘤治療效果[50]。由于TME免疫抑制和物理屏障限制T淋巴細胞接觸腫瘤細胞(運輸和歸巢)、腫瘤異質性和抗原丟失、工程T淋巴細胞擴增和持續性有限、抗原脫靶嚴重毒性反應等原因,腫瘤出現免疫逃逸以及導致復發或治療無效。因此,聯合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局部經肝動脈給藥等方法將能極大的提高過繼免疫細胞治療的療效。聯合治療包括免疫+放化療、免疫+靶向等。
4 小結
微環境細胞呈現連續、可逆、動態網絡。開發新技術,明確微環境復雜的細胞成分及其作用、鑒定新亞群和新治療靶點對更全面了解肝癌的發生發展機制具有重要意義。肝癌微環境的異質性和患者靶向與免疫療法的不同響應率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通過對肝癌免疫微環境進行分型,可以更好的指導臨床治療,實現精準醫療。隨著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放化療、腫瘤疫苗、過繼免疫治療、分子靶向藥物以及聯合治療的進一步探索,針對肝癌微環境的更高效的腫瘤治療方式及藥物也會即將問世。在精準醫學背景下,探索成熟的TME分型的臨床分期系統,將有效評估、預測免疫治療的療效,促進肝癌精準醫學治療的發展。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朱明強負責撰寫論文;丁佑銘指導撰寫文章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