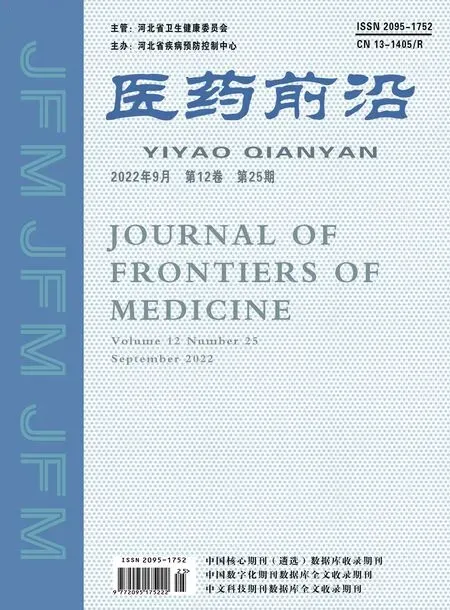應用經顱多普勒超聲評估不同方法治療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的效果
李玉呈,劉冉冉(通信作者)
(揚州大學附屬醫院重癥醫學科 江蘇 揚州 225001)
自發性蛛網膜下腔出血主要指非外傷原因導致的蛛網膜下腔出血,其中約80%是顱內動脈瘤破裂所致,臨床將其稱之為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SAH)[1]。腦血管痙攣是aSHA術后一種常見的早期危險并發癥,發生率為30%~70%,病死率為10%~15%[2]。腰大池置管外引流術可有改善腦脊液循環,緩解腦血管痙攣[3]。終板造瘺術能夠改變aSAH 患者術后腦脊液循環方式。目前臨床關于終板造瘺聯合腰大池置管外引流效果方面的研究較少。既往認為經顱多普勒(transcranial Doppler, TCD)可以監測溶栓前后的血管再通情況及栓子位置。近來,有研究指出,TCD對腦血管痙攣存在一定的預測價值[4]。本研旨在探討應用TCD 評估不同治療方法治療aSAH 的效果。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揚州大學附屬醫院2015 年1 月—2020 年1 月收治的188 例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患者的病歷資料,根據治療方法的不同將其分為夾閉組(n= 65)、腰大池組(n= 63)、造瘺組(n= 60)。三組患者的年齡、性別、Hunt-Hess 分級等臨床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符合《赫爾辛基宣言》要求。

表1 三組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
納入標準:①患者從發病到送入我院治療的時間窗≤72 h。②急診行頭部CT/CTA 或DSA 檢查證實存在顱內動脈瘤且因其破裂導致aASH。③簽署手術相關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術前有顱內病變及其并發癥影響本文結果者。②凝血功能障礙相關疾病者。③Hunt-Hess 分級Ⅴ級者。④不配合治療、病歷資料不完整或不能配合隨訪者。
1.2 方法
夾閉組65 例行單純動脈瘤夾閉治療,腰大池組63 例行開顱夾閉聯合腰大池置管引流,造瘺組60 例行開顱夾閉及終板造瘺聯合腰大池置管引流。(1)單純夾閉組患者根據病情選擇合適的手術方式夾閉動脈瘤。(2)腰大池組行動脈瘤夾閉術聯合腰大池引流術。腰大池引流步驟:患者取側臥位,首選在L3~4椎間隙為穿刺點,從穿刺點進針至有腦脊液流出,沿針芯植入引流管,拔除穿刺針,連接外引流裝置并固定,協助患者更換至手術體位。術中剪開硬膜時,打開引流管閥門,緩慢釋放腦脊液,待腦組織塌陷后關閉閥門。為避免院內感染,引流管留置時間最長2 周,每日引流腦脊液量約200 mL[5]。(3)造瘺組行動脈瘤夾閉聯合腰大池引流和終板造瘺。終板造瘺步驟:在術中輕柔牽拉額葉腦組織,直至顯露終板,沿中線切開終板膜,在視交叉后上方穿透終板結構,造瘺直徑5 ~6 mm,若見腦脊液從瘺口流出表明造瘺成功[6]。
1.3 觀察指標
(1)TCD 檢查及腦血管痙攣的評估方法:在術后三組患者均每日行TCD 監測,監測大腦中動脈、頸內動脈顱外段的血流流速,若大腦中動脈血流流速>120 cm/s,且Lindegard 指數(大腦中動脈的平均流速/頸內動脈顱外段的平均流速)≥3,則考慮存在血管痙攣[7],如圖1。(2)采用改良Barthel 指數量表(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對三組患者術前及術后2 周后的日常生活能力進行評價,總分100 分,分數與日常生活能力呈正相關。(3)采用美國國立衛生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對3 組患者術前及3 個月后的神經功能缺損情況進行評價,總分42 分,分數與神經功能缺損呈負相關。(4)采用格拉斯哥結局量表(Glasgow outcome scale, GOS)評價患者12 個月后的預后情況,其中Ⅳ和Ⅴ級為預后良好。

圖1 左側大腦中動脈的血流流度>120 cm/s,且Lindegard 指數為3.16,考慮為血管痙攣
1.4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 22.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處理。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 s)表示,三組間比較采用方差分析中的SNK q 檢驗;計數資料用頻數(n)和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 三組患者手術前后NIHSS 評分、MBI 評分比較
術前,三組NIHSS 評分和MBI 評分組間兩兩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三組NIHSS 評分組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三組MBI 評分組間兩兩比較,夾閉組與腰大池組和造瘺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腰大池組與造瘺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三組手術前后NIHSS 評分、MBI 評分比較( ± s,分)

表2 三組手術前后NIHSS 評分、MBI 評分比較( ± s,分)
注:NIHSS,美國國立衛生院卒中量表;MBI,改良Barthel 指數量表。
MBI 評分術前 術后3 個月 術前 術后2 周夾閉組① 65 30.60±4.10 17.29±3.67 56.93±9.16 72.20±8.81腰大池組② 63 31.07±3.89 15.30±2.62 55.81±8.25 82.28±7.22造瘺組③ 60 30.78±3.59 12.10±2.87 54.62±7.92 83.88±6.65 t/P(①與②比) 0.665/0.507 3.539/0.001 0.727/0.468 7.090/0.000 t/P(①與③比) 0.262/0.794 0.843/0.000 1.511/0.133 0.405/0.000 t/P(②與③比) 0.430/0.668 6.449/0.000 0.816/0.416 1.279/0.203組別 例數NIHSS 評分
2.2 三組術后腦血管痙攣發生率、痙攣持續時間以及預后良好率比較
術后,三組的腦血管痙攣持續時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三組術后的腦血管痙攣發生率、預后良好率兩兩比較,夾閉組與造瘺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夾閉組與腰大池組、腰大池組與造瘺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三組術后腦血管痙攣發生率、痙攣持續時間以及預后良好率比較
3.討論
腦血管痙攣是顱內動脈瘤破裂出血后最常見、最嚴重的并發癥之一,也是導致患者病情加重、死亡風險明顯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腦血管痙攣通常在疾病發生后的第3 ~4 d 出現,后逐漸進入高峰期,至發病7 ~14 d后逐漸緩解。腦血管痙攣的主要危害是造成腦組織缺血或(和)遲發性缺血性腦損害。若及時診治有助于改善患者的預后,降低患者死亡風險[8]。目前,有效診斷腦血管痙攣的方法包括DSA、磁共振血管造影、螺旋CT 血管造影等,但由于磁共振血管造影、螺旋CT 血管造影具有創傷性、造影劑不良反應以及不能實時監測等缺點,限制了其在臨床中的應用。TCD 具有無創性、安全可靠、操作方便、可床旁操作、診斷敏感較高等優點,且可有效檢測血流動力學改變[9]。因此,可將其可以作為診斷腦血管痙攣的有效方法。
aSAH 導致的腦血管痙攣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主要病理機制是血液刺激以及大量紅細胞遭到破壞后釋放多種血管活性物質導致血管痙攣[10]。早期快速去除可能的致腦血管痙攣因子尤為重要。腰大池外引流術能持續引流腦脊液,改善腦脊液循環,加快腦脊液中致腦血管痙攣相關因子的稀釋和排出,使血性腦脊液快速廓清,以達到降低腦血管痙攣發生率和縮短腦血管痙攣持續時間的目的[11-12]。本研究發現,三組術后腦血管痙攣發生率以及痙攣持續時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終板造瘺聯合腰大池置管引流有效。究其原因,可能是終板造瘺改變了原有的腦脊液循環通路,改變了腦脊液的動力學,使腦脊液的循環較單純腰大池引流增快,繼而使血液及其裂解產物更容易快速排出[13]。
本文結果顯示,三組術后NIHSS 評分組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三組MBI 評分組間兩兩比較,夾閉組與腰大池組和造瘺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腰大池組與造瘺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三組術后的腦血管痙攣持續時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三組術后的腦血管痙攣發生率、預后良好率兩兩比較,夾閉組與造瘺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夾閉組與腰大池組、腰大池組與造瘺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分析其原因可能是通過腰大池引流術聯合終板造瘺術可起到進一步改善患者的腦室順應性、降低腦組織的繼發性損傷以及減輕患者的神經功能損害等作用,有助于促進患者預后恢復,有效降低慢性腦積水發生率[14]。發病1 年后,三組的預后良好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可能與本研究的納入病例數較少、存在失訪偏倚、信息偏倚等誤差影響了研究結果有關,今后將進行多中心、大樣本量、隨機性、長期隨訪的進一步研究。
綜上所述,應用終板造瘺聯合腰大池置管引流治療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不僅可以降低腦血管痙攣的發生率,縮短血管痙攣持續時間,而且可減輕神經功能損害。應用TCD 評估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患者的腦血流情況價值顯著,可幫助臨床醫師及時發現血管痙攣情況,避免遲發性腦出血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