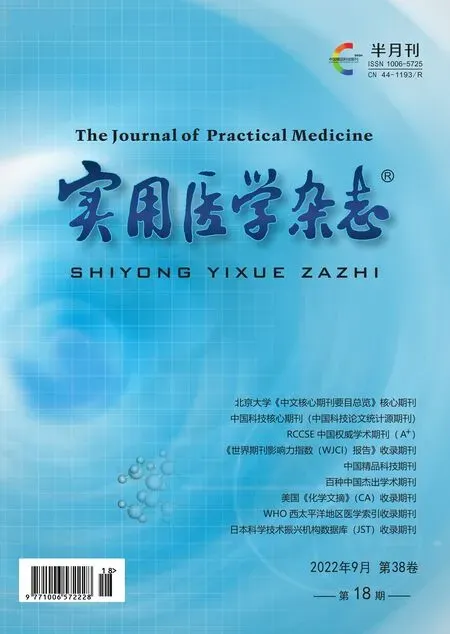幽門螺桿菌毒力因子血型抗原結合黏附素在胃癌中的研究現狀
俞陽 王娜 王博方 李玉民 陳昊
1蘭州大學第二醫院(第二臨床醫學院)腫瘤外科(蘭州 730030);2蘭州大學第二醫院甘肅省消化系腫瘤重點實驗室(蘭州 730030)
幽門螺桿菌(H.pylori,Hp)感染是嚴峻的公共衛生問題,我國人群H.pylori的流行率約為50%[1]。大量研究證據提示H.pylori感染與各類胃腸道疾病的發生存在密切聯系,尤其重要的是H.pylori已被國際癌癥研究機構確定為I 類致癌物,全球胃癌患者中89%與H.pylori感染有關[2],嚴重影響國民的身體健康。如今,H.pylori的治療主要以抗生素為主,但耐藥菌株的廣泛出現給H.pylori的防治帶來了巨大挑戰。因此,闡明H.pylori的致病機制,尋找新的潛在防治靶點,變得尤為重要。
血型抗原結合黏附素(blood group antigen-binding adhesion,BabA)是H.pylori最重要的黏附素,同時也是一種新識別的毒力因子,在H.pylori致病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BabA 與胃癌的發生發展存在密切聯系,BabA 陽性的H.pylori感染者具有更高的胃癌發生風險[3]。對BabA 的全面認識有助于H.pylori新型防治策略的研發,然而目前尚無相關綜述類文獻對其作用及致病性進行系統梳理。
本文系統回顧相關文獻,對BabA 在胃癌中的作用及其應用進行總結,旨在為認識H.pylori致癌機制提供新的角度,并為胃癌防治提供新思路。
1 BabA 的發現
BabA 屬于外膜蛋白家族(outer membrane proteins,OMPs),進一步細分屬于Hop蛋白。BabA最早由ILVER 等[4]于1998年從人胃黏膜分離的H.pylori中鑒定并純化獲得,利用免疫電鏡顯示位于菌體的表面。BabA 具有LewisB 血型抗原結合活性,親合實驗顯示兩者間的結合常數(Ka)為1×1010M-1[4]。2015年,HAGE 等[5]的研究詳細闡述了BabA 及其受體LewisB 間相互作用的結構基礎,為開發相關靶向藥物奠定了基礎。
BabA 分子量約為8 000 Da,由744 個氨基酸組成[6],其與LewisB 結合的結合域稱為crown 區,由4 個反向平行的β 折疊構成[7]。其編碼基因為babA1 和babA2,表達型由babA2 編碼。BabA 有兩個同源蛋白BabB 和BabC,編碼基因分別為babB 和babC。babA、babB 和babC 三個等位基因之間在5'和3'區域的序列十分相似,而中間區域存在明顯的序列差異[8-9]。bab 基因位點具有菌株多樣性,同時具有高度的可變異性,這有助于H.pylori對不同宿主環境的適應[9-10]。不同地區H.pyloriBabA陽性率存在明顯差異,總體上亞洲地區高于西方地區,我國菌株BabA 陽性率據報道在38.36% ~91.5%不等[11-12]。
2 BabA 功能與調節
H.pylori利用外膜蛋白BabA 與宿主細胞上的LewisB 結合作用,實現黏附并定位到胃上皮細胞[13]。在胃和口腔均存在BabA 受體,因為多種黏蛋白含有LewisB 成分,例如MUC1、MUC5AC 和MUC5B 等[10]。BabA 對于H.pylori感染的初始黏附階段具有重要意義,有研究通過體外實驗探討了BabA 缺失對于H.pylori與胃癌AGS 和MKN45 間黏附作用的影響,發現BabA 缺失導致兩者間的黏附水平顯著下降[14]。可見,BabA 是H.pylori重要的黏附定殖因子。此外,在H.pylori進化過程中,基因變異可動態調節BabA 的表達。B?CKSTR?M 等[15]在無LewisB 結合活性的菌株中偶然鑒定出了具有LewisB 結合活性的菌株,進一步研究發現在CCUG17875 菌株中,通過將沉默型babA1 基因重組到表達且部分同源的babB 位點上,可獲得babA2-cam 基因,該基因表達BabB/A 黏附素。這種雜合BabB/A 同樣具有LewisB 結合活性,親和力與野生型BabA 類似,但其表達水平更低。另一項動態研究中,NELL 等發現在23株個體來源的H.pylori菌株中,只有5 株的LewisB 結合活性在感染過程中出現了缺失或者降低,這證實了H.pylori的LeiwisB 結合活性相對較為穩定,但由于基因突變和重組的驅動,babA 基因的微進化時常發生[16]。這或許能部分解釋BabA 與LewisB 之間的結合活性具有酸反應性,即當附近酸性增加時,兩者結合活性下降,H.pylori可從胃細胞中釋放下來,待酸性環境中和后,恢復結合活性導致再次感染[17]。這些證據提示在H.pylori感染過程中,babA 基因可隨環境的變化發生進化,動態調節BabA 的表達,從而增強H.pylori對宿主清除機制的應對能力。
3 BabA 與胃癌的聯系
3.1 BabA 的促胃癌作用及機制胃癌的發生發展是一個多步驟、多階段的過程,大量研究已經證實了H.pylori感染與胃癌發生之間的相關性[18]。H.pylori誘導胃癌的發生涉及多重機制,致病過程主要依賴于各類毒力因子。BabA 是目前研究得最為充分的H.pylori黏附分子,大量研究發現H.pylori的babA 基因型與其致病性和胃癌風險密切相關。ABDI 等[19]評估了不同H.pylori基因型與胃癌發生風險的聯系,利用回歸分析調整性別和年齡以后,發現babA2 陽性是胃癌的獨立危險因素,可將胃癌發生風險增加約5 倍。類似地,ROMáNROMáN 等[20]也發現babA2 基因陽性可增加胃癌發生風險,盡管統計學意義不顯著。不過HEIDARI等[21]得出了陰性結果。研究間結果不一致可能是因為存在多方面的異質性,例如患者的種族、babA檢測方式和胃癌定義不同等。為了減少偏倚,提高評估的真實性,一項Meta 分析合并了20 項研究的數據,最終發現babA2 陽性菌株感染者胃癌發生風險是陰性菌株感染者的2.05 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OR= 2.05,95%CI:1.30 ~3.24,P<0.01),亞組分析提示該結果在亞洲人群中依然顯著[3]。總之,babA 基因增加H.pylori感染者胃癌風險已得到較為充分的證實,尤其是在亞洲人群更為明顯。這些證據提示在亞洲人群中或許更需要注重針對babA2 基因陽性H.pylori的防治。
關于BabA 參與H.pylori誘導胃癌發生發展的機制,目前認為可能與Ⅳ型分泌系統(type Ⅳsecretion system,T4SS)有關。PALRASU 等[22]發現BabA 可以增強H.pyloriT4SS 活性。T4SS 可協助毒力因子CagA 進入宿主細胞,誘導宿主細胞增殖、遷移、β-actenin以及上皮間質轉化等致瘤通路的激活[23]。此外,T4SS自身可以通過NF-κB信號通路促進宿主細胞炎癥因子的釋放,例如IL-8 等[24]。QIN等[25]還發現T4SS 可以調節H.pyloriDNA 轉移進入胃癌細胞,從而誘導與胃癌進展相關的TLR9反應活化。這種T4SS 依賴的致瘤信號通路激活或許是BabA 促進胃癌發生發展的主要途徑。然而,目前這些線索多來自于間接證據,仍有待更多直接證據的證實。除了T4SS 途徑外,BabA 促胃癌機制中是否涉及其他途徑抑或是否存在與宿主細胞的直接相互作用,也是未來值得關注的研究方向。
3.2 BabA 與其他毒力因子的相互作用H.pylori的主要致病因子包括CagA 和VacA,它們通過影響宿主細胞的生理功能和形態發揮致病作用。一些證據提示BabA 與這些毒力因子具有協同作用,可以增強H.pylori的致病性。BabA 更常見于CagA 陽性菌株中,而在CagA 陽性菌株中,BabA 同LewisB的結合活率較在CagA 陰性菌株中更高,這提示BabA 與CagA 之間存在功能協同性,導致BabA 與CagA 雙陽性的致病性更強[4]。ZAMBON 等[26]根據各毒力因子基因狀態評估了不同亞型菌株與感染者臨床結局之間的關聯,發現cagA+/s1m1/babA2+亞型菌株感染者的內鏡表現最差、炎癥最嚴重和腸化生的風險最高。此外,BabA 與唾液酸結合黏附素(sialic acid-binding adhesion,SabA)似乎也有類似的協同關系。然而,對毒力因子共表達的現象及其協同致病的認識依然不足,其背后的相互作用關系以及復雜的致病機制仍不清楚,在未來利用一些生物新技術,例如多組學分析,或許有助于對這些現象背后的機制進行深入地闡釋,從而設計相應的靶向治療方案提高H.pylori防治效率。
4 基于BabA 的潛在應用
4.1 H.pylori 防治根除H.pylori已成為防治胃癌的共識,臨床上主要通過多聯抗生素進行治療。鑒于BabA 在H.pylori致癌發生中的重要作用,一些研究探討了靶向H.pyloriBabA 的H.pylori根治策略。一些天然物質含有類似BabA 受體的成分,通過競爭性結合發揮抗H.pylori黏附作用。GOTTESMANN 等[27]發現具有黏膜黏附特性的蘋果果膠可以識別結合BabA,利用該物質作為載體,呈遞抗生素,可實現更高效的靶向治療。MESSING 等[28]從黑加侖種子中提取出一種糖蛋白,具有阿拉伯半乳聚糖結構,體外實驗證實了該物質可抑制BabA 與其受體間的結合,降低H.pylori 的黏附性。除了天然藥物外,有相關專利報道了一種靶向BabA 的免疫球蛋白(Abba3),利用生物工程技術開發了BabA 的特異性抗體[29]。還有的研究[30]利用基于結構的藥物設計(structure-based drug design,SBDD)方法篩選出了六種BabA 高親和力的分子成分,為研發BabA 小分子抑制劑提供了選擇。此外,另一些物質通過破壞BabA 與LewisB 之間的相互作用或干擾BabA 的表達,抑制H.pylori的黏附作用。例如,具有氧化還原活性藥物如N-乙酰半胱氨酸被發現可以破壞BabA 與LewisB 間的二硫鍵,頭花蓼水提物則可以下調babA、alpA 和alpB的轉錄,從而抑制H.pylori黏附至胃上皮細胞[31]。總的來說,靶向BabA 的防治藥物多來自于天然物質或其提取物,主要抑制策略為阻斷BabA 與其受體間的結合,當前藥物研發尚處于初始階段,臨床應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仍有待進一步的探索。BabA具有較強的抗原性,因此也可作為H.pylori疫苗的候選分子。白楊等[32]通過體外實驗探討了BabA 的生物活性和免疫原性。通過構建的重組BabA(rBabA)蛋白,發現了rBabA 可刺激H.pylori陽性感染者血清來源的T 細胞增殖,具有同時誘導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的潛力。URRUTIA-BACA等[33]通過生物信息學,利用計算機生物模擬和驗證的方法,開發驗證了一種含BabA 的多表位口服疫苗。然而,目前研究仍處于探索階段,仍無可供使用的治療性或預防性疫苗,有待投入更多的研究與開發。
4.2 胃癌危險因素胃癌的早發現、早診斷以及精準分型對于提高胃癌患者的生存、降低不良事件具有重要意義。H.pylori與宿主胃上皮細胞間復雜的相互作用,使H.pylori相關的毒力因子成為潛在的胃癌生物標志物。對于BabA,一些研究探討了其在輔助胃癌診斷和預后分型中的應用價值。SU 等[34]利用蛋白組學的方法篩選出具有胃癌鑒別能力的H.pylori毒力因子,其中就包括BabA分子。進一步實驗驗證了不同患者血清對BabA的抗原反應性,發現胃癌患者血清的陽性反應顯著高于十二指腸潰瘍患者與其他非胃癌患者,提示BabA 是胃癌相關的抗原。同時,作者利用對H.pylori三個毒力因子(OipA、BabA 和SabA)的血清反應性構建了胃癌風險預測模型,并開發了相應的臨床芯片,具有良好的胃癌篩查能力。另外,BARTPHO 等[35]評估了BabA 聯合其他因子在胃癌中的預后價值。根據VacA、BabA 和OipA 的基因狀態,將患者分為兩組,發現毒力因子雙陽性胃癌(vacA+/babA2+、vacA+/oipA+和babA2+/oipA+)患者的總生存優于三陽性胃癌(vacA+/babA2+/oipA+),盡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些證據提示BabA 是胃癌的潛在危險因子,對于胃癌篩查、診斷和臨床結局預測具有一定意義。
4.3 免疫治療反應預測以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抗PD-1/PD-L1/CTLA-4)為代表的腫瘤免疫治療近年來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在胃癌領域,免疫治療仍然面臨著獲益人群少、藥物抵抗等問題,尋找相關因素篩選優勢人群,提高免疫治療療效就變得尤為重要。羅萍等[36]提示H.pylori毒力因子和相關代謝物參與調控宿主的免疫反應及炎癥因子的釋放。此外,OSTER 等[37]提示H.pylori與免疫治療療效間存在明顯關聯。OSTER 等[37]利用動物模型(結腸腺癌和黑色素瘤移植模型)探討了在接受抗CTLA-4、PD-L1 或腫瘤疫苗后,不同H.pylori感染狀態小鼠的療效差異,發現未感染H.pylori小鼠的腫瘤體積明顯小于感染的小鼠。H.pylori的這種免疫治療抑制作用與腸道菌群無關,而與其自身誘導的免疫抑制有關。進一步研究發現同為螺桿菌屬但缺乏毒力因子的H.felis并不會像H.pylori一樣影響免疫治療效果,這提示在H.pylori消弱免疫治療療效的過程中,其毒力因子起到了關鍵作用[37]。由此可見,隨著諸如BabA 這樣的毒力因子在胃癌中的角色逐漸被發現,利用這些毒力因子開發預測免疫治療療效和改善結局的方案將成為可能。
5 展望
隨著相關技術的發展,BabA 的結構、功能及與胃癌之間的聯系逐漸被發現和解析。然而,對于一些現象背后的具體機制仍然知之甚少。例如,雖然大量證據證實了BabA 陽性菌株與胃癌風險之間的聯系,但仍然不清楚BabA 在胃癌發生過程中扮演的確切角色。未來需要更多的機制研究來闡明是否BabA 如同其他致病因子(如CagA 和VacA)一樣,可直接對宿主細胞發揮毒性作用,誘導致癌信號的激活。此外,對于BabA 與其他毒力因子間的相互作用目前也同樣不明確。基因、RNA 表達和蛋白組學等新技術可幫助全面、深入地認識生物過程,在將來針對BabA 的研究中利用這些技術或許有助于取得新突破。一些新藥的獲批上市將胃癌的診治帶入了精準治療時代。然而,在這些新藥的應用過程中,也隨之產生了許多新的挑戰,例如免疫治療存在有效人群比例低、缺乏有效的療效預測標志物等。近年來,H.pylori感染被發現與胃癌預后相關[38],這提示H.pylori及其毒力因子(如BabA)或許是影響治療的重要因素,基于這些因素開發相應策略或許有助于解決胃癌診治中的難題。當然,這些的基礎依然在于全面地了解H.pylori、相關毒力因子及宿主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
BabA 是H.pylori重要的黏附素,通過與宿主細胞上的受體結合,介導H.pylori的感染和定殖過程。BabA 編碼基因存在多個等位基因,編碼基因的高度可變異性有助于H.pylori對外部環境的適應,增強致病性。大量證據證實了BabA 在胃癌發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BabA 陽性菌株感染往往與胃癌風險增加相關,然而BabA 具有的致癌機制尚未明確,可能與T4SS 系統誘導的致瘤信號激活有關。鑒于BabA 與胃癌間的密切聯系,BabA 具有巨大的臨床轉化潛力。基于干擾BabA 與其受體結合或抑制BabA 表達的設計,開發相應的靶向藥物可阻斷H.pylori的黏附作用,有助于解決目前H.pylori耐藥的問題。BabA 同時也可以作為抗原分子,用于治療性或預防性的H.pylori疫苗研發。此外,作為胃癌的危險因素,BabA 在胃癌診斷和預后分型方面也具有一定價值。然而,當前對BabA的認識依然不夠充分,未來全面地認識BabA 與宿主以及其他毒力因子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明確BabA 在H.pylori促胃癌發生中的確切角色,并更好地挖掘其臨床應用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