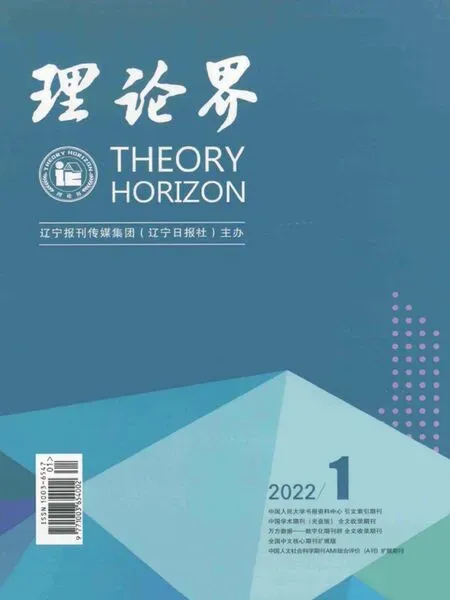客觀性與美國史學——讀《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史學界》
王 娟
彼得·諾維克(Peter Novick,1934—2012)是20世紀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他所寫的《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史 學 界 》 (That Noble Dream:The"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1988)一書,獲得了1989 年美國歷史協會的艾伯特·J.貝弗里奇獎(Albert J.Beveridge Prize)。獲獎詞是這樣的:“諾維克的作品表明,歷史學家在選擇他們的研究對象,并對其作出評價和解釋時,往往受到自身思維和職業標準的影響。作者憑借自身技藝,運用各種材料,說明了一個公眾十分好奇但又深感困惑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歷史知識的“客觀性”問題,它因其復雜性、變動性和重要性,成為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諾維克參與了這一問題的討論,他以“客觀性”這一史學假設在美國的演變為線索,分析了百余年來美國史學是如何與時代互動、與政治勾連的,呈現了無數的成果以及通過這些成果展現的主張,他的目的是恢復歷史學家關于史學客觀性的自覺意識和專業自信。學者評價這部“美國歷史學界實際發生了什么”的編年史,說它“是給當下和未來的歷史學家以及其他學者的一份禮物”。〔1〕
一、“客觀性”概念的演變
古典時代是西方史學的古典傳統,開山之作為希羅多德的《歷史》。此書開篇陳明其寫史宗旨:將已發生的事件如實地記載下來以永垂后世。此時,人們多相信世界是由命運支配的,根本不存在歷史發展的余地,其歷史意識是指向過去的。濫觴的英雄史觀演變成道德史觀,整個古典時代的史學都被這種意識支配著,史學家的注意力更多地被吸引到道德方面來了。同時,人們于自然中常見日月光華,四季輪替,因此,相信歷史就是一個循環往復、周而復始的過程。在他們看來,“只有永恒不變的東西才是可理解的(Intelligible)或可知的(Knowable),有關它的知識才是可證明的(Demonstrative),因而成為‘真知’(Knowledge Proper)”。“在有關歷史的真實性問題上,古希臘羅馬時代的人們都會多多少少認同西塞羅(Cicero)的那句名言:‘誰不知道歷史學的首要律令是非證無言?’”〔2〕所以,“客觀性”的含義在這一時期除了“真實地再現過去的經驗”之外,還有“超然”以及嚴格的史料批判原則,〔3〕在史學實踐中較多地表現為寫作當代史,即親眼所見、親耳所聽、親身所歷的歷史,并以歷史故事通達民情,以城邦英雄化育人心。
基督教史學奠定了西方史學的中世紀傳統,其內容可于《上帝之城》一書中窺見一斑。此書宣揚的是天命史觀,認為上帝主宰著人類的命運,現實的悲劇并非歷史的中斷或倒退,而是上帝意志對人類世俗罪惡的懲戒,其歷史意識是指向末日審判的未來的。古典時代的時間循環論被拋棄了,因為它既無法確證《圣經》的唯一啟示性,又否定了人類最終得救的可能性。中世紀史學家“關注的是重復的經驗、習俗的順序,而不是對事件的原因或獨特性的解釋”,這樣才能將歷史看成是一個有始有終、有末世期待的神意計劃。他們記錄的歷史事件是“明顯可感知的”,且“與事件發生的先后順序相符”。〔4〕“他們尤其注重族群的綿延不絕與王朝的萬世一統。有了這一言之鑿鑿的譜系,過去和現在之間就有了‘客觀而真實’的聯系,過去對現在的指引意義就不再虛幻,現實的社會政治生活也就有了合法化的支撐。”〔5〕所以,此時的“客觀性”概念即為符合《圣經》,符合前代經典,有譜系繼承,在史學實踐上通常是寫作通史,并以上帝意旨為解釋歷史的唯一動因。
史學自近代始,內涵不斷豐富,史學觀念也在進步,對“客觀性”的撻伐亦不期而至,其作為不證自明的公理信條的權威逐漸式微。基督教史觀在歷史場域中失效與近代歷史意識的產生不無關系。“所謂近代歷史意識,即是認為人類歷史是線性的,走向光明未來的,不斷進步的變化。”〔6〕從歷史時間觀的發展過程來看,呈現圓圈—線段—直線—平面的變化。新的歷史時間意識沿襲了科學那種標準性、俗世性、確定性的概念,“歷史的走向不再被定義為人類背離上帝恩寵之墮落,而是朝向現代推進”。“現代歷史學的創立過程完畢后,圣經的時間表已然崩潰,千禧年的盼望變成華麗的自欺幻想。”〔7〕繼新的時間概念產生之后,對待歷史事實的新態度順勢而生。然終究是時移世易,歷史真相掩埋在殘垣斷壁之下,層累的時間碎片雜糅交錯,亦時常與時代有從權之計,科學歷史學的衰落、相對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興起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的沖擊,使“客觀性”逐漸成為一個“高尚的夢想”。
彼得·諾維克的《那高尚的夢想》續寫了“客觀性”概念的演變。一開篇他就指出:“‘歷史客觀性’并不是單一的觀念,而是各種主張、態度、愿望和憎惡相互糾纏在一起的集合體”,“它的準確含義究竟是什么,永遠存在著爭議。”他認為,在這一個多世紀里,“客觀性”概念發生了如下變遷:“在19世紀,‘客觀性’往往是針對‘主觀性’而言,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客觀性’的對立面卻是‘相對主義’。”相對主義在這里并不是指一種明確的立場,而是指一種批判的態度:“懷疑客觀性的觀念在歷史學的運用是否具有一貫性。”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歷史學家們以更寬容的態度對待假設,他們更加強調歷史解釋應接受事實的檢驗,而不是從事實中獲得的歷史解釋”。“客觀性”的含義范疇再一次發生改變,逐漸成為“公正”“明智”和“平衡”等溫和詞語的同義詞,被用來“指對假設所做的嚴格檢驗,而不是指‘不帶任何預設地研究某個主題’或‘讓事實自己說話’”。〔8〕
對于“客觀性”問題,諾維克堅定地表明了立場:“至于客觀性思想,在我看來,它的特征自始至終都被人們夸大了。”雖然“近年來不時被修正,但傳統的用法依然屬于強勢,甚至占據主導地位。歷史學家最初提出的實現客觀性的綱領,無論從其基本內容還是從指導方向而言,依然有著十分持久的生命力”。〔9〕雖然諾維克沒有賦予“客觀性”一個明確定義,這是他屢受批駁的點,但這也是他的理論基礎,因為他發現了“客觀性”概念在不同時期的變化——從“堅持真理只有一個”轉變為“駛向真理的集體航行”。同時,他強調了“客觀性”概念的原初可靠性(Primal Validity)。不論“客觀性”概念如何爭論不休,它始終包含如下成分:“忠于過去的事實”“事實獨立于解釋”“區分歷史與虛構”“堅守中立”“不受價值觀念支配”以及“權威的知識”。〔10〕不過有學者指出,諾維克并不滿足于認為客觀的理想是有益的。“它促進了一種不真實的、誤導性的、令人厭惡的區分,歷史敘述也被意識形態或政治目的歪曲了。”〔11〕
二、“客觀性”問題與美國專業歷史學
美國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形成于19世紀的最后30年,此時正值哲學上的自然主義和實證主義一統思想領域。雖然19世紀被譽為歷史學的世紀,但美國史學與同期的德國、英國和法國史學相比,顯得頗為滯后。是時,美國學人多涉德國探尋史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他們將自然科學的法則運用于歷史學科,加之對德國模式的誤解,將“客觀性”認定為核心的專業標準。在他們看來,歷史應該以真正的培根歸納法識別并排列確切事實,就像是牛頓式物理學家和達爾文式生物學家所做的那樣。他們不僅認為自己是一個學科的建造者,還試圖在大學中借鑒德國的“習明納爾”(Seminar)式教學模式,有意識地通過強調“客觀性”來提升學術威望。〔12〕另外,這些學者都是男性盎格魯-新教徒,他們認為生活在美國的其他社會群體沒有理性和客觀的能力,因而排除了印第安人、非裔美國人、墨西哥裔美國人、來自南部和東歐的移民以及所有婦女的歷史書寫。〔13〕學者們還相信“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當今的歷史”,他們有意識地借助歷史作品深化民眾的國族團結意識,撫平民眾的內戰創傷。這些舉措,使美國的歷史學者群體獲得了高度的思想同質性,這對樹立客觀性作為學者們公認的標準是非常重要的。〔14〕這些策略確實奏效了,“客觀性”的正統地位一直持續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此期間一系列專業團體、專業期刊得以出現。
然而,南北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卻極大地侵蝕了“客觀性”的根基。前者涉及美國族群矛盾,白人史學家所著美國史令黑人不滿。后者涉及愛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史學家通過兩種途徑幫助美國:一是直接參軍;二是修正對德國的看法并寫進教科書中,這些舉動侵蝕了史學的根基——“客觀性”。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接連發生激烈的學術爭論,尤其是一戰的戰爭罪責問題和美國內戰的起因問題,打破了學術共識,成為美國歷史相對主義興起的直接背景。〔15〕到20 世紀30 年代,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Austin Beard)、卡爾·貝克爾(Carl Lotus Becker)與其相對主義盟友正式向“客觀主義”發起攻擊。他們認為,歷史事實不是整齊地存放在某個地方,“像童話里等待被喚醒的睡美人一樣,等待著一位戴眼鏡的、受過專業訓練的研究者的到來”;歷史學家不僅不可能收集任何歷史事件的全部事實,而且他們對歷史事實的選擇和解釋還受到自身的先入之見與價值判斷的影響。〔16〕還有一些因素也動搖了歷史學界對客觀性的信仰:一是科學的發展,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數學的概率論及物理的“測不準”定理;二是鄰近的學術領域中的新方法,如廣義相對論、實用主義、法律現實主義、文化相對主義;三是歷史學家對私人資助人的依賴,不同政治聯盟之間的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歷史學家開始指責相對主義,尤其是歐美國家在面對法西斯主義時的軟弱,客觀性的興起與衰落的又一個循環便開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扭轉了這個行業的衰落,并使歷史學家們相信他們有能力披露真相。”〔17〕這場大戰的道德確定性使學者們能夠回到更實證的立場,在20 世紀50 年代,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共識”的標志。對許多歷史學家來說,從激進的相對論撤退,便是危險的意識形態狂熱給他們的警告。〔18〕歷史學家們吸納了相對主義思維對史學客觀性的部分否定,構建了一個新的“客觀性”理解,恢復了歷史作品及歷史學家的權威。在這些年里,專業歷史學家的數量上升了,歷史作品的質量和數量也有所提高。〔19〕
到20世紀60年代末,婦女和非裔美國人更多地在歷史研究中出現,沖擊了白人歷史學家的地位。〔20〕科學知識的發展也給歷史研究帶來了新的挑戰,比如庫恩的“范式”概念,福柯(Michel Foucault)對知識與權力間關系的分析,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和費什(Stanley Fish)等哲學家提出的多重真理的可能性,打破了意義確定性的假設。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和其他人類學家強調的“相對的現實”和“意義之網”等概念,賦予了歷史細節以意義,否定了“獅子代表勇武”這類簡單的對應。由此,歷史客觀性的新危機出現了,歷史學家群體不能再就一個共同的議程達成一致。部分學者甚至認為歷史學應該放棄其科學抱負,成為文學的一個分支,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前職業化的重現。相應地,這一時期歷史學的專業地位逐漸邊緣化,歷史專業的畢業生面臨就業困境,教授們在學校管理上的權威也下降了。〔21〕
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歷史學界對客觀性的懷疑氣氛越來越濃。關于歷史事實是什么以及歷史學應該如何進行研究的截然不同的假設已經擴散開來。到了20 世紀80 年代,歷史學界作為一個整體而言,早已不再是任何實質意義上的共同體了。“歷史上第一次,相當一部分美國史學家對整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和假設抱有敵意,致力于美國史學標準的失格而非合法化。”〔22〕歷史信息驚人地過度生產,不僅是新歷史記錄本身的泛濫,還包括新的歷史主題、新的視角、新的詮釋、新的理論和新的呈現方式。不寧唯是,寫作的鐵律同樣適用于歷史:解釋越有力、越權威,就越會產生反解釋。強有力的解釋不僅不能澄清過去、平息爭論、指導新的研究,反而會引發新一輪的討論——更多的會議和座談會、更多的書籍和文章、更多的解釋,以抗衡以前的解釋。〔23〕
三、客觀性的變化性與原初可靠性
所有的史學研究都是在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生產場所進行的。始自20世紀60年代末的混亂,給史學帶來了諸多礪石。一方面,20 世紀60 年代的政治激進主義:民權運動的分裂,種族、階級和宗教反抗的興起,越南戰爭,水門事件的憲法危機以及經濟停滯等,沖擊了學者對美國有能力帶領“自由世界”走向空前穩定和幸福的期望。另一方面,史學的語言轉向、文化轉向以及后現代主義的沖擊,推動歷史學家追溯文化為權力服務的方式,啟發他們分析語言闡釋與客體的相互關系,促使他們質疑宏大敘事的建構。這些新發展挖掘了一系列在傳統歷史敘事中被忽視的故事,給歷史研究提供了許多研究主題和研究方式。無論是社會史學家、文化史學家,還是其他的特殊群體史學家,都沒有在他們的研究議程、方法論或認識論上達成足夠的共識。〔24〕當時,歷史客觀性思想引發的爭論之多,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期。在課堂上,在各種形式的校園騷動中,在學會內部各種形式的爭吵中,與“客觀性問題”相關的術語和概念不斷地掛在人們的嘴邊。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自主學科得以形成的基礎是聲稱對某個獨特的研究對象擁有唯一的主權。每個學科要求有自己的領域,同時也要求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理論基礎與研究對象。然而,這樣的信念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開始瓦解了。
諾維克196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歐洲歷史博士學位,畢業論文還獲得了克拉克·M.安斯利獎(Clark M.Ansley Award)。從他所接受的教育和學術背景來看,他很可能會在20世紀的法國史研究中取得成果。但就其后發表的學術作品看,他將自己的研究范圍從歐洲轉移到了美國,并且出現了從史實研究到理論研究再回到史實研究的變化。作為一名受過專業訓練的、成熟的歷史學家,諾維克為什么幾次改變研究對象和主題,這一問題目前還沒有材料可以直接解釋。但他之所以研究“客觀性”問題,必然與當時的史學氛圍和時代環境有關。他自己在書中也說:“一個又一個史學意識的出現,推動了當代史學的加速發展。對美國史學家而言,20 世紀50 年代是學術共同體的十年共識期,是‘意識形態分化’前的十年。緊隨其后的60年代是思維和情緒分化的時期,這種分化不僅持續到80年代,而且造成了歷史學的碎片化。”他說,這是近幾十年來學術研究不斷加速的漸進性演變的結果。這些演變,或是單獨的,或是結合的,共同推動歷史學達到了某個“臨界點”。即是說,歷史學已經分裂成大量各自獨立的領域。“當一個學術共同體發展到一定程度,它就不再是一個共同體。它會被分解成若干規模較小的共同體,這些小共同體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又將再細分,于是一個個更小的學術共同體出現了。”這些大大小小的共同體,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進行研究,都有各自的對話對象和話語”。〔25〕
不過,他并沒有全盤否定這種變化。在他看來,這種變化“并不意味著不穩定或末日降臨”,相反,它只意味著某些事物發生了變化,而且在某些時期比其他時期更快。這種變化對歷史研究有一定的啟發作用,擴大了歷史研究的范圍和方法;但同時,這種變化也給歷史研究帶來了一些挑戰,使歷史研究失去了確定性。“當沒有人能想象到能有什么東西是歷史學家無法研究的時候,他們又怎么能說清楚歷史學家究竟是做什么的呢?”〔26〕為應答時勢,諾維克將自己的寫作目的定為:“為了我的歷史同行們,對我們從事的工作的本質有更多的自我意識;也是為了讓歷史學界以外的人們,對歷史學家正在從事的事業有更好的理解,以便他們多一個視角來看待歷史學家的學術成果以及通過這些成果所表達的思想。”〔27〕
要實現這一目的,諾維克要做的是,如何在這種語境下重新闡釋歷史學的理論基礎,重建歷史學家的學術自信和歷史學科的專業權威。他將當前的客觀性危機看成歷史學發展的又一個階段,既尊重學科外的攻擊和學科內的反思所產生的學術成果,又警惕可能造成的碎片化。因此,諾維克以時間為經,以“客觀性”概念的演變和歷史專業的發展為緯,呈現客觀性和歷史學科的互動及演變。他敘述了客觀性概念在美國歷史學界遭遇的命運,提出了“客觀性”的變動性和原初可靠性的觀點,分析了“客觀性”概念與歷史專業化的相互關系。在他的觀點中,現下這場客觀性危機于美國歷史學界而言,并非新鮮事,這與之前史學的相對主義危機如出一轍。這都是因為專業方法和技術上的改變,以及對世界和人類狀況的基本看法的改變所帶來的沖擊,是歷史學走向成熟所必經的一個階段。歷史學家并沒有因為后現代主義運動而被要求改變他們收集史料、考據史料的工作方法,不過他們必須更準確地觀察客觀性的變化性和原初可靠性,重視客觀性與專業化的關系。
可以說,《那高尚的夢想》給歷史學者提供了一種擺脫客觀性爭論旋渦的思路。戴維·霍林格(David A.Hollinger)就說,諾維克給讀者提供了一個急需的解釋,它不是歷史學家的技藝,也不是歷史哲學,而是這個專業的常備知識。同時,他又把這個問題解釋得非常寬泛,使讀者能夠跟隨他的理解去認識這個專業發展的有趣之處。〔28〕諾維克對客觀性問題與美國史學的演變的回顧,為重新肯定傳統歷史認識論的基本假設奠定了基礎。如果說史學客觀性的變動性具有生產力,那么史學客觀性的原初可靠性便有凝聚力。在這些變與不變所維持的空間里,歷史專業中試圖創新的人,試圖維持歷史學的學科地位和學術團結的人,都可以尋找到新的方向和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