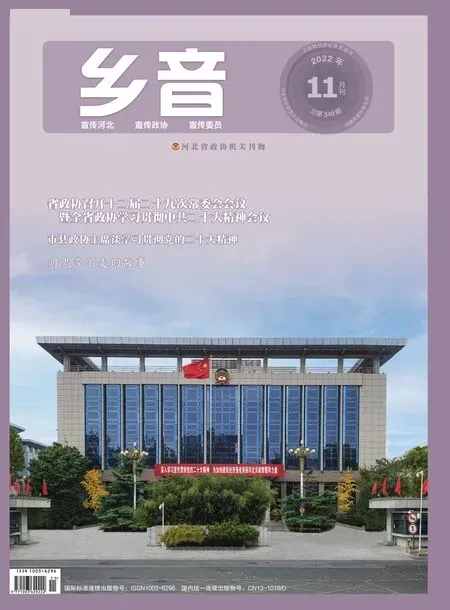及殘碑揭秘千年往事『天下第一赑屃』
■ 李立華

石家莊市正定開元寺,因唐代鐘樓與須彌塔聞名于世。21世紀初,開元寺院內再添一“寶”:一座長8.4 米、殘寬3.2 米、高2.6 米、殘重107噸的巨型赑屃連同幾塊殘碑,如小山一樣出現在游人面前。文史學家撥開重重迷霧,通過對殘碑碑文進行考證,為我們揭開了1200多年前的一段塵封往事。曾經的歷史,一幕幕重現在眼前,既生動又鮮活。
“天下第一赑屃”出土記
2000 年6 月22 日,石家莊市正定縣城府前街一處建筑工地,一臺挖掘機正在努力地深挖地基。突然,挖掘機一斗探下去,隨即傳來“哐啷”一聲。司機師傅以為碰到了石頭,為了避免損傷機器,他和工友們決定改用鐵鍬挖。于是,大家拿起鐵鍬,一鍬一鍬地挖了起來。挖著挖著,一件將近10 米長、3 米高的“巨無霸”石雕,完整出現在眼前。施工隊長立刻與當地文物管理部門取得聯系,文物工作者趕到現場后,初步考察認定,這件體積龐大的石雕是傳說中的神獸“赑屃”。為了方便研究,重約107 噸的巨型赑屃被移置開元寺院內。
古代民間傳說中,赑屃又稱“龜趺”“霸下”,屬靈禽祥獸。俗話說“龍生九子,種種個別”,赑屃就是龍之“九子”中的第六子。赑屃有齒,力大可馱三山五岳。傳說,上古時代赑屃經常在神州大地的江河湖海興風作浪,禍亂人間。大禹治水時將其收服,從此跟著大禹推山開河,挖渠疏溝,造福人間。大禹治理洪水后,怕它閑下來又去作孽,搬來一塊頂天立地的巨型石碑讓它馱著,上面記載著治水功績。自此之后,赑屃就成了一位吃苦耐勞的“大力士”,無論背上馱的石碑多高多重,總是一副頑強支撐四腳、昂首奮力向前的姿態。由此,文物工作者認為,這座赑屃的背部應該馱有一塊巨碑。隨后,他們又對赑屃出土地點認真進行了挖掘清理,陸續出土了10 余塊殘碑,大約相當于全部碑身的三分之一,而碑首只找到二分之一。從殘碑的出土情況判斷,碑身、碑座應是被砸毀后深埋于地下的。
當時,國內已知存世最高、最大的石碑及碑座是河北大名的“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德政碑”。“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德政碑”也稱“五禮記碑”,這通碑原是唐碑(立于唐文宗開成五年,即840 年),為著名書法家柳公權奉唐文宗之命為魏博節度使何進滔撰寫的德政碑。宋徽宗大觀二年(1108 年),宋徽宗修編《五禮新儀》,詔諭大名府尹梁子美為《五禮新儀》立碑刻記,梁子美為討好皇上,毀何進滔德政碑,以其石改刻《五禮新儀》,改稱“五禮記碑”。“五禮記碑”赑屃碑座高2.2 米,重61 噸有余;碑身高6.45 米,寬3.3 米,厚1 米,重58 噸。兩相比較,石家莊市正定出土的赑屃碑座,比“五禮記碑”赑屃碑座大一倍!于是,“天下第一赑屃”之說橫空出世,一時之間轟動全國。天南海北的文物學者專家紛紛來到正定一探究竟:這通巨碑的主人到底是誰?雕刻如此精美的巨型碑刻,為何被砸毀并深埋于地下?
撲朔迷離的巨碑主人
一眼看去,開元寺院內這只體型肥碩的神獸,萌萌的,非常可愛。大赑屃雖然四腳不全,渾圓的腹部上卻有一道向兩側突出的石刻紋路,以顯示其馱碑所承受的重壓。它圓睜雙眼,兩只小耳朵向后抿著,鼻頭寬鼻孔圓,大嘴緊閉卻有兩只尖牙外露,似乎負重前行有些吃力卻全然一副心甘情愿的樣子……石雕手法簡潔,造型生動逼真,神態活靈活現,堪稱一件精美的石雕藝術品。

正定開元寺院內殘碑碑文(局部)
讓人深感遺憾的是,這座巨型赑屃與殘碑,除赑屃碑座基本完整之外,碑文凡涉及人名處全被刻意砸毀,這就為確定碑主人增加了難度,只能從碑刻殘留的一些帝王年號、廟號、官職爵位及所記事件,對照相關史料分析,在相關的歷史人物中查找可能相關的線索。
著名文史學家梁勇應邀進行了實地考察,并對殘碑上所有文字進行研究,首先明確這通碑刻不是立在墓地前的神道碑,而是立在成德軍牙城門前的紀功碑。但是,這通碑的形制、體量都遠遠超過歷代帝王將相的紀功碑,顯示出碑主人標新立異的個性與目空一切的心境。初步劃定年代范圍之后,梁勇先生通過翻閱唐書、五代史等文獻典籍,尋找這一時期與真定相關的各類人物的蛛絲馬跡。在排除了五代最后一位成德軍節度使王镕、后唐投降契丹的趙延壽、遼世宗委任的中京(真定)留后契丹人麻達之后,將目光鎖定后晉石敬瑭時期的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
1200年前的塵封往事
五代時后晉大將安重榮有句名言:“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這句話,雖然是他感于后梁、后唐、后晉帝王都是由藩鎮節度使起家奪取皇位,卻暴露出擁兵自重,心懷異志。對于后晉皇帝石敬瑭割讓幽云十六州,甘當契丹“兒皇帝”,認賊作父、割地賣國的行為,安重榮十分蔑視。他反抗契丹的情緒非常激烈,經常大罵途經自己管轄范圍的契丹人,公開向契丹叫板。據《資治通鑒》記載: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恥于向契丹稱臣,每見契丹使者,必然岔開兩腿坐著,謾罵使者,使者經過他的轄境,有時竟暗中派人殺掉。契丹為此責備后晉皇帝,石敬瑭常常替他道歉謝過。有一次,安重榮把一個名叫拽剌的契丹使者抓了起來,并派出騎兵掠奪幽州南境,把軍隊駐扎在博野縣,向石敬瑭上表聲稱:吐谷渾和東、西突厥等部族不堪契丹欺凌,率眾歸附,情愿自備人馬,與晉軍共擊契丹。上表全篇幾千字,大部分篇幅是斥責石敬瑭“父事”契丹、竭盡中國所有向貪得無厭的胡虜獻媚。而且,安重榮不僅向石敬瑭上表,還把這層意思寫成書信,送達朝廷權貴和各藩鎮,說已經調兵遣將,誓與契丹決戰。安重榮旗幟鮮明反對石敬瑭、反抗契丹的態度,可見其為人處事之高調。因此,目空一切、霸氣外露地為自己樹立一通歌功頌德的巨碑,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公元941 年臘月,安重榮擁兵南下,意欲推翻石敬瑭的偽庭。石敬瑭急忙派大將杜重威出兵鎮壓,安重榮兵敗被誅——他的功德碑之所以被砸毀,這可能就是原因所在了。碑文中出現的“勝州刺史”“□□軍節度使、鎮深等州觀察處置……”等官職,都與安重榮的任職經歷吻合。碑文中“偽庭失德、群盜挺(埏)起”等字樣,也與安重榮反抗偽庭、抗擊契丹的情節相符。
安重榮高調反抗契丹,自然成為契丹人最痛恨的對象,契丹主“數欲親討重榮”,直到收到后晉朝廷送來的安重榮頭顱才作罷。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評價說:“事雖逆而名正者,安重榮也……”雖然,封建社會史書將安重榮定性為“謀反的叛逆之臣”,但近現代地方文化學者卻認為:安重榮反的是契丹入侵,反的是石敬瑭賣國,雖敗猶榮。他的民族氣節,值得后世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