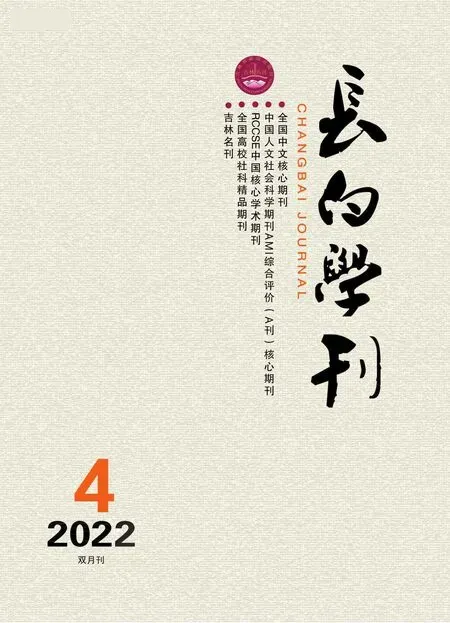《資本論》與“空間”的生命政治
許恒兵,許 迪
(國防大學政治學院,上海 201602)
與列斐伏爾更多地關注空間生產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不同,福柯對空間的關注更多地側重于政治性,特別是內含其中的施加于人的身體的權力技術。基于對“監獄”這一典型權力空間的細致分析,福柯發現現代社會在權力運作上的重要特點在于,空間憑借其自身的內部構造而成為一種權力機制,這種權力機制能夠對個人展開持續不斷的監視和規訓,使其變成一種新的主體形式。福柯指出:“如果一種機構試圖通過施加于人們肉體的精神壓力來使他們變得馴順和有用,那么這種機構的一般形式就體現了監獄制度,盡管法律還沒有把它規定為典型的刑罰。”[1]259監獄體現了典型的空間生命政治。在監獄空間中,犯人接受監視和規訓,以達到“改造”犯人的目的。正因為如此,福柯認為監獄的誕生意味著“規訓機制征服了法律制度”[1]260。在福柯看來,這種權力空間彌散于現代社會之中,如工廠、學校、軍營、社團等,都是監獄般的權力空間,都發揮著對人的身體進行規訓和懲戒的權力性作用。福柯由此揭示了空間的生命權力作用。從空間的權力作用視角解讀《資本論》,其中馬克思通過分析和批判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揭示了資本生產過程既是物質生產的過程,也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而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同時也是一個借助于空間規劃和重塑予以權力控制和規訓的過程。由此,《資本論》揭示了現代社會“空間”的生命政治。
一、“空間”的生命政治與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
在福柯看來,古代社會的“君主權力”是“讓你死”,即通過懲治乃至消滅肉體的方式來彰顯自己的權威和威懾力,并以此達到政治權力的統治作用。與此根本不同,現代社會的“規訓權力”表現出的則是“使你生”的歷史特質,即其通過一系列權力技術對個體的身體進行操縱、塑造、駕馭、使用、改造,以使其按照一定的意圖和方向發生變化,讓其變得有用、有效。由此,規訓權力便具有了“生產”的意味。同時,君主權力運作總是由一定的主體單向實施,而現代社會的規訓權力則是通過形成一系列的機制來實現,這些機制都表現出密封的空間特質,即如福柯所說,“這種機制是以一種更靈活、更細致的方式來利用空間”[1]162,從而在現代社會,空間自身便具有了權力操控的作用,它基于自己內部的獨特構造持續實現對人的監督、規訓和改造。福柯認為,“這是一種把個人既視為操練對象又視為操練工具的特殊技術”[1]193。規訓“造就”個人,其目的在于制造出“有用”的個人。在福柯看來,現代社會就是特殊的空間化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各種空間并置,共同發揮著規訓作用。因而,現代社會的權力運作的一個重要特質就在于通過空間來統治和管制社會,其目標在于“使人體變得更有用時也變得更順從,或者因更順從而變得更有用”[1]156。
雖然馬克思與福柯在對空間的理解上存在著視角的差異,即福柯主要是從權力技術的視角來理解和把握空間的權力運作,而馬克思則首先基于社會生產的視角來理解和把握空間的生成,并基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批判性分析來揭示內含其中的權力運作。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生產的過程既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同時也是通過空間規劃和重塑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空間成為資本對勞動者實施政治規訓的重要工具。福柯認為,從18 世紀開始,建筑開始成為政治學的討論對象,而其緣由則在于空間成為政治統治的工具,但由于福柯側重于從權力技術的視角來分析空間的權力運作,從而未能揭示這種轉變的現實根源。馬克思則基于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形成過程的描述來把握現代社會統治形式的變化,并以此把握空間的生成和內含其中的權力運作。在馬克思看來,空間絕非自行產生和延展的抽象存在,它的形成和變化始終建立在物質生產形式變化的基礎上。特定的物質生產形式就會產生特定的空間形式,并生成特定的歷史本質,包括福柯所揭示的空間的生命權力特質。當代左翼學者哈維指出:“每個社會形態都建構客觀的空間概念,以符合物質與社會再生產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據這些概念來組織物質實踐。”[2]377這一論斷無疑言明了馬克思對于空間的理解路徑,即相比于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在生產模式上的重要變化就是,“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融合在一起了”[3]273,274,而在封建社會,農民為維持自身生活所完成的必要勞動和他為領主所完成的剩余勞動“在空間上是分開的”[3]274。從勞動者的生存空間的視角來看,這種變化所帶來的權力關系方面的變化在于:在封建社會,由于剩余勞動與必要勞動相分離,從而在必要勞動階段農奴有著相對自主的空間,“農奴可以獨立于為地主的工作而生產其生存手段,因而剩余勞動必須通過超經濟手段來榨取”[4]44;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伴隨著剩余勞動與必要勞動的領域合一,勞動者的生存空間開始變得完全屈從于剩余價值的生產,成為資本運作的場域,這就為資本家規劃和重組勞動者的整個生存空間以實現對勞動者的權力操控奠定了基礎。
正如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通過規劃和重組空間來強化對勞動者的統治并貫穿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確立和發展的整個過程。在馬克思看來,“資本關系以勞動者和勞動實現條件的所有權的分離為前提”[5]821,822。按照詹姆遜的理解,這個分離過程本身就充斥著異化,并且體現為一個空間轉移和變形的過程。對此,他指出,“異化是一個歷史事件,但也是發生在空間中的事件,如土地和農民、圍場、從鄉村向城市的遷移,等等”[6]87。也就是說,勞動者變成勞動力并被納入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勞動者的生命空間被暴力所改變的過程。正如馬克思在考察資本原始積累時所揭示的,“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5]823。這種暴力性的“被拋”強行隔斷了他們與自然之間的古已有之的聯系,徹底摧毀了勞動者的既有的生活秩序。來到陌生的市場之后,他們感到無所適從,為了生活所需,他們有的很快將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有的被迫淪為乞丐、盜賊、流浪漢。但后者絕不是資本家所需要的。為此,資本家及其政治上的代表者很快制定出了法律,使得鞭打、監禁、割耳等變得合法化,其目的就是要將這些“被拋者”統統趕到工場之中。馬克思描述到,這一過程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5]822。
在資本主義社會,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之所以會“合一”,就在于勞動者喪失了一切生產資料,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他們一無所有。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他們只能將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正如馬克思所揭示的,大量自由勞動力的出現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前提。從歷史進程來看,“勞動力”的出現不僅意味著一種特定的生產關系的形成,而且意味著空間的生命政治之發端。正如維爾諾所指出的,“要想理解‘生命政治’這一術語的理性內核,我們應該從另外一個概念開始,一個來自哲學觀點的更復雜的概念:勞動力(labor-power)的概念”[7]104。在他看來,勞動力是一種“非現實的潛力、活力”,它與實際的行動截然不同。對此,馬克思也明確指出,“談勞動能力并不就是談勞動,正像談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談消化一樣”[3]201。當資本家購買了這種生產能力之后,就可以隨自己的意愿將其當作商品使用了。維爾諾認為,“勞動力模棱兩可的矛盾特性(虛構的一些東西,卻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樣被買賣著)是生命政治的前提”[7]106。為了讓作為“潛力”的勞動力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最大限度地實現資本的增殖,資本家便開始對作為勞動力之“載體”或“基質”的生命或身體進行干預、控制、規訓、管理,而“對身體的管教是為了提高勞動的生產率水平”[7]107。雖然維爾諾僅僅只是從“基質”的角度來談論勞動力,而沒有認識到“勞動力”的出現本身意味一種特定的生產關系的形成,因而內含著歷史性的特質,但其無疑指明了“勞動力”之于生命政治運作的前提性作用。勞動力形成以后,資本家通過購買的方式將其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并通過將勞動者的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結合起來開始組織生產和再生產,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實現資本的增殖,而資本實現增殖的關鍵在于最大限度地剝奪工人的生命時間。為了更好地達到這個目的,資本及其人格化的代表——資本家便通過空間塑造對工人展開監督和規訓,以使其轉變為適合的主體形式。
二、資本的空間塑造與“空間”的生命政治
正如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確立過程經歷了協作、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化生產三個階段。其中,每個階段都體現出了資本系統富有自身獨特性的空間重組和規劃,并以此對勞動力的生命實施控制和規訓。我們首先來看協作中的空間重組與規劃及其生命權力作用。正如馬克思所指認的,無論是從歷史上來看,還是從概念上來看,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就在于同時雇傭人數較多的工人,他們在同一個資本家的指揮下,在同一時空中生產某種商品。具體來說,資本確立其統治地位的過程首先在于將大量勞動力集中到資本家設置的特定空間中從事商品生產。對于資本而言,這種集中導致了許多個人之間相互“協作”的開始。通過這種協作,不僅個人的生產力得到提高,而且還能創造出一種生產力。馬克思指出,“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5]378。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協作的效能,資本家便開始制定嚴苛的紀律對工人實施監控、協調和管理,而這種通過集中所形成的“封閉空間”則為紀律發揮作用鋪平了道路。正如福柯所指出的,“紀律有時需要封閉的空間,規定出一個與眾不同的、自我封閉的場所。這是貫徹紀律的保護區”[1]160。通過工人集中所形成的空間由此成為權力操控的場域,它以雇傭工人完全服從資本的指揮和管理而獲得具體表現。在由資本集中所形成的封閉空間中,資本家通過嚴苛的紀律對工人的行為進行規范,其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保護生產資料和駕馭勞動力,防止出現偷盜、怠工、騷亂和“密謀”等,而這些正是阻礙資本增殖的因素。
在協作階段,資本生產的組織是建立在既有的個體勞動方式的基礎上的,而工場手工業則使它徹底地發生了革命,并從根本上侵襲了個人的勞動力。這一侵襲的過程,同時就是資本對空間重新規劃和塑造的過程。對于18 世紀所形成的規訓機制,福柯從空間的視角分析指出:“這種機制以一種更靈活、更細致的方式利用空間。它首先依據的是單元定位或分割原則。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個位置都有一個人。……其目的是確定在場者和缺席者,了解在何處和如何安置人員,建立有用的聯系,打斷其他聯系,以便每時每刻監督每個人的表現,給予評估和裁決,統計其性質和功過。因此,這是一種旨在了解、駕馭和使用的程序。”[1]162與福柯從權力技術的視角分析空間的生命權力作用不同,馬克思則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批判的視角展開分析和批判。正如馬克思所揭露的,資本增殖的關鍵在于將作為價值之活的源泉的勞動力納入資本生產系統中,使其成為資本增殖的工具。但如果說任何工具只有經過磨合和鍛造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用,那么作為工具的勞動力也是如此。對于資本而言,必須將其置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不斷地予以規訓,以使其變得有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資本權力便具有了“生產”的作用。而這種“生產”必須置于特有的空間中才能取得實效。如果說在協作階段,資本還沒有形成自己特有的生產方式,因而還無法讓勞動力從屬于自身,那么伴隨著工場手工業的產生,資本則實現了對勞動力形式上的吸納。在此前提下,資本逐漸建構起一整套規訓、使用、駕馭工人身體的空間運作機制,即馬克思所說的“以人為器官的生產機構”,以實現對工人生命時間的攫取。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協作階段推進到工場手工業階段,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工人生命空間的變化。對此,福柯在其《規訓與懲罰》著作中指出,“個人分割化的原則變得更加復雜。這涉及如何將人員分配在一個既能隔離又能組合的空間中,而且還涉及如何根據具有獨特要求的生產機制進行這種分配。必須把人員的分配、生產機制的空間安排以及‘崗位’分配中的各種活動結合在一起”[1]164,并設置一個能夠通觀內部全局的監視點,這樣就能讓勞動能力分配在一系列工人身上,并使其最大限度地形成“集合力”。正如馬克思所揭示的,相比于協作,工場手工業最大的特點在于擴大了分工,其鮮明的表現就在于,一個完整商品的生產被拆分成了各個環節,而每一個工人則被安排在其中的一個環節中,并逐漸固化為其專有的職能,個人由此成為“局部工人”。對于資本而言,基于分工而形成的這種空間劃分和位置固定,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但伴隨著分工的固化,局部工人“把自己的整個身體轉化為這種操作的自動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費在這一操作上的時間,比順序地進行整個系列的操作的手工業者要少。……因此,與獨立的手工業比較,在較短時間內能生產出較多的東西,或者說,勞動生產力提高了。在局部勞動獨立化為一個人的專門職能后,局部勞動的方法也就完善起來。經常重復做同一種有限的動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這種有限的動作上,就能夠從經驗中學會消耗最少的力量達到預期的效果”[5]393,394。正是通過分工的擴大以及對工人的固化,工場手工業儼然成為一個“規訓系統”,這個系統有著自己獨特的空間運作,并對作為其“器官”的工人持續實施規訓、支配和壓榨,或如馬克思所說,“總機構的聯系迫使他以機器部件的規則性發生作用”[5]404,405。在這種空間規訓中,局部工人不僅變得日益片面,而且變得日益遲鈍。正如弗格森所描述指出的,“無知是迷信之母,也是工業之母。……所以,可以把工場看成是一部機器,而人是機器的各個部分”[5]418。福柯也指認,“在大工業嶄露頭角之時,人們在生產過程的分割后面可以發現勞動力的個人片面化”[1]165。正是由于固守在完整的生產過程的某一環節之中,并反復從事著同樣的操作,工人的生產志趣和才能得到了壓抑,日益成為片面化的存在,工人個人的發展也由此遭到徹底消弭。進一步來看,總體工人的各種職能存在著簡單和復雜、低級和高級之分,而分工所形成的總結構將各種職能強制性地分配給工人,并硬化為他們的專門職能,從而在工人內部造成了等級之分。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資本將勞動力吸納到自身系統中,并通過空間規訓以實現對勞動力生命時間的最大限度地榨取,以此實現自身價值的增殖。但是,由于工場手工業自身的技術基礎的限制,資本的增殖仍然受到了限制。具體來說,在工場手工業中,資本生產仍然以工人的活動為基礎,工人相互之間的轉化和聯結仍然會受到工人熟練程度以及人自身的力量的限制,這就造成了資本無法完全支配工人的勞動時間。這對于“時間就是一切”的資本而言,顯然是一個致命的缺陷。為此,資本家發展出了機器體系。機器體系的最大特點就在于,它不再依賴于工人,而是能夠自行運轉,自己與自己分離和結合。由此,作為資本的機器體系再次實現了對空間的重新規劃。正如詹姆遜所指出的,“馬克思對資本描述的高潮——機器大生產的出現——也是空間的,因為機器大生產用將生產集中起來的工廠新空間墾殖了空間”[6]87,88,并指認馬克思《資本論》中關于機器大生產的章節“探討的是主體性的空間”[6]91。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如果說分工的擴大造成了一個特殊的空間系統以對工人的生命進行權力規訓,通過這種規訓,工人被逐漸塑造為符合資本增殖要求的“工具”,那么伴隨著機器體系的出現,資本實現了對空間的全新塑造,并進而造成了新的控制人的身體的方式。對此,福柯指出:“隨著工廠的發展,也形成了大面積的單純而明確的工業空間:首先是綜合制造廠,到了18世紀后半期,形成嚴格意義上的大工廠。……這不僅是規模上的變化,而且是一種新的控制方式。”[1]161正如馬克思所揭示的,機器與工具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工具的特點在于必須經過人手才能發揮作用,而機器則是一個能夠自行運轉的客觀系統,即“整個過程是客觀地按其本質的性質分解為各個組成階段,各個局部過程如何完成和各個局部過程如何結合的問題,由力學、化學等等在技術上的應用來解決”[5]437。具體來說,所有發達的機器由三個不同的部分構成,即發動機、傳動機、工具機或工作機。其中,發動機和傳動機的功能在于通過自身運動將動能傳給工具機,而工具機則將動能施加于勞動對象之上,并按照預定的目的來改變它。特別是伴隨著發動機、傳動機和工具機在技術上的不斷改進,單個的機器逐漸發展成為機器體系。在機器體系的運作中,工場手工業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并沒有消失,而是變成了作為機器體系的局部工作機的“結合”[1]436。這個自行運轉的客觀系統將工人納入其中,并以自己的節律對工人進行規訓。奈格里和哈特認為,“馬克思的資本對勞動的實質吸納這個概念非常有用,這個概念的意思是,資本不再簡單地在規訓式裝置和生產過程中吸納之前就外在于資本創造出的勞動行為(這只是形式吸納),而是創造出新的、真正的資本主義勞動形式,也就是說,將勞動完全整合進資本主義的軀體內”[8]105,這種整合正是通過資本的機器體系來完成的。而后,這個“死機構”以其連續的、劃一的運動對工人的身體進行規訓,使其變得適合自己的運轉節奏。而從工人的角度來看,其更深層次的效應乃在于,這種規訓逐漸消解了工人的任何“不適”,使其逐漸習慣了機器的節奏。從這個意義上講,布若威認為“馬克思在他的勞動過程理論中沒有為同意的組織留出空間”[4]47,實為對馬克思的誤讀。機器體系還基于分工的原則在工人之間造成了新的等級關系,“過去是終身專門使用一種局部工具,現在是終身專門服侍一臺局部機器”[5]485,486。由于在技術上服從于勞動資料的劃一運動,工人的神經系統受到嚴重損害,實現工人的肌肉健康的多方面運動也受到壓抑。總而言之,機器體系奪取了雇傭工人身體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動。適應機器運轉節奏對工人所造成的超負荷工作,使得工人陷入一種赤裸的生活,“這種生活比阿甘本的集中營中絕望的居民所面對的還要更深地植根于經濟系統”[6]100。
總之,福柯所確立的“空間”的生命政治視角,主要是從權力技術的角度揭示現代社會空間規劃對人的生命的政治權力作用。與福柯不同,馬克思則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視角揭示資本通過空間規劃和重塑馴化工人的生命權力作用。正是通過這種揭示,馬克思暴露了現代社會空間的生命權力的深層根源,同時為空間的生命政治批判提供了方向指引。
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批判與生命空間的解放
正如前文所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重要特質在于通過規劃和塑造空間對工人的身體進行控制和規訓,以此達到最大限度榨取生命時間、實現自我增殖的最終目的。既然如此,要徹底消除現代社會施加于工人的生命權力作用,實現工人的生命空間解放,最根本的路徑無疑應該是顛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福柯在其規劃的權力抵抗路徑中同樣內含著對生命空間解放的思考。在福柯看來,現代社會到處彌漫著針對人的身體的權力空間,監獄是其中的典型,它通過權力的運作改造人。學校、工廠、精神病醫院、慈善團體等空間同樣隱藏著權力運作。表面來看,這些機構都是“用于減輕痛苦,治療創傷和給予慰藉的,因此表面上與監獄炯然有異,但它們同監獄一樣,卻往往行使著一種致力于規范化的權力”[1]353。面對現代社會無處不在的內涵權力運作的密封空間,福柯努力尋求實現人的生命空間解放的路徑。與其對微觀權力的關注相一致,福柯倡導通過局部斗爭的方式來減弱現代社會的權力空間施加于個人身體與思想的各種控制,并特別強調特殊型知識分子在局部斗爭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面對四處彌散的空間權力網絡,福柯最后走向了個體自我的審美救贖。在他看來,每一個人都應該關注自身,“想象和建立我們可能之所是”[9]287。遵循這個路徑,福柯認為,反抗權力斗爭的根本目標不是奪取權力,而是告別舊的主體,成為新的主體,即通過“對數個世紀以來強加于我們身上的個體性進行拒絕”,以此“促發一種新的主體性”[9]287,288。在福柯看來,如果否定種種歷史決定論,并走向主體化的生存美學和自我技術,將獲得一種根本性的獨立意義。這種審美的生存——既是身體上的,也是精神上的——目的在于,使個體化的自我生存不再依賴于外在于個人的任何原則,而是達及一種自由自覺的生存狀態。很顯然,福柯倡導的是一種“后主體時代”的抵抗,這種抵抗以孤立的個體為主角,并將“斗爭”的主戰場設置在了人的“內心”。但是,面對現代社會龐大而隱匿的空間權力關系網絡,個體的局部反抗必定是無力的。福柯最后選擇退守“內心”的自我審美救贖,則是這種無力抵抗的反映。而由于生存美學特別依賴于個體自我的創造性,因而并不適用于普通大眾,從而所謂的審美救贖便只能局限于少數社會精英。更為重要的是,內心的審美救贖實屬一種“消極抵抗”,其不僅無法觸動現代社會的空間權力運作,而且以無聲的方式默認了現代社會的權力,因而從深層次上來看,這仍然屬于馬克思所說的“無批判的實證主義”。正因如此,凱文·安德森認為福柯的“抵抗”概念里“缺少一種解放的觀念”[10]。
與福柯規劃的局部斗爭和個體自我審美救贖的路徑不同,馬克思認為,個體是社會性的存在,在階級社會中,個體總是隸屬于一定的階級,因此任何局部斗爭只有置于階級斗爭的框架內才是有效的,而個體的生命空間解放必須以階級革命和社會解放作為前提。正如馬克思結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遷對內含其中的空間權力運作機制所作的揭示表明的,對馬克思而言,任何權力結構歸根到底源自于經濟結構,因而要徹底打破現代社會的空間權力牢籠,最根本的不是停留于純粹的權力技術分析,更不是退守“內心”而任由權力肆虐,而是要徹底顛覆權力關系由以衍生出來的經濟結構,即對現實世界進行徹底的變革。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11]527。
要求徹底變革世界,體現了馬克思遵循主體行動邏輯規劃生命空間解放的路徑。那么,由此引發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這種主體的顛覆行動何以可能?對此,馬克思在1845年左右實現哲學變革后,逐漸轉向更加注重從客體結構的邏輯視角探究生命空間解放的現實可能性,并以此為主體行動的邏輯奠定基礎。在馬克思看來,人是一種社會性存在,總是隸屬于特定的社會關系。而人成為什么樣的人,或者說人的歷史性本質則是由人所隸屬于其中的歷史性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所塑造和規定的。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序言中專門做了說明。他明確指出:“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5]10這為馬克思從客體結構的邏輯展開“空間”的生命政治批判以及規劃生命空間解放路徑提供了指引。與主體行動的邏輯立足于主客體對峙的框架理解和把握人的生存境遇不同,客體結構的邏輯則將人視為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承擔者,并基于生產關系批判來論證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化空間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形成的,歸根到底是服從于資本增殖需要的。因此,要徹底擺脫施加于人的身體的各種空間權力,徹底實現人的生命空間的解放,最根本的路徑就是顛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并代之以一種全新的生產關系。
那么,這種取代何以可能?對此,馬克思基于客體結構的邏輯分析和把握資本運動自身中必然遭遇的矛盾和困境,以此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新型生產關系所取代的歷史必然性。在馬克思看來,“一種歷史生產形式的矛盾的發展,是這種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歷史道路”[5]562。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不僅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先后經歷了協作、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化生產等各個階段,而且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崩潰,即“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5]874。我們知道,資本生產的唯一目的在于實現自身的增殖,為此,資本不斷推進技術革新,提升資本的有機構成,隨之而來的則是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的比值越來越小,從而資本的利潤率不斷下降。集中來講,其中的矛盾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包含著絕對發展生產力的趨勢”,而其用來達到此目的的方法卻是“靠犧牲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力來發展勞動生產力”。正因如此,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12]278。伴隨著資本的不斷拓展,其歷史局限性會日益暴露,最終會因其內在具有的“自我否定”性而退出歷史的舞臺,從而“資本并不像經濟學家們認為的那樣,是生產力發展的絕對形式,資本既不是生產力發展的絕對形式,也不是與生產力發展絕對一致的財富形式”[13]96。由此可見,《資本論》對現代社會之空間的生命政治的揭示同時就內含著對“空間”的生命政治的批判,而其中對生命空間解放的路徑規劃就內蘊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批判之中,這一規劃展現了《資本論》的深層次政治批判潛能。因此,當詹姆遜指認《資本論》“沒有政治結論”[6]110時,實為一種誤讀。
馬克思辯證地把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遷過程,認為這一過程既是通過塑造權力化的空間對人的身體進行干預和規訓的過程,同時也為人的生命空間解放奠定了基礎。從本質上來看,相比于以往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改變了人與人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即從“人的依賴關系”的歷史階段轉入“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歷史階段。在這個階段,雇傭勞動者雖然獲得了身份上的獨立,但卻由于喪失了一切生產資料而不得不將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這也是資本之空間權力運作的必要前提,并由此造成了人的奴役。但是,這一構成的另一面卻在于,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這種聯系是各個人的產物。它是歷史的產物。它屬于個人發展的一定階段”,并且這種聯系為人的解放奠定了基礎。因為正是資本主義生產“在產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相異化的普遍性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系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3]56,而它的自我展開必然會導致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社會上的一部分人靠犧牲另一部分人來強制和壟斷社會發展(包括這種發展的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現象將會消滅”,從而“剩余勞動能夠同物質勞動一般所占用的時間的更大的節制結合在一起”[12]928。馬克思由此闡明了實現人的生命空間解放的兩個重要前提,一個是社會關系的解放,即人真正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一旦這一目標實現,就會徹底瓦解資本——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的代表——與雇傭勞動的對峙結構。在這種結構中,資本顛倒為主體,并通過空間塑造對雇傭勞動者不斷進行再生產。另一個是伴隨著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作為物質生產領域的“必然王國”所耗費的勞動時間越來越短,“而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12]929。在這個自由王國,每個人的能力素質的提升成為目的本身,因而就不會有任何外在的力量將個人限制在特定的空間內,而是每個人依憑自己的興趣愛好來發展自己,從而使得生命的時間真正成為發展的空間,而且還可以在不同的領域自由轉換。
總而言之,馬克思對人的生命空間解放路徑的規劃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批判的基礎上的,因而與種種關于人之美好未來的烏托邦式構想劃清了界限。就此而言,當詹姆遜指認“對馬克思來說,未來的工廠,資本主義之外的烏托邦生產空間,應該被看做也是生產、建構主體的空間,以及方方面面教育的基本場所”[6]94,并認為“這是一個烏托邦式的逆轉”[6]95,則并沒有真正理解馬克思基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批判所規劃的生命空間解放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