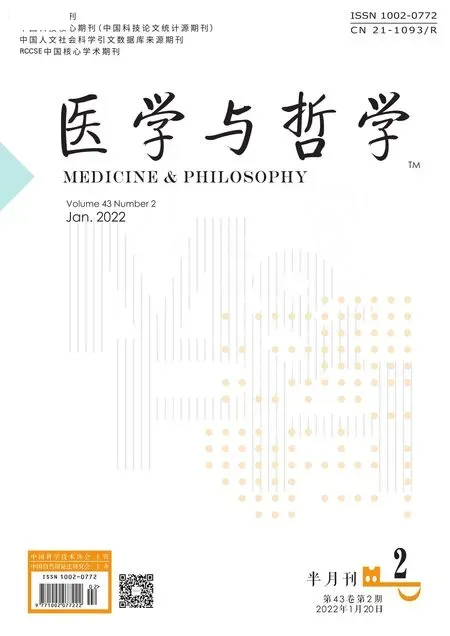隨附性物理主義視角下對心身關系的考察*
楊 平 張效初
心身關系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心靈哲學的研究熱點,研究視角隨時代變遷幾經演變,直到笛卡爾的心身二元論的出現,挑戰了中世紀傳統的心身統一學說,標志著心身問題上的一次革命性轉向。然而心靈如何發揮作用?笛卡爾的實體二元論始終無法做出合理解釋[1]。
在近現代物理學和心腦科學的成就下,很多哲學家都試圖在物理主義和還原論的框架里解決心身問題,此時心—身關系變成了物—物關系。然而20世紀60年代普特南、福多等提出功能主義的多重實現論題,還原論也暴露出其內在困境,普特南強調心理特性在物理領域中具有多種可能的實現,因此,物理學不能為心理學提供精準的描述[2]。
這使得物理主義陷入難以解決的困境,20世紀70年代戴維森提出的無律則一元論,為困境中物理主義找到了新出路,并首次將隨附性(supervenience)引入關于心-身問題的討論。戴維森既沒有脫離物理主義的框架, 又避免了二元論的桎梏,賦予了心理事件某種相對獨立的地位。他認為“心理特性在某種含義上依賴于或隨附于物理特性”[3]79-102。此概念一經提出,立刻成為了學術界探討心身問題不可忽視的重要資源,也成為了此后的心-身問題探討中的一個具有獨立性的議題。隨附性物理主義因其自身獨特的包容的特質,為在非還原的物理主義(nonreductive physicalism) 進路下理解心身關系問題創設了一套嚴謹的可行的哲學論證。
1 無律則一元論以及隨附性的概念
1.1 戴維森的無律則一元論
1970年,戴維森在他的代表作《心理事件》一文中,對心身關系問題做了歷史性總結。他將心身關系問題概括為四種:以心身還原論、同一論為代表的“合律則一元論”;以副現象論為代表“合律則二元論”;以笛卡爾實體二元論為代表的“無律則二元論”;以及由戴維森本人提出的“無律則一元論”。此時的戴維森旨在幫助物理主義走出困境,發展一種既堅持物理主義的心身關系的解釋,又能擺脫傳統還原論的解釋局限的理論。
無律則一元論三個原則[4]如下:
(1)因果相互作用原則(principle of causal interaction):“至少有些心理事件同物理事件可以發生因果相互作用。” 因果相互作用原則屬于本體論范疇,這條原理比較符合人們的常識經驗,也被大多數的哲學家認可。戴維森這樣強調了心身交互的作用: “因果作用是整合世界的黏合劑; 因果作用使我們持有一個完整世界的圖象, 否則的話, 世界就將被分裂成了心理和物理的雙折畫。”[5]214
(2)因果關系的法則學特征原則(principle of the nomological character of causality):作為原因與結果能被關聯起來的兩個事件,必然從屬于嚴格的規律的限制。因果關系的法則學特征原則屬于認識論范疇。其實質為,兩個被因果關聯的事件在某些描述下例示了一條普遍的規律。
(3)心理的異常性原則(principle of the anomalism of the mental):不存在嚴格的律則可以對心理事件做出預知和解釋。心理的異常性原則屬于語言學范疇。戴維森認為心理屬性具有整體性特征,首先從心理語句具有命題態度的角度否定了心理詞匯可以用來描述嚴格的規律,任何心理事件都不可能獨立存在,它必然與其他心理事件發生相互作用——“信念和愿望造成僅僅由不加限制的進一步的信念和愿望、態度和傾向來修正和調整的行為”[3]448。
這三條原則支撐了無律則一元論,不過這三條原則也招致了一些爭議,金在權等學者批評這三條原則相互矛盾,不能自恰,前兩個原則至少可以推斷出某些心理事件依據規律可以被預測和解釋的,然而第三個原則卻又馬上否認了前兩個原則,認為不存在可以對心理事件做出預測解釋的規律[4]。
戴維森解釋說其實這個矛盾本身并不存在,前兩個原則是以個別事件或個體所談,后一原則是以一類事件或性質為對象所談。因此無律則一元論可以解釋為:某個單一的心理事件可以被還原為某一物理事件,但作為一類心理事件或者心理性質則不能還原。
盡管給出了解釋,但此時戴維森并沒有給出系統的論證來,而只是通過比較心理概念和物理概念的不同表達(實現)來說明這一點。這樣的說法并不能讓很多學者滿意,既然無律則的一元論認為事件僅當它們例示物理的規律時才發揮因果效力, 那么這種因果效力如何得以體現呢?金在權更是構造出因果排斥性論證(causal exclusion argument),進一步指出:如果“無律則一元論”宣稱沒有心身規律,心身關系不可還原,那么獨立的心理屬性就必然被物理屬性排斥在外[4]。
而戴維森針對心理因果效力的質疑,提出了關鍵的概念——“隨附性”(supervenience),他在堅持物理主義路線的同時,還強調了心理屬性不是物理屬性,但可以隨附在物理屬性之上,或者心理屬性可以通過隨附于物理屬性得以實現其本身作用。
1.2 隨附性概念
那么什么是“隨附性”?其又是如何幫助心理屬性實現自己的效力的呢?
“隨附性”概念最早在道德哲學中出現,英國突現論學派(British emergentism)的摩爾、黑爾等哲學家都曾在各自著作中表述過隨附性的涵義,戴維森首次將其引入心靈哲學、心身關系問題的描述中[6]。他認為,精神、心理特征從某種意義上說依賴于物理特征,并首次在心靈哲學中使用該術語描述一種非還原主義的物理主義方法:如果物理基礎相同的事物,那么其在心理屬性方面也是相同的,不可能出現兩個事物物理基礎相同而心理屬性不同的情況[5]208-224。
隨附性是用以描述系統的不同層次屬性的本體關系,一般來說較低層次的屬性決定了較高層次的屬性或者較高層次屬性隨附于較低層次屬性。曾有學者表示我們的世界就是由不同層次的屬性構建的,并符合低層次屬性決定高層次屬性這樣的規律。由此而來,化學屬性決定了生物屬性,生物屬性決定了心理屬性,心理屬性決定了社會屬性[7]。
這個范式的界定如下:A(隨附集)和B(隨附基礎)。A隨附B,如果B沒有變化的話,A也就不會表現出差異。
由此看出,隨附性是一種決定(或依賴)關系,如大腦(物理)狀態可能決定了精神(心理)狀態。也就是說,通過這種隨附關系獲取了兩者間的相互關系。假定某一心理屬性A(焦慮)依附于某一屬性B(大腦區域)。如果兩個個體X與Y都具有屬性B的物理特征,那么這兩個個體也就具有A的屬性特征,也就是說相同的大腦某一物理特征會帶來相同的焦慮(心理)狀態。換言之,X、Y兩個個體只要擁有了相同的物理基礎就會表現出相同的心理特征。同樣,在隨附屬性上,如果兩個對象不同,那么他們的基礎屬性也一定不同[3]448。但是這里有一個前提,即基礎屬性B一定是最小基礎屬性,B無法識別。
盡管隨附性用來描述不同屬性之間的關系,但隨附性本身蘊含了一種“反還原”的關系。物理主義認為宇宙的一切現象的本質屬性都是由物理屬性所決定,都是可以用物理法則解釋的,物理法則控制了一切失控對象。如果說心理屬性依附于物理屬性,這是因為在物理主義學者看來兩個世界從物理意義上完全相同。 不過,這不意味著心理學可以直接還原為物理學。也就是說,“高層級的現象”最終取決于物理狀況,但不意味可以利用物理學方法來研究心理學中高層級的現象。例如,Churchland[8]在倒置感受的思維實驗中,發現如果紅色變為綠色,這只是說明我們視覺狀態(心理)的變化,而非大腦狀態(物理)。心理上感知不同的顏色,但不意味著產生了新的本體顏色或大腦基礎的改變。
因此,心理屬性可以具有其因果效力,只不過其因果效力需要附屬于物理屬性基礎之上,二者共同起作用。同時隨附關系不能僅從整體和部分角度理解,更不能簡單認為整體是部分簡單相加的集合。有時部分相加會超過整體,而整體有時候會超出部分之和,因為部分互動的非線性本質所致。
可以看出,隨附性理論對非還原物理主義的無律則一元論,做了很好的補充,隨附性理論認為心靈一定依附于身體,也就是說物理屬性決定了心理屬性,堅持了物理主義一元論,同時又認為心理現象無法還原,因為沒有心理法則。心理特征無法還原為物理特征,但是它們可能依賴于這些特征,這種依賴取決于隨附性。
2 隨附性物理主義對于心身關系的解釋
人類對心身關系的理解會受到非科學因素的影響, 這阻礙人們對其理性認識,使得人們走向兩個極端。14世紀前, 受到宗教思想的束縛, 人們普遍認為心理問題、心理疾病由超自然力量所致, 完全忽視了生理因素對心身關系的影響。而19世紀后隨著生物醫學模式的興起, 學者們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過度強調生理因素和遺傳性的作用, 這也導致當時人們對心理疾病、心身疾病產生了誤解和恐慌, 也極大阻礙人們對心身問題的深入理解。
而戴維森的這種“折中”隨附性物理主義似乎在解決心身關系上找到了一條更“準確”、更“有效”的路線,為解釋精神本源問題開啟一個新視角:他堅持了物理主義的道路,堅持了物理屬性對心理屬性的決定作用,避免了走向二元論的死胡同,同時提出隨附性概念強調了心理的因果效力,避免了還原模式的束縛。
2.1 無律則一元論三原則對心身關系的解釋
戴維森始終堅持的無律則一元論就是堅持一切事件都是物理事件的本體論,無律則一元論的因果關系的法則學特征原則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思路:當心理事件與物理事件有因果關聯時,這些事件就被嚴格的規律所支配,而這樣的規律出現在物理學中的一種封閉系統中。 簡單來說既是心理事件依賴于物理事件,心理狀態取決于腦基礎(物理事件)的影響。
這種思想隨著20世紀以后人們對大腦認識的加深而不斷深入,不僅單純地解釋腦本身的生理基礎,而且更致力于了解人腦是如何反映外界現實環境中的事物,如何產生心理活動,如何反映社會現象。心身關系也是沿著生物學(物理學)的角度來思考心理(行為)與大腦的關系。早在1929年著名的心理學教授博林提出了神經心理學(Neuropsychological)一詞,用以研究動物腦機能與行為的關系問題,也開創了用腦機能解釋行為學的實驗科學。
而神經心理學的歷史起點可以追溯到1861年,當時法國的神經科醫生布羅卡發現一個患者受到腦外傷后不能說話,后經尸檢發現此患者左腦額下回受損,布羅卡提出額下回是引起運動性失語癥的原因,后把額下回命名為言語運動性中樞。此后神經心理學的“定位主義”迅猛發展,德國精神病醫生韋尼克找到了左側顳上回后部損傷是感覺性失語的根源,1876年費里爾通過動物實驗發現了聽覺中樞在大腦顳葉;孟克于1881年對狗的實驗發現,被破壞大腦枕葉的狗看不到任何的影像,繼而確定了枕葉為視覺中樞。1906年德國醫生阿爾茨海默發現了首例腦退行性疾病,后以本人的名字命名此病,當時的神經病學家通過顯微鏡發現,患者大腦腦葉明顯萎縮,大腦下部區域存在明顯的神經元缺失,并且神經元細胞出現了纖維病變,并有許多類似球形斑塊的生物沉積物遍布患者的大腦和大腦血管。
此時在物理主義思潮影響下,生物醫學也得到快速發展,醫生們發現很多精神癥狀似乎都有其物理(腦)基礎的證據。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醫學技術的進步,如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computerized tomography,CT)、單光子檢測(single photon detector,SPD)、事件相關電位技術(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技術(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等技術的出現,使腦功能研究進一步加快。有關心身疾病的生物學標志(biological marker)的研究,越來越引起醫生以及學者們的關注,其對臨床診斷、治療效果評估以及預后等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心理(精神)癥狀似乎依賴腦基礎而形成,然后,戴維森因果相互作用原則中也強調了心身因果交互的作用。對于某一心理癥狀,我們并不能孤立地考察,如焦慮(狀態),當我們試圖給出焦慮(狀態)一個清晰描述時或者考察它與某一腦區域(物理基礎)的因果關系時,我們總是要涉及到其他的心理癥狀,如緊張、恐懼、抑郁等,而這個心理狀態又要涉及更多的心理屬性,也就是說,我們不得不在一個整體論的角度上討論我們所要考察的那個心理狀態。心理領域的這種整體性、容貫性以及相互性的特征,物理領域并不具有。
同時,我們在考慮心理癥狀(狀態)時,也不得不把這些癥狀(狀態)歸于某一特定的主體,而每一個主體又不完全一樣,癥狀總帶有個人特征,與個人的心理特質、成長環境都有關,因此正如戴維森的心理異常性原則所表述的一樣,不存在嚴格的心身還原規律,這種因果關系存在于一切個別事件之間,但是作為一類的心理事件無法由物理科學來說明,這也是目前很多腦機制的研究中并沒有得到一致性結論,甚至是矛盾結論的原因。例如,對神經質人格特質的腦機制研究中有些學者發現,被試在觀看情緒圖片過程中的腦電活動的差異主要出現在大腦右半球的頂枕區[9],而另有研究發現高神經質人格特質的個體表現出更強的額葉中部的腦電活動的偏側化效應[10]。
關于抑郁癥發病機理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現象,有學者認為一種負性認知加工偏向是抑郁患者典型的認知特點,這種認知反映的是對負性情緒刺激自下而上的反應增強,與杏仁核、梭狀回(fusiform gyrus)等腦區的過度活躍有關[11]。相反有研究則發現抑郁患者表現為不能抑制負性情緒信息,導致了消極認知,這反映的是自上而下的認知控制功能不足,與背外側前額皮質(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12]、背側前扣帶回皮質(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dACC)[13]、前喙扣帶皮質(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rACC)[14]等腦區激活下降有關。
2.2 心身關系中心理因果效力的實現
“精神或心理的原因作用如何實現”,這一心理因果性討論一直以來都是哲學研究以及精神病學領域的經久不衰的話題,1977年美國學者恩格爾在《科學》雜志上撰文《需要一種新的醫學模式——對生物醫學的挑戰》,提出了應該將人類目前取得巨大成就的生物學與心理學、社會學成果結合起來,創建一種新的醫學模式——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不僅從個人的、生物學角度,而是從整體的以及群體、生態學系統綜合的視角研究健康與疾病的關系。
傳統的生物醫學模式在過去的上百年時間里為人類的健康做出巨大的貢獻,特別是在控制傳染病、減低死亡率等方面,目前生物醫學技術依然在迅猛發展,如器官移植、基因工程等。但是生物醫學模式也存在著不可彌合的缺陷,主要原因在于其堅持心身二元論和自然科學的分析還原論,堅持認為心身之間并沒有相互作用,每一種疾病都有確定的生物學或理化方面的特定原因。
醫學模式的轉變也改變著醫生們對心身問題的看法,對心身問題的看法也更加深入,20世紀60年代,關于研究精神與軀體相互關系的學科——心身醫學出現,它成為當代新興醫學科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心身醫學最早起源于美國,美國醫生首先使用心理生理障礙的命名,又改用心理因素影響的軀體狀態,我國一般采用國際通用的分類合并使用心理生理障礙與心身疾病的概念描述這一類疾病,此類疾病一般是指主要的或者完全的由心理社會因素導致,并伴有不良情緒、精神痛苦感,并表現出生理功能障礙而沒有明顯的精神活動與行為障礙的疾病。
許多實驗和臨床證據也證明了,心理活動的自我調節對維持健康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一些心理治療不僅可以達到緩解壓力、消除不良情緒的作用,甚至還可以改變腦基礎。
一項關于通過心理療法治療抑郁癥患者的研究[15]發現,治療后患者扣帶中回及膝下扣帶的自發活動顯著下降,同時dACC與DLPFC的功能連接與左側輔助運動區的功能連接明顯升高。可以看出有效的心理治療不僅僅可以改變孤立的功能異常的腦區,還可以通過調節某些重要的節點間功能來重塑整個情感網絡從而改善情緒。在這個過程中扣帶回可能是干預作用的起始點,膝下扣帶自發功能的改變可能是潛在的治療反應標志物,而心理治療通路中的重要機制可能是通過大腦網絡自上而下的調節模式而形成。相似的,一項團體認知行為療法對抑郁癥患者神經成像影響的研究發現,采用認知行為療法進行4周的團體輔導后,受試者右側額中回灰質體積顯著增加,低頻波動顯著降低,同時左側中央后回灰質體積顯著降低。進一步的相關分析表明,右側額中回灰質體積百分比的增加與貝克抑郁評分的降低正相關,左側中央后回百分比的下降與貝克抑郁評分的下降負相關。功能連接結果顯示,訓練后右側額內側回與島葉之間的連接性下降,左側中央后回與海馬旁回之間的連接性增強[16]。
因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心身疾病中心理(精神)因素有作用,甚至在某些疾病中有頗為重要的作用,但是問題是心理的因果效力如何實現?心理因素是否獨立起作用?心身關系到底何種關系?可以說這些問題始終沒有一個讓大家滿意的結論,現代的心身醫學的產生是經歷著一個心身合一-心身分離-心身合一的螺旋上升的發展過程,這意味著人們對健康和疾病的認識發生著重要變化。而在這些認識中隨附性物理主義顯然有其獨到的見解,戴維森借用隨附性的概念給了一個較為完善的解釋:心理事件所表現出的心理狀態(精神癥狀)都與其隨附的物理事件發生交互作用,共同產生結果。心理狀態可能不是實時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不可否認,心理狀態會伴隨著每一次的行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結果是否能完成以及完成的質量。不過正如戴維森所說,心理因果效力無法明確其具體而完整的作用,也不能做出準確的預測,但是心理事件始終影響著事件完成以及發展。心理事件是通過隨附于它的基礎物理事件之上,二者產生不同的反應模式共同施加影響,共同對事件產生因果效力。
具體來說心身疾病的心理中介機制:可以理解為一些心理應激(事件)主要通過中樞神經系統再影響到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和免疫系統,進而影響生理活動(如內臟器官)的功能。同時心理應激所引起的情緒變化,又可以通過邊緣系統、下丘腦影響植物神經系統功能改變,進而影響生理活動,而達到心理的因果效力。
3 結語
戴維森在解決心身關系這一難題中的貢獻極其顯著,隨附性物理主義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綜合性的系統觀點。這一觀點不僅完善了我們心與物質世界關系的理解,也確定了心理的規范性界限,這些促使人們對心理因果性問題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轉向。這種轉變也對具體學科的深入理解提供了指導方法,也為我們理解精神疾病的心身關系以及精神疾病的共病現象開啟了一個新的視角,本文正是做了這樣的嘗試。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隨附性的概念還是很清晰的, 它“只是一個思想描述范疇下對認識論的討論,并是一個本體論的關系”,它只是對隨附性自身特性做了統一與討論。隨附性的模糊還在于其在還原和非還原之間的搖擺不定,隨附性理論強調了心身屬性的依賴關系,強調了物理意義上的相似性,決定了心靈屬性的相似,強調的是一種共生的要求,而非構成因果決定論的普遍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