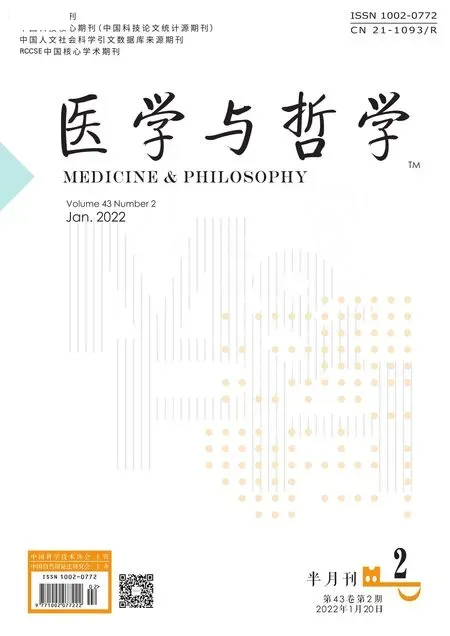扁鵲醫派相關問題探析*
閆敏敏 楊必安 黃作陣
扁鵲是我國醫學史上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但因其人生活時代久遠,可考文獻證據缺乏,關于其本人事跡、醫學理論傳承、醫學文本流傳等問題至今仍存在諸多爭議。對原始史料結合現代研究成果進行重新梳理,就扁鵲人物形象及其醫學源流進行分析解讀,為廓清扁鵲、扁鵲醫派及先秦醫學概貌提供參考。
1 扁鵲醫派傳承的源與流
1.1 “扁鵲”是否可以作為一個學派的名稱
扁鵲學派的說法,最早當始于謝觀先生,其在所著《中國醫學源流論》中云:“《史記·扁鵲列傳》,載其所治諸人,多非同時,或疑史公好奇,不衷于實,不知扁鵲二字,乃治此一派醫學者之通稱,秦越人則其中之一人耳。此其各有師承,猶兩漢之經師也。特醫學之顯,不及儒術,故其傳授世次不可得而考耳。”[1]認為“扁鵲”二字非特指一人,而是有專門理論與技術的一個醫學派別之通稱;李伯聰[2]154更是認為“扁鵲是中醫之‘醫宗’,扁鵲學派是中醫史上出現最早,在戰國、秦漢時期享譽最高、影響最大的學派”。盡管如此,由于相關史料不多,且可信度待考,關于“扁鵲”及“扁鵲學派”在概念上如何定義的問題至今仍爭議不休。
首先是“扁鵲”,目前學界有兩種說法流傳較廣,一是“二人說”,根據記載扁鵲事件的史料(主要是《扁鵲傳》)時間跨度達兩百年以上,判定“扁鵲非一人”,至少有二,第一位生活在春秋末年,第二位生活在秦武王時期(或漢初),另有“二人說”認為有黃帝時扁鵲和秦越人之扁鵲,前者為主砭石之“官”,后者為“閭閻醫工”(民間醫生)[3];另一種說法則認為“扁鵲”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上指生活在春秋末年的一位醫技高明的醫者,“扁鵲”為其人之名,廣義上則是在狹義“扁鵲”的基礎上,對某一類醫家的概稱[4]。拋開史料的作偽問題不談,扁鵲在歷史上確有其人當是確鑿無疑的,且形成醫學流派者當為最早的那位扁鵲。
而對于扁鵲學派,李建民先生《扁鵲別脈》一書指出,“扁鵲作為一個‘學派’的標簽可謂問題重重”,一方面如柯馬丁所說,古代學術的“‘家’之一字,司馬遷曾用來區分其他各個思想大師,絲毫沒有‘學派’”的意味”[5]150,另一方面,因相關文獻的缺如,厘清扁鵲學派核心學術思想、代表性醫家及傳承譜系非常困難。考《辭海》對“學派”的定義為:“一門學問中由于學說師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別”,而根據陳吉生[6]的研究,“東西方學派的形成,大致有賴于三種因緣:即師承、地域、問題,因而大體上可歸為三類:即‘師承性學派’‘地域性學派’和‘問題性學派’,三者互有聯系,它們之間的劃分界限絕非涇渭分明”,陳吉生所言較《辭海》的定義多出“地域”一項,從我國歷史上諸多學派的形成與演變來看,地域確為一項重要條件,有不少學派即以學術團體所在地域命名,如“錢塘醫派”“新安醫派”等,但實際凝聚學術派別的中心其實仍在于核心人物的學術思想或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學說,據此而言,則扁鵲學派的稱法是完全成立的,史料證據顯示,其有鮮明的學說特征,亦存在連續的繼承活動,故“扁鵲學派”之說當得到肯定。
1.2 扁鵲醫派在戰國秦漢時期影響很大
扁鵲在戰國乃至西漢時期被普遍認為是醫學之祖。據學者研究,太史公在編纂《史記》時著錄人物的第一標準乃是人物對社會世事實際影響力的強弱和人物對歷史進程作用的大小[7],聯系自序所言,“扁鵲言醫,為方者宗”“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可見扁鵲自春秋末直至西漢時期的社會影響力是很大的。我國范行準、任應秋等先生及日本學者山田慶兒皆認為戰國和秦漢時期有過多個醫學學派,而扁鵲醫派毫無疑問是其中之一。《漢書·藝文志》載醫經七家,《黃帝內經》《黃帝外經》《扁鵲內經》《扁鵲外經》及《白氏內經》《白氏外經》,可認為是三家不同醫派的學術思想集成之作。同時,秦漢以前文獻中含有大量描述扁鵲醫學相關的信息,如《韓非子·喻老》中不僅記載了扁鵲診桓侯一事,并有“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此二臣皆爭于腠理者也”“聞古扁鵲之治其(甚)病也,以刀刺骨”等;《戰國策》載“或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癰腫;使善扁鵲而無癰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史記·高祖本紀》載:“高祖擊布時,為流失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曰‘病可治’,于是高祖謾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雖不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其他諸如《淮南子》《鹽鐵論》《法言》《論衡》等文獻材料亦頗為豐富,在此不一一列舉。這些傳世文獻足以證明,扁鵲之學在先秦兩漢是影響力很大的醫學流派。
1.3 扁鵲醫派以脈學為宗
成都老官山漢墓醫簡的問世,再一次將扁鵲醫學推向了學術研究的前沿。根據出土醫簡所載內容,證實這些醫簡與扁鵲醫派密切相關。如《敝昔診法》中有諸多關于脈診的論述,并且提出了脈診是診病關鍵這一觀點,這與扁鵲醫派重視脈診一致,從時間關系上也是相符合的。另外條文中多處出現“敝昔”字樣,經考證二字即扁鵲無誤。柳長華[8]指出,老官山醫簡的發現主要是扁鵲醫經的重新被理解。而據已有對經脈學說之演變的研究[9],馬王堆、張家山等地出土的《脈灸經》《脈死候》和《脈法》《脈書》等亦當屬于扁鵲經脈醫學。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載秦越人飲“上池之水”三十日后,“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10]591,明確指出扁鵲醫派以脈學為宗。只是學者研究認為,扁鵲經脈醫學傳至倉公時已然失去了其核心之術。公乘陽慶給倉公淳于意“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倉公傳》所載淳于意的25個診籍,其中大約有2/3都是“診其脈”與“切其脈”分別陳述,先是說通過“診脈”可以得出診斷與預后(幾日如何死,或不死);然后再“切其脈”,按摸橈動脈的搏動于“脈口”或“氣口”,根據所候五臟之氣的所得進行“切脈分析”;最后則根據“脈法曰”為其血脈診斷找到理論根據,以圓其說(血脈診的方法在倉公時期已顯成熟)。而扁鵲依靠經脈診所要判斷的是十二經脈的“病脈之所在”;倉公淳于意依靠血脈診所要判斷的則是五臟六腑的“病臟之所在”[11],即我們今天脈診的確立實際上源于倉公,扁鵲依經脈診斷“知生死”“決嫌疑”的技術未能被繼承下來。
1.4 扁鵲醫派傳承有跡可循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載扁鵲診虢太子“乃使弟子子陽,厲針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10]592,說明其時扁鵲已有弟子相隨;唐代賈公彥《周禮·天官》疏云:“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厥之病,使子明吹耳,子儀脈神,子游案摩。又《中經薄》云《子義本草經》一卷。(子)儀與(子)義,一人也。若然,子義亦周末時人也,并不說神農”,東漢鄭玄在《周禮·天官》注中說:“五藥,草、木、蟲、石、谷也。其冶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12],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第十二卷中,提出本草之書乃扁鵲弟子子義首創,《子義本草》乃是《漢志》經方《扁鵲俞拊方》中的一卷,“神農嘗藥,子儀著書,其功相埒”[2]201-205,李伯聰先生受余先生之論的啟發,傾向于同意這一說法,且進一步考證認為《吳普本草》《李當之本草經》《李當之藥錄》為扁鵲學派的著作。此外,李伯聰先生《扁鵲和扁鵲學派研究》一書對扁鵲學派傳承人物及著作進行了細致系統的考證,包括《扁鵲內經》《扁鵲外經》是扁鵲學派的醫經、《扁鵲俞拊方》是扁鵲學派的經方,《難經》《中藏經》《褚氏遺書》和《扁鵲心書》等是扁鵲學派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著作;扁鵲學派傳承人物有淳于意及其弟子、涪翁、程高和郭玉、華佗及其弟子、南北朝世醫徐氏及宋代醫家竇材等,其證據充實、考證嚴謹,結論基本為多數學者所認可。另有學者考證提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張子和亦為扁鵲醫派傳人[13], 日本醫家梶原性全所著《萬安方》中引用的《究原方》(已佚)亦為扁鵲學派之傳習之作[14],《隋書·經籍志》有《扁鵲陷水丸方》一卷、《扁鵲肘后方》三卷、《扁鵲偃側針灸圖》三卷等,原書雖佚,但可表明扁鵲醫學在晉隋時期仍有傳承。可見扁鵲醫學在歷史上并不曾真正消亡,文本的亡佚導致了扁鵲醫學理論和技術直接傳承的中斷,但仍以間接的方式被不斷詮釋。
2 扁鵲醫派衰落原因探析
上文提到,扁鵲學派在戰國秦漢時期是影響很大的醫學流派,何以有唐之后會眾口一詞地“公認”岐黃為中醫唯一之所宗,扁鵲診療方法和學術思想也幾近消失,讓今天的學者只能從傳世其他文獻的記載中去推測和想象他神秘的面貌呢?綜合分析,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2.1 扁鵲醫經的亡佚
《漢書·藝文志·方劑略》載醫經七家,將醫學分為黃帝、扁鵲、白氏、旁篇等幾家,古書多不題撰人,同時也不題其為何氏何子之屬,則侍醫李柱國是如何辨別其學派歸屬,柳長華先生根據《列子書錄》《戰國策書錄》所載圖書整理的方法,認為“劉向校書,合中外之本,辨其為某家之學,出于某子,某篇之簡,應入某書,遂刪除重復,另行編次,定著為若干篇,這是劉向等校書的一般情況。醫經、經方之書,今雖不傳其書錄,但大抵不出此例”[15],說明李柱國校方技,亦采用此法。令人不解的是,《扁鵲內經》《扁鵲外經》在《漢書·藝文志》出現后,歷代中醫古籍著作中不見其蹤影,如同憑空消失。以扁鵲之名著錄的著作如《難經》《子午經》亦多有爭議,《難經》甚至被公認為闡釋《內經》醫理之作,唐以前醫書《肘后備急方》《脈經》《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等雖引用不少“扁鵲方”“扁鵲法”“扁鵲陰陽脈法”等條文,然內容零散不集中,且臨床實踐的運用上已不常用,扁鵲醫經名存而實亡,文本作為承載思想和技術的重要載體,是中醫知識傳承的主要依據,失去了文本上的繼承和詮釋,以口耳相傳勢必不能流傳久遠。何以在西漢時期與黃帝醫經并列的扁鵲醫經、白氏醫經皆佚失,而《素問》《靈樞》作為《內經》的重要內容卻能流傳至今,拋開戰爭、天災、文字載體的形式等客觀因素不談,同樣條件下,《內經》被保留了下來,而扁鵲、白氏醫派的原始學術著作自魏晉以后鮮少被提起,毋論傳播和繼承,這其中的原因或涉及政治因素,具體還有待進一步考查。
2.2 禁方傳授的限制
春秋以前,學在王官,包括醫學在內的專職技術掌握在上層貴族手中,其傳授并非是開放的,《靈樞·口問》中描寫黃帝“辟左右而問于岐伯曰:愿得口問”。岐伯曰:“此先師之所口傳也。”黃帝又曰:“愿聞口傳。”在《靈樞·師傳》中,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于方。”《靈樞·禁服》中則有“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這種師徒之間私密傳授的形式持續了整個中醫史,所不同者,春秋以后,隨著周王室的衰落,學術下及民間,私學興起,書著于文本漸漸增多,學術爭鳴隨之興盛[16],醫學技術的傳承亦多來自文本的解說這一項,但醫學文本涉及技術內容,并非僅靠自己閱讀就可以掌握的,師說在醫學傳承中仍占據著主要地位,唐代楊上善就明確提出醫學授受“文傳得粗,口傳得妙”[17]的原則,只有師徒之間的口耳相授方能得其精妙。《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載長桑君傳授扁鵲方書時說“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禁方”“公毋泄”都昭示著長桑君所傳醫方要求扁鵲不能將其傳授給他人,后世未能有扁鵲醫學流傳的原因也就明了了。“非其人勿傳”一方面保證了醫療技術的高水平精準化傳承,同時也造成了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隨著社會科技水平、經濟發展等的變化而泥守古法之下的失傳。
2.3 理論難度的增大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載“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說明秦越人本身即有特殊之處,受禁方后飲上池水“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秦越人服用長桑君所傳懷中藥后獲得了眼睛透視能力,暫不論當時是否真的有這樣的神藥可以令人獲得超能力,但秦越人不同于普通人這一結論是肯定的,其所掌握的醫學技術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來說,都必然有一定難度。倉公淳于意接受“扁鵲之脈書”,需要“受、讀、解、驗”,凡“三年所”,而淳于意也常常會“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淳于意是當時名醫,接受了老師所授的扁鵲脈書,可謂扁鵲直系傳承人了,尚對扁鵲醫書不能完全理解和掌握,遑論其他普通的醫生了。淳于意的老師公孫光說“吾有所善者皆疏”,是說和他結識的醫人,除個別人外,水平都不太高[5]9,也從側面反映出扁鵲醫學之難。《肘后備急方》卷一云:“扁鵲治忤,有救卒符并服鹽湯法,恐非庸醫所能,故不載”[18],皆說明了扁鵲醫學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這也就注定了其失傳于后世的命運。
3 扁鵲神醫形象詮釋之變遷
據《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及先秦相關文獻的記述,扁鵲在先秦兩漢時期是非常有名的大醫,有關其人物形象的詮釋亦充斥著一些神話色彩,《史記》首次為醫學人物列傳的做法更是直接確立了扁鵲醫宗的地位;魏晉以降,這種形勢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醫學不再言必扁鵲,而以岐黃為宗,黃帝醫派的《素問》《靈樞》開始被尊奉為醫學之經,有關岐伯、黃帝人物形象的描寫與詮釋也越來越豐滿。根據陳昊[19]87-92的研究,魏晉醫家對舊有醫經的整理,是對醫經正典性的發掘,從而重新劃定了“醫學”的邊界,并塑造醫學知識的正統。與之相伴隨的是一連串根本性的變遷:醫學集團的擴大、文本公開化、醫書撰寫格式的改變、作者意識強化、方書形式的變化、古醫經的改動以及不同醫書位階的確立,自然地導致了扁鵲醫學地位的下降。至隋唐時,對扁鵲的評價已與漢初大不一樣,楊玄操云:“黃帝有《內經》二帙,帙各九卷,而其義幽賾,殆難窮覽,越人乃采摘英華,抄撮精要,二部經內凡八十一章,勒成卷軸,伸演其首,探微索隱,傳世后昆。”[20]根據這種評價,扁鵲已從醫學的“醫方之宗”降為“傳道者”了,《難經》為解《內經》之作的說法亦開始于此。到了宋代,扁鵲醫派的著作和傳承人已寥寥無幾,僅宋仁宗因病封扁鵲為神應侯、神應公,為其筑廟,太醫局將扁鵲作為醫學行業主祀之神,以岐伯從祀。南遷之后,宋高宗等于臨安府依在京舊制修建神應王廟,金代部分醫生沿襲尊扁鵲的習俗。迨至元代,官方以三皇為醫家之祖,以十大名醫從祀,其中無扁鵲,明初沿襲元代之制,明嘉靖年間,增從祀的18位名醫,扁鵲位列其中。清代基本沿襲明制,扁鵲在太醫院祭祀先醫之祀中,失去主祀身份,被看成醫學的傳承者之一,降為從祀的地位[21]。
扁鵲神醫形象的詮釋,反映了后世不同時代人們對其認識觀念上的變遷,扁鵲從戰國西漢時期舉世聞名的大醫,至明清先醫祭祀中的從祀之一,與其文本著作的失傳、魏晉時期醫學邊界的重新塑造與劃分有直接性的關系。根據顧頡剛先生“古史是層累地造成”這一觀點,中國醫學史上相關人物形象的描寫也體現了這一特點:《史記》以前諸文獻的記載皆直以“扁鵲”呼之,至《史記》時,扁鵲有了姓名、里籍以及活動事跡的具體描述,至隋唐《難經集注》楊玄操序云:“越人受桑君之秘術,遂洞明醫道,至能徹視藏府、刳腸剔心,以其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乃號之曰扁鵲”[20],此時又出現了“軒轅時扁鵲”,讓本就帶有神化色彩的扁鵲形象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宋以后,隨著對《黃帝內經》《傷寒論》等醫學經典文本的定型,岐伯醫宗、張仲景醫圣地位的確立,扁鵲漸漸退出醫學中心,而其所擅長的經脈醫學亦多為血脈醫學所替代,在臨床實踐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弱。
4 相關問題討論
4.1 扁鵲里籍新證
關于扁鵲里籍一事,因記載不一而多有爭議,其中“河北鄚縣(今任丘)”和“山東省長清縣”是流傳較廣的兩種說法,前者理由在于《扁鵲倉公列傳》載“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晉朝徐廣注云:“‘鄭’當為‘鄚’。鄚,縣名,今屬河間”,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云:“勃海無鄭縣,當作鄚縣,音莫,今屬河間”,后人多從之,認為司馬遷“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中“鄭”為“鄚”之誤,系后人傳抄有誤導致。后者則以楊雄《法言·重黎篇》:“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準南子·齊俗訓》許慎注:“扁鵲,盧人,姓秦名越人”,《漢書·高帝紀下》韋昭注:“泰山盧人也,名越人”等為據,同意扁鵲為齊國盧地人的看法。但實際上,這兩種說法皆有矛盾之處,考鄚縣,“西漢置。治今河北任丘市鄚州北,初屬河間國,后改屬涿郡。東漢改屬河間國”[22],可見鄚縣并非勃海郡轄下,因此“鄚縣”說無法確立;而“盧醫”說的依據在于戰國時期,“勃海非郡”,且“東漢和三國人的注文比六朝人徐廣之說更為可信”[23],以東漢和三國的注文與西漢司馬遷正史之記載相較,顯然后者更為可信,而當前最大的問題在于渤海郡下無鄚縣。查考相關歷史文獻可見,《漢書·地理志》載“鄚”在“涿郡”條下,“勃海郡”條在“涿郡”之后,二者均為“(漢)高帝置”,同屬“幽州”,清·朱鶴齡《禹貢長箋》一書中“河間”條下的注解為:“春秋屬晉,戰國為燕趙齊三國之境,秦屬上谷鉅鹿,漢置河間國及渤海郡,隋唐曰瀛州,宋置瀛海軍,后升河間府,其地西倚太行,南枕滹沱,東瀕滄海”[24]85,由此可知勃海郡(勃、渤為古今文,在此不做區分)和河間國是有關系的。無獨有偶,根據周振鶴先生的研究,《漢書·地理志》載渤海郡“高帝置”不可信,勃海郡是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河間國除以后所分置的新郡,文帝十五年,河間王薨無后,國除分為河間、廣川、渤海三郡[25],在此之前,渤海之稱包括的地域當更為遼闊,《禹貢長箋·卷二》云:“北岸海則漢書所謂北海也,古稱小海即渤海,愚按:志稱沙門島大海以西皆為青州,北海今青州,古北海、濟南、河間,古渤海地名分而海則一”[24]199-200,可見河間是古渤海之下的地名,則隸屬于河間的鄚縣自然亦屬渤海,加之西漢政區地理變動頻繁,故“郡”為衍文或后人誤加可能性較大。又據《扁鵲倉公列傳》“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鄭(鄚)”“為醫,或在齊,或在趙”[10]591,漢初鄚地確屬故趙國土,則《史記》所云“勃海郡鄚人也”之“郡”當是據扁鵲自述加工而來,因此“鄭”為“鄚”之說當得到肯定。
4.2 扁鵲與天醫
現存中醫古籍中,除《中藏經》《肘后方》《脈經》《千金要方》等有引載扁鵲醫派的理論和治方外,《黃帝蝦蟇經》出現的“扁鵲”相關文字似乎信息更多,《黃帝蝦蟇經·推天醫天德生氣淫第七》云:“凡陽月以大吉加月建功曹下為天醫,傳送下為扁鵲,陰月以小吉加月建功曹下為天醫,傳送下為鶣鵲”,附錄陳祖同抄《醫心方》引《蝦蟇經》佚文“正月扁鵲在酉,二月扁鵲在辰,三月扁鵲在亥,四月扁鵲在午,五月扁鵲在丑,六月扁鵲在申,七月扁鵲在卯,八月扁鵲在戌,九月扁鵲在己,十月扁鵲在子,十一月在未,十二月扁鵲在寅。凡病人不差,當從天醫治之,不避眾忌,所治之處百鬼當不敢,天醫所在,雖有兇神,不能為害也。”[26]《黃帝蝦蟇經》是一部論述四時刺灸禁忌的專著,現存日本文政六年癸未(1823年)敬業樂群樓刻衛生匯編本,書中載丹波元胤識文,認為此書正是《隋書·經籍志》所載《黃帝針灸蝦蟇忌》,成書年代約在兩漢時期。而根據本書中對扁鵲的描述,其與“天醫”有聯系,“天醫者,天之巫醫,其日宜請藥避病,尋巫禱祀”,扁鵲與“天醫”并稱,可見其時亦以扁鵲為神醫,據之推算適合針灸治療的吉時。現存古籍有關“天醫”的最早記載是《千金要方》,但有關天醫法的推算并未提及扁鵲,這說明《黃帝蝦蟇經》的成書應在東漢以后,《醫心方》之前,原因在于:《千金要方》中引用兩漢時期醫學文獻很多,若《黃帝蝦蟇經》成書于兩漢,《千金要方》提到“天醫”推法時定會與《黃帝蝦蟇經》所描述一致,但《千金要方》中所引扁鵲醫方時已然是將其看作一位名醫而非帶有神話色彩的人了;此外,有關天醫的記載較多出現在唐宋以后的文本中,這也從側面印證了《黃帝蝦蟇經》當成書與《千金要方》同時代或稍早時(“天醫”帶有道教色彩,正與魏晉時道教的興盛相合),《中醫古籍珍本提要》載本書成書年代為419年(魏晉時期),當有所據。
5 結語
本文通過對扁鵲醫派源流、衰落原因及人物形象變遷、里籍等相關問題的考察,傾向于認為秦越人與先秦時扁鵲當非同一人,《史記》所載里籍及相關師承史記當屬秦越人,全文中雜糅了先秦扁鵲相關史料,扁鵲醫派是由與趙簡子同時代的扁鵲所創立,醫學核心以經脈診為宗,且善于治療癰腫等外科疾病。表面來看,《扁鵲內經》《扁鵲外經》等扁鵲醫派核心理論著作的亡佚、禁方傳授傳統的限制及經脈診斷理論的難以理解和掌握,導致了魏晉重新整理醫學經典時確立了岐伯黃帝醫派為醫學之宗[19]88,扁鵲醫派由此開始滑離醫學發展的中心,漸漸走向衰落,但扁鵲醫學并未真正消亡,而是通過后世學者對中醫知識的重構與詮釋被間接傳承。本文另就扁鵲里籍問題及《黃帝蝦蟇經》所記載“天醫扁鵲所在”推算針灸治療時間提出了不同理解,希求教于大家,進一步提供相關線索,或能使懸疑之問柳暗花明。
李伯聰先生在20個世紀90年代就前瞻性地指出:由于我們要研究的是戰國秦漢時期各醫學學派影響大小的問題,所以在方法上就必須以搜尋戰國秦漢人寫作的有關材料或出土文物為主;在判斷標準上,就必須以戰國秦漢大多數人的認識、評價、心理為準[2]154。這一看法不自覺地運用了詮釋學原則,即將其人放入其所處時代背景下去認識,方有可能得出最符合實際的答案,問題在于,扁鵲所處的時代在時空距離上已和我們相去甚多,先秦傳世文獻的匱乏及相關史料真實性的難以辨別,給我們認識扁鵲醫學帶來了最大的障礙,然隨著近年來出土醫籍信息的不斷揭示,相信扁鵲及中國先秦醫學的面貌會逐漸在我們面前清晰。
(本文撰寫過程中得到中國中醫科學院顧漫老師指導,在此謹致以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