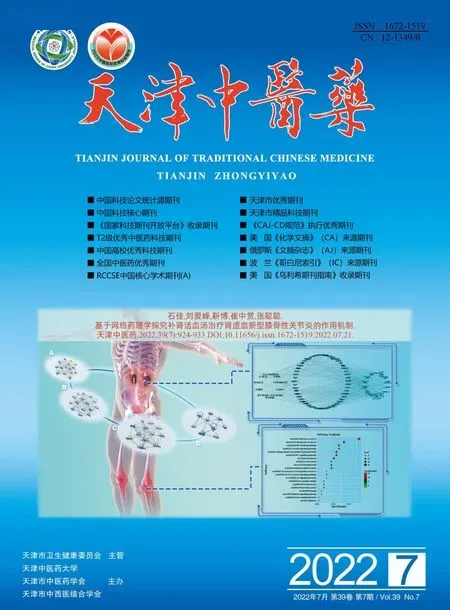從肺炎病程的新認識探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西醫結合康復實踐*
郭安,張碩,封繼宏,付鯤,周勝元,雒明池
(1.天津中醫藥大學研究生院,天津 301617;2.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天津 300250;3.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科研科,天津 300250;4.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治未病科,天津 300250;5.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天津 300250)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是一種以發熱、咳嗽、乏力為主要臨床表現的呼吸系統傳染性疾病。截至2021年11月初,全球已有累計超過2.5億人感染,其中約20%在感染后進一步轉為中重度感染甚至危重癥(約1%~2%)[1],研究發現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可分為3個時期:急性感染期、多系統炎癥期、后遺癥恢復期[2]。COVID-19患者在出院后仍然存在長時期、多系統的后遺癥,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COVID-19患者出院后的遺留癥狀主要包括呼吸系統后遺癥,如咳嗽、心肺運動耐量降低、間質性肺損害等[3-4];循環系統后遺癥,如高血壓、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等[5-7];神經系統后遺癥,如嗅覺減退、認知障礙等[8-9];心理和認知障礙有關的后遺癥,如焦慮、抑郁、睡眠障礙等[10-11]。大部分患者出院6個月后仍可存在疲勞、睡眠障礙、焦慮或抑郁、腎功能損傷等癥狀[12]。隨著毒株突變、應急反應能力的提升、臨床救治手段的提高,患者的生存率逐步升高,改善COVID-19患者的功能障礙逐漸成為研究焦點。文章通過分析COVID-19的致病特點及古代醫家對疫病的認識結合現代醫家在COVID-19后遺癥恢復期的康復經驗,基于肺炎病程的新認識,提出COVID-19“瘥后防復”的中西醫結合康復實踐原則及措施,以期降低該病的不良后遺癥,改善疾病預后,為臨床提供新的思路與方法。
1 肺炎病程的新認識
無論是傳統感染性疾病社區獲得性肺炎,還是新型感染性疾病COVID-19,患者感染初期均面臨著病原體入侵、內化、繁殖以及伴隨而來的炎癥反應。如果這一狀態不能被機體免疫系統抑制,形成炎癥風暴則進一步導致多臟器衰竭,成為全球疾病負擔的主要原因[12]。既往針對感染性疾病的研究多側重于急性階段,認為感染性疾病是一種孤立的急性事件;而最新研究則發現肺炎增加了罹患慢性疾病的風險,加速其他并發癥進展和反復感染的風險[13]。因此課題組基于“肺炎并不是單純的急性事件,而是以急性期為主要矛盾的多系統慢性持續性疾病”的肺炎病程新認識,主張肺炎是包括急性感染期、多系統炎癥期、后遺癥恢復期的全病程觀念。其對機體的損害不局限于肺炎急性期,急性期過后所誘發的機體免疫穩態破壞、持續低度炎癥和微循環障礙等均將持續影響身體機能,帶來多器官損傷,存在二次感染的風險,且與基礎病相互影響導致惡性循環[14]。因此治療的重點不能局限在急性期損傷,更要著眼于整體功能的恢復與改善,調平調衡,恢復機體“陰平陽謐”狀態,“瘥后防復”以治未病。
2 基于肺炎病程新認識的中西醫康復治療原則
2.1 先期干預 先期干預是指在疾病病勢變化前就施以治療的原則,是“趨勢辨治”的重要體現,COVID-19病勢危急,病情危重,多數患者從輕癥到重癥的轉化過程迅速而隱秘。其康復介入時間窗口短、康復介入手段缺乏,后續變證復雜多變,因此課題組依據“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的“早診斷,早治療,早康復”的思想[15]。主張在COVID-19的康復治療中,中西醫結合康復治療應盡早介入,在COVID-19患者入院伊始,即對患者功能障礙進行評估,主要包括:呼吸功能評估、軀體功能評估、心理功能評估、日常生活能力評估等,對患者病情評估后由多學科專家組制定“個體化”的中西醫結合康復治療方案,講解康復訓練方案并詳細示范,如功法訓練(八段錦、太極拳等);呼吸肌康復訓練(如腹式呼吸訓練、縮唇呼吸訓練、對抗阻力呼吸訓練);軀體功能訓練(如力量訓練、柔韌性訓練)等[16]。提倡康復與臨床救治同步進行,形成“臨床-康復一體化”的局面,這是COVID-19康復的先決條件,亦是制勝關鍵,通過先期康復干預,將疾病控制在初步階段,減少后遺癥,為進一步治療及康復創造機會[17]。鄧彪等[18]在COVID-19機械通氣患者的治療初期即采取中西醫肺康復干預措施,康復第3天氧合指數(P/F)均能上升至200 mm Hg(1 mm Hg≈0.133 kPa)以上,平均住院日遠低于重癥COVID-19的平均住院時間。
2.2 全程干預 全程干預是指康復干預應貫穿疾病始終,而不是僅僅局限于某一時期。COVID-19急性期所引發的急性損傷與患者的基礎病相互影響,遷延不愈造成患者生理功能恢復受限,因此COVID-19后遺癥的康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康復治療應貫穿于疾病全過程,即全程干預[19]。課題組主張建立完整的三級康復網絡,一級康復指在COVID-19診療醫院對患者進行初步、早期的床旁康復治療,依靠專業收治醫院控制COVID-19急性期間的功能障礙;二級康復治療是指根據患者的主要后遺癥而安排患者去相應的康復中心進行康復治療,制定個體化的康復方案,依靠專業康復中心提供肺康復、軀體康復、心理康復等方面的指導;三級康復是指經康復師評估后,COVID-19患者在社區和家中進行康復治療,這一時期的主要康復手段包括中醫功法鍛煉及呼吸肌康復等,可參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出院患者中西醫結合康復指導》[20],幫助患者建立個性化的康復方案,強化患者的健康意識、規范患者的生活方式。各系統“分部門、細職能、全時段”參與到COVID-19后遺癥的康復治療之中。三級聯動的全程康復可更有效分配醫療資源,有利于推動康復患者流轉途徑,為COVID-19患者的全程康復提供“無縫式”指導。
2.3 多學科干預 多學科干預是指多學科合作團隊共同參與到COVID-19康復過程中,通過各學科專業人員的戮力協作對COVID-19患者實施康復治療,目的在于建立更科學全面的COVID-19康復計劃,提高COVID-19患者的康復鍛煉依從性及康復效果,進一步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基于COVID-19患者康復需求,臨床收治機構需建立多學科康復小組,包含肺康復、心臟康復、心理康復、運動康復等多個領域的專業技術人員[21],制定符合患者個性化的康復治療方案,并進行后續康復評估以及康復中心的推薦。其所涉及的康復介入手段也包括中西醫的各個領域,針灸、推拿、傳統功法、中藥貼敷、熏洗等中醫手段與呼吸肌康復、神經康復等現代康復方法均可以發揮所長,通過多維度、多手段的康復介入手段,使生理功能盡快恢復正常。相關臨床試驗研究結果顯示[22-24],多學科合作制定的綜合性肺康復方案能有效改善多種肺系疾病患者的呼吸困難、營養水平、運動耐力及焦慮情況,提高生活質量。
3 基于肺炎病程新認識的中西醫康復核心治法
課題組依據COVID-19“濕毒膠結,郁閉氣機”的急性期核心病機以及“氣虛血瘀”的新冠肺炎恢復期核心病機[25]。提出“清”“透”“養”的 COVID-19中西醫康復核心治法,清化痰瘀以疏機通絡;透散毒邪以防“灰中有火”;養正培元以“瘥后防復”。需要明確的是“清”“透”“養”三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協調、互為助力的,清法之施為化其痰瘀、清凈肺竅諸臟;透法之施為開達肌表、舒暢表里三焦;養法之施為培元固本,杜絕復發之機。清中有透、透中兼養。互為犄角而奏標本同治,表里雙解之功。
3.1 清化痰瘀,調暢氣機 相關組織學檢查發現[26],COVID-19引發肺損傷的主要機制在于炎癥風暴產生的過度自由基損傷肺泡,機體過度修復,形成纖維細胞增值與細胞外基質富集的成纖維狀態,誘發肺間質損傷,而肺間質損傷導致的肺功能下降又是新冠后遺癥中危害最大、時間最長的后遺癥之一。中醫對這一病理階段主要從痰濁、瘀血兩個方面來進行認識[27-28]。認為痰濁瘀血痹阻肺竅,影響氣機宣化,不能調達,從而形成惡性循環。針對這一病機,課題組主張在COVID-19康復治療中,酌情加用滌痰化瘀之法,中草藥如半夏、丹參等;成方如桃紅四物湯、二陳湯等;穴位如三陰交、豐隆、血海等;現代康復技術如有助于排痰的氣道廓清技術;防止血栓形成的間歇性充氣加壓護理等,可以改善肺間質病變,增加機體血氧水平,改善機體慢性缺氧狀態,恢復整體功能。相關藥理學研究認為,滌痰化瘀類中藥的主要作用在于調節機體免疫,通過細胞吞噬作用、清除炎癥損傷細胞,從而改善炎癥后狀態。楊彥偉等[29]通過采取益氣化痰、活血通絡法治療COVID-19恢復期核酸復陽患者,在改善癥狀、促進核酸轉陰方面取得滿意療效。
3.2 透散余邪,祛邪外出 “伏邪”一詞出自吳又可《溫疫論》,伏邪指外感邪氣侵襲機體,逾時而發。COVID-19的發病初期具有潛伏性,部分COVID-19患者出院后可出現再次發熱、核酸檢測的“復陽”現象,這符合伏邪發病的特點,可能與新型冠狀病毒的生物學特性、患者免疫功能低下、基礎疾病嚴重等因素有關。但不論是何種因素,均表明了新冠病毒“伏留于內,不能透達”的病機特點[30-31]。提示COVID-19恢復期存在“余邪未清”的情況,因此在COVID-19的全程康復治療中,課題組主張重視“透法”的應用,透達內伏之邪,絕“灰中之火”,以杜復燃之機。在藥物的選取方面,可酌情選用蟬蛻、僵蠶、藿香等芳香清透之品,宣泄余邪,透達肺竅,以祛達余邪。成方如升降散等亦可酌情配伍;刮痧、拔罐等有助于暢泄余邪的中醫外治康復方法亦可選用。現代藥理研究發現[32],升降散復方具有退熱、抗病毒、減輕氣道炎癥、抑制炎癥反應造成的急性肺損傷等多方面的藥效學作用。
3.3 培元固本,瘥后防復 吳又可于《溫疫論》中言“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指出人體正氣在疫病發生、發展和轉歸中的重要作用。從肺炎病程的新認識看,患者的基礎病是肺炎的重要始發基礎,COVID-19的炎癥后狀態又是慢性基礎病急性加重的危險因素,兩者互為因果形成惡性循環。因此在COVID-19后遺癥期應重視對基礎病的康復與治療,益氣補虛、培元固本以改善基礎狀態,對于預防肺炎發作,改善預后均有重要意義。因此課題組主張在COVID-19患者的治療中,酌情選用扶正培元之品,中草藥如黃芪、人參、熟地黃等;成方如四君子湯、玉屏風散等;中成藥如清感飲系列制劑等[33];穴位如關元、足三里、百會等;現代康復技術如日常生活能力訓練,建立契合患者個體性的運動處方,對于肌力減退的患者著重進行力量訓練及作業治療訓練,對于呼吸困難的患者注重進行呼吸肌力量訓練、呼吸體操訓練等[34]。方邦江教授基于“急性虛證”理論,制定“全程扶正”的COVID-19治療方案,在住院時間、抗生素使用、醫療費用方面較單純西醫治療有明顯優勢。相關藥理研究亦顯示人參單體可以通過多靶點作用,調節機體促炎/抗炎因子的失衡。使患者由炎癥風暴后的“無序狀態”恢復到“陰平陽謐”的和合狀態[35]。
4 討論
COVID-19起病急、病勢猛、傳播廣,COVID-19患者在經過救治后仍存在部分后遺癥。且COVID-19后遺癥的出現也會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因此基于“肺炎并不是單純的急性事件,而是以急性期為主要矛盾的多系統慢性持續性疾病”的肺炎病程新認識。課題組結合張伯禮教授提出的全周期干預理念,主張中西醫結合、早期、全程、多學科、多手段共同參與到新冠肺炎康復治療之中,以實施科學全面的中西醫結合康復實踐方案,發揮中醫藥“辨證論治”“治未病”“整體觀念”的COVID-19康復治療優勢,以清透養3法并施,表里標本并治,改善疾病預后,為COVID-19的康復治療貢獻中國力量,發揮中西醫結合在COVID-19康復治療中的獨到優勢。最終達到COVID-19患者早期康復、全程康復、系統康復的目的,以清其本源、瘥后防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