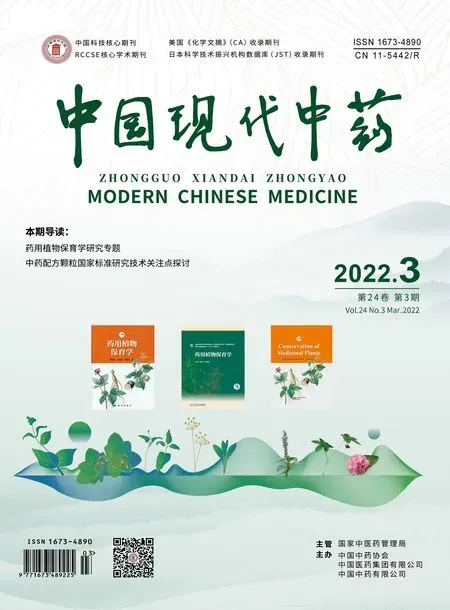藥用植物保育學研究進展與展望△
梁瑩,秦雙雙,韋坤華,湯丹峰,喬柱,郭曉云,韋范,朱艷霞,繆劍華
廣西壯族自治區藥用植物園 廣西藥用資源保護與遺傳改良重點實驗室/廣西壯族自治區中藥資源智慧創制工程研究中心,廣西 南寧 530023
藥用植物保育學是一門以保護生物學為基礎,研究藥用植物物種保存和環境脅迫條件下藥效物質變化的機制,探索生物多樣性保護與藥效形成的原理和方法,制定保育策略,實現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學科[1]。相比于傳統的植物保育學,藥用植物保育學在物種遺傳多樣性保護的基礎上增加了藥效的形成與保護工作,以期實現物種與藥效維持的“雙保護”,并從遺傳、生態、馴化技術等方面開展藥用植物的保育理論研究與實踐,在理論、技術、平臺等方面實現突破,形成特色鮮明的藥用植物保育理論體系,進而解決藥用植物保育中藥效保護和利用的問題[2]。近年來,陸續開展了白及[3]、蘿芙木[4]、密花豆[5]、金花茶[6]等藥用植物的保育研究。本文簡要闡述了藥用植物保育學學科建設歷程和藥用植物發源中心,總結了在藥用植物遺傳保育、生態保育、馴化保育、繁育和復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對未來藥用植物保育學學科發展方向提出幾點展望。
1 藥用植物保育學學科建設歷程
隨著人類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逐漸開始重視人類經濟活動對環境的破壞及其所導致的野生物種生存危機,保護生物學作為一門危機學科應運而生。在過去幾十年間,保護生物學的發展理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主要表現為從20世紀60年代前的“保護自然本身”到20 世紀70—80 年代的“防止人類破壞自然”,再到90 年代的“人類利用大自然”,以及現在的“人與自然共存”理念[7]。植物保育的思想也在保護生物學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并創建了植物保育學這一專門學科來指導植物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將之用于藥用植物的保育中。植物保育學的保護對象是植物,但在具體的藥用植物保育實踐過程中不能有效地解決藥效的維持問題。為解決植物保育學在藥用植物保育中的局限性問題,廣西藥用植物園提出一門新的學科——藥用植物保育學,指導藥用植物的保育實踐。
藥用植物保育學學科籌建于2002 年。該學科是在總結廣西藥用植物園多年來開展的大量藥用植物引種、馴化與保護實踐經驗和技術研究的基礎上逐漸形成。2009 年和2012 年先后被批準為第3 批廣西醫療衛生重點(建設)學科、第4 批廣西醫療衛生重點(建設)學科;2013 年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確立為中醫藥重點學科;2017年《藥用植物保育學》專著出版;2020年英文專著《Conservation of Medicinal Plants》出版,同時《藥用植物保育學》入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十三五”規劃教材,并于2021 年正式出版發行,這標志著藥用植物保育學學科進入新的發展期。藥用植物保育學也將更加廣泛地指導藥用植物保護和利用研究。
2 藥用植物保育研究現狀
藥用植物保育一方面是對藥用植物物種本身的保護,另一方面是對藥效這一藥用植物核心價值的有效維持。藥用植物保育學的研究內容包含保育理論、保育技術和保育策略等方面。其中,藥用植物保育理論在植物保育學的基礎上增加了藥用植物發源中心學說和藥用植物藥效形成機制等內容,從遺傳、生態、馴化、藥用植物經濟規律等方面拓展了藥用植物保育理論,形成了遺傳保育、生態保育、馴化保育原理,各原理相對獨立又相互關聯。在藥用植物保育過程中,遺傳因素是藥用植物藥效形成的基礎,適宜的生態因子是藥用植物藥效維持的必備條件,馴化則是將藥用植物種質與藥效形成的關鍵因子有機結合,并協調好藥用植物保護與藥材生產的關系。
2.1 藥用植物發源中心學說
藥用植物發源中心是指該藥用植物被首次發現并利用的發源地[1]。藥用植物之所以成為藥用植物,是人?自然?時間?地理位置之間的完美邂逅與發現,是人類進化歷史上認識自然、了解植物的一次重大突破。現在流傳下來的、藥效優良產區的藥用植物資源或多或少受到人類選擇作用的影響,區別于原始野生植物,其被稱作栽培植物或馴化植物。往往不同地域出產的同種藥用植物藥效不同,甚至差別較大。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既有環境因素,也有不同地理居群之間的遺傳差異。因此,進行藥用植物保育學研究,需要對藥用植物的發源地進行追溯,找到藥用植物形成藥效并被人類發現和利用的“原點”,發掘藥效形成相關的遺傳與環境機制。
藥用植物的起源地與其作為藥物的發源地在地理位置上可能出現差異或重合2 種情況。藥用植物自然與人文的雙重屬性決定了藥用植物物種的發源中心不一定是該植物物種起源的地點。一些適應能力強的廣布種,在部分地區為了適應不同的生態環境,加上植物自身的基因變化,從而特化出有藥效的生態類型。這種特異的有藥效分化的植物類型被人們發現并且使用,使其生長地區最終成為了藥用植物的發源地點。例如,黃花蒿廣布于歐洲和亞洲的溫帶、寒溫帶及亞熱帶地區,生境適應性強,野生資源分布較廣。我國重慶、四川、貴州、廣西、云南、湖南等地的黃花蒿不僅青蒿素含量高,而且黃花蒿適宜生長指數也較高,可作為生產高品質黃花蒿的首選區域[8]。另外,一些窄布種環境適應能力弱,其作為藥用的發源地點都是在距植物起源地不遠的地區,這類分布極為狹窄的藥用植物發源中心往往與植物起源中心是一致的。例如,已有600 多年應用歷史的三七分布較為狹窄,最早發現于廣西,受自然、人文和社會等因素的影響,三七主產地從20 世紀70 年代開始逐漸由廣西向云南文山轉移[9]。云南東南部、廣西西北部和貴州東南部三七適宜區分布較集中,三七種植過程中復雜的栽培技術決定了只有少數地區(云南、廣西)最終發展成為三七的主產區[10]。對藥用植物發源中心的研究能更加有效地發掘出與藥效形成相關的關鍵遺傳因子與生態因子,實現對藥用植物的保護與開發。
2.2 遺傳保育
藥用植物遺傳保育的目的是揭示藥用植物的遺傳特性形成機制、多樣性維持的一般規律及藥效形成的遺傳學原因。不同于普通植物,藥用植物的藥用品質是通過人類醫學實踐發現的,藥用植物的利用與人類醫學傳統密切相關[11]。公元前1600 年,埃及的《紙本草》及其后古印度的《壽命吠陀經》都有植物藥物的記載[12]。同其他植物一樣,生態或地理隔離是藥用植物群體產生遺傳分化的主要外因,遺傳漂變、突變及由于自然或人為原因導致的遺傳混雜等內在因素也會直接造成藥用植物個體的遺傳差異[13]。例如,河池地區的越南槐資源相較其他地區資源有著獨特的遺傳成分[14]。
在藥用植物遺傳多樣性研究方面,對半夏資源的研究證實了野生種的遺傳背景較栽培種更為豐富[15]。這種現象說明,人為篩選和栽培已對半夏的遺傳多樣性造成了影響,而野生種的遺傳多樣性則由于平衡選擇的作用而得以維持。同一種藥用植物也因品種不同而表現明顯差異,如廣西桂北地區不同品種羅漢果(青皮果和紅毛果)中總苷、羅漢果甜苷Ⅴ含量均有明顯差別[16]。這些差異主要來源于自身的遺傳基因。藥用植物的保育遺傳原理,一方面通過探索涵蓋保護物種基因庫的遺傳信息和反映足夠遺傳多樣性的DNA 分子標記方式,為物種的保護與恢復奠定基礎;另一方面通過數量遺傳學的理論與分析方法,結合分子生物學的技術手段,揭示藥用成分形成的分子機制及其生產應用潛力,揭示珍稀瀕危藥用植物應對環境變化的進化潛力與未來命運。
2.3 生態保育
藥用植物的生態保育是從生態環境的角度揭示藥用植物品質形成與維持的一般規律。由于不同物種耐受性存在較大差異,在一定生態幅(生物對某一生態因子耐受的上限和下限之間的范圍)內,藥用植物品質呈現多種變化[17]。
從廣西道地藥材山豆根產區7 個氣候條件差異明顯的樣地選取21 份山豆根樣品進行測定發現,年平均降水量是影響山豆根生物堿含量積累的主導氣候因子[18]。干旱脅迫時,山豆根幼苗中酶活性總體表現出彼此協調的變化趨勢,是山豆根抗干旱的生理基礎之一[19]。實驗證明,環境因素會影響藥用植物有效成分的形成和積累,如唐古特大黃酚酸類成分含量主要受環境因素的影響,游離蒽醌類、結合蒽醌類和二蒽酮苷類成分含量受環境因素影響所占比重較大[20]。從連翹在我國的潛在分布區研究中發現,我國中部和東部地區為連翹的核心分布區,以此推測了影響連翹分布的主導環境因子及最適宜生長的生態位參數[21]。開展藥用植物生態保育研究,運用耐受性原理指導尋找藥用植物藥效形成的最優生態因子,為科學合理選擇藥用植物栽培區域提供了依據。
2.4 馴化保育
我國藥用植物野生資源豐富,但由于無序開發、利用過度、采收時間和采集方法不當、環境破壞等多種原因,導致不少藥用資源物種逐漸處于珍稀瀕危狀態,甚至有滅絕的可能性[22]。因此,對藥用植物,尤其是瀕危和緊缺藥用植物資源的修復和再生迫在眉睫。
由于一些生態因子對藥用植物的脅迫有可能會促進藥效成分合成,因此在馴化過程中,應注意其發源中心是否存在一定的脅迫,這可能在藥效成分形成和穩定過程中起重要作用[23]。適度脅迫有時對于藥用植物藥效的形成是必需的[24?25]。例如,山豆根是生長在喀斯特地區的一種藥用植物,在栽培山豆根時,通過施加適量外源鈣能夠促進山豆根苦參堿和氧化苦參堿含量的積累[26];降低穿心蓮氮代謝強度可以促進其生長并提高穿心蓮內酯積累,同時實現穿心蓮高產與優質[27];金銀花遷地保育后,黃酮類成分木犀草苷含量顯著提高[28],在金銀花的栽培過程中,修剪能夠提高金銀花產量[29],施加赤霉素(GA3)能夠顯著提高金銀花中綠原酸和木犀草苷的含量[30]。藥用植物的保育馴化以充分發揮馴化對象與環境之間“互利”“互惠”因素為主線,實現“最優”藥用種質與和藥效形成相關“最優”生態因子的有機結合,填補藥用植物物種保護與藥用植物資源利用之間的空白。
2.5 藥用植物繁育
藥用植物繁育可以通過保護區內自然繁育、種子繁育和組織培養等方式實現藥用植物資源生存空間的擴大。為了加強道地藥材、珍稀瀕危品種的保護和繁育研究,我國在20個省區布局建設了28個中藥材種子種苗繁育基地,分布于西北、西南、中部、東北、東南等地區,子基地合計近180 個,繁育中藥材種子種苗近160種[31]。
在離體繁殖方面,采用山豆根無菌播種規模化快速成苗生產技術可使山豆根叢生芽增殖7 倍/30 d[32]。在種子繁殖方面,為降低山豆根繁育成本,解決山豆根坐果率低、生理落莢及病蟲害問題所導致的山豆根種子缺乏現象,本團隊制定了山豆根種子生產標準操作規程(SOP)[33],助推山豆根產業的發展。此外,超低溫保存是公認的最安全、經濟、有效的藥用植物種質資源保存方法[34]。目前,已成功實現高山紅景天、百合、莪術等藥用植物莖尖的超低溫保存[35],以及人參[36]、肉豆蔻[37]、九里香[38]等多種藥用植物種子的超低溫保存,有效保證其遺傳穩定性,控制其遺傳性狀的基因不發生突變,同時便于隨時快速繁殖大量健康植株。
2.6 藥用植物復育
復育是對藥用植物資源的恢復性手段[39],是藥用植物保育學的最終實驗。藥用植物的復育主要通過協同栽培和人工撫育的方法實現。
在藥用植物協同栽培研究中,不同種植模式三七根際核心微生物特征不同,林下種植根際微生物屬總相對豐度高于田間種植[40]。從林下栽培的角度,種植于闊葉林下的七葉一枝花生物量和成活率均較高[41];種植于郁閉度0.5~0.6 杉木林下的白及產量最高[42]。在兩面針生態種植技術規程[43]中,兩面針套種廣金錢草、雞骨草等適應性強、生長旺盛的豆科植物[44],可以化解兩面針、廣金錢草、雞骨草等中藥材野生資源即將枯竭的危機,解決原料緊缺的瓶頸問題。在藥用植物人工撫育研究中,通過在野外選擇合適的環境進行藥用植物人工種植,可增加野外藥用植物群體數量,同時保證良好的藥效。在金線蓮道地產區,契合金線蓮原初生境的林下進行栽培,其長勢最佳,折干率高,多糖、生物堿和類黃酮等藥用成分含量較高[45]。野生撫育樣方中野菊平均產量顯著高于人工栽培與野生條件下的野菊[46]。由此可見,人工補種及適當人工管理的野生撫育是一種獲得高品質、高產量野菊花藥材的生產方式。
2.7 保育策略與評價
保育策略的研究涉及物種瀕危程度、資源蘊藏量、市場需求量等具體數值的計算,也涉及對生態環境的適應性強弱、不同居群間的遺傳差異大小、化學成分和藥效一致性等非量化指標。
廣西鹿寨縣和融安縣野生重點藥用植物有一定的自然蓄積量,但年允收量小、稀缺物種多、可利用資源少,應加強兩縣重點藥用植物資源保護與可持續利用[47]。浙江省九龍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梵凈山石斛蘊藏量不足10 kg,應采取人工繁育措施將梵凈山石斛群落內的林木進行撫育改造[48]。根據藥用植物資源生態學特征,結合藥用植物對喀斯特地貌獨特環境的響應特點,可在中國南方喀斯特地貌合理實施藥用植物保育[49]。藥用植物保育的效果評價是衡量保育策略實施一段時間后對預定目標和指標的實現程度。例如,以藥材性狀為指標,結合揮發油中主成分含量評價家種蒼術品質,解決家種蒼術種苗質量良莠不齊、標準體系不完善的問題[50]。通過對藥用植物保育的效果評價能夠及時反饋信息,以便調整實施方案,是實現藥用植物物種保存和藥效的保證。
3 藥用植物保育學多組學研究
從藥用植物保育學的研究內容來看,藥用植物保育學涉及多個學科的交叉,如遺傳學、生態學、分子生物學、保護生物學、中醫文獻考證、藥理學、化學、臨床研究、管理學、經濟學等,是涉及學科廣、研究范圍寬、內容龐雜的綜合性學科。
近年來,隨著以高通量組學檢測技術為代表的生物技術的發展,生物醫學研究領域開始進入大數據時代,藥用植物保育學研究也迎來前所未有的時機。2013 年,研究人員提出在藥用植物研究中采用大數據分析思想[51],并將其用于傳統復方研究中。這項研究采用大數據分析并引入了多維偏最小二乘?判別分析(NPLS?DA),分析中引入數學能定量解釋各個藥用植物在復方中的效力,體現了藥用植物研究中大數據分析的巨大威力。在藥用植物研究中,藥效的判斷,特別是藥效成分作用機制的確定是藥用植物保育研究必須解決的問題。對此,則需要引入大數據分析中的一些統計方法,對藥效的分析可以綜合生物實驗數據、臨床數據、傳統指標等,通過綜合方法對藥用植物的藥效進行定量化處理。這種綜合方法顯然優于傳統的單一指標判別分析,更容易被具有不同研究背景的藥用植物研究者接受。同樣,對于藥效相關基因、生態因子、表型的尋找也可以采用大數據分析方法。
當前,在生物研究中,大數據分析的研究范式主要集中于醫學和藥學,在藥用植物研究中只涉及簡單的組學研究,遠遠不能滿足藥用植物保育學的要求。為此,廣西藥用植物園開展了“藥用植物4.0”研究,廣泛采集藥用植物研究大數據,通過大數據分析方法加快、加強藥用植物保育學的研究。例如,通過對雞血藤基因組進行組裝,構建雞血藤全基因組圖譜,為該物種主要活性成分的生物合成和種子發育調控機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資源[52]。在完成藥用植物大數據采集后,通過大數據分析,解釋藥用植物發源中心的定位、解析藥效成分積累相關基因和生態因子,為藥用植物保育策略制定提供依據,從而實現藥用植物科學保育。
4 展望
在藥用植物保育理論指導下,通過遺傳保育、生態保育、馴化保育、繁育和復育實現了藥用植物物種與藥效維持的“雙保護”及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基于目前多組學大數據,下一步藥用植物保育學研究將重點闡述藥材品質形成的機制,通過精準栽培促進藥用植物資源的開發利用。
4.1 藥材品質形成的遺傳機制
植物種質資源是中藥材生產的源頭,也是中藥材品質形成的物質基礎,而遺傳因素則是藥用植物價值實現(藥材品質形成)的基礎。藥用植物遺傳保育不但要實現遺傳多樣性的保護,還要穩定藥效相關基因,從而實現藥用植物藥效的保護。當前,對于藥用植物遺傳多樣性現狀、群體遺傳結構的揭示等工作已經廣泛開展,但由于其局限于對已有布局的靜態觀察,未能揭示藥用植物藥效形成的歷史脈絡,限制了藥材品質形成遺傳機制的研究工作。
在開展藥用植物遺傳保育工作時,首先,應通過地理親緣學研究種內關系,揭示藥用植物的進化歷史及遺傳多樣性豐富的發源中心,通過對影響藥材品質形成的相關基因進行分析,揭示藥材品質形成相關基因的進化機制,結合藥用植物的歷史沿革,為藥材品質形成機制的研究提供基礎;其次,基于高通量測序技術,通過多組學數據分析,精準定位藥材品質形成相關基因,分析藥用植物群體的遺傳結構與藥材品質關系,闡明藥用植物藥材品質形成機制,從而更好地在藥用植物保育中針對藥材品質相關基因進行監測,實現藥用植物藥效成分保護及資源可持續利用。
4.2 藥材品質形成的生態機制
目前,模式植物的生長發育機制研究比較深入,然而對于多數非模式植物,特別是具有明顯種屬特異性性狀且具有特殊藥效成分的藥用植物,其生長發育機制及藥效形成生態因子等方面研究還很少。
藥用植物生態保育工作將不斷從生態因子的角度揭示藥用植物藥效形成機制,針對不同物種間耐受性存在較大差異和在一定生態幅內藥用植物品質差異較大問題,通過開展生態保育研究,尋找不同藥用植物藥效形成的最優生態因子,闡明藥用植物耐受范圍內特異性生態因子對藥用植物品質形成的影響機制,通過調節生態因子實現物種與藥效維持的“雙保護”。
4.3 藥材品質形成的馴化機制
由于藥用植物的馴化時間并不長,機械地將作物生產上的管理體系移植到藥用植物馴化實踐可能會導致藥用植物藥效丟失。如何在遺傳保育、生態保育研究基礎上,實現特定藥用植物種質與藥效形成關鍵生態因子的有機結合并應用到藥用植物馴化中是藥用植物保育研究的重點問題。未來,將通過3 個方面進行藥效形成馴化機制研究:1)遺傳基礎研究,分析藥用植物馴化過程中藥效相關基因突變群體發揮的正選擇作用和間接負選擇作用;2)同化物分配規律研究,基于源庫理論解析藥用植物生長及藥效形成機制;3)群體配制規律研究,通過復合種植填補生態位空白、提高光能利用率、維護土壤肥力及根際微生物結構,構建質量穩定的藥用植物栽培群體。
4.4 藥用植物精準栽培
近年來,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國家和地方政府對現代農業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要提升農業裝備和信息化水平,大力發展數字農業[53]。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中國共產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印發的《數字農業農村發展規劃(2019—2025 年)》提出,加快生產經營數字化改造,推動智能感知、智能分析、智能控制技術與裝備在大田種植和設施園藝上的集成應用,建設精準種植、環境控制、水肥藥精準施用、農機智能作業與調度監控、智能分級決策系統,發展智能農業,推進種植業生產經營智能管理[54]。現代農業主要包括設施農業、精準農業、觀光農業、無土栽培、太空農業等農業生產經營模式,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農業生產種植和經營,實現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精準化發展,促進農業附加值增長。其中,精準農業是由信息技術支持的,根據空間變異,定位、定時、定量地實施一整套現代化農事操作技術與管理的系統,是當今世界農業發展的新潮流。近年來,中醫藥行業迎來新機遇,但當前中藥材種植栽培技術落后、機械化程度低、農藥殘留嚴重等問題嚴重影響了中藥材產量和品質。藥用植物精準栽培技術以現代栽培學為基礎,融合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自動化、機器人等技術,實現藥用植物栽培的智能化與定量化生產,能有效保證中藥材規范化種植,有利于穩定或提升中藥材產量和品質。因此,在現有政策下,結合現代科學技術,根據藥用植物自身特性或用途(如藥用植物按照生活型可分為喬木、灌木、草本植物和藤本植物等類型;按照藥用部位可分為根、莖、花、種子、全草等類型;按照功能可分為藥用和藥食同源等類型),實施藥用植物精準栽培策略,是實現中醫藥現代化、產業化,推動中醫藥事業和產業高質量、可持續性發展的途徑之一。
5 結語
通過對藥用植物的深入研究,普遍認為其在特定的環境中生長才具有較高的藥用價值,但目前對相關的機制研究還十分薄弱。如今,大量野生藥用植物面對無序引種與采挖,藥用植物面臨物種與藥效喪失的風險。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本團隊創建了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學科——“藥用植物保育學”并出版了相應的專著和教材,通過藥用植物保育學研究達到保護資源、穩定藥效、實現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目的。同時,藥用植物保育學研究也是藥用植物園的一個重要科學使命,使未來藥用植物園能成功保存藥用植物物種,并為藥物開發和使用提供豐富的藥用植物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