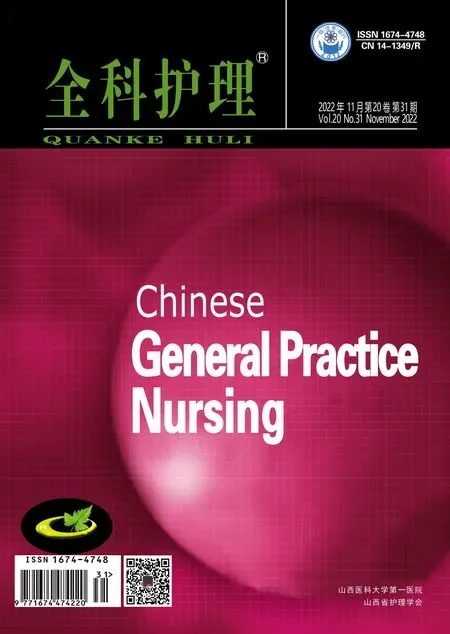護生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準備研究進展
徐園園,張 艷
近年來,世界范圍內不可預測的自然或人為災害日益增多,對人類健康、經濟和環境造成了極大的影響[1]。在應對由各種災害引起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護理人員是提供醫療保障服務的重要群體,在應急救援中發揮著重要作用[2]。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期間,全球出現醫療資源短缺、醫護人員嚴重不足等現象,部分國家的醫學生參加了一線隊伍,以減輕一線工作者的工作量,緩解勞動力短缺的現象[3]。美國護理學會提議在COVID-19流行期間,護理學校應制訂應急計劃,將預防感染和防控貫穿到課程中,或對學生進行短期培訓以應對緊急情況下日益增加的醫療保健服務需求[4]。護生作為未來護理行業主力軍,其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準備情況會直接影響未來的醫院災害應急救援能力。本文梳理了近幾年護理學生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認知、應急準備能力及參與意愿的研究文獻,從相關概念、評估工具、認知情況、應急準備能力水平、意愿高低及影響因素等方面進行綜述,以期為相關部門制訂有針對性的護生應對災害能力培訓方案提供參考依據。
1 概念與內涵
1.1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指突然發生造成或可能造成社會公眾健康嚴重損害的重大傳染病疫情、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職業中毒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公眾健康的事件。在文獻回顧中研究者常根據事件的規模和發展階段用突發事件、緊急情況、危急情況、災害、災難等表示,不同的定義在內容和意義上有著相似和重疊之處[5]。
1.2 應急準備 應急準備目前沒有統一的定義,Slepski[6]認為應急準備是準備和應對受到威脅的、實際的或可疑的化學、生物、輻射、核或爆炸事件、人為事件、自然災害或其他相關事件所需的綜合知識、技能、能力和行動。張文娟等[7]認為應急準備是指為有效應對突發事件而提前采取的各種措施的總稱,所采取的準備行為或活動,包括意識、認知、心理與文化、行為、知識與技能等方面。應急準備包含災害準備和其他緊急事件的應急準備,對于災害的應急準備,研究者常用備災或者災害準備度來表示。Mikovits[8]提出應急準備和災害準備可以交替使用。本文結合上述概念及相關文獻,將應急準備界定為:護理人員為有效應對突發危急事件所做的態度、知識和能力準備,包括基礎護理及急救、病情觀察、心理支持、職業防護、醫院感染防控以及冷靜的應變、全面的協調能力、慎獨的職業精神8個維度的知識和技能及綜合運用能力。
2 評估護生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準備情況的工具
2.1 應急準備信息問卷(Emergency Preparedness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EPIQ) 威斯康辛護士協會(WNA)通過對注冊護士應急教育和培訓需求的調查,制定了EPIQ[9]。該問卷包含8個維度44個條目,8個維度分別為檢傷和基本急救、監測、訪問關鍵資源和報告的能力、事件指揮系統(ICS)、隔離和凈化、心理問題、流行病學和臨床決策、溝通和協作。問卷采用Likert 5級評分法,從“不熟悉”到“非常熟悉”分別計 1~5分,各維度Cronbach′s α系數為0.827~0.940[9]。Garbutt等[10]對EPIQ進行了修訂,修訂后的EPIQ包含7個維度:①流行病學和生物制劑的臨床決策;②事故指揮系統;③溝通和協作;④心理問題和特殊人群;⑤隔離、消毒、檢疫;⑥檢傷分類;⑦報告和獲取關鍵信息。各維度Cronbach′s α系數為0.92~0.96,總Cronbach′s α系數為0.98[11]。李書梅[12]對EPIQ進行了翻譯修訂,形成護理人員災害應急知識量表,該量表包含6個維度40個條目,6個維度分別為事故指揮系統、檢傷分類、溝通和聯絡、特殊護理及隔離去污、報告和獲取重要資源、生物制劑。各維度Cronbach′s α系數為0.768~0.860,總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75[13]。EPIQ由權威機構研制,在國外廣泛應用于護理人員應急準備度的評估,經檢驗信效度較好。國外有研究者將其應用于實習護生的應急準備情況的調查,但其中部分條目不太適合用于國內護生和實習護生,有待進一步修訂完善。
2.2 護理本科生災害反應自我效能量表(The Disaster Response Self-Efficacy Scale,DRSES) DRSES量表由Li等[13]于2017年編制,旨在評價中國護理本科生對災害的應對能力,并對其心理測量特性進行測試。該量表以ICN勝任力框架為理論指導[14],包含災害評估能力、災害應急救援能力、災害心理護理能力、災害角色素質和適應能力4個維度,共22個條目。該量表采用Likert 5級評分法,從完全沒有自信到完全自信計1~5分,得分越高代表在災難反應中的自我效能感得分越高。整體量表的內容效度指數(CVI)為0.91,總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12,3個維度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93,0.862,0.832,信效度較好[13]。該量表適用人群為我國護理本科生,部分國外學者使用該量表對其護理學生進行調查研究,但在國內尚未得到廣泛應用,可能與該量表原文尚未有中文版有關。
2.3 護理本科生災害護理能力問卷 護理本科生災害護理能力問卷由楊美芳等[15]編制,旨在評價護理本科生災害護理能力。該問卷包括知識體系、實踐技能、身心素質3個維度,共47個條目。問卷采用Likert 5級評分法,做到最差到做到最好計1~5分,得分越高表示災害護理能力越高,反之越低。問卷總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649,3個維度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924 2,0.945 8,0.889 6,信度較好。該問卷人群針對性強,主要適用于我國護理本科生,被廣泛應用于我國護理學生的災害護理能力和應急能力的評價。但是該問卷在消毒隔離、自我防護、凈化去污及生物生化事件的緊急救護方面缺乏相關的評價條目,對目前頻發的災害和緊急事件類型包含還不全面。
3 護生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準備現狀研究
3.1 護生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準備現狀 麥劍榮等[16]報道,護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風險認知處于中等水平。陳霞等[17]對120名實習護生進行災害急救認知調查,發現98.3%的實習護生認為災害后果嚴重,65.8%認為現場救護很需要心理護理,與曹瑩等[18]研究結果類似,72.5%的實習護生認為自己現有的災害救援知識只能勉強適應現場救援的需要。Kamanyire等[19]對阿曼51名護生的調查結果顯示,有52.9%的護生不了解如何為災害做好準備,與Longo等[20]研究結果相似,56.9%的護生不明確自己在災害發生時能擔任什么角色,只有17.6%的護生認為自己可以擔任做檢傷分類的角色。同時該51名護生在知識、技能、災后管理、勝任力、自我效能等各方面均處于中等水平,大多數(52.9%)護生不了解如何為災難做好準備。Liou等[21]的調查顯示,護生災害護理能力處于較低水平,有13.3%的護生認為自己非常熟悉災害管理程序,42.2%的護生對災害管理程序非常不熟悉。 Yoshida等[22]對287名日本國立大學護生進行調查,發現護生對輻射知識的了解程度較低,與李敏杰等[23]的研究結果一致。總之,國內外護生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認知水平均不高,需要進一步接受相關知識培訓。華小倩等[24]對358護生進行了新發傳染病防治知識的認知調查,發現護生對相關知識答題的正確率為78.0%,認知程度處于中上等水平,這可能與COVID-19流行期間相關知識普及度較高有關,但同時也提醒我們需進一步加強對護生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能力培訓。麥劍榮等[16,25-27]在對我國護生的應急準備能力進行調查,發現在校本科護生和實習護生的應急準備水平均處于中等或偏下水平,急救技能得分較高,應急知識得分較低,防災知識及救災儲備的能力不足,但救災態度積極。
綜上所述,目前國內外護理專業學生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應急準備情況不夠理想,尚需開展更多的研究,盡快提高護生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危急事件的準備度。
3.2 護生參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意愿研究現狀 護理人員的工作意愿和應急態度直接影響其獲取知識的主動性及開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救援的能力。在COVID-19流行期間王君等[28]對我國107名實習護士進行調查,發現98.13%的實習生愿意參與臨床一線的抗疫活動,這與Choe等[29]對日本和韓國的護生調查災害救援意愿結果相近。Hung等[1]對157名我國香港護生的調查中顯示,自愿參加大流行事件的護生占77.4%,并表示如果具備相關的災難知識和技能會更愿意上崗。有調查發現,有90.0%的護生畢業后愿意從事護士工作,27.8%的護生表示愿意參與社區救災[21],這可能與大部分院校未開展災害管理課程,護生對社區救災了解不全面有關。Inal等[30]在對839名醫學生參與不同災害類型災害意愿調查中顯示,他們更愿意在地震(71.1%)和交通意外(66.2%)等災害期間工作,在傳染病(35.1%)和氣體泄漏(33.5%)災害期間工作的意愿相對低于前者。雖然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護生對參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意愿存在較大的差異,但整體上參與救援工作的意愿較高,同時對不同類型災害和公共衛生事件的參與意愿不盡相同,對健康風險高的災害參與意愿較低。
4 影響護生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準備的因素
4.1 自我效能感 根據Bandura提出的認知理論,自我效能感是個體對實現某種行為目標的能力的信心,它與個體的行為能力和行為結果呈正相關[13]。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個人的應急準備行為與自我效能感存在很強的關系,應急準備的自我效能感可能會提高應急準備行為能力[31]。自我效能感高的護生可能態度更積極,對環境的適應能力也越強,更愿意參與救援工作。Kilic等[32]在對護生進行心理急救培訓的研究中顯示,經過培訓的護生自我效能感明顯提高,在應對災害的各個階段(準備階段、干預階段、災后階段)的平均得分均高于未培訓的護生,與Jonson等[33]研究結果一致。因此,在災害培訓中注意增強護生的自我效能感,將有助于提高其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
4.2 教育與培訓內容 目前國內外已有高校和實習醫院正在積極開展護理學生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培訓和演練,以此來提高護生的應急準備能力,培訓形式包括開展災害護理課程、短期培訓、微視頻、線上授課、跨專業模擬演練等。鄭偉等[34]采用情景模擬聯合視頻教學的方法對護生進行急救演練教學,參加過培訓的護生在知識、技能、綜合能力等方面均高于未參加培訓的護生,這與尹靜等[35]研究結果相似。Currie等[36]研究顯示,大規模傷亡護理教育有利于發展其臨床分析思維能力,提高防災知識和護理技能。在Koca等[37]對護生進行災害護理教育時,發現隨著知識水平的提高,護生對防災準備和應對自我效能感的認知也會增加,進而提高了護生的應急準備能力和參與緊急救援意愿。在我國護生的應急準備能力評價中應急知識得分最低,可能與災害和應急護理教育開展較晚有關[16,26]。Koca等[37-38]研究發現,通過應急準備培訓可以增強護生對救援角色認識,提高應急知識儲備、護理技能以及參加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信心,進而提高自我效能感和參與救援意愿。也有學者認為多學科跨專業模擬演練可以培養護生的應急準備能力,包括溝通、計劃、凈化和防護,以及對事故指揮系統的理解和災難期間的道德規范[39]。我國目前對護生開展的應急知識培訓和應急演練較少,各個院校可開展以學生為中心、線上線下相結合、跨專業合作的應急演練,以全面提高護生的應急知識、技能、團隊合作能力等。
4.3 其他因素 另有研究顯示本科實習護生急救知識得分高于專科護生,可能與其接受教育時間長有關[17]。Li等[40-41]研究均顯示救災經歷使護生更有能力和心理準備應對災害,真實的救災體驗有助于提高其應急準備能力水平。護生參加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意愿較低,可能與疾病發展的不確定性、擔心自身健康、怕感染家人有關[1]。也有研究顯示男生的應急能力高于女生,可能因為男生在救援工作中更具有體力和思維優勢,能更好地適應救援艱苦、機動的工作環境[27]。
5 啟示與展望
5.1 亟待構建護生應急準備教育體系 目前,自然災害、各種突發傳染病導致的公共衛生事件不斷出現,護生須做好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知識、技能及心理準備,才能應對將來要面對的工作挑戰。因此,當前的護理教育內容體系需進行根本性的變革。應急準備教育是提高護生應急準備和救援能力的關鍵途徑,包括提高災害應對能力、增加實踐和理論知識,減輕陌生環境對心理的影響等[42]。國外護生的應急準備教育發展比較成熟,美國護理學院協會(AACN)在2001年提出所有護士都必須接受護理應急準備教育培訓,2008年將疫情背景下護理應急準備教育納入護理本科教育中[43]。AACN于2021年發布的護理專業課程標準的修訂要點中包含了災害應對能力標準。我國自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之后,加快了公共衛生應急體系的建設,并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一系列護理應急準備培訓活動,但教育內容的開發尚有待完善,目前尚未形成標準化的培訓體系[43]。
5.2 亟待發展更適合護生的應急準備評估工具 目前多數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準備情況的評估工具適用于注冊護士和執業護士,ICN-WHO framework 2.0版提出應根據護士的個人職業經歷和專業知識確定不同層級護士所應具備的災害準備度和災害護理能力[44]。目前適合護生的評估工具較少,部分工具在研制過程中缺乏理論依據,且沒有被廣泛應用,需要更全面的評估工具來準確評價護理學生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準備情況。該評估工具的開發,將為構建護生應急準備能力指標體系,明確護生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的態度、知識及能力準備提供指引框架,也為有針對性地開展護生應急準備教育提供有價值的參考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