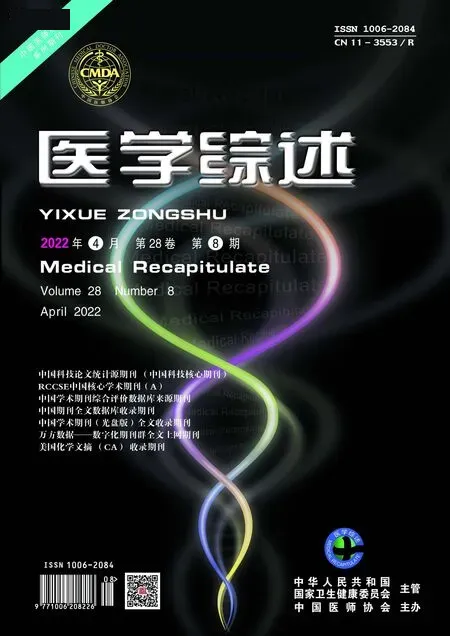葡萄糖水平對自噬的影響研究進展
楊瀾,楊磊,周春雷,范彩紅,王東強,穆紅
(1.天津醫科大學一中心臨床學院,天津 300192; 2.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 a.檢驗科,b.中西醫結合科,天津 300192)
自噬是膜包裹部分胞質和細胞內受損、老化的蛋白質或細胞器等成分形成自噬體,自噬體再與溶酶體融合形成自噬溶酶體,進而內容物被溶酶體酶降解,物質得以重新利用和更新的生物學過程[1]。自噬除了發生在營養饑餓、能量耗盡等應激壓力下,也發生于細胞正常狀態。自噬不僅與機體的饑餓反應、細胞分化、早期生長發育等生理活動有關,近年的研究證實其也參與腫瘤的發生、糖尿病、神經退行性病變等病理過程[2]。自噬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適度的自噬可以實現物質的循環利用,保障細胞內物質質量;另一方面,過度自噬可引起細胞凋亡,癌細胞也可利用自噬促進自身成活[3]。因此,自噬也成為神經退行性疾病、胰腺癌、乳腺癌、其他腫瘤發生及耐藥性的治療靶點[4-7]。
葡萄糖是一種單糖,是體內主要的能源物質。當機體血糖水平異常時,細胞會通過一系列分子物質的調控表現為促進或抑制自噬。自噬的有益或有害作用與細胞類型、細胞狀態、自噬的激活形式等因素有關[1]。現從葡萄糖水平與自噬的關系出發,綜述近年葡萄糖影響自噬的機制,旨在為葡萄糖失衡狀態下調控正常細胞成活或癌細胞凋亡提供新的方向和途徑。
1 細胞自噬的分類
根據細胞內需降解物質進入溶酶體的途徑不同,自噬可分為巨自噬、微自噬和分子伴侶介導的自噬[8]。巨自噬是自噬最常見的類型,其以依賴環境的方式促進細胞成活或加速細胞凋亡,其特征性標志是具有部分細胞質的雙膜結構自噬體的形成。大致過程為:首先在自噬體形成部位產生隔離膜,隨后膜邊緣伸長和閉合,形成自噬體,再與含有水解酶的溶酶體融合,自噬體成熟為具有高電子密度的單膜結構自噬溶酶體,最后膜內容物被降解[9]。微自噬是通過液泡內膜或溶酶體的直接吞噬作用降解細胞中大分子物質,近年研究提出根據被降解物質進入溶酶體的分子機制可將其細分為兩種微自噬:依賴轉運必需內體分選復合物的裂變型微自噬和需要自噬核心蛋白、可溶性N-乙酰基亞胺敏感因子附著蛋白受體的融合型微自噬[10]。分子伴侶介導的自噬選擇性降解具有特定氨基酸序列賴氨酸-苯丙氨酸-谷氨酸-精氨酸-谷氨酰胺樣基序的細胞蛋白質[11],底物蛋白與分子伴侶熱激蛋白70結合并被轉運到溶酶體,然后被溶酶體酶消化。
根據底物降解的選擇性,自噬分為非選擇性自噬和選擇性自噬[12],非選擇性自噬主要用于饑餓條件下大量細胞質的更新[13],隨機降解細胞質成分。選擇性自噬則專門針對受損或多余的細胞器,由自噬體中選擇性自噬受體和銜接蛋白決定,包括線粒體自噬、內質網自噬、過氧化物酶體自噬、核糖體自噬、細胞核自噬等[14]。
2 葡萄糖水平與自噬
2.1血糖相關調控通路 在哺乳動物中,葡萄糖剝奪會引起細胞內AMP/ATP比值增加,進而激活AMP活化的蛋白激酶(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AMPK是一種葡萄糖傳感器,也是細胞能量傳感器,幾乎存在于所有真核生物中。AMPK一旦激活后,便促進產生ATP的分解代謝途徑,抑制消耗ATP的合成代謝途徑[15]。AMPK激活后,哺乳動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復合體1(mTOR complex 1,mTORC1)受抑制,p53、p27 Kip1激活,誘導細胞自噬。自噬是細胞的主要分解代謝過程,可在面對代謝壓力時促進成活。它受到一系列對營養狀況有反應的激酶的嚴格調控,包括mTORC1、AMPK、促分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2/3、Rho相關激酶1、c-Jun氨基端激酶、酪蛋白激酶等[16]。自噬的調控機制復雜,其上游信號通路主要涉及mTOR依賴性通路和mTOR非依賴性通路,mTOR非依賴性通路包括AMPK、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3-kinase,PI3K)、人第10號染色體缺失的磷酸酶及張力蛋白同源基因等[1]。同時葡萄糖剝奪和高水平的葡萄糖會改變氧化磷酸化,導致線粒體超極化,活性氧增加,信號傳遞給AMPK、p38促分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c-Jun氨基端激酶、胞外信號調節激酶等激酶,進而誘導細胞自噬。葡萄糖調控自噬除了與能量變化和活性氧誘導相關的信號通路有關外,還與IκB激酶/核因子κB、煙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依賴性去乙酰化酶和叉頭框蛋白O1或叉頭框蛋白3有關[17]。
2.2葡萄糖剝奪與非選擇性自噬 Liu和Wang[18]發現第9號染色體上開放閱讀框72基因是營養應激反應期間自噬溶酶體途徑負反饋控制的關鍵調節因子。第9號染色體上開放閱讀框72基因缺乏的細胞,會出現共激活因子相關精氨酸甲基轉移酶1異常積累,并在葡萄糖饑餓應激下出現細胞自噬和脂質代謝異常。共激活因子相關精氨酸甲基轉移酶1 是一種轉錄共激活因子,而且是一種自噬表觀遺傳調節劑。在營養缺乏時,共激活因子相關精氨酸甲基轉移酶1 不僅可被細胞核中的蛋白酶體泛素化降解,也可進入溶酶體降解,而且第9號染色體上開放閱讀框72基因是共激活因子相關精氨酸甲基轉移酶1 在溶酶體降解所必需,可防止自噬和脂質代謝的過度激活。Yoon等[19]發現,亮氨酸-轉移RNA合成酶1可負向調控葡萄糖剝奪產生的自噬反應。葡萄糖剝奪時,亮氨酸-轉移RNA合成酶1的亮氨酸結合殘基在unc-51樣激酶1的作用下磷酸化。磷酸化的亮氨酸-轉移RNA合成酶1亮氨酸結合減少,進而蛋白質合成受到抑制,自噬激活。通過這種方式,磷酸化的亮氨酸-轉移RNA合成酶1可以減少ATP消耗并將亮氨酸用于ATP的生成,提高細胞對葡萄糖饑餓的耐受性。
Liu等[20]發現葡萄糖剝奪時,Toll樣受體9和自噬相關蛋白(autophagy related,ATG)Beclin1會相互作用,并隨著能量應激,蛋白質相互作用增加,但這種相互作用不受其他應激因素(如氨基酸剝奪或線粒體損傷)的影響。Toll樣受體9/Beclin1相互作用可改變含Beclin1的Ⅲ類PI3K復合物的構象進而誘導自噬。Cui等[21]發現,葡萄糖剝奪激活AMPK使β-轉導重復相容蛋白1磷酸化,并促進β-轉導重復相容蛋白2對β-轉導重復相容蛋白1的泛素化和降解,但不促進β-轉導重復相容蛋白1對β-轉導重復相容蛋白2的降解。β-轉導重復相容蛋白2優先降解mTORC1的抑制劑以激活mTORC1,從而抑制自噬和細胞生長。
Yao等[22]發現,ATG11是啟動葡萄糖饑餓誘導的自噬所必需,在葡萄糖饑餓時,ATG11促進酵母中AMPK同系物Snf1和ATG1之間的相互作用。吞噬細胞組裝位點的形成需要ATG11控制ATG17與ATG29-ATG31的結合,因此ATG11可作為控制葡萄糖饑餓誘導的自噬中多個步驟的關鍵起始因子。Yang和Klionsky[23]使用多種細胞系證明了一種依賴于5-磷酸磷脂酰肌醇合成的新型非經典自噬途徑。該通路受AMPK-unc-51樣激酶1-含FYVE鋅指磷酸肌醇激酶軸調節。Unc-51樣激酶1在葡萄糖饑餓時被AMPK激活,導致S1548上的脂質激酶含FYVE鋅指磷酸肌醇激酶磷酸化。激活的含FYVE鋅指磷酸肌醇激酶增強了含有5-磷酸磷脂酰肌醇的自噬體的形成,從而驅動自噬上調。
Bao等[24]發現,葡萄糖饑餓可以誘導依賴鎂/錳離子的蛋白磷酸酶1B從RAS蛋白激活類似物2解離,蛋白磷酸酶1B從RAS蛋白激活類似物2的S351位點被AMPKα1磷酸化,然后磷酸化的RAS蛋白激活類似物2與Ⅲ類PI3K-ATG14-Beclin1復合物結合,增強Ⅲ類PI3K的活性并促進自噬。研究表明,蛋白磷酸酶1B從RAS蛋白激活類似物2 S351的磷酸化可以作為分子開關來抑制或促進AMPK介導的自噬。Jiang等[25]證明了鈉-葡萄糖協同轉運蛋白2抑制劑可抑制心肌細胞自噬性細胞凋亡,對心臟有保護作用,可降低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病死率。鈉-葡萄糖協同轉運蛋白2可直接抑制心肌細胞中Na+/H+交換器1的活性,以調節過度自噬。Na+/H+交換器1的過表達可加重饑餓引起的心肌細胞凋亡,而鈉-葡萄糖協同轉運蛋白2治療可有效緩解饑餓引發的細胞凋亡。
2.3葡萄糖剝奪與選擇性自噬 有報道顯示葡萄糖饑餓時,AMPK通過調節細胞內還原型煙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的穩態促進癌細胞成活。在營養缺乏和缺氧期間,細胞內AMP/ATP的比值增加,肝激酶B1通過磷酸化激活AMPK,通過葡萄糖饑餓誘導的氧化應激觸發肝激酶B1-AMPK信號通路促進選擇性自噬,從而增強Kelch樣環氧氯丙烷相關蛋白-1降解,激活核轉錄因子紅系2相關因子[26]。Zheng等[27]利用氧-葡萄糖剝奪和再灌注神經元模型模擬腦缺血,在這種情況下已被證實會發生線粒體損傷和線粒體自噬。通過選擇性標記軸突線粒體,發現這些受損的軸突線粒體會逆行出現在神經元胞體中,并優先通過自噬體消除。通過該機制,神經元可以識別、分類受損的軸突線粒體,并將其輸送到神經元胞體中進行降解。
Kulkarni等[28]發現在缺乏或含有葡萄糖的人工腦脊液中,饑餓培養原代星形膠質細胞會抑制原代星形膠質細胞的自噬流量,并抑制其選擇性自噬水平。他們通過將星形膠質細胞饑餓在以碳酸氫鹽和磷酸鹽緩沖的含有5.6 mmol/L葡萄糖的Earle′s平衡鹽溶液和以4-羥乙基哌嗪乙磺酸緩沖的人工腦脊液溶液中,發現饑餓誘導的自噬流量依賴于饑餓溶液的緩沖系統。處理于4-羥乙基哌嗪乙磺酸緩沖液中的原代星形膠質細胞抑制了自噬流量,而處理于碳酸氫鹽和磷酸鹽緩沖液中的細胞誘導了自噬流量。除此之外,他們還發現強烈激活星形膠質細胞自噬的饑餓條件對神經元自噬的影響較小,這也充分說明在不同的代謝應激模式下,大腦不同細胞類型調節自噬的復雜性。
聚合酶相關因子1復合物是ATG基因的轉錄抑制因子,其通過結合ATG32基因的啟動子在富含葡萄糖的條件下維持低水平的線粒體自噬[29-30]。在葡萄糖饑餓時,聚合酶相關因子1復合物與ATG32的解離,導致該基因表達增加,同時誘導線粒體自噬。在葡萄糖剝奪的細胞中,Lee等[31]發現了一種控制溶酶體膜轉換的機制,葡萄糖饑餓的細胞表現出顯著但選擇性的溶酶體膜蛋白轉換,這種選擇性轉換由自噬蛋白通過微自噬調節。選擇性微自噬與微管相關蛋白1輕鏈3脂質化有關,脂質化又可通過微自噬調節溶酶體的大小和活性。
2.4高糖水平與非選擇性自噬 高糖可誘導血管內皮細胞發生氧化應激、線粒體損傷等改變,導致內皮細胞發生自噬和凋亡[32-33]。Niu等[34]發現二甲雙胍通過以膠質瘤相關癌基因同源1 (Hedgehog通路的轉錄因子)依賴性方式激活Hedgehog信號通路,下調高糖觸發的內皮自噬,減輕高糖引起的內皮損傷。熊果苷已廣泛用于治療皮膚色素沉著癥,Lv等[35]研究了在高糖誘導的人腎皮質近曲小管上皮細胞中,熊果苷對凋亡和自噬的作用,發現通過熊果苷上調微RNA(microRNA,miRNA/miR)-27a/c-Jun氨基端激酶/mTOR軸抑制高糖狀態下的人腎皮質近曲小管上皮細胞凋亡和自噬,對糖尿病腎病有保護作用。Zhou等[36]發現,高血糖水平與胰腺癌患者的不良預后相關。固醇調節元件結合蛋白1在胰腺癌組織和胰腺癌細胞系中均過表達。高糖微環境通過增加固醇調節元件結合蛋白1的表達促進腫瘤細胞增殖、抑制細胞凋亡和自噬水平,證明了固醇調節元件結合蛋白1與自噬之間存在負反饋調節。
Zhao等[37]發現高糖環境下,血管內皮細胞的長鏈非編碼RNA CA7-4通過誘導miR-5680和miR-877-3p作為競爭性內源性RNA,促進內皮細胞自噬和凋亡。其機制為miR-877-3p可通過與β聯蛋白相互作用蛋白1的3′非編碼區結合,下調β聯蛋白相互作用蛋白1,進而上調β1聯蛋白;miR-5680通過靶向二肽基肽酶4,抑制AMPK的磷酸化。Bai等[38]發現高糖通過抑制AMPK-mTOR-PI3K途徑,抑制小窩蛋白-小窩相關蛋白-微管相關蛋白1輕鏈3B介導的小窩蛋白自噬降解,進而小窩蛋白在胞質中積累,積累的小窩蛋白可促進低密度脂蛋白跨內皮細胞轉運,增加導致動脈粥樣硬化的脂質在內皮下的滯留。Chang等[39]研究了高糖誘導的自噬在骨髓間充質干細胞衰老中的作用,發現高糖環境增加了Beclin1、ATG5、ATG7、ATG12的表達、微管相關蛋白1輕鏈3-Ⅱ的產生以及自噬體形成,但抗氧化劑可減少活性氧,從而減少自噬和細胞衰老。脂肪組織干細胞在高糖應激下表現出自噬、活性氧水平、凋亡增加[40]。活性氧/c-Jun氨基端激酶信號轉導參與了高糖狀態下上調的自噬,且增加的自噬在高糖誘導的脂肪組織干細胞凋亡中具有保護作用。
2.5高糖水平與選擇性自噬 線粒體功能障礙和過量的線粒體活性氧是糖尿病狀態下內皮損傷的根本原因。Zhu等[41]觀察到人臍靜脈內皮細胞暴露于高糖會引發線粒體損傷,導致線粒體斷裂和活性氧生成,在高糖狀態下人臍靜脈內皮細胞線粒體自噬會減弱,從而加速功能障礙的線粒體積累,啟動線粒體凋亡途徑,并最終導致內皮功能障礙。他們進一步研究發現,間充質干細胞可以通過人第10號染色體缺失的磷酸酶及張力蛋白同源基因誘導激酶1/Parkin(由PARK2基因編碼的一種蛋白)介導的線粒體自噬改善線粒體功能障礙,從而保護內皮細胞免受高血糖誘導的損傷。
3 自噬與細胞凋亡方式的轉化
有研究使用抗糖酵解劑和自噬抑制劑對腫瘤細胞進行共處理,發現這種共處理對腫瘤細胞的能量剝奪產生了加強作用,腫瘤細胞在這種治療干預下凋亡增多,說明饑餓療法聯合細胞自噬抑制可有效促進腫瘤細胞凋亡[42]。這也說明了在面對應激反應時,自噬在細胞成活和凋亡之間處于重要地位。已被證實哺乳動物細胞主要有3種凋亡方式:凋亡、自噬性細胞凋亡和壞死[43]。自噬與這3種凋亡方式之間具有復雜的相互作用,同時這3種凋亡方式也可單獨或共同誘導細胞凋亡。自噬在細胞凋亡中的作用可以分為4種[44-45]:①自噬相關的細胞凋亡,自噬的誘導與其他細胞凋亡途徑的誘導一致,其中自噬只是伴隨細胞凋亡過程而在其中沒有積極作用;②自噬介導的細胞凋亡,其中自噬誘導觸發細胞凋亡或壞死;③自噬性細胞凋亡,這是一種獨立于細胞凋亡或壞死發生的獨特細胞凋亡機制;④自噬聯合性細胞凋亡:特定于某環境的細胞凋亡模式涉及細胞凋亡或壞死和自噬的協同作用,這是由刺激形式、強度和任一凋亡方式的閾值決定[46]。
4 小 結
葡萄糖水平與自噬相關,兩者之間的作用機制近年來又有了新的完善。通過葡萄糖調控自噬有望達到“趨利避害”的目的,自噬調節成為疾病治療的潛在靶點,但需要臨床實踐進一步驗證,明確熱量限制的具體劑量、周期、葡萄糖與相應自噬調控的水平、表觀現象等。未來可進一步豐富相關的基礎研究,然后將理論機制逐步大量應用到動物模型,進而再應用于臨床實踐,通過調整應用方案為疾病早日探求有效的治療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