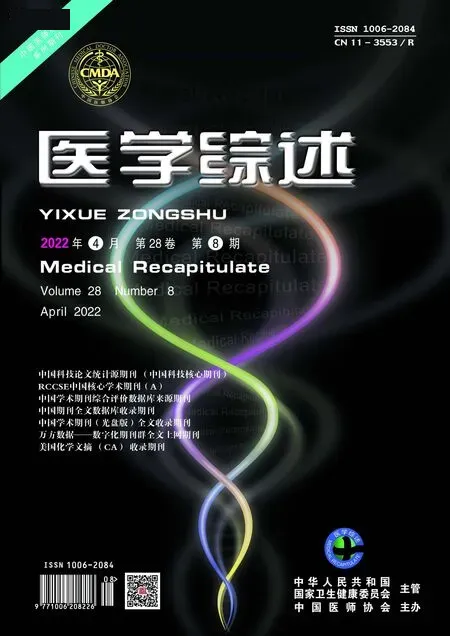韁核的生理功能及其在精神疾病中的作用
劉馨雅,葛菲菲,劉德康,史婷婷,關曉偉
(南京中醫藥大學醫學院·整合醫學學院,南京 210023)
韁核是脊椎動物所特有的在系統發育上高度保守的腦神經核團。在哺乳動物中,韁三角、韁聯合與松果體和丘腦髓紋四者構成上丘腦,位于第三腦室頂。韁核內部結構界限清晰,分為內側亞區和外側亞區[1],兩個亞區在解剖聯系、神經化學和基因表達譜及功能上存在差異。韁核及兩個纖維束構成背側間腦傳導系統,為神經信息從端腦向間腦傳遞提供了一條通路[2]。韁核的結構異常、功能紊亂與多種精神疾病的臨床癥狀密切相關。王紹[3]研究發現,抑郁癥患者外側韁核的異常興奮可導致中縫核釋放的5-羥色胺顯著減少,并由此全面闡述了韁核的生理功能;2018年胡海嵐課題組揭示了外側韁核簇狀放電是抑郁發生的充分條件,闡明了快速抗抑郁的作用機制[4-5];2019年該課題組基于韁核這一重要作用發現,氯胺酮通過阻斷外側韁核的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達到快速抗抑郁目的[6]。現就韁核的生理功能及其在精神疾病中的作用進行綜述。
1 韁核的神經元類型和神經通路
1.1韁核的神經元類型 外側韁核各亞核主要是谷氨酸能神經元核團,同時也表達5-羥色胺受體2C、酪氨酸羥化酶和多巴胺受體d2基因[7],表明外側韁核神經元能夠合成5-羥色胺和多巴胺。而內側韁核神經元表達多種神經遞質,上部區大量表達谷氨酸能和白細胞介素-18,同時接受去甲腎上腺素能輸入,中部背側區表達谷氨酸能和P物質能,而中部腹側區、下部區和外側區主要表達谷氨酸能和乙酰膽堿能[8]。
1.2韁核的輸入和輸出神經通路 外側韁核包括10個亞核,細胞排列松散、染色淺[9]。外側韁核的纖維聯系相對復雜,同時接受前腦邊緣神經系統和基底神經節的谷氨酸能的投射[10],其中最主要的輸入來源為蒼白球,其次為邊緣神經系統的多個腦區,包括Broca斜角帶、外側視葉前區、外側下丘腦、無名質和終紋基底核。根據外側韁核的亞核位置又可為外側韁核外側部分和外側韁核內側部分[11]。外側韁核內側部分主要接受來自基底前腦的信號輸入,側韁核外側部分主要接受來自基底神經節的信號輸入。外側韁核的傳出纖維最主要投射至中腦,包括中腦中央灰質、中縫背核、腹側背蓋區(ventral tegmental area,VTA)和黑質致密部(substantia nigra compacta,SNc)。
內側韁核包括5個亞核,體積較外側韁核略小,細胞排列緊密、染色深,輸入和輸出的投射路徑不同。內側韁核主要接受來自邊緣系統的信號輸入,少部分來源于Broca斜角帶和外側視葉前區。同時內側韁核也接受來自藍斑的去甲腎上腺素能投射和來自VTA的多巴胺能投射。內側韁核的傳出主要通過后屈束投射至腳間核。其中,內側韁核上部區主要投射至腳間核外側區,底部外側主要投射至腳間核喙部,底部內側主要投射至腳間核中部。
2 韁核的生理功能
2.1外側韁核參與多巴胺獎賞的調控 作為大腦反獎賞系統的核心組成部分,外側韁核整合來自外部和內部的刺激,以調節對厭惡相關刺激的適應活動,參與獎賞和厭惡的調控。Matsumoto和Hikosaka[12]首先開始了對外側韁核作為負性獎賞信號來源的開創性研究,從2007年開始逐漸揭示外側韁核通過對多巴胺能神經元的抑制作用達到調控獎賞抉擇的目的。Matsumoto和Hikosaka[12]采用兩只獼猴為實驗對象,發現在獎賞缺失時,首先記錄到外側韁核神經元興奮,接著SNc多巴胺能神經元放電活動被記錄到受抑制;如果在預期無獎賞時給予獎賞刺激,則先是外側韁核神經元抑制,然后SNc多巴胺能神經元放電活動增加。該實驗結果首次證明,外側韁核發放信號調控獎賞過程中多巴胺的釋放——外側韁核神經元在對懲罰刺激的反應中活動增加,而在對獎勵刺激的反應中減少活動。外側韁核被描述為一個負性獎勵中心,其編碼一個與厭惡相關的“預測錯誤信號”,當獎勵相關結果的實際值小于預測值時,該信號被激活[13]。
通過同樣的策略,Hikosaka[14]隨后發現了追蹤調控信號的來源為內部蒼白球邊緣區。外側韁核并不直接抑制多巴胺神經元,而是先投射至吻內側被蓋核(rostromedial tegmental nucleus,RMTg),RMTg內主要是γ-氨基丁酸能神經元,這些γ-氨基丁酸能神經元將來自外側韁核的信號投射至VTA和SNc,從而達到抑制多巴胺能神經元的目的[15],這種外側韁核-VTA通路在傳遞負性獎勵預測錯誤和動機的信號中起關鍵作用。綜上所述,外側韁核被認為是整合紋狀體和邊緣系統獎賞相關信息并向中腦單胺能核團傳遞的主要結構,在影響主觀決策偏差方面起主要作用。
2.2對晝夜節律的調節 晝夜節律系統負責協調內部生理和外部世界,涉及生理和行為的各個方面,在大腦中影響著神經元活動、神經化學的合成釋放和受體可用性。該系統以下丘腦視交叉上核(suprachiasmatic nucleus,SCN)的主晝夜節律起搏器為中心,通過直接從眼睛接收的環境光信息與外界同步。SCN神經元的節律性時鐘基因表達驅動其電活動的變化,從而實現時間信息的交流,并組織下游靶細胞的晝夜節律。外側韁核是大腦晝夜節律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
電生理學顯示,刺激SCN可以引起韁核神經元活動變化[16]。從外在神經結構上分析,韁核與SCN存在直接纖維聯系,SCN可以通過精氨酸升壓素直接向外側韁核發送晝夜節律的計時信號。此外,SCN支配下丘腦背內側區,并通過背內側區支配下丘腦外側區,將SCN的晝夜節律計時信號投射至外側韁核。由此可見,外側韁核是晝夜節律相關信息的接受者,對外在的時間信息做出反應。
從節律相關基因來看,整個韁核大量表達生物鐘基因Period1、Period2和Clock[17],且在外側韁核內側部分發現Per2表達存在明顯節律性變化[18]。小鼠實驗發現,外側韁核內c-fos的表達也有明顯晝夜節律性,白天休息時,外側韁核內側部分中的c-fos低表達,而在夜晚外側韁核內側部分中的c-fos高表達[19]。此外,與晝夜節律相關的Cry基因被敲除后,韁核神經元的自發放電不再具有晝夜節律性。同時,在黑暗環境中飼養的小鼠腦部切片中,神經元活動的晝夜變化是持續的,表明在環境光照不變的情況下,晝夜節律可以驅動外側韁核細胞放電速率的節律性變化[20]。這些證據表明,外側韁核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內在晝夜節律計時能力。外側韁核涉及獎賞、厭惡、動機行為等一系列神經過程,其中多數表現出每日或晝夜節律的變化,但晝夜節律變化的產生機制以及這些變化是否與外側韁核的節律性有關尚不清楚。
2.3對痛覺的調節 韁核與對獎賞和厭惡刺激反應的調控有關,當缺失預期獎賞或給予厭惡性刺激時,谷氨酸能神經元發放激活;獎賞刺激時發放被抑制[21]。疼痛和疼痛的緩解可分別看作是厭惡性刺激和獎賞性刺激。從纖維聯系上分析,外側韁核直接連接脊髓背角的纖維投射,接受來自外周的痛覺信號,同時也從外側下丘腦間接接受來自脊髓的投射纖維[22]。此外,外側韁核也接受來自其他與痛覺緊密關聯核團的信息,如中腦中央灰質和VTA,同時傳出投射至中縫核等疼痛調節區域[23]。電生理實驗發現,傷害性刺激可興奮外側韁核,而局部注射利多卡因抑制外側韁核神經元的放電活動有鎮痛作用[24]。以上證據表明,機體受到疼痛刺激后外側韁核神經元可被激活,而抑制外側韁核的放電活動可以減輕疼痛感。此外,外側韁核高表達μ阿片受體,給予局部激活可減輕疼痛[25];局部注射嗎啡也可減少韁核釋放興奮性神經遞質,抑制放電活動產生鎮痛作用[24,26]。同時,注射阿片類受體拮抗劑納洛酮可抑制在中腦中央灰質內注射嗎啡所產生的鎮痛作用;伏隔核內注射納洛酮也可減弱韁核內注射嗎啡所產生的鎮痛作用[27],說明韁核在從伏隔核至中腦中央灰質的痛覺下行調控系統中具有積極的調節作用。同時,外側韁核可通過RMTg投射至VTA,VTA又可通過蒼白球投射至外側韁核,進而形成另一個反饋調節環路,表明韁核在鎮痛過程中起重要作用。
在功能學上,嗎啡對韁核神經元存在雙向調節作用。在體電生理實驗發現,部分韁核神經元被周圍疼痛刺激興奮的同時也有部分被抑制[28]。對給予疼痛刺激后的外側韁核進行c-fos免疫組織化學染色,發現外側韁核內c-fos表達顯著增加;同時在外側韁核內由牙髓痛導致的c-fos表達可被嗎啡鎮痛抑制[29]。另一方面,加入μ阿片受體選擇性激動劑(D-Ala2,N-Me-Phe4,Gly5-ol)-腦啡肽既可減少突觸前谷氨酸的釋放從而抑制部分韁核神經元,又可抑制突觸前的γ-氨基丁酸釋放激活部分韁核神經元[29]。因此,這種雙向調節被認為是由于韁核神經元的興奮性輸入和抑制性輸入之間的平衡被打破所致。
3 韁核在精神疾病中的作用
除了正常行為中的生理功能,韁核在精神疾病的病理生理學中也起重要作用。
3.1抑郁癥 抑郁癥是與韁核有關的一個常見精神疾病,發病率逐年升高,其發生機制與海馬和前額葉皮質等相關[30]。基于對抑郁癥嚙齒動物模型的大量研究,人們開始探索外側韁核與抑郁癥的關系,提出了改善外側韁核內的適應不良可能是治療抑郁癥狀的潛在方法[31-32]。以人類韁核為靶點的腦深部刺激的臨床研究也在進行中,腦深部刺激治療抑郁癥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已在一些臨床試驗和臨床前研究中得到證實,但目前關于韁核功能障礙導致抑郁狀態的理論并不能完全解釋所有觀察結果[33-35]。
有研究顯示,在健康群體中給予腳部電擊的條件刺激,韁核活性增強,但在抑郁癥患者中結果相反,提示抑郁癥患者韁核發生了功能紊亂[36];同時發現外側韁核是抑郁狀態動物的全腦成像中唯一活性增強的腦區[37]。賈曉寧等[6]在這一研究方向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提出外側韁核的神經元活動是抑郁情緒的來源,抑郁的發生與β-鈣調蛋白激酶Ⅱ有關,其在外側韁核過表達時表明多巴胺系統受到抑制。
針對抑郁的分子機制,賈曉寧等[6]發現韁核抑制下游獎賞中心的簇狀放電是由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介導,而氯胺酮作為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阻斷劑阻斷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抑制簇狀放電,有效逆轉其對獎賞中心的抑制,呈現抗抑郁效果。同時,通過高通量定量蛋白質譜技術發現外側韁核神經元的突發性放電模式依賴于這些神經元靜息膜電位的變化,而靜息膜電位的變化又是由于致密包裹這些神經元的星形膠質細胞中鉀離子通道Kir4.1的表達水平發生變化。外側韁核膠質細胞中β-鈣調蛋白激酶Ⅱ和Kir4.1過表達可引起神經元細胞外鉀離子濃度降低,神經元細胞超極化,T型鈣離子通道激活,最終導致由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介導的韁核神經元簇狀放電[5]。
在動物實驗中,通過腦深部電刺激或化學抑制劑和藥物等方式靶向調節外側韁核活動能有效減少抑郁樣行為[38],但目前腦深部電刺激的臨床試驗較少。由于腦深部電刺激的機制依賴于刺激部位而抑郁癥的神經病理學尚不明確,腦深部電刺激治療抑郁癥仍被視為一種實驗性療法[34-35]。
為了構建一個更完整的理論體系,有研究通過視網膜傳遞的非侵入性光療法來調節外側韁核活動[39]。除多巴胺系統外,5-羥色胺與抑郁發病機制也有密切關系。有研究發現在抑郁大鼠模型中,除外側韁核外,內側韁核神經元的放電活動也明顯增加,通過釋放P物質興奮腳間核神經元[40];抑郁大鼠模型中,中縫核的5-羥色胺基礎釋放水平低于正常大鼠,損毀外側韁核后中縫核的5-羥色胺水平升高,大鼠的抑郁癥狀減輕[41],證明內側韁核神經元的高興奮性與抑郁癥相關。內側韁核高表達磷酸二酯酶2,磷酸二酯酶2抑制劑可改善應激所誘導的抑郁癥狀[42],提示內側韁核中磷酸二酯酶2可作為抑郁癥的治療靶點。
3.2精神分裂癥 精神分裂癥是臨床常見的與韁核有關的一類慢性精神疾病,主要表現為思維、情感、感知覺和行為異常。韁核的病變和功能紊亂可影響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認知障礙,導致類精神分裂癥癥狀的出現和發展。雖然臨床研究中對于精神分裂癥患者韁核體積變化的結果不統一[43-44],但與正常人相比,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韁核的鈣化更常見[45],且患者腦內血管密度選擇性地在韁核內降低[46],同時相應出現第三腦室擴大。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的韁核活性也發生改變,正常受試者在完成匹配任務時發生錯誤并被給予錯誤反饋后韁核被激活,而精神分裂癥患者的韁核無明顯激活[47]。同時,韁核損傷的大鼠表現出工作記憶、注意力的缺陷等類似于精神分裂癥的認知功能障礙[48]。大量研究提示,精神分裂癥患者的韁核病變可導致VTA和SNc中的多巴胺能神經元難以獲取來自韁核的抑制信號,最終導致患者在學習和認知中存在缺陷[44-48]。作為與精神分裂癥病情嚴重程度有重要結構,韁核有望成為其臨床輔助診斷的生物標志物。
3.3藥物成癮 成癮是一種認知性的大腦障礙,往往從娛樂或自愿最終發展為厭惡性的強迫性使用。在長期接觸濫用藥物后,韁核及其后屈束在中樞神經系統中受損最顯著;對于長期接觸可卡因造成的退行性病變,韁核及其后屈束也是中樞神經系統中受損的唯一部位[49]。因此,韁核被認為是濫用藥物損害中樞神經系統的最薄弱部分,也提示韁核活動的改變是導致對濫用藥物的使用失去控制和出現強迫性吸食行為的重要因素。
越來越多的可卡因覓藥行為研究發現,外側韁核或RMTg的失活會極大地損害對可卡因的條件性回避,而外側韁核神經元及其在RMTg中的靶點被負性刺激激活[50-51]。覓藥行為的強度與外側韁核神經元呈雙向反應:初吸食可卡因會使VTA大量釋放多巴胺到NAc,使大鼠對可卡因成癮而主動吸食和復吸,此時抑制外側韁核放電會增加這種行為,刺激外側韁核則使之顯著減少[52];后續吸食則反而會增加外側韁核神經元放電活動,抑制VTA釋放多巴胺,對可卡因產生厭惡[53]。可卡因激活外側韁核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對外側韁核神經元的直接作用,反復吸食可卡因后可選擇性增加外側韁核神經元中α-氨基-3-羥基-5-甲基-4-異唑丙酸受體的數量,增強其興奮傳遞,通過RMTg途徑實現對VTA多巴胺神經元的抑制[54]。
另有研究表明,可卡因戒斷期間腳內核到外側韁核的投射纖維神經末梢釋放γ-氨基丁酸減少,外側韁核神經元活化;增加釋放γ-氨基丁酸則可抑制神經元興奮并能防止復吸[55]。研究發現單次注射可卡因可誘導外側韁核投射腳內核喙部神經元的c-fos 表達[56]。此外,接受腳內核喙部輸入的外側韁核神經元投射到RMTg而不是VTA[50],而可卡因在部分腳內核神經元中產生與外側韁核和RMTg神經元中類似的雙相反應[57]。提示腳內核喙部、外側韁核和RMTg之間的串聯連接在編碼可卡因的厭惡效應中起關鍵作用,提供了預防成癮靶點的新選擇。
內側韁核與藥物成癮機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尼古丁的成癮和戒斷。內側韁核和腳間核均廣泛表達乙酰膽堿受體,內側韁核具有腦中最高密度的煙堿型乙酰膽堿受體亞單位,尤其是α3、α5和β4亞單位[58],是中樞神經系統主要的膽堿能通路來源,并通過后屈束纖維束支配腳間核神經元,尼古丁乙酰膽堿投射通路即內側韁核到腳間核的膽堿能投射[59]。研究表明,尼古丁通過活化煙堿型乙酰膽堿受體的α5亞單位增強內側韁核神經元的內在興奮性,從而促進神經激肽釋放,神經激肽-1和神經激肽-3受體活化,導致尼古丁戒斷的軀體癥狀[60]。此外,缺乏α5亞單位的小鼠暴露于尼古丁后腳間核活性顯著降低[61],表明在內側韁核-腳間核通路中,α5亞單位可有助于確定尼古丁能促進大腦獎賞回路活動的劑量范圍。同時,煙堿型乙酰膽堿受體的β4亞單位對尼古丁攝入量的影響與α5亞單位相似[59],增強β4介導的煙堿型乙酰膽堿受體電流會增加小鼠對尼古丁的厭惡,相反則會減弱對尼古丁的厭惡。這些發現進一步支持了內側韁核-腳間核途徑控制尼古丁回避行為的假設,強調了含α5和β4的煙堿型乙酰膽堿受體作為新型戒煙目標的潛在重要性。除尼古丁外,內側韁核-腳間核通路可能不是大多數精神運動興奮劑的直接藥理學靶點,但它可能代表了一個急性調節精神運動興奮劑的系統,并有助于發出潛在的戒斷和復發信號。
4 小 結
韁核是背側間腦傳導系統聯系邊緣前腦與中腦、后腦的重要中繼站,參與一系列生命活動,韁核的紊亂直接影響抑郁癥、精神分裂癥等精神疾病。內側韁核是一個重要的膽堿能核團,與尼古丁等藥物成癮有關。外側韁核直接調控多巴胺、5-羥色胺、去甲腎上腺素能系統,參與獎賞與懲罰、焦慮與抑郁等活動調節。目前在臨床上外側韁核已成為治療抑郁癥的新靶點,在神經病理性疼痛的鎮痛、藥物成癮的減輕、毒品戒斷、精神分裂癥的治療等中也發揮重要作用。而未來關于藥物影響韁核活性的機制以及逆轉濫用藥物對韁核神經元損害的方法仍需要進一步研究,為確定特異性靶點和研制新的治療藥物提供可靠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