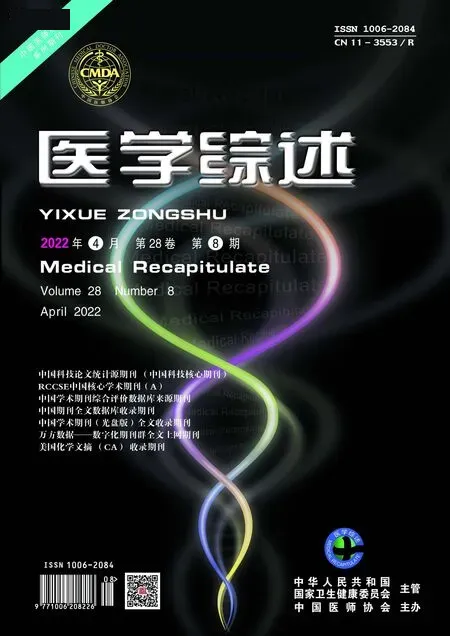外泌體介導微RNAs在骨肉瘤中的作用與應用
任偉,郭世炳,徐翔,王亞超,劉曉強,趙偉,王紫橫,王玉鑫,李宇
(1.內蒙古醫科大學,呼和浩特 010000; 2.內蒙古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 a.骨腫瘤科,b.微創脊柱外科,c.麻醉手術科,呼和浩特 010030)
骨肉瘤是臨床最常見的原發性惡性骨腫瘤,其發生率約占惡性骨腫瘤的60%[1-2]。骨肉瘤常見于5~20歲的兒童和青少年及70歲以上老年人血運豐富的干骺端,如肱骨近端、股骨遠端和脛骨近端[3]。骨肉瘤極易發生遠處血行轉移,約80%的骨肉瘤患者術后最終發生遠處轉移[4],繼發性肺癌是骨肉瘤患者病死的主要原因[5]。目前臨床外科醫師多采用術前化療、手術切除病灶和術后化療等方法治療骨肉瘤,但是患者5年生存率也僅有60%~70%,骨肉瘤患者的預后仍很差[6-7]。化療藥物的耐藥性、腫瘤復發及轉移等問題嚴重影響骨肉瘤患者的預后[8-9]。迄今為止,調控骨肉瘤轉移過程的因素和途徑尚不清楚。
近年來,眾多學者從骨肉瘤患者的體液中發現并提取出攜帶有各種核酸、蛋白質和脂類的微囊泡,微囊泡中含有大量的外泌體,而外泌體又攜帶多種微RNAs(microRNAs,miRNAs),其可以充當細胞間通信的關鍵信使。而且腫瘤細胞釋放的外泌體量遠高于其他正常細胞,腫瘤釋放的外泌體miRNAs可以介導腫瘤微環境中的細胞表型變化,促進腫瘤生長[10]。因此,外泌體介導的miRNAs可能參與了骨肉瘤的發生發展、侵襲轉移、化療耐藥等過程。此外,研究發現腫瘤細胞與正常細胞外泌體中的miRNAs表達譜有明顯差異[11];同時,Xu等[12]研究發現骨肉瘤中含有差異表達的miRNAs。因此,外泌體miRNAs在未來可能被作為骨肉瘤診斷、治療和預后評估的生物標志物。現通過詳細介紹骨肉瘤、外泌體以及外泌體miRNAs與骨肉瘤相關性的最新研究進展,進一步明確外泌體miRNAs與骨肉瘤之間的聯系,同時為骨肉瘤的治療提供更多新思路。
1 外泌體
外泌體是在電鏡下呈杯狀或茶托狀的直徑為40~100 nm的雙層脂質胞外囊泡[13]。然而與其他胞外囊泡不同,外泌體是細胞內多泡體中的小囊泡與細胞膜融合后通過胞吐作用釋放至胞外微環境中而形成。外泌體最初于20世紀80年代由Nelson和Veshnock[14]在綿羊網織紅細胞體外培養中發現。2007年,Valadi等[15]首次證實外泌體中包含有功能性信使RNA(messenger RNA,mRNA)和miRNA,被稱為“外泌體穿梭RNA”,可以轉移到其他細胞并發揮作用。隨著研究方法和技術的發展,人們現在已經認識到外泌體是一種新的細胞間通信物質,并在健康和疾病的廣泛生物學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外泌體來源于各種細胞[16-17],并且存在于血液、尿液、腦脊液等體液中,可通過非侵入性途徑獲取。此外,其還參與機體的生理與病理過程。
外泌體來源于內吞途徑[18]。典型的外泌體形成經歷了多個過程,如細胞質膜內陷形成早期的分泌型內體、多囊泡體形成、內體通過酸化成熟,通過與質膜融合,最終將多囊泡體作為外泌體釋放到細胞外。同時研究發現,核內體分選復合體機制在多囊泡體的生物過程中起重要作用[19]。外泌體內成分非常豐富,包括9 769個蛋白質,3 408個mRNA,2 838個miRNAs和1 116個脂質。其成分可作為自分泌和(或)旁分泌因子,包括特定的脂質、蛋白質、DNA、mRNA和非編碼RNA。這些外泌體的成分可作為腫瘤診斷、預后標志物和癌癥進展分級的基礎。它還可調節腫瘤的生長、轉移、血管生成,并介導腫瘤細胞的耐藥性[20]。在骨肉瘤的發生發展過程中,miRNAs被骨肉瘤細胞通過外泌體傳遞途徑遞送至其他靶細胞中,一起參與細胞間信息交流。miRNAs作為長度在20~22個核苷酸之間的小型非編碼RNA的重要成員,通過與靶mRNA的3′非翻譯區或開放閱讀框結合,介導翻譯或降解mRNA,從而起到靶向調控腫瘤發生發展和診治預后的作用。此外,外泌體可作為骨肉瘤新的治療物質,并可作為標志物用于骨肉瘤的臨床診斷、藥物載體、治療靶點和預后監測。廣泛的應用價值使其近年來成為骨肉瘤診治的研究熱點。
2 外泌體介導miRNAs在骨肉瘤中的作用
腫瘤微環境為骨肉瘤的發生和發展提供必要的生長和生存環境。骨肉瘤細胞通過不同的方式調節腫瘤微環境內的通信,其中腫瘤來源的外泌體支持腫瘤的進展和轉移,Raimondi等[21]研究發現了其在骨重建機制和腫瘤血管生成中的誘導作用,同時證明外泌體可以促進破骨細胞分化和骨吸收活性。此外,外泌體還可促進內皮細胞的管狀形成,增加血管生成標志物的表達。外泌體源性miRNAs參與了腫瘤微環境的構建。因此,外泌體miRNAs可能在骨肉瘤的發生發展、侵襲轉移、化療耐藥及免疫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2.1外泌體介導miRNAs參與骨肉瘤發生發展 外泌體是腫瘤微環境中細胞間通信信號和遺傳物質的重要載體。在腫瘤發生過程中,腫瘤細胞通過外泌體與免疫細胞、內皮細胞和相關成纖維細胞等相互作用,從而促進腫瘤的發生發展。通過改變周圍微環境,外泌體驅動腫瘤細胞增殖,加速血管生成,并促進腫瘤細胞伴隨著體液運輸。攜帶miRNAs的外泌體可引起受體細胞活性和功能的改變,如促進破骨細胞分化和骨吸收活性,促進血管形成和內皮細胞生長,從而上調血管生成標志物的表達。研究表明,miR-21可顯著影響癌細胞的可塑性,導致腫瘤轉移和血管生成,并參與腫瘤免疫調節[22]。骨肉瘤細胞分泌的外泌體攜帶的miR-148a和miR-21-5p可參與腫瘤微環境的建立,刺激內皮細胞分泌更多的血管生成因子并形成管狀結構,對于破骨細胞表型和內皮細胞活性的改變非常重要[22]。此外,性別決定區相關高遷移率族蛋白4可以被miR-25-3p靶向調控,Wu等[23]研究發現miR-25-3p通過靶向骨組織中性別決定區相關高遷移率族蛋白4的表達,抑制骨肉瘤細胞的增殖、遷移和侵襲,從而發揮抑制骨肉瘤的作用。Yoshida等[24]的研究表明,將miR-25-3p嵌入骨肉瘤細胞來源的外泌體可促進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和毛細血管形成。上述研究顯示,外泌體miRNAs與骨肉瘤的增殖及凋亡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2.2外泌體介導miRNAs參與骨肉瘤侵襲轉移 在腫瘤微環境中,來自骨肉瘤和骨髓細胞的外泌體可以通過尿激酶型纖溶酶原激活物依賴的信號通路在體外和體內特異性地促進骨肉瘤細胞的遷移[25]。腫瘤細胞分泌的外泌體通過調節腫瘤微環境促進腫瘤生長、轉移和血管生成,并可逃避宿主免疫監視[26]。此外,基質外泌體可以誘導骨肉瘤細胞獲得癌變表型,García-Silva和Peinado[27]發現癌細胞來源的外泌體可以影響骨肉瘤細胞的增殖、遷移、耐藥性和上皮-間充質轉化。研究表明,腫瘤相關成纖維細胞可以將攜帶miR-1228的外泌體轉移到骨肉瘤細胞,導致骨肉瘤細胞侵襲抑制因子表達降低,從而促進骨肉瘤細胞的遷移和侵襲[28]。腫瘤細胞分泌的外泌體不僅可以為骨肉瘤轉移營造適宜的微環境,還有助于間充質干細胞的腫瘤樣轉化。當干細胞被募集到腫瘤基質中時,腫瘤外泌體進入干細胞并誘導其獲得惡性表型,反過來,干細胞分泌外泌體以促進骨肉瘤細胞增殖、遷移和侵襲[29]。Zhao等[30]研究表明,骨髓間充質干細胞外泌體包裹漿細胞瘤變異易位基因1(一種致癌物)并將其轉運至骨肉瘤細胞,進而促進骨肉瘤生長和轉移。Qi等[31]進一步研究發現,間充質干細胞外泌體促進骨肉瘤細胞生長和遷移的機制可能涉及Hedgehog信號通路和白細胞介素-6/信號轉導及轉錄活化因子3信號通路的激活。此外,Huang等[32]的研究表明骨髓間充質干細胞外泌體可通過促進骨肉瘤細胞的自噬,從而促進骨肉瘤細胞的增殖、遷移和侵襲;進一步研究發現,在骨肉瘤細胞中沉默自噬相關基因5可以減弱人骨髓間充質干細胞外泌體促進骨肉瘤細胞增殖、遷移的作用。總之,腫瘤微環境中的外泌體miRNAs是骨肉瘤生長和轉移的關鍵因素。Qin等[33]發現,miR-208a通過下調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4和激活胞外信號調節激酶1/2通路,從而促進骨肉瘤細胞增殖、遷移和轉移。Gong等[34]研究發現,miR-675促進骨肉瘤細胞發生肺轉移。同時進一步的研究表明,與非轉移性MG63細胞(骨肉瘤細胞的一種)來源的外泌體相比,轉移性MG63細胞來源的外泌體誘導受體成骨細胞遷移和侵襲作用增強。Jerez等[35]使用miRNA測序技術發現,骨肉瘤細胞外泌體微囊泡中數量最多的miRNAs是miR-21-5p、miR-143-3p、miR-148a-3p和miR-181a-5p,它們在轉移性人骨肉瘤細胞SAOS2來源的微囊泡中的豐度是非轉移性MG63成骨樣細胞的3~100倍,同時發現微囊泡中的miRNAs可能通過調節細胞凋亡、細胞相關基因網絡,進而影響細胞遷移和黏附來調節骨肉瘤細胞侵襲遷移。綜上,骨肉瘤細胞具有高度侵襲性和轉移作用,而外泌體miRNAs可以通過影響腫瘤微環境及相關信號轉導通路,進而影響骨肉瘤的侵襲和轉移。
2.3外泌體介導miRNAs參與骨肉瘤化療耐藥 近30年來,盡管骨肉瘤臨床治療方法和新輔助化療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仍有許多骨肉瘤患者對治療藥物的反應較低,這是導致骨肉瘤患者發生遠處轉移及預后不良的主要原因。目前臨床上治療骨肉瘤的多藥化療方案包括阿霉素、順鉑、甲氨蝶呤和異環磷酰胺,使患者的5年總生存率維持在60%~70%。然而,耐藥性是導致治療失敗的主要原因,獲得性多藥耐藥的發生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骨肉瘤耐藥機制尚未完全闡明,是由多水平、多因素、多基因和信號通路參與調控的復雜過程。研究表明人骨肉瘤細胞系中P-糖蛋白的過表達與多藥耐藥相關,是骨肉瘤產生耐藥的重要因素。如Torreggiani等[36]研究發現,含有多藥耐藥-1 mRNA及其產物P-糖蛋白的外泌體使得先前對阿霉素敏感的細胞產生了化療抵抗,同時發現阿霉素耐藥骨肉瘤細胞的外泌體可被周圍細胞吸收,從而誘導出阿霉素耐藥細胞表型。
隨著對miRNAs的深入研究,許多研究證實了miRNAs參與骨肉瘤耐藥。Chen等[37]研究發現,這些致癌或腫瘤抑制因子miRNAs通過DNA損傷、細胞凋亡逃逸、自噬誘導、腫瘤干細胞活化、信號通路改變等機制在化療敏感性中發揮作用。研究發現,骨肉瘤組織miR-22表達水平較正常骨組織以及化療后的骨肉瘤細胞中miR-22水平下調[38]。所以,miR-22在骨肉瘤發生和化療耐藥中發揮重要作用。之前許多研究集中于細胞miRNAs,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腫瘤傳遞系統,其臨床應用受到限制。miRNAs也存在于細胞外,包括血液和其他體液。由于miRNAs可以被外泌體包裹,隨著外泌體主動進出細胞。因此,來自耐藥腫瘤細胞的外泌體作為一種信息傳遞的介質及其調控腫瘤細胞-微環境細胞間相互作用,可以將特定的miRNAs分子傳遞到藥物敏感的腫瘤細胞并促進其耐藥性[39]。Mao等[40]研究發現,外泌體通過傳遞miRNAs降低乳腺癌細胞對阿霉素的敏感性,所以外泌體很可能通過內源性或細胞特異性途徑調控耐藥性,通過排出藥物和負責藥物代謝的功能性miRNAs/RNAs傳遞給受體細胞,使其對藥物產生耐藥性。總之,不論哪種情況,外泌體均能很好地調控腫瘤微環境,從而形成治療上的異質性腫瘤表型。迄今為止,有關外泌體介導的分子在骨肉瘤耐藥性中的研究較少。Yoshida等[24]研究發現,骨肉瘤耐藥與外泌體中miR-25-3p的上調有關。Xu等[41]通過比較化療反應不良與反應良好的骨肉瘤患者血清外泌體中miRNAs發現有12個miRNAs上調和18個miRNAs明顯下調。他們在骨肉瘤順鉑耐藥細胞分泌的外泌體對骨肉瘤敏感細胞的增殖及耐藥性影響的最新研究中,觀察到MG63成骨樣細胞和順鉑耐藥MG63成骨樣細胞均可分泌外泌體。外泌體miRNA測序和生信分析篩選發現,耐藥株細胞外泌體中miRNAs表達上調的是miR-16、miR-101、miR-233、miR-152、miR-181、miR-590、miR-1271、miR-224、miR-183、miR-145;而miR-22表達下調。綜上所述,目前有關外泌體miRNAs及其多藥耐藥調控在骨肉瘤耐藥性的作用和機制研究甚少。希望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可以有更多關于外泌體miRNAs在骨肉瘤化療耐藥機制中的研究,從而為骨肉瘤患者的治療帶來新希望。
3 外泌體介導miRNAs在骨肉瘤中的應用
骨肉瘤是一種高度惡性的骨腫瘤,現有的治療手段仍不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患者的預后仍不理想。找到能夠早期監測骨肉瘤病變的高敏感性及高特異性生物標志物依然是目前骨肉瘤臨床亟須解決的科學難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報道miRNAs在外泌體中為差異性表達。因此,外泌體介導的miRNAs可以作為骨肉瘤診斷、治療及預后評估的重要生物標志物。
3.1外泌體介導miRNAs參與骨肉瘤臨床診斷 缺乏早期特異性的診斷與有效的治療是骨肉瘤患者5年生存率低、預后較差的一個重要原因。目前,骨肉瘤的主要診斷方法是根據臨床表現、X線表現以及組織病理活檢。而早期的臨床表現往往不典型;X線表現缺乏特異性,且容易漏診早期病變;組織病理活檢為有創檢查,且骨肉瘤患者就診時往往是腫瘤進展階段,活檢并不能對疾病的早期診斷與治療提供實質性幫助。骨肉瘤外泌體miRNAs可以穩定存在于人體體液,同時存在差異性的表達,其檢測具有微創、精準等優勢,因此越來越多地被用于骨肉瘤的早期診斷。Xu等[12]研究發現,骨肉瘤患者血清和血漿中外泌體miR-21的表達遠高于健康對照者,表明miR-21可以作為骨肉瘤的生物標志物。Ye等[42]通過高通量測序分析發現,骨肉瘤患者外泌體中miR-92a-3p、miR-130a-3p、miR195-3p、miR-335-5p和let-7i-3p的表達水平高于健康對照者。體外和體內研究表明,骨肉瘤細胞外泌體中的miR-195-3表達上調,從而促進腫瘤細胞增殖和侵襲。該實驗結果驗證了血漿中骨肉瘤細胞外泌體miRNAs可以作為新的診斷生物標志物,并可能為骨肉瘤治療提供新的選擇。Fujiwara等[43]成功證實血清外泌體miR-25-3p可作為骨肉瘤患者腫瘤監測的生物標志物。該方法作為一種非侵入性診斷策略,將為骨肉瘤的早期診斷及早期治療提供新思路和有力證據。綜上所述,外泌體miRNAs為差異性表達,將為骨肉瘤的特異性診斷與早期治療提供新思路。
3.2外泌體介導miRNAs參與骨肉瘤的治療 目前臨床針對骨肉瘤患者的治療方案為術前化療、手術切除病灶和術后化療。但化療耐藥性使得骨肉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仍較低,治療后復發、轉移的難題依舊困擾著骨腫瘤科醫師。外泌體miRNAs影響骨肉瘤細胞的增殖、侵襲、遷移。因此,其在骨肉瘤的治療中也勢必會扮演重要的角色。
目前,miRNAs被認為是一種潛在的抗癌藥物。然而,傳統的傳遞性miRNAs、蛋白質和化療藥物等方法通常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外源性miRNAs在體內很容易被降解,外源蛋白由于缺乏天然構象而不能發揮所需的功能,使用化療藥物會對機體產生許多不良反應。然而,使用外泌體作為載體可以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外泌體是一種生物相容性高、免疫原性低、給藥效率高的藥物傳遞媒介。Shimbo等[44]評估了通過外泌體將合成的miRNAs導入骨肉瘤細胞以降低其致病性,通過誘導間充質干細胞中miR-143的表達,該miRNAs被轉移到骨肉瘤細胞中,在不影響體外增殖率的情況下降低了骨肉瘤細胞的遷移能力。Wei等[45]開發了一種由阿霉素和間充質干細胞外泌體組成的納米藥物,與單獨使用阿霉素相比,制備的納米藥物在MG63骨肉瘤細胞中表現出更高的給藥效率和抗腫瘤作用,能有效殺滅骨肉瘤細胞。Kim等[46]研究發現,抗有絲分裂化療藥物紫杉醇可以通過超聲波加載到外泌體中,這些裝載的外泌體對體外耐藥癌細胞的細胞毒性是游離紫杉醇的50倍。此外,與直接給藥相比,基于外泌體的給藥可以大大減少化療藥物對機體的不良反應。化療是骨肉瘤的主要輔助治療手段,但患者嚴重的全身化療不良反應依舊是難以解決的問題。然而,外泌體可以通過輸送適量的化療藥物來抑制腫瘤,極大地減輕患者的痛苦,同時與其他人工載體相比,外泌體作為化療藥物的天然載體,可以防止巨噬細胞吞噬,從而延長化療藥物的半衰期[47-48]。間充質干細胞外泌體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焦點,其可以保護所攜帶的物質免受細胞外降解,并將遺傳物質、免疫調節蛋白、酶和生長因子等直接運送到受體細胞[49]。Abello等[50]將人臍帶間充質干細胞外泌體注射到骨肉瘤小鼠體內,在注射后1~2 d內,人臍帶間充質干細胞外泌體在腫瘤細胞內持續積聚,并在較低劑量下便可起到治療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減少化療藥物的不良反應。
3.3外泌體介導miRNAs可用于骨肉瘤的預后評估 通過監測骨肉瘤細胞分泌的外泌體中miRNAs水平差異,可以預測細胞對化療的反應。Xu等[41]發現,在有化療不良反應的骨肉瘤患者中,miR-124、miR-133a、miR-199a-3p和miR-385的表達下降,而miR-135b、miR-148a、miR-27a和miR-9的表達上調。這些外泌體miRNAs可以作為區分不同化療敏感性骨肉瘤的可靠生物標志物。Zhou等[51]研究發現,在預后不良的骨肉瘤患者中有22種外泌體miRNAs上調。Liu等[52]研究發現,miR-1258在骨肉瘤組織和骨肉瘤細胞系中的表達顯著降低,并與骨肉瘤患者的惡性臨床表現和不良臨床預后呈正相關,miR-1258上調可顯著抑制細胞增殖;進一步的研究發現,miR-1258可使骨肉瘤細胞發生G0/G1期阻滯,而且蛋白激酶3(位于第1號染色體的基因)被確定為miR-1258的直接靶點,它與蛋白激酶3 mRNA的3′非翻譯區結合。因此,miR-1258-蛋白激酶3軸可能是一個很有前途的骨肉瘤預后標志物和治療靶點。綜上所述,外泌體miRNAs與骨肉瘤的預后相關,其可以作為生物標志物參與骨肉瘤患者的預后評估,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
現有證據表明,基于外泌體miRNAs在靶向骨肉瘤治療中具有巨大的潛力與廣闊的前景。然而,在miRNA和靶mRNA之間并沒有“一對一”的聯系,一個miRNAs可以有多個靶點,一個mRNAs也可以被多種miRNAs調控。目前對miRNAs靶點的研究還不完善,其中一些潛在靶點在骨肉瘤進展中的作用尚不清楚。關于外泌體用于基因治療的靶向作用還不清楚。未來,需要開展進一步的研究來確定miRNAs的靶標及其在骨肉瘤中的作用。
4 小 結
外泌體作為細胞間的通信分子,在骨肉瘤的發生發展、侵襲轉移和化療耐藥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時在骨肉瘤的臨床診斷、治療、預后評估中發揮重要作用。但迄今為止,大多數研究是從血清中提取外泌體。然而,許多研究人員已經開始專注于非侵入性途徑如唾液和尿液獲取樣本,今后應開發更多新的非侵入性途徑,如陰道分泌物、糞便或淚水獲取外泌體。此外,外泌體的具體功能和機制尚未完全了解,外泌體長期治療的安全性也無法預測。所以,未來應著重對外泌體治療骨肉瘤的安全性、有效性、內在成分和機制進行研究,以期為外泌體的臨床應用提供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