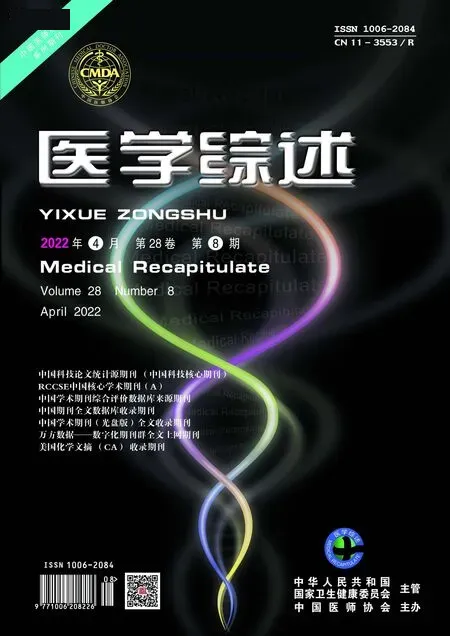口腔白斑癌變相關因子研究進展
馬雅君,宋國華,張芳
(山西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 口腔醫院黏膜科 山西省口腔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太原 030001)
口腔白斑是發生在口腔黏膜上以白色為主的損害,不能擦去,也不能以臨床和組織病理學方法診斷為其他可定義的損害,屬于癌前病變,是口腔鱗狀細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OSCC)的重要來源之一,近年來發病率呈上升趨勢,為0.69%~2.03%,癌變率高達5.9%~14%[1-2]。從病理學角度看,口腔白斑的發生伴隨上皮過角化和上皮增生,當上皮異常增生時癌變風險隨異常增生程度的增加而增加[3]。從分子學角度看,口腔白斑的發生主要與異常的細胞周期、細胞增殖、DNA損傷修復和凋亡等有關[2,4]。
口腔白斑目前尚無理想的治療方法,主要采用藥物治療和去除病損的治療。治療藥物主要有維生素A類藥物、環加氧酶2和表皮生長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受體抑制劑、β-胡蘿卜素及非甾體抗炎藥等,但不良反應大,安全性低;去除病損的治療包括手術、激光、冷凍和光動力療法,但都存在繼發癌變和復發可能,癌變率分別為7%、4.9%、5.4%和7.5%,復發率分別為25%、24%、16%和11.6%,且復發也是惡性轉化的指標之一[1]。目前沒有可靠的方法評估癌變風險,迫切需要研究預測指標,有些指標早已被大家認可,如細胞周期蛋白、p53和環加氧酶,而有些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如平足蛋白、程序性細胞死亡受體1(programmed cell death receptor 1,PD-1)等。因此,明確癌變原因將有助于評估口腔白斑的病情和制訂治療方案。
1 與細胞周期相關的因子
1.1細胞周期蛋白 細胞周期蛋白是一個蛋白質家族,包括G1期細胞周期蛋白和M期細胞周期蛋白,依賴細胞外有絲分裂信號,調節多種細胞過程,如轉錄、翻譯和蛋白質的穩定性等[5]。細胞周期蛋白D1屬于G1期細胞周期蛋白,通過結合并激活細胞周期蛋白依賴性激酶(cyclin-dependent kinase,CDK)4和CDK6,控制細胞的黏附、遷移和轉移,調節細胞從G1期進入S期。在口腔白斑和OSCC中的表達逐漸增加,與細胞周期蛋白D1大量擴增有關,參與細胞增殖、分化和阻止細胞凋亡[6]。p16可與細胞周期蛋白D1競爭同CDK4的結合,使CDK4/細胞周期蛋白復合物活性受到抑制,細胞分裂生長受阻[7]。視網膜母細胞瘤蛋白基因可在G1期被細胞周期蛋白-CDK磷酸化后變成磷酸化視網膜母細胞瘤蛋白,促進S期所必需的細胞周期蛋白、CDK的轉錄,使細胞從G1期進入S期[8]。
細胞周期蛋白A2屬于M期細胞周期蛋白,與DNA復制和有絲分裂進入有關,其與CDK2結合,參與激活位于S/G2期過渡區的有絲分裂激酶Polo樣激酶1,是S期DNA合成以及通過G2/M期過程所必需的[9]。p53蛋白可促進p21(CDK2的抑制劑)的表達,抑制G1/S期的轉換并調節G2/M期,導致細胞周期停滯[10]。在口腔癌前病變和惡性病變中高表達,與疾病復發、淋巴結轉移和臨床分期等相關[6]。
因此,某些細胞周期蛋白在口腔白斑癌變過程中可能發揮重要作用,早期檢測可作為治療靶點,且細胞周期蛋白A2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預測復發。
1.2甲狀旁腺激素樣激素(parathyroid hormone-like hormone,PTHLH) PTHLH是一種細胞因子,以自分泌或旁分泌的方式編碼少數正常組織和多種腫瘤細胞分泌的甲狀旁腺激素相關蛋白,在包括OSCC的多種腫瘤組織中過表達,影響細胞周期相關蛋白的表達,改變細胞周期,調節細胞生長,與預后不良相關。PTHLH在口腔白斑中過表達,導致細胞周期蛋白D1和CDK4的下調及p21的上調,且口腔白斑伴PTHLH過表達時更容易癌變,當下調口腔白斑細胞中PTHLH的表達后,細胞周期、細胞增殖、遷移、侵襲和集落形成能力明顯降低,與上皮異常增生程度有關[11],PTHLH可能是預測口腔白斑癌變的標志物之一。
2 與細胞增殖相關的因子
2.1分化型胚胎軟骨發育基因1 分化型胚胎軟骨發育基因1是一種轉錄因子,參與細胞增殖、凋亡、缺氧及上皮-間充質轉化等過程,與人類多種癌癥相關[12]。在正常口腔黏膜(normal oral mucosa,NOM)、口腔白斑和OSCC組織中的表達隨惡性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且在口腔白斑伴上皮異常增生中的表達也高于不伴上皮異常增生者[13]。因此,分化型胚胎軟骨發育基因1的不同表達在一定程度上可評估口腔白斑惡性轉化的風險。
2.2B細胞淋巴瘤濾過性病毒插入位點1 B細胞淋巴瘤濾過性病毒插入位點1是一種轉錄因子,在多種腫瘤組織中過表達,通過激活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3-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PKB/Akt)信號通路,誘導上皮-間充質轉化并促進腫瘤細胞的增殖、侵襲和轉移,阻止細胞凋亡,在NOM、口腔白斑和OSCC中的陽性率逐漸增高,與基質金屬蛋白酶9和p16的表達分別呈正相關和負相關,與細胞增殖有關,可作為口腔白斑癌變標志物之一[14-15]。因此,B細胞淋巴瘤濾過性病毒插入位點1可影響細胞周期、凋亡、上皮-間充質轉化及腫瘤轉移等,在一定程度上可評估癌變風險。
2.3EGF受體 EGF受體屬于受體酪氨酸激酶家族,其可調節上皮組織發育和體內平衡,頭頸部鱗狀細胞癌的發生發展與吸煙有關,煙草釋放尼古丁,分泌 EGF并與其受體結合,導致酪氨酸激酶的自磷酸化,激活PI3K/Akt、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促分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胞外信號調節激酶以及JAK激酶(Janus kinase,JAK)/信號轉導及轉錄活化因子(signal transduction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STAT)信號通路,促進腫瘤細胞的增殖、分化和成活,是腫瘤發生和耐藥的標記[16]。在NOM、口腔白斑和OSCC組織中,EGF受體的表達隨惡性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與p53相關,是診斷口腔白斑及其惡性轉化風險的標志物[17]。提示抗EGF受體治療可能成為一種有效的治療方法。
3 與細胞凋亡相關的因子
3.1PD-1 PD-1是一種跨膜蛋白,在腫瘤特異性T細胞中過表達,可激活抗原特異性T細胞的凋亡,抑制調節性T細胞的凋亡,在免疫抑制反應中起重要作用。PD-1與其配體(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PD-L1)(B7-H1)結合可激活細胞增殖,PI3K/Akt、MAPK、Wnt(細胞外因子)、核因子κB等信號通路的激活可促進PD-1/PD-L1軸的表達,從而促進腫瘤進展[18]。干擾素也可通過激活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6/JAK/STAT信號通路促進OSCC細胞中PD-L1的轉錄,導致免疫逃逸[19]。
近年研究發現PD-1/PD-L1軸可能與口腔白斑癌變有關,有望在預防口腔白斑惡性轉化方面發揮作用,Ries等[20]以NOM和OSCC為對照,評估了PD-1/PD-L1軸對口腔白斑惡性轉化風險的作用,發現隨著惡性程度的增加,PD-1和PD-L1表達增加,且在有惡性轉化的口腔白斑中的表達高于無惡性轉化者,表明PD-1阻斷劑可預防口腔癌變。因此,PD-1/PD-L1軸可能與疾病進展有關,可用于評估口腔白斑惡性轉化風險。
3.2p53蛋白 在癌癥中,蛋白質錯誤折疊/聚集主要影響p53蛋白,p53屬于腫瘤抑制蛋白,可促進細胞凋亡和DNA修復,突變時促進腫瘤細胞增殖,還可使細胞損傷后停留在G1期,若損傷修復失敗,則進入凋亡[10]。胱天蛋白酶3 是一種內源性蛋白酶,介導多種形式的神經元程序性細胞死亡,已被確定為p53的下游蛋白,是實現細胞凋亡的關鍵酶,可通過抑制細胞溶質DNA的釋放來減弱放療誘導的抗腫瘤免疫反應,在多種癌癥的發生發展中起重要作用[21]。在異常增生口腔白斑和OSCC組織中存在p53突變、胱天蛋白酶3表達降低及凋亡抑制存活蛋白表達增加,且沉默存活蛋白后可抑制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的表達[21-22]。因此,p53、胱天蛋白酶3等細胞凋亡的因子亦有望成為口腔白斑癌變的預測因子。
4 與血管生成相關的因子
4.1VEGFA 在血管生成因子中,VEGF是最重要的,可由多種細胞釋放。VEGFA是一種強陽性的血管生成調節因子,刺激血管內皮前體細胞遷移分化和內皮細胞增殖,促進血管新生,其低表達可誘導內皮細胞凋亡,在口腔白斑發生及癌變過程中,血管生成增加,VEGFA表達增加[23]。提示單獨或聯合使用抗血管生成藥物可能成為一種有前途的治療方法。
4.2血管細胞黏附分子-1 血管細胞黏附分子-1屬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是一種細胞表面糖蛋白,主要表達于血管內皮細胞,可被抗炎性細胞因子、活性氧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Toll樣受體激動劑和剪切應力等激活,調節炎癥相關的血管黏附和細胞跨內皮遷移[24]。王亞敏等[25]證實,血管細胞黏附分子-1的表達隨口腔白斑的發生發展呈增加趨勢,可能參與其癌變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口腔白斑癌變的可能性。
4.3白細胞分化抗原(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CD)31 CD31同p63可對口腔白斑進行分級,口腔白斑伴輕/中度異常增生病例中血管生成密度增加,而在重度異常增生中降低,是血管生成標志物之一[26]。miR-185在OSCC中低表達,是與炎癥相關的腫瘤抑制因子,用其轉基因間充質干細胞外泌體治療后,CD31和增殖細胞核抗原的表達顯著降低,炎癥反應減輕[27]。由此可見,CD31本身與血管生成密切相關,其他因子也可影響其表達,從而影響炎癥等過程。
5 與炎癥相關的因子
5.1平足蛋白 平足蛋白是一種跨膜黏蛋白樣糖蛋白,是淋巴管內皮標志物,須通過與蛋白質相互作用發揮作用,與其配體結合后可激活多條信號通路,在炎癥和癌癥中表達上調,調節細胞增殖、上皮-間充質轉化、遷移和細胞外基質的重塑等細胞過程[28]。研究發現,平足蛋白與口腔白斑異常增生顯著相關,是評估惡性轉化風險的可靠預測指標[29]。
5.2環加氧酶2 環加氧酶2,又稱前列腺素內過氧化物合成酶,是一類重要的生物中間體,是一種被抗炎性細胞因子誘導的酶。在炎癥部位活化的巨噬細胞和其他細胞中大量存在,可增強前列腺素合成,促進腫瘤細胞增殖和血管生成,抑制免疫和細胞凋亡,在OSCC中過表達,與淋巴結轉移、組織學分級、腫瘤局部復發和生存率等有關[30]。崔真真和柳志文[31]發現環加氧酶2和肝細胞生長因子受體在NOM、口腔白斑和OSCC中的表達依次增高,并有明顯的協同作用,提示環加氧酶2可能與細胞增殖、凋亡、血管生成及腫瘤復發等有關,是預測口腔白斑癌變及腫瘤復發的一個重要生物標志物,環加氧酶2抑制劑可能是臨床應用的研究熱點。
5.3IL IL是由多種細胞產生并作用于多種細胞的一類細胞因子,與炎癥、免疫及細胞增殖等均有一定作用,如IL-6可通過與其受體結合,激活JAK/STAT、PI3K和MAPK等通路,促進腫瘤細胞的分化、遷移、增殖和血管生成,抑制凋亡,導致免疫逃逸并加速腫瘤進展[32]。
研究發現,與正常組織相比,血清中IL-6、IL-8及IL-18,唾液中IL-1β、IL-6、IL-8及IL-10等在口腔白斑和OSCC中的表達依次增加,而血清IL-37在口腔白斑中表達升高,在OSCC中降低,與上皮異常增生有關[33-34]。因此,某些IL的不同表達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預測口腔白斑癌變傾向,靶向治療可能為阻斷口腔癌變提供一種有前途的防治策略。
6 與缺氧相關的因子
缺氧或低氧通過降低效應細胞的活性,減少效應細胞因子的產生和釋放,增加免疫抑制細胞因子的產生和釋放,支持免疫抑制細胞及誘導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表達,在免疫反應中發揮重要作用,是癌癥的標志之一[35]。
6.1缺氧誘導因子(hypoxia inducible factor,HIF)-1α HIF-1是一種轉錄因子,是由HIF-1α和HIF-1β組成的二聚體。在缺氧條件下,HIF-1α過表達,與癌細胞增殖、成活和血管生成等途徑密切相關,當沉默HIF-1α基因后,細胞增殖活性受到抑制,在OSCC發生、發展過程中起重要調控作用[35-36]。
研究發現,從NOM到口腔白斑再到OSCC的過程中,HIF-1α表達依次增加,并可導致VEGF過表達,與患者總生存期及術后復發顯著相關,可作為判斷口腔黏膜組織發生口腔白斑及癌變的標志物之一,且是口腔白斑患者術后復發的預測指標[37],提示HIF-1α可能作為預測口腔白斑發生、癌變及復發的指標之一。
6.2碳酸酐酶Ⅸ(carbonic anhydrase Ⅸ,CAⅨ) CAⅨ是一種與腫瘤相關的細胞表面糖蛋白,由缺氧誘導,受HIF-1α調控,被認為是一種特定的缺氧標志物,通過水和CO2催化碳酸形成,在調節細胞內和細胞外的pH值中起關鍵作用,在多種腫瘤中表達上調,與預后不良有關。腫瘤微環境的酸化可通過多個過程促進腫瘤進展,包括減少細胞黏附、增加遷移和侵襲等。而CAⅨ抑制劑可抑制上皮-間充質轉化并損害基質金屬蛋白酶的活性,從而抑制腫瘤細胞的增殖、侵襲和轉移,還可激活p53和胱天蛋白酶3的活性促進腫瘤細胞凋亡[38-39]。
通過觀察CAⅨ在口腔白斑中的表達,發現不吸煙者、紅白斑、舌部病損、多部位發生、病損面積大及復發的口腔白斑中,CAⅨ陽性率高,并具有高特異性,且CAⅨ免疫組織化學標志物可用于篩選伴或不伴上皮異常增生的樣品[40],提示CAⅨ可能與口腔白斑的多種臨床表現相關,在一定程度上可預測其危險程度及復發可能,CAⅨ抑制劑既可單獨使用,也可與其他抗腫瘤藥物聯合應用,有望成為一種新的抗腫瘤藥物。
6.3微RNA(microRNA,miRNA/miR)-31 miRNA是內源性小RNA,可在轉錄后調節基因表達,單個miRNA 可以靶向數百個信使RNA,并影響參與功能相互作用途徑的多種基因的表達,是基因表達的關鍵調節因子,也是開發生物標志物的候選者[41]。miRNA介導的轉錄后調控與干細胞自我更新和腫瘤發生密切相關,在不同的腫瘤中表現出不同功能。miR-31是針對HIF-1α信號轉導和細胞骨架蛋白的miRNA,調節多種信號通路,如催乳素受體/STAT5,轉化生長因子-β和Wnt/β聯蛋白等[42-43]。
研究發現頭頸部鱗狀細胞癌組織中miR-31水平高于口腔上皮異常增生及正常組織,且miR-31過表達的口腔上皮異常增生者更容易發展為癌,miR-31過表達與不良臨床表現及預后正相關[44]。通過使用miRNA微陣分析口腔白斑和惡性轉化的口腔白斑組織樣本中miR-31的表達,發現miR-31可調節細胞周期、細胞增殖、細胞凋亡、遷移和侵襲的生物學過程,在惡性轉化的口腔白斑中過表達,且miR-31的上調與復發或新形成的口腔白斑負相關,miR-31可能對具有不同惡性潛能的口腔細胞的生物學功能產生不同的影響[45]。因此,從某種角度來講,miR-31表達上調對口腔白斑的癌變及復發可能都有一定的作用。
7 小 結
通過從以上不同的生物學過程探討相關因子對口腔白斑癌變的影響,發現同一因子可作用于多個生物學過程,不同因子間可相互影響形成網絡體系,如血管生成因子CD31可促進血管生成,同時在miR-185影響下可介導炎癥反應。而目前主要研究單個因子及通路對口腔白斑癌變的影響,未來可以應用生物信息學的方法深入了解多因子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及機制。此外,T細胞的免疫調控、細胞自噬和miRNA等逐漸成為腫瘤機制研究的熱點,未來在口腔白斑中也可深入研究,對評估口腔白斑癌變和早期治療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