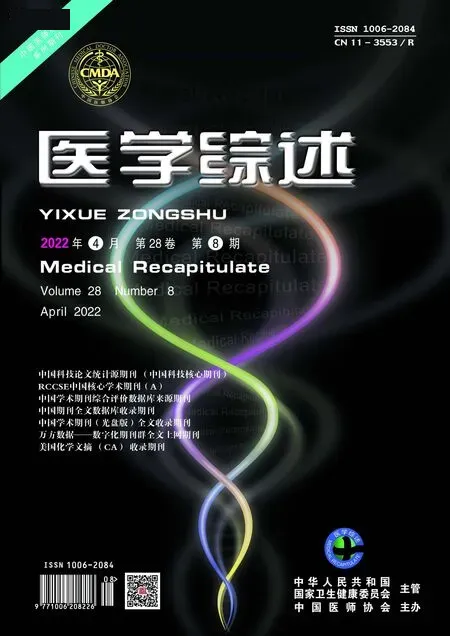肺移植治療特發性肺纖維化的研究進展
梁佳龍,陳靜瑜,鄭明峰,葉書高,劉峰,王梓濤,紀勇
(南京醫科大學附屬無錫人民醫院胸外科,江蘇 無錫 214023)
特發性肺纖維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是一種確切病因不明、進行性加重、不可逆性的肺部疾病,目前認為其發病機制是上皮細胞損傷等因素的共同作用。IPF確診后中位生存期為2~3年[1],被認為是一種惡性的癌癥樣疾病。IPF的典型特征包括進行性呼吸困難、陣發性干咳以及肺功能減退。肺功能檢查通常顯示限制性通氣功能障礙和一氧化碳彌散能力顯著減退。臨床上,當影像學檢查提示肺部浸潤性間質性改變且進行性加重,結合臨床病史并排除了其他致病因素,即可診斷為IPF[2]。如果存在診斷不明的情況,也可以通過肺穿刺活檢來明確診斷。現階段IPF的治療策略多樣,主要包括肺移植手術[3]、肺康復鍛煉[4]和抗纖維化藥物治療[5]。其中,肺康復鍛煉和抗纖維化藥物治療僅能起到緩解作用,并不能阻礙疾病的進展,疾病最終都會發展為終末期呼吸衰竭。因此,肺移植手術治療是唯一能提高IPF患者預期壽命的干預措施[3,6]。現主要對IPF的發病機制、診斷標準及肺移植治療IPF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1 IPF的發病機制
近年來,人們對IPF的發病機制的了解逐漸深入。最初,針對IPF發病機制提出了慢性炎癥假說,認為IPF是由某種細胞因子引起肺部炎癥反應,從而導致肺損傷與肺纖維化。然而,目前認為IPF的發病機制涉及多個因素:①上皮細胞損傷;②肺組織的破壞;③衰老相關因素,包括基因組不穩定性、端粒磨損、線粒體功能障礙、自噬不足和提示肺泡上皮細胞衰老的表觀遺傳學改變。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導致相關炎癥介質的釋放,從而誘導遷移、增殖以及激活成纖維細胞和成肌纖維細胞,以此來抵抗細胞凋亡并分泌細胞外基質,最終導致疾病的不斷進展[2]。此外,吸煙、環境暴露、病原體感染等環境因素和遺傳因素是IPF的潛在危險因素[7]。在環境危險因素的持續刺激下,肺泡上皮細胞和成纖維細胞會加速衰老,并顯示出一個獨特的衰老相關分泌表型,即釋放生長因子、趨化因子和蛋白酶,引起氧化應激、炎癥和纖維化,并促進活化的成纖維細胞/肌成纖維細胞灶的形成和細胞外基質的過度積累,最終重塑肺泡間隔[8]。而近年來遺傳因素(如基因突變)也被證實可破壞肺泡上皮的完整性。黏蛋白5B啟動子區rs35705950多態性被認為是IPF的高風險因素[9-10]。
纖維化過程的主要參與者是源自上皮-間充質轉化的活化肌成纖維細胞、常駐成纖維細胞和循環成纖維細胞(骨髓源性祖細胞成纖維細胞)[11-12]。肌成纖維細胞表達α-平滑肌肌動蛋白,并產生大量的細胞外基質,包括膠原蛋白、糖蛋白和蛋白多糖,最終破壞肺結構,影響肺功能[13]。在這一過程中,促纖維化介質如血小板源性生長因子、轉化生長因子-β、腫瘤壞死因子-α、結締組織生長因子、內皮素-1和CC趨化因子配體2已被確定為重要的調節因子,并作為開發抗IPF藥物的潛在靶點進行研究。其中,轉化生長因子-β可能是最強的促纖維化介質。
2 IPF的診斷
肺穿刺活檢、胸部高分辨率CT是診斷IPF的主要依據。其中,肺穿刺活檢是IPF最直接的確診手段。根據2018年美國胸科協會、歐洲呼吸病學會、日本呼吸學會、拉丁美洲胸科學會等專家聯合發布的IPF診斷臨床實踐指南[14],IPF的胸部高分辨率CT影像表現及組織病理學表現可分為4種:普通型間質性肺炎型、可能普通型間質性肺炎型、不確定普通型間質性肺炎型、其他診斷。其中最典型的普通型間質性肺炎型影像學表現為:①病變以胸膜下肺基底部分布為主,分布往往具有異質性;②伴或不伴外周牽引的牽拉性支氣管擴張或支氣管擴張的蜂窩影。該指南還規定了IPF的最新診斷標準[14-15]:①間質性肺疾病,排除了其他已知原因;②胸部高分辨率CT表現為普通型間質性肺炎型,或者取得肺組織標本患者可根據具體胸部高分辨率CT類型和組織學類型判斷。
3 肺移植治療IPF
現階段IPF的治療策略多樣,包括肺移植手術[3]、肺康復鍛煉[4]和抗纖維化藥物治療[5]。抗纖維化藥物包括吡非尼酮和尼達尼布,可有效減少中晚期IPF患者用力肺活量的下降。尼達尼布是一種細胞內酪氨酸激酶抑制劑。吡非尼酮是一種抗纖維化分子,其靶點仍不確定,但已被證明可以減少成纖維細胞的增殖和分化[16-17]。盡管這兩種藥物都有明顯的胃腸道不良反應,但大多數患者可以長時間耐受這種治療,并且治療仍能有效減少用力肺活量的下降[18]。研究表明,用力肺活量下降是一個IPF臨床療效相關的替代終點,并且尼達尼布和吡非尼酮可能具有長期的疾病緩解作用[19],但這兩種藥物均未顯示能減輕IPF患者的癥狀或改善其生活質量。肺康復鍛煉是一項綜合性、多學科的計劃,結合運動訓練、教育和行為矯正技術來減輕癥狀。勞累時呼吸困難和運動耐力差是IPF的主要癥狀,肺康復可以改善這些癥狀,從而提高患者生活質量[20]。雖然抗纖維化藥物治療和肺康復鍛煉對于IPF患者均能起到一定作用,但疾病最終都會發展為終末期呼吸衰竭。對于終末期或進行性疾病的患者,肺移植是首選的治療方法,也是唯一能提高預期壽命的干預措施[6]。
3.1供體的選擇 根據2018年發布的《中國肺移植供體標準及獲取轉運指南》[21],臨床醫師應首選ABO血型與受者相容的供體進行移植。供肺的生理功能、供體的年齡、吸煙史均需納入考慮范圍。此外,供肺的大小也影響肺移植的預后。肺是人體僅有的隨著所在空間變化而變化的器官。與IPF相關的肺容量減小會不可逆地收縮胸壁,導致胸腔小于正常值。供肺和受體肺的匹配是基于兩者的總肺容量而言。使用最廣泛的參數是預測全肺容量(predict total lung capacity,pTLC)[22],其主要根據性別和身高來進行計算,公式為[7.99×身高(m)-7.08]×1 000(男性),[6.60×身高(m)-5.76]×1 000(女性),且只適用于年齡為18~70歲,身高為1.55~1.95 m的男性及1.45~1.80 m的女性。目前國際上的共識是供體pTLC應在受體pTLC的75%~125%。pTLC過小可能導致呼吸功能不全,過大可能引起胸部功能紊亂,導致肺部受壓。在一項對6 656例限制性肺部疾病患者進行肺移植的研究中,使用過小的供肺進行單肺移植(供體與受者pTLC比值<0.8)的死亡率顯著增加,采用偏大供肺(供體與受者pTLC比值為1.1~1.2)的患者預后也較差[23]。因此,未來可能需要更嚴格地選擇供肺大小。現階段如果供肺過大,手術時通常通過解剖切除右肺中葉或左肺舌段來調整供肺大小。
3.2受者的選擇 被列為肺移植受者的患者通常沒有其他治療的選擇,他們在沒有移植的情況下2年內死亡率超過50%,移植后生存90 d以上的概率超過80%,并且術后生存5年以上的概率超過80%[24]。受者的評估需要綜合考慮其肺部疾病的嚴重程度、共病概況和年齡。由于IPF患者多為老年人,通常存在一些共患病,如冠心病、胃食管反流病等[3]。肺動脈高壓是一種較為常見的共患病,患病率高且預后較差。目前,雖然在肺移植前治療肺動脈高壓尚未被證明是有益的,但評估平均肺動脈壓和右心室功能是移植前檢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IPF患者冠心病的發生率約為30%[25]。對年齡>55歲且有吸煙、血脂異常、糖尿病等心血管危險因素的患者,建議進行冠狀動脈造影。此外,胃食管反流病在IPF患者中也很常見,患病率為70%~90%[25]。移植前行手術治療胃食管反流病可以預防慢性排斥反應[26-27]。骨質疏松癥在肺部疾病晚期患者中非常常見,可增加骨折發生風險,影響移植后患者的生活質量。IPF患者肺移植的適應證:①用力肺活量在6個月內下降>10%;②一氧化碳彌散量在6個月內下降>15%;③6 min步行試驗中血氧飽和度<0.88或6 min步行試驗<250 m或隨訪6個月內行走距離下降>50 m;④肺動脈高壓;⑤因呼吸困難、氣胸或急性發作住院治療;⑥一氧化碳彌散量<39%預計值。
3.3肺移植術前受者管理 患者移植前一般情況的管理目標是為患者提供盡可能好的生活質量和生理儲備,等待移植。保持良好的營養狀況是其中一個主要目標,因為隨著IPF的進展患者體重會加速下降,預后也較差[28]。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抗纖維化治療帶來的消化不良和腹瀉。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對患者行經皮內鏡下胃造口術給予腸內營養。肺康復也同樣重要,可改善IPF患者的去適應狀態。去適應狀態與移植患者的生存時間縮短有關。對大多數IPF患者,肺康復是可行的,應定期進行。此外,應該給予患者足夠的關愛以及心理疏導,疾病癥狀與心理狀態往往呈雙向作用。間質性肺疾病患者的抑郁癥發生率高達49%,而焦慮的發生率為31%[29]。目前關于移植前是否應使用抗纖維化藥物維持治療公認的做法是持續抗纖維化治療直至手術。雖然抗纖維化藥物的使用會帶來移植后切口愈合不良的風險,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證據表明移植前抗纖維化治療與愈合不良或出血風險增加有關,而且停止抗纖維化治療可能會加速疾病的進展。
3.4肺移植手術 肺移植手術方式主要分為單肺移植、雙肺移植以及肺葉移植。
目前單肺移植和雙肺移植在IPF治療中哪種術式更好尚無定論。與雙肺移植相比,單肺移植操作速度更快、更容易執行,圍手術期死亡率和發病率較低。然而,雙肺移植長期生存率更高,慢性肺移植物功能障礙(chronic lung allograft dysfunction,CLAD)發生率更低[30]。另一種方法是序貫式雙側單肺移植,從而獲得單肺移植的短期益處和雙肺移植的長期益處[31]。此外,由于目前供肺依舊不足,在決定手術方式時臨床醫師不得不考慮這一問題。因此,為了縮短IPF患者的等待時間及降低等待期內的死亡率,有時可用1例供體的雙肺同時進行2例單肺移植。肺葉移植也是近年來采用較多的一種肺移植術式,其按供體是否死亡分為兩種:死體供肺肺葉移植和活體供肺肺葉移植。與標準的單側/雙側全肺移植相比,死體供肺肺葉移植挑戰性更大。這項技術需要臨床醫師在肺移植方面有相當豐富的經驗,能夠靈活面對術中、術后可能出現的各種狀況。雖然死體供肺肺葉移植可能會增加原發性移植物功能障礙的發生風險,但這種手術方式的使用極大程度上擴大了不同大小的肺用于移植的可能性。一般來說,存在以下兩種情況時考慮采用死體供肺肺葉移植:①當一個肺葉因非傳染性原因不符合移植條件時,可以使用剩下的一個肺葉。②當供肺體積大于受者胸腔容積時,可以使用其中一個肺葉。而活體供肺肺葉移植是南加州大學研究者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開發的,主要用來解決死體肺移植供需不匹配的問題。標準的活體供肺肺葉移植是來自兩個健康捐贈者的右下肺葉和左下肺葉分別被植入受者體內,以取代整個右肺和左肺。此外,日本Date及其團隊開創了保留受者上葉的活體供肺肺葉移植及右下葉供肺反轉至左側的活體供肺肺葉移植等新的術式[32-34]。研究顯示,活體供肺肺葉移植的生存率始終與腦死亡供體的生存率相當甚至更高[35],但這種術式也存在活體移植共有的弊端,即治療既影響了終末期器官疾病患者,也影響了活體器官捐贈者。目前,這種術式主要在一些捐獻供肺極度短缺的國家(如日本)采用。
3.5肺移植術后并發癥管理 肺移植術后常見的并發癥有感染、急性排斥反應、腎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CLAD、糖尿病、支氣管胸膜瘺等[36]。其中,移植后1年內最常見的并發癥是感染和急性排斥反應,1年后的主要并發癥是腫瘤和CLAD[37]。
感染是早期和晚期死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術后高免疫抑制水平有助于感染的持續存在。在IPF受者中,感染占所有并發癥的56%[38],在移植后2個月內最為常見,可分為細菌感染、病毒感染和真菌感染。細菌感染最常見的是綠膿桿菌,其次是金黃色葡萄球菌。病毒感染在術后第1個月較為顯著,主要是巨細胞病毒。巨細胞病毒是肺移植患者感染的第二大原因。巨細胞病毒可通過供體、輸血或在受體中潛伏感染的重新激活而獲得,其會導致不同的臨床綜合征,如流感樣綜合征、肺炎、血細胞減少(白細胞減少和血小板減少)、消化系統疾病和肝炎。有研究表明,移植后的前3個月使用更昔洛韋進行預防可顯著降低巨細胞病毒的感染率和嚴重程度[39]。真菌感染可在術后即刻或第1個月后出現,是肺移植受者發病和死亡的常見原因。曲霉菌屬是大多數患者的致病菌,特別是煙曲霉菌。肺移植受者中最常見的曲霉菌感染為氣管支氣管炎[40]。
CLAD是影響肺移植患者遠期預后最主要的并發癥,其發生的可能性隨著移植后患者生存時間的延長而增加。CLAD的主要表現是閉塞性毛細支氣管炎綜合征和限制性同種異體移植綜合征。閉塞性毛細支氣管炎綜合征是肺移植后第1年死亡的最重要原因,占每年死亡的30%[38],是一種繼發于細支氣管纖維化病變的梗阻性疾病。限制性同種異體移植綜合征則表現為與基線值相比,總肺活量不可逆性下降10%以上,并且纖維化病變發生在肺外圍(臟層胸膜、肺泡和小葉間隔)。增強免疫抑制是目前CLAD的核心治療策略,一般使用鈣調磷酸酶抑制劑、抗代謝藥物和糖皮質激素聯合治療[41]。
3.6體外膜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輔助治療 ECMO是一項生命支持技術,其可替代部分的心肺功能,主要用于呼吸或循環衰竭患者的救治。ECMO主要分為靜脈-靜脈ECMO和靜脈-動脈ECMO兩種[3]。靜脈-靜脈ECMO主要用于低氧血癥患者,以避免高壓通氣或高流量氧療的有害影響。靜脈-動脈ECMO主要用于伴有嚴重急性呼吸衰竭和肺動脈高壓的IPF患者。在肺移植中,ECMO技術廣泛用于術前、術中及術后的輔助支持治療。目前肺移植治療的IPF患者大多為老年人,容易并發心功能不全等并發癥,導致急性呼吸衰竭。對于此類患者,當常規治療無效時,術后使用ECMO支持治療可以有效改善循環,減經心肺負擔以及降低術后移植物功能障礙的風險,從而改善患者預后,提高生存率。ECMO的術后適應證主要包括:①急性排斥反應,早期出現或預計出現原發性移植物功能障礙;②嚴重的肺動脈高壓患者的治療,恢復其心臟功能及改善肺水腫;③術中使用體外循環支持,術后難以脫離的需ECMO輔助撤離[42]。
3.7預后 肺移植患者術后的生存率比其他實體器官(如心臟、腎臟或肝臟)移植更差。這是因為在長期生存的情況下,移植肺更容易發生慢性排斥反應。圍手術期管理和免疫抑制可有效改善早期結果,但對長期生存率的影響較小。目前,IPF患者肺移植術后全球生存率第1年為80%,第3年為64%,第5年為54%,第10年為32%[43];國內生存率第1年為67%,第3年為58%[36]。
4 小 結
在IPF可用藥物治療的新時代,早期肺移植的需求可能較低,但肺移植是終末期肺部疾病的唯一治療方法。現階段,肺移植費用高昂以及手術療效的不確定性讓一部分患者抗拒肺移植,直到疾病發展至終末期才尋求治療,從而錯過了進行肺移植的最佳時機,而這種極度惡劣的身體條件加上目前合適供肺的短缺問題,也導致了許多患者在等待的過程中失去了生命。受限于此,肺移植只能幫助到少數的IPF患者。因此,必須加大肺移植的科普宣傳力度,并且鼓勵器官捐獻,緩解供肺短缺問題,以使更多的患者能夠得到及時的評估與治療。此外,臨床醫師提升手術技巧以及圍手術期管理也是尤為重要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