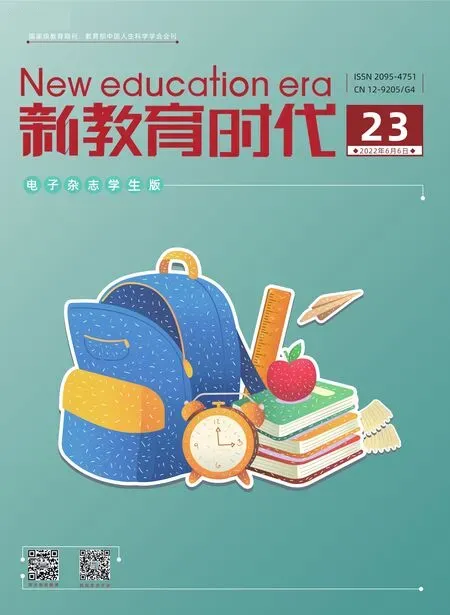學前兒童使用電子媒介與家長媒介干預研究
房陽洋 宋 璐 陸亦婷 陳 怡
(中華女子學院 北京 100101)
電子媒介是指以智能手機、智能電視、平板電腦為代表的電子產品作為傳播的載體。在學前兒童使用電子媒介已成為普遍現象的互聯網時代,開展學前兒童使用電子媒介的相關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由于家長在干預學前兒童使用電子媒介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深入研究改善家長的媒介干預方式,會有助于家庭減少學前兒童的屏幕暴露,化屏為友。
一、學前兒童使用電子媒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互聯網科技的發展、應用與普及,電子媒介承載著信息交流、休閑娛樂、網絡教育等多種功能,成為兒童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以電子游戲、動畫、短視頻為主的多種電子媒介活動所構成的豐富的“圖像符號空間”與兒童的現實生活空間交相互動,使得二者之間的邊界愈發模糊。并且,前者在不斷侵占后者在學前兒童成長中的時空比,以至于人們擔心電子媒介等屏幕類產品過分擠占兒童的學習空間,帶來不良后果。
1.兒童使用電子媒介的年齡日趨低齡化
兒童使用電子媒介進行社交、玩游戲和瀏覽動畫片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研究顯示,信息化進程已從成人延伸到低齡兒童群體中,智能手機的使用與普及使低齡化趨勢更甚,約10%的孩子在1歲之前開始接觸電子媒介[1]。另有調查顯示,幼兒電子媒介接觸率高達80%。英國一項調查顯示,96%的幼兒每周觀看電視累計時長達15h。上海市新入園兒童的日均屏幕時間為2.7h[2]。新冠疫情期間,電子媒介單日使用總時長超過1h的幼兒占比高達74.13%,另有22.26%的幼兒日均使用時長超過2個小時[3]。日本倍樂生的調查發現20%以上的2歲幼兒在一周內使用智能手機超過三次。2020年,7/10的兒童在使用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等這些常用的電子媒介。兒童使用電子媒介的年齡日趨低齡化,且呈現出使用時間長、頻率高的特點。
2.學前兒童過度使用電子媒介為其身心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電子媒介雖有可能為兒童提供互動學習環境與豐富的感官刺激,但過度使用電子媒介會給兒童身心發展帶來消極影響。在身體健康方面,兒童使用電子媒介久坐不動,易提升超重、肥胖、視力減弱等健康風險。研究發現,電子媒介的使用時間與兒童超重或肥胖的風險率呈正相關,且每日使用時間超過2h會使風險加劇。此外,還有研究發現,過早接觸電子媒介會影響大腦發育,從而導致多動癥等癥狀出現,對兒童視力、脊椎發育產生消極影響,且對低齡幼兒危害更甚。在心理健康方面,過度使用電子媒介對兒童的注意力及早期閱讀書寫易產生負面影響。經常使用電子媒介的學前兒童在步入小學后更容易出現注意缺失、語言表現和認知成就差等問題。
二、家長媒介干預是學前兒童使用電子媒介的重要影響因素
1.家長媒介干預的方式具有多樣性
家長干預(parental mediation)是指為了發揮媒介正向功能,避免媒介對兒童產生消極影響,而由家長主動采取的措施,包括家長對子女所接觸的媒介及內容進行控制、監督和解釋等策略。已有研究將家長媒介干預方式分為限制性干預、監督、禁止使用、共同使用和積極性干預。限制性干預主要指家長對兒童使用電子媒介的內容、時長及時間的控制,家長通過安裝過濾性軟件或監控軟件,屏蔽未經家長同意的媒介內容。與間接的限制控制不同,監督是一種直接控制,要求兒童必須在家長視野范圍之內使用電子媒介。禁止使用是指家長采用禁止策略不允許兒童使用電子媒介。家長共同使用與積極性干預常常同時出現。家長與兒童共同使用媒介是指家長通過用兒童能理解的語言解釋、討論、指導的方式干預其媒介使用。積極干預指家長先為兒童篩選特定媒介內容,在媒介使用同時或之后與子女進行指導性、教育性的看法交流,促進子女對媒介內容的思考,從而逐漸樹立正確的媒介認知態度,進而改變自身的媒介行為。
2.家長對兒童電子媒介的干預受到多種因素影響
(1)家長的教養態度影響家長的媒介干預
家長對于兒童使用電子媒介的態度歸為四種:忽視型、依賴型、拒絕型與中立型。忽視型家長把電子媒介單純作為子女的娛樂工具,對其使用從不加以控制。依賴型家長把其視為教育和娛樂的工具,認為電子媒介可以教給兒童新的知識。他們大多將電子媒介作為“保姆”或玩具來陪伴孩子,從而對其使用時間和內容很少或幾乎不予以控制。拒絕型家長直接拒絕或嚴格控制兒童使用電子媒介,認為電子媒介會影響其身心發育,例如損害視力健康,限制其語言能力的發展等。中立型家長看到了電子媒介影響的雙面性,認為電子媒介不是學前兒童生活的剛需,一般會限制兒童使用電子媒介的時間,但也易忽略對媒介內容方面的監督。家長的教養態度影響兒童使用電子媒介的動機。調查結果顯示,有52.89%的家長會在孩子表現優良時作為獎勵給孩子使用,26.74%的家長因自己無法陪孩子,15.39%的家長會用電子媒介安撫哭鬧的孩子[4]。
(2)家長的受教育水平影響家長的媒介干預
家長自身的文化程度間接影響家長的媒介干預。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家長互聯網技能越強,參與和限制子女電子媒介使用的程度越高,采用積極性干預措施更多。低教育水平的家長與子女之間存在電子媒介專業知識代溝,他們往往更傾向于使用限制性干預方式,對子女媒介使用時間進行管控。也有研究發現,家長文化程度與學前兒童使用電子媒介時間呈負相關。其中,教育工作者的家庭對兒童電子媒介的使用把控得更好。此外,部分文化程度較低的家長即使干預意識萌芽,也受限于知識儲備,并不清楚如何有效施行家長媒介干預,進而提升學前兒童的媒介素養。調查結果顯示,家長對媒介素養教育非常了解和比較了解占比4.8%,其余家長表示了解一些和完全不了解[5]。這也說明了開展學前兒童及其家長媒介素養教育的必要性。
(3)家庭的人員結構影響家長的媒介干預
當今,幼兒的家庭結構可分為完整家庭(包括親子、祖孫三代共同生活)和非完整家庭(單親家庭、留守兒童家庭)等類型。不同的家庭結構影響幼兒使用電子媒介。研究顯示,與完整家庭中的幼兒相比,來自非完整家庭的幼兒手機使用頻率更高。非完整家庭的家長,往往需要承擔著父母的雙角色,一邊為生計奔波,同時還需兼顧家務及養育子女,精力有限,繼而導致其在生活中對幼兒使用電子媒介疏于管教,使其成為幼兒穩定的伙伴。另有調查發現,三代共育家庭中的幼兒比其他家庭結構的幼兒使用電子媒介時間長[6]。父母平時多外出工作,將幼兒交由祖父母看管,隔代教養易出現溺愛的傾向,導致幼兒使用電子媒介的行為頻率上升,時間延長。此外,有調查發現,是否為獨生子女也是影響幼兒使用電子媒介的因素之一。非獨生子女家庭的父母一般需同時照料多個子女,精力被分散,沒有充裕的時間陪伴具體,導致幼兒使用電子媒介的時間與內容得不到良好控制,從而讓使用電子媒介淪為幼兒消遣的一種方式。
(4)家庭的經濟水平影響家長的媒介干預
研究發現,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兒童,電子媒介日均使用時間越少。通常,經濟條件優渥的家庭可為幼兒提供更多可替代電子媒介的玩具、圖書,社區戶外活動設施也更加充足。另外,各類興趣培訓班會擠占幼兒的一部分閑暇時間,進而反向限制其使用電子媒介的時間。但是,經濟條件提升也伴隨著幼兒可支配的電子媒介種類、數量增多,幼兒接觸電子媒介的機會又相應增加。有調查顯示,有26.0%的幼兒擁有自己的電子媒介。此外,城鄉家庭間的經濟差異間接影響教養人對電子媒介的認知水平。研究發現,鄉村家庭對兒童接觸電子媒介的篩選和控制力較弱,鄉村兒童更容易被娛樂化的消遣所裹挾,沉浸在重復甚至低俗化的內容中。而城市家長一方面對電子媒介所致的負面影響保持警惕,另一方面也在積極尋求代替電子媒介教育價值的方式。
三、改善家長的媒介干預方式以減少兒童屏幕暴露
學前兒童使用電子媒介雖已成為普遍現象,且往往超出世界衛生組織(WHO)所規定的1h時長限制,但對于如何改善家長的媒介干預方式,發揮兒童使用電子媒介的正向作用的研究較少。為此,通過改善家長的媒介干預方式,來減少兒童屏幕暴露時間具有可行性,研究者提出以下策略。
1.改善家庭教養方式,提升限制性干預意識
家庭的教養方式是影響兒童使用電子媒介的重要因素。當父母采取忽視型和依賴型教養方式時,幼兒電子媒介的使用水平最高。對媒介持忽視型和依賴型教養態度的家長的限制性干預意識仍有待提升。減少幼兒使用電子媒介的限制性干預策略可以從三方面實施:一是從技術上予以限制,即在電子媒介上安裝監控、過濾等軟件,限制幼兒瀏覽網頁的類型,使其不能接觸部分媒體內容。二是從互動形式上采取措施,即監控并限制其進行互動游戲、瀏覽社交軟件等行為,或限定幼兒在使用部分網頁、軟件時需家長陪同。三是制定電子媒介使用規則,家長通過限制學前兒童使用某種電子媒介,從而減少其在特定媒介上的時間。有研究表明,規則的建立可以增加學前兒童從電子媒介中獲得學習與成長,將使用電子媒介的消極影響降到最低。
2.控制媒介使用時間,給予適當監督和禁止
3-6歲兒童每天接觸電子媒介時長不超過30分鐘為宜。家長可以直接控制學前兒童使用電子媒介的時間,可用方法有:在電子設備上設置密碼、開啟青少年防沉迷模式等。為避免出現兒童對家長限制媒介使用產生“媒介叛逆”的抗拒心態,在使用時間和使用內容的控制上,家長可以通過與兒童共同制定相應規則,并設立獎勵機制和懲罰機制,督促雙方履行規定。另有研究證明,電子媒介在家庭中的位置會影響學前兒童使用電子媒介的時間,家長通過合理安排媒介擺放位置,如將電視等電子媒介擺放在客廳,從而減少其接觸電子媒介的機會,達到監督的效果。
家長通過進行電子媒介替代類活動,也可以變相控制學前兒童使用電子媒介的時間。例如,家長可以在室內創設音樂情境,與兒童共同扮演音樂劇中的角色,提升音樂素養的同時增進親子間的關系。家長也可以制作簡易實驗,如蔬菜水果沉浮游戲等,兒童可以直接動手操作,在操作過程中掌握科學知識,減少屏幕接觸時間。
3.提升家長媒介素養,創造共同使用的契機
家長媒介素養的提升,不僅對學前兒童媒介素養的獲取有所幫助,還可改善因家庭經濟水平較弱及家長對媒介教育的認知不足所導致的學前兒童使用電子媒介的不利環境。為提升家長媒介素養,家長首先需明晰自身的教育責任,積極學習兒童身心發展的規律,從而進一步對學前兒童使用電子媒介做出科學的判斷,并規避有可能導致家庭使用電子媒介的不良因素。其次,家長需要主動學習、更新媒介知識,完善關于電子媒介的教育理念,學會將屏幕化敵為友,選擇有益信息擴大兒童視聽認知。同時,政府可以委托相關社區、學校通過講座、家訪、親子活動等形式進行家長的媒介素養教育。
家長主動為兒童挑選優質的媒介內容,搭建其與優質媒介之間的溝通橋梁。通過對媒介知識的學習與自我反思,家長不僅可以對使用電子媒介的種類、內容和影響有進一步判斷,還可以通過與學前兒童共同使用電子媒介來塑造獨特的家庭文化,營造良好的電子媒介使用氛圍。例如,家長可以與孩子共同談論電子媒介的內容,尋求與兒童建立共同的興趣,獲得一家人更多共同使用電子媒介的機會。
4.提高親子陪伴質量,營造積極性干預氛圍
2019年《中國親子陪伴質量研究》中指出,高質量的親子陪伴會引導兒童提升主動思考及語言表達能力。家長可以通過陪伴過程中的積極干預傳達教育性的看法和意見,讓學前兒童逐漸樹立正確的媒介認知態度,并改變自己的行為。在親子深度溝通的過程中,可以減少使用媒介的負面影響,并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學前兒童對電子媒介的強迫性使用傾向。
在營造積極性干預氛圍時,家長與學前兒童的交流是最重要的。家長可以主動提問兒童媒介中的信息,與兒童進行實時互動。在面對電子媒介所呈現的內容與真實世界產生差異時,家長需要及時厘清其內容,并引導學前兒童進行主動思考,培養兒童的批判性思維以及對信息的辨別能力。家長為兒童解釋電子媒介中人物塑造時能較好地培養兒童的性別意識,發掘兒童對自我的認識。例如,家長可以在陪伴過程中通過共同扮演一些角色或參加一些角色游戲來與兒童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