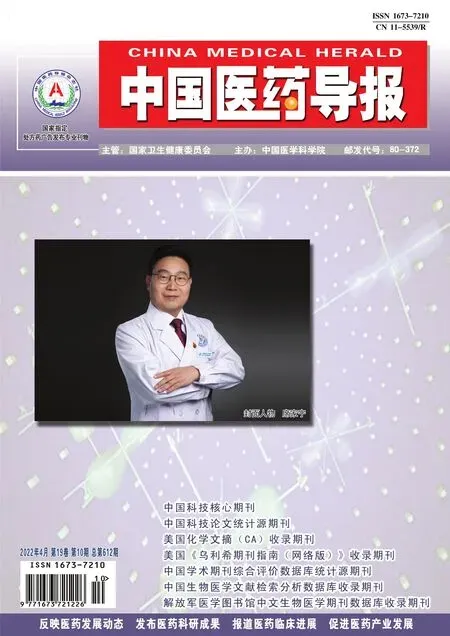宮廷理筋流派臧福科筋傷推拿學術思想的形成與特色
韓思宇 甘葉娜 張桐桐 程潞瑤 苑藝 王賓 劉長信 李多多
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推拿科,北京 100700
臧福科是第五、六批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的指導老師,他從醫58 載,理驗俱豐,醫術精湛,醫德高尚,是目前中醫骨傷學界和推拿學界的權威專家[1]。臧福科1963 年從原北京中醫學院(現北京中醫藥大學)畢業后入職東直門醫院,師從我國著名中醫骨傷科大師劉壽山先生[2],從事骨傷科15 載,后于1978 年創辦東直門醫院推拿科,將從劉壽山先生傳承的筋傷推拿手法與不同流派進行對比、融合,并結合現代醫學對傳統理、法、方、藥、術進行了創新發展,形成現代宮廷理筋診療體系,目前業界公認臧福科是宮廷理筋學術流派的代表性繼承人和傳承人之一[3]。本文探討臧福科筋傷推拿學術思想的形成與特色,以期為中醫相關學科的傳承與發展提供借鑒。
1 學術思想形成
1.1 臨證伊始,師承劉壽山先生
1963 年臧福科于原北京中醫學院中醫系畢業后分配至東直門醫院骨傷科工作,在院黨委引薦下榮拜科室主任,時年59 歲的我國著名骨傷科泰斗劉壽山學習。拜師伊始,劉壽山要求臧福科每日清晨練習八卦掌,日間侍診臨證,每周日和同事們聆聽老師講課并認真做記錄,通過“速記”的方法把劉壽山所講內容進行詳細整理,最后編著成《劉壽山正骨經驗》一書[4]。當時參與速記的同仁主要有臧福科、孫樹椿、劉佑華、孫呈祥等,臧福科老師和同事們將劉壽山先生傳承的宮廷骨傷和理筋診療全套精華毫無保留地記載了下來,為中醫骨傷科事業做出了杰出貢獻。臧福科回憶劉壽山畢生所學均系師祖文佩亭口傳心授,故劉壽山授課不僅貼近臨床實際,更能將昔日秘不外傳的清宮綽班處[5]正骨理筋手法要旨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他們。同時,臧福科也深刻體會到中國傳統的師承教育是現代中醫院校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
1.2 中西互鑒,守正創新
為更好地傳承中醫骨傷科事業,探索中西醫結合的道路,更好地繼承和創新東直門醫院骨傷科學術精華,臧福科先后于1965 年3 月至1966 年3 月公派河南省洛陽正骨醫院進修傳統骨傷手法,20 世紀70 年代初公派原中蘇友誼醫院(現北京友誼醫院)進修現代骨科手術。臧福科根據現代骨科學理念,將北方骨傷手法和方藥與現代骨科診療體系相結合,在擴展中醫治療范圍的同時,充分發揮了中西醫結合的優勢。臧福科認為在他從事骨傷科的15 載中,日常診療的重點為骨折和脫位,而對于筋傷病并未予以足夠的重視。
1.3 投身推拿,道法骨傷
1978 年經院領導任命,臧福科調離骨傷科,創辦東直門醫院原按摩科[6](現推拿科),該科室成為當時我國北方地區首家公立醫院獨立開設的推拿科,這一平臺為臧福科在推拿學界今后的巨大影響力奠定了基礎。在科室成立之初,臧福科認識到當時北方推拿從業人員的醫學知識和技能多源于師承教育模式而缺乏系統的院校教育經歷。相比之下,臧福科從事推拿專業則具備諸多優勢,如他曾接受過6 年完整而系統的全日制中醫本科教育,臨床技能則是繼承劉壽山的正骨經驗,并有骨傷科15 年的實踐積累,系統進修過現代骨科的先進理念、知識和技術。這些優勢讓臧福科對以接診筋傷病為主的推拿事業有了異于傳統的思考,雖然干預的病種和手段發生了變化,但均不離骨傷領域,在傳統的“筋骨并重”[4]核心理念指導下,他將骨傷手法與筋傷推拿進行了深度的融合與創新。
1.4 勤求博采,大成萌芽
在推拿科建設的初期,臧福科還意識到,僅有過硬的推拿技法是不夠的,只有構建屬于北京地區的推拿學術體系才是推動推拿學科發展的長遠方向。當代國內成人筋傷推拿領域相對歷史最悠久、學術體系最完善、臨床和科研水平最高的地區是上海,擁有眾多較為成熟的學術流派,如一指禪推拿流派[7]、法推拿流派[8]、內功推拿流派[9]等。對此,臧福科帶領多名科室年輕醫師赴滬遍訪各流派代表性傳人,在此過程中,他不但與業界同仁如俞大方和曹仁發[10]等結下深厚友誼,更呼吁他們一起成立了全國性的推拿學術組織,使推拿療法有望發揚光大。此后,在臧福科和東直門醫院針灸科楊甲三先生等前輩們的共同努力下,1982 年北京中醫學院成立了針灸推拿系,而臧福科則成為日后北京中醫藥大學針灸推拿學院的奠基人之一。1992 年臧福科主張從整體觀點出發,強調在臨床實踐過程中運用手法不可拘泥于一法一派之醫技,應兼取百家所長,發起成立大成推拿學派和中國大成推拿學會,被業界譽為“大成宗師”[11]。從1996 年至今,臧福科始終致力于補充、完善和推動其師祖文佩亭所創宮廷理筋學術流派的發展,經過20 多年的努力,該流派已構建出較為成熟的現代宮廷理筋診療體系。今天,84 歲高齡的臧福科依然站在推拿學醫、教、研的前沿,指導和協助后輩進行流派的建設工作。
2 學術思想特色
2.1 手法大成
臧福科認為骨傷科手法包括正骨手法和理筋手法,而劉壽山辨治筋傷突出的學術思想為“治筋喜柔不喜剛”[12],該理念對推拿手法的學習和運用可能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臧福科通過對不同推拿流派手法發力方式的異同,總結出指導筋傷推拿發力要領的核心學術思想,即“手為模,巧用力,意氣和,暗勁生”的十二字要訣,這是他從醫43 載至今對筋傷推拿技法真諦的感悟。
2.1.1 手為模 臧福科認為,不同推拿流派辨治筋傷病,靜態舒筋類[13]手法是最為常用的,即患者肢體在基本保持靜止狀態下,醫者在受術部位施以形態各異的單式或復合手法,如一指禪推法、法、按揉法等,以求舒筋通絡、開郁散結、活血化瘀等治療作用。在治療過程中,醫者的手或肢體的一定部位始終接觸患者,即推拿所說的“功力”[13]主要傳遞媒介,無論手法外觀存在如何的差異,都應遵循“持久、有力、均勻、柔和”[13]的發力要點,讓患者感到身心放松。因此手部只要求在治療過程達到“接觸”患者的目的即可,手指的指間各關節盡量不要主動屈伸。即在推拿過程中手部本身僅保持一個正確的形態以便力的正確傳導就可,而不可過分追求外觀的美觀和所謂的“規范”,即“手為模”。
2.1.2 巧用力 臧福科談到劉壽山所傳的骨折脫位整復手法,其要點在于“暴烈剛強”[2],以求迅速糾正骨折斷端和脫位關節的正確位置,減少患者的痛苦;而理筋手法的要點恰與前者不同,應遵循“輕巧柔透”的原則[14]。因為筋傷普遍較骨折和脫位癥狀輕微,病史遷延而易反復發作,故其理筋首務在于“舒導”,以恢復筋的柔順和條達之性;醫者如運用剛暴猛烈的手法易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使瘀阻者更滯而拘攣者更甚,且患者心理亦難以接受。“輕柔”不是無力,而是就發力方式而言,醫者可運用自身體重的分量作為力的來源,使患者感到局部沉穩溫熱而舒適,這樣醫者的力就在不知不覺中透達深層;醫者采用體重且無需上肢的額外發力,自身亦不疲勞,更利于力的穩定傳遞。這樣可以將“輕巧”理解為緩和而持久,而“柔透”理解為“自然而然深入的過程”[15]。此外,“巧”還體現在根據患者身體的實際情況來調整力的運用和指導手法的選擇,對新傷則當用力輕動作緩,陳舊者可用力稍重,對體質弱或病較重的患者采用摩擦類手法更為適宜。
2.1.3 意氣和 臧福科指出,推拿不僅屬于物理療法范疇,更是身心同治的干預手段[16]。在治療過程中醫患之間始終有肢體的直接接觸,這有別于多數療法。力作用于人體,即使再熟練的技法也必然通過皮膚和皮下各組織的感受器傳入,不但會對施治部位產生一系列的生物、物理和化學作用,還會對患者的情緒產生影響。這一特點要求醫者在治療中要時刻關注患者接受手法時心理的微妙變化。“意氣和”[17]即指醫師專注于患者的感受,采用適度的言語引導患者接受治療的意圖并建立康復的信念,這也是推拿起效的重要保證。醫者切記在治療中言語不當或心不在焉,這樣會使患者產生反感、延誤甚至是恐懼的感受,一旦產生這種負面情緒,任何精湛的手法技巧皆不能達到預期的治療效果。
2.1.4 暗勁生 臧福科將推拿發力方式從宏觀角度分為“明勁”和“暗勁”[15]。“暗勁”是醫者運用自身體重的分力施加于治療部位,它較醫者上肢主動發力的“明勁”[15]更易讓接受者感到舒適和放松而產生“力透”的作用。臧福科提出的“暗勁”概念源于其師所傳授的八卦掌,在其練習之初往往只關注招式,多以“明勁”為主;當熟練后,肌肉會對招式產生“記憶”,達到“力發自腰而根于足”的階段,此時上肢與手僅輕觸體表,患者即能感知到“暗勁”,其形式不是剛猛和直接,而是一種類似間接而溫熱的彌散感與向某方向緩和的延伸感,此種感覺類似針灸的“得氣”[18]感。臧福科認為在推拿領域目前運用“明勁”,同時追求“盲目”“大力”且“成套”的推拿技法可能仍是主流。這樣的刺激可能是通過短暫提升局部組織痛閾達到止痛效果,但從現代醫學認識來看,該方法的遠期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暗勁”更易讓機體接受,故可作用于更深層次的組織,其對于緩解痙攣與輔助消除炎癥可能更具優勢。所以,臧福科認為“暗勁”是“柔”字的更深層次含義。
2.2 手方大成
臧福科認為筋傷病的病因屬“不內外因”范疇,以局部辨病結合整體辨證為大法,而筋傷自《正體類要》就有“肢體損于外者氣血傷之于內……不可純任手法”之說[19],即筋傷必有氣機和血液的運行受阻不暢而五臟六腑的整體平衡被打破[20],對此,內外兼治更為推薦。故臧福科在劉壽山先生學術思想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出“治筋傷當明內損,判預后重調氣血”的學術觀點,注重營衛氣血、脾胃肝腎與筋骨的相互關系,此外,體質差異與七情所傷亦是重要的內因。臧福科言其師劉壽山歷來就有“七分手法三分藥……辨治筋傷病不可單純采用手法”[12]的觀點,強調了手法與藥物互助互用。而臧福科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手法理筋僅可矯其“形”,通其“痹”而難以治其“萎”,中藥可促其“質”的恢復。可知在筋傷臨床診療中,手法結合方藥,基于“筋”的特性來遣方加減化裁以運用,可能會達到更好的效果,即“手方大成”。
2.2.1 內服藥組方要旨——筋濡則和而不濡則萎 臧福科常引《靈樞》的“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而利關節者也”,教導后輩要熟悉“筋”的特性方可辨治取效[15]。因為“筋”屬血肉之品,賴人體之氣血濡養,感受暴力或外邪均可造成氣血瘀滯而失養攣急,日久則先痹后萎。筋傷病分為“新鮮”和“陳舊”兩類,兩者實為銜接關系,其病機可用一主線貫穿始末,即早期因跌撲勞損致使局部氣滯血瘀,經脈閉阻;失治誤治則遷延日久;久之筋失所養,拘攣失用。如《雜病源流犀燭》言“跌撲閃挫,由外及內,氣血俱所傷”[15],可知筋傷無論急緩均以陰陽失衡為本。故臧福科提出“筋濡則和而不濡則萎”的學術觀點,認為內服組方應以“氣血并重,協調陰陽,祛瘀蠲痹”為總則。根據“新舊”筋傷之別,臧福科采取早、中、后三期的辨治法則[21],早期重在行氣活血,化瘀通絡;中期強調和營順氣,行血柔筋;后期補血活血,肝腎同補,其中“活血養血”當貫穿始終[22]。早期臧福科提倡運用湯劑內服達到“滌蕩瘀滯”的目的,即短期消腫止痛,以血府逐瘀湯為基本方加減引經藥;中期重在活血生新兼調營衛,常用正骨紫金丹加減化裁;后期筋的功能尚未完全恢復,需氣血與肝腎同補,可服用補腎壯筋湯合補腎養血丸加減。
2.2.2 外用藥組方要旨——筋喜溫熱而惡寒冷 《素問》有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筋必得機體陽氣的溫煦,方能活動自如而發揮正常的生理功能[15]。臧福科認為,寒主收引,筋最惡之,故筋遇寒則易發為拘攣疼痛。此外筋傷之后的調養也應格外注意保暖,禁用寒涼之藥物。在此基礎上,臧福科認為陳舊筋傷多兼痹萎之功能失用的特點,更應以溫通法治之,故熥、洗藥物外治不可或缺。熥藥和洗藥均有溫經、通絡、活血等作用,而區別僅為給藥的途徑有別;洗藥為將中藥煎煮后泡洗,多用于四肢的損傷。而熥藥是將中藥裝入藥袋后蒸熱外敷,多用于肩、背、腰、髖等大關節。兩者在使用中均要注意局部與全身的保暖,且溫度不宜太高,以免引起燙傷。
3 小結
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均壽命延長,運動系統退行性疾病居于各種疾病發病率的前列[23]。此類疾病雖然不直接危及生命,但它造成生活質量的下降和由此引發的連鎖反應逐漸成為一大社會問題而備受關注[24]。對此,臧福科認為該疾病應屬于“身心醫學”診治的范疇[25]。運動系統退行性疾病與軟組織急性損傷多屬于中醫“筋傷病”的范疇,縱觀臧福科辨治筋傷病,看似他對手法和方藥的臨證運用嫻熟,實則屢起沉疴的驗效是他在數十年學術積淀中積累的結果。臧福科常言療法起效的前提是對“筋”的中西醫認識均十分深刻,在此基礎上豐富的多學科知識和深厚的人文素養可以起到正向的心理干預作用,最后才是療法運用的嫻熟與否。而臧福科提倡的“大成”并非單純的手法互鑒和療法互通,而應是文理學科間的“大成”、思維方式和方法的“大成”和醫德與素養的“大成”。筆者認為這才是臧福科筋傷推拿學術思想最突出的特色。學術流派的形成促進了中醫藥學術的發展和繁榮,流派的爭鳴和互鑒是當代中醫藥可持續發展的基石和紐帶,研究和發掘流派特色對傳承和發展中醫藥事業、提高中醫臨床水平具有重要意義。筆者希望本文能給中醫推拿學的傳承與發展提供借鑒,同時也期待能將“大成”的理念分享給其他醫學從業者,為攜手共筑“健康中國”奉獻微薄之力,不足之處還望同道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