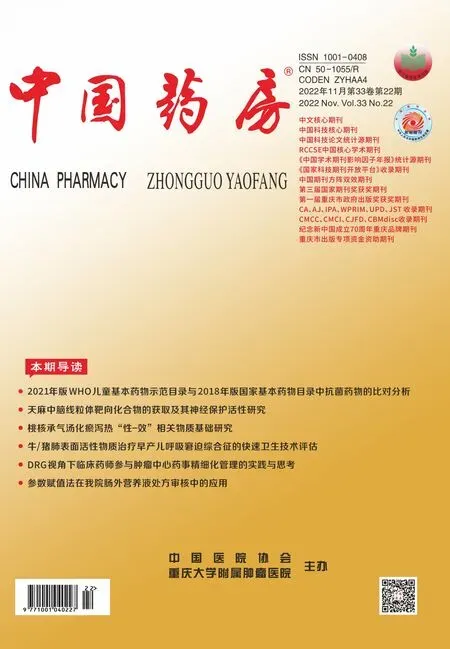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治療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Δ
季 鵬,寧麗娟,陳泳伍,朱鵬里,吳 菲,吳穎其,顏 輝,耿亞迪,張圣雨,沈愛宗[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安徽省立醫院)藥學部/安徽省藥品臨床綜合評價技術中心,合肥 230001]
2022年2月,國家癌癥中心發布的最新一期全國癌癥統計數據顯示,肺癌發病率位列第二,病死率位列第一;2020年我國癌癥死亡總人數為300萬,肺癌死亡人數(約71萬)遙遙領先,占癌癥死亡總人數的23.8%[1]。紫杉類藥物是晚期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主要化療藥物,美國國家綜合癌癥網絡(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非小細胞肺癌臨床實踐指南(2022,V1)》、中國臨床腫瘤學會(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CSCO)《2021 CSCO非小細胞肺癌診療指南》等國內外臨床指南均推薦紫杉醇作為NSCLC的一線治療藥物[2―3]。傳統的溶劑型紫杉醇由于疏水性強,需要以聚氧乙烯蓖麻油為溶劑,而后者容易引發嚴重的過敏反應和腎毒性、心臟毒性等不良反應,使得臨床用藥的安全性受到影響;結合型紫杉醇為新型紫杉醇制劑,以人血白蛋白為載體,藥物溶解度有所增加,且不會存在由聚氧乙烯蓖麻油所造成的不良反應,在臨床上顯示出較好的療效和較低的毒性[4]。2012年,結合型紫杉醇被美國FDA批準用于NSCLC的臨床治療。
NCCN《非小細胞肺癌臨床實踐指南(2022,V1)》指出,患者在必要時(如發生過敏反應時)可使用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替代紫杉醇或多西他賽[2]。對于無驅動基因突變的晚期(Ⅳ期)NSCLC患者,《2021 CSCO非小細胞肺癌診療指南》推薦一線使用紫杉類藥物,包括紫杉醇、多西他賽、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3]。雖然國內外臨床指南均推薦紫杉類藥物作為NSCLC的一線治療藥物,但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尚未在我國獲批用于NSCLC;同時,NSCLC患者使用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無法獲得醫保報銷,加之該藥上市時間短、價格相對較高,使得其臨床應用受限,因此有必要從藥物有效性、安全性等多方面入手對其進行綜合評估。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真實世界研究方法,回顧性分析了我院2018年1月-2021年12月收治的使用含紫杉醇制劑(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和普通紫杉醇)化療方案的晚期NSCLC患者的臨床資料,對兩種紫杉醇制劑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進行比較,旨在為保障臨床合理、規范地使用抗腫瘤藥物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使用我院臨床藥學管理系統PASS PharmAssist 2.0抽取2018年1月-2021年12月我院收治的使用含紫杉醇制劑化療方案治療的200例晚期NSCLC患者的臨床資料。納入標準包括:(1)經病理組織學或細胞學檢查確診為NSCLC Ⅳ期,診斷標準參照《2021 CSCO非小細胞肺癌診療指南》[3],病理學分期參照國際肺癌研究協會第7版TNM分期[5];(2)有CT掃描或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可測量的客觀病灶;(3)美國東部腫瘤協作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評分為0~2分,完成化療周期≥2個;(4)從治療開始預計生存期>3個月;(5)無化療禁忌證;(6)獲得患者超說明書用藥知情同意。排除標準包括:(1)嚴重的心腦血管、糖尿病及精神疾病患者;(2)嚴重的全身性感染患者;(3)伴有重度肺纖維化的患者;(4)大量胸腔積液、心包積液無法控制者;(5)乙肝表面抗原陽性者。根據患者所用化療方案,將其分為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組和紫杉醇組,各100例。本研究方案經我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倫理批件號為2022-RE-060。
1.2 治療方案
醫師根據患者的體表面積和預后評分選擇適宜的方案化療。化療前,所有患者均進行血常規、肝腎功能、電解質檢查,排除化療禁忌證。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組患者接受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結合型)(江蘇恒瑞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183378,規格100 mg)治療,用法用量為130 mg/m2,d1+d8,每次滴注30 min,給藥前均未預防性使用抗過敏藥。紫杉醇組患者接受紫杉醇注射液(哈藥集團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59962,規格 5 mL∶30 mg)治療,用法用量為 175 mg/m2,滴注時間長于3 h,給藥前使用抗過敏藥處理[給藥前30~60 min靜脈滴注地塞米松磷酸鈉注射液(辰欣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37021969,規格1 mL∶5 mg)20 mg]。每21 d為1個周期。所有患者至少完成2個周期的治療,且嚴格按照給藥方案執行,無患者減量。
1.3 療效及安全性評價
治療2個周期后,依照實體腫瘤療效評價標準1.1(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urs,RECIST 1.1)評價兩組患者的近期客觀療效,包括完全緩解(com‐plete remission,CR)、部分緩解(partial remission,PR)、病情穩定(stable disease,SD)和疾病進展(progressive disease,PD),并按下式計算有效率(response rate,RR)和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RR=(CR患者數+PR患者數)/患者總數×100%,DCR=(CR患者數+PR患者數+SD患者數)/患者總數×100%[6]。記錄兩組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PFS定義為從化療開始至PD或任何原因導致死亡的時間。記錄兩者患者的毒副反應發生情況,并按常見不良事件評價標準5.0版(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CTCAE 5.0)進行分級(1~5級)判定[7]。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5.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s表示,采用t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M(P25,P75)表示,采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或率表示,采用χ2檢驗、Fisher檢驗或R×C列聯表檢驗。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兩組患者的生存情況,繪制生存曲線并進行Log-rank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
本研究共納入男性患者159例、女性患者41例;年齡為38~80歲;所有患者均為Ⅳ期,其中鱗癌92例、非鱗癌108例。兩組患者的性別、ECOG評分、治療方案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組年齡顯著高于紫杉醇組(P<0.05)。結果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
2.2 兩組患者的化療完成情況和PFS比較
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組患者共完成化療430個周期,平均4.3個周期,中位PFS為4.0個月。紫杉醇組患者共完成化療476個周期,平均4.8個周期,中位PFS為4.0個月。兩組患者的中位PFS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經Log-rank檢驗,P=0.936 9)。結果見圖1。
2.3 兩組患者的療效比較
治療2個周期后,兩組均無CR患者,共有PR患者22例、SD患者166例、PD患者12例,總RR為11.00%,總DCR為94.00%。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組患者的RR為13.00%,與紫杉醇組的9.00%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組患者的DCR為99.00%,顯著高于對照組的89.00%(P<0.05)。結果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的療效比較
2.4 兩組患者的毒副反應比較
兩組患者的血液毒性反應主要包括白細胞減少、中性粒細胞減少、血小板減少和貧血,大多為1~2級;非血液毒性反應主要是為感覺神經病變、關節肌痛、惡心嘔吐和乏力,均為1~2級;兩組均無患者發生5級毒副反應。紫杉醇組患者上述各毒副反應的發生率均顯著高于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組(P<0.05)。結果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的毒副反應比較
3 討論
紫杉醇是從紅豆杉類植物中分離得到的天然產物,具有抗腫瘤活性,其作用機制是在細胞增殖過程中抑制紡錘體的形成和DNA的復制,從而誘導腫瘤細胞凋亡;另外,紫杉醇還可以與微管蛋白結合,穩定微管蛋白構象,抑制微管蛋白解聚,使腫瘤細胞阻滯在分裂期,從而抑制有絲分裂[8]。傳統的紫杉醇注射液在水中的溶解度極低,所以制劑中加入了聚氧乙烯蓖麻油作為增溶劑。聚氧乙烯蓖麻油可在體內被降解并釋放組胺類致敏物質,引起全身皮疹等過敏反應;同時,其也可引起神經細胞內顆粒釋放及脫髓鞘改變,加重紫杉醇的外周神經毒性[9―10]。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由美國Abraxis Bio-Science,LLC研發,是以人血白蛋白為載體的新型納米制劑(粒徑約130 nm),可通過與細胞膜上的白蛋白受體糖蛋白60結合來激活細胞膜上的小窩蛋白,再經血管內皮細胞將藥物轉移至腫瘤組織中,從而發揮抑瘤作用[11―13]。由于不需要聚氧乙烯蓖麻油等增溶劑,患者在使用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時無須行抗過敏等預處理,且輸注時間短、使用方便。
有報道指出,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治療晚期NSCLC患者的客觀緩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為26.09%,DCR為67.39%,中位PFS為4.80個月;治療鱗癌患者的ORR為27.78%,DCR為69.44%,中位PFS為5.30個月;在二線及以上化療方案中,患者的ORR和DCR可分別達到23.81%和61.90%,中位PFS為4.30個月[14]。另一項回顧性研究顯示,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組患者接受該藥二線治療的DCR為73.1%,中位PFS為6個月;普通紫杉醇組患者的DCR為57.7%,中位PFS為4.5個月[15]。楊宇等[16]的研究顯示,經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二線治療3個療程后,晚期NSCLC患者的ORR為61.29%,高于對照組的29.03%。本研究結果顯示,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組患者的RR(13.00%)雖略高于紫杉醇組(9.00%),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兩藥療效相當;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組患者的DCR(99.00%)顯著高于紫杉醇組(89.00%),表明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比普通紫杉醇能更好地控制疾病的進展。
骨髓抑制和神經毒性是紫杉類藥物常見的不良反應,一般以白細胞計數下降為主[17]。有文獻報道,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致復發難治性小細胞肺癌患者發生3~4級中性粒細胞減少的概率為35.5%[18]。本研究結果顯示,200例患者發生的血液毒性反應以貧血、中性粒細胞減少和白細胞減少居多,總發生率分別為65.00%、39.50%和39.50%。紫杉醇組患者的血液毒性反應以貧血和白細胞減少為主,各不良反應的發生率均顯著高于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組,分別是77.00% vs.53.00%、57.00% vs.22.00%(P<0.05)。200例患者發生的非血液毒性反應以關節肌痛和乏力為主,總發生率均為32.00%。紫杉醇組患者感覺神經病變、乏力、惡心嘔吐、關節肌痛的發生率均顯著高于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組(21.00% vs.8.00%、48.00% vs.16.00%、31.00% vs.18.00%、57.00% vs.7.00%,P<0.05)。總之,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組的各毒副反應發生率均顯著低于紫杉醇組,提示其在治療晚期NSCLC安全性方面有一定優勢。
綜上所述,與紫杉醇相比,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治療晚期NSCLC的療效較好,在安全性方面有一定優勢。但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本研究為回顧性、單中心設計,其研究結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同時,本研究并未對患者的生存質量變化進行評估,部分患者的治療目標是延長生存期,有的則是改善生存質量,不同治療目標對研究結局均有一定的影響,故有待后續研究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