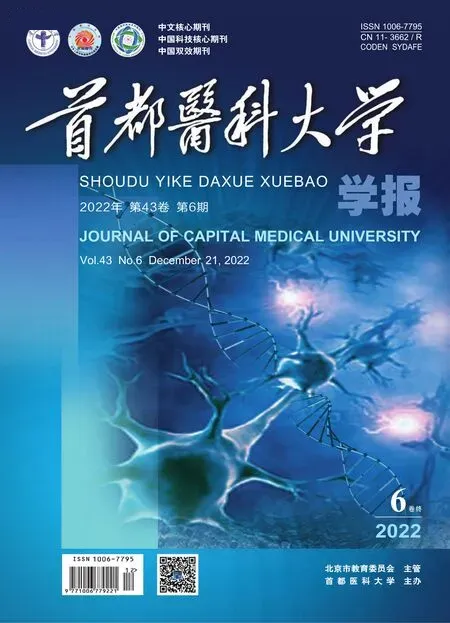長程治療管理哮喘兒童的肺功能軌跡特征分析
李 昂 皇惠杰 楊世青 侯曉玲 向 莉
(國家兒童醫學中心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過敏反應科 兒科重大疾病研究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北京 100045)
支氣管哮喘(bronchial asthma,BA)(以下簡稱哮喘)是兒童時期最常見的慢性氣道炎癥疾病,20年間患病率已從1.09%上升至2010年的3.02%[1-3]。此外,哮喘的控制水平也不容樂觀。一項納入中國42所三級醫院共計4 223名2~16歲哮喘患兒的橫斷面觀察性研究[4]顯示,中國兒童哮喘未控制率近20%。存在可變的呼氣氣流受限為哮喘患兒典型的疾病特征,常通過肺通氣功能檢查進行評估。流量型即間接描記法為目前常用的肺功能檢查方法[5],采用最大呼氣流量-容積曲線(maximal expiratory flow-volume curve,MEFV)方式完成。
哮喘患兒的典型肺功能異常多表現為阻塞性通氣功能障礙,主要為呼氣氣流受限,反映在流量-容積曲線(flow-volume curve,F-V)圖形表現為呼氣相下降支向橫軸凹陷[6],反映在具體參數上則表現為第1秒用力呼氣容積(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和(或)FEV1/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降低,其中FEV1減低(尤其≤60%預計值)可以識別有哮喘惡化風險的患者[7]。我國指南[1]建議,在以下時點需完善肺功能評估,即啟動控制治療前(首次診斷時)、治療后3~6個月(獲得個人最佳值)以及后期定期進行風險評估時。因此在哮喘患者的治療管理過程中會產生一系列的肺功能數據,這些數據為肺功能轉歸提供了重要的線索。通過檢索文獻,可以發現國內相關研究較少,而國外此類隊列研究較多,其結論是否同樣適用于國內人群,有待商榷。因此,本文就5~17歲哮喘兒童群體中肺功能軌跡特征以及其可能的影響因素進行初步探索,以期為早期識別肺功能受損表型提供一定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納入2018年11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就診于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以下簡稱北京兒童醫院)過敏反應科門診并確診為哮喘的5~17歲患兒為研究對象。參照課題組已發表文獻[8],對每一個研究病例評估哮喘控制總體穩定性并分為控制穩定組和控制不穩定組。本研究經北京兒童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批準文號:2018-203)。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利用的研究信息不含有使受試者的身份被直接識別或通過與其相關的識別物識別的信息,免除簽署知情同意書。
(1)納入標準:①年齡5~17歲;②根據我國《兒童支氣管哮喘診斷與防治指南(2016年版)》[1]確診為支氣管哮喘或咳嗽變異性哮喘。診斷標準:主要依據呼吸道癥狀、體征及肺功能檢查,證實存在可變的呼氣氣流受限,并排除可引起相關癥狀的其他疾病;③在北京兒童醫院過敏反應科門診定期復診及病情評估累計≥3年;④每3~6個月進行復診評估且MEFV監測評估肺通氣功能;⑤每6個月至1年至少有1次可用于分析的肺通氣功能數據。
(2)排除標準:①合并呼吸系統其他慢性疾病或其他系統性和全身性慢性疾病,但不包括過敏性鼻炎及結膜炎、花粉癥、蕁麻疹、特應性皮炎、過敏性皮炎、食物過敏、腺樣體肥大;②在門診電子病歷系統未查詢到可用于分析的病史信息;③持續>6個月中斷復診評估或不能準確提供復診間期病史信息。
(3)分組標準:①哮喘控制穩定組:自初診開始至末次復診,治療管理期間藥物治療不需要升級即可達到且保持哮喘控制狀態;②哮喘控制不穩定組:自初診開始至末次復診,治療管理期間因控制不佳需要使用升級治療≥1次或采用4~5級治療方案控制效果仍欠佳。
1.2 資料收集
經北京兒童醫院過敏反應科肺功能信息化系統采集歷次肺功能監測數據,同時結合門診電子病歷系統核查肺功能檢查時日病史信息,內容包括:①基本信息:性別;②濕疹史、一級親屬過敏史;③臨床信息:診斷類型,哮喘控制總體穩定性,合并其他過敏性疾病種類數(過敏性鼻炎、過敏性結膜炎、特應性皮炎、蕁麻疹、食物過敏、腺樣體增生或肥大),就診時疾病病程(單位:月),首診時哮喘控制狀態,就診前是否曾進行哮喘控制治療,初診啟用哮喘控制治療級別,是否合并變應原特異性免疫治療,是否應用鼻用糖皮質激素,復診間期哮喘急性發作次數,復診間期是否停用哮喘控制藥;④輔助化驗及檢查:首次肺功能是否正常、過敏原種類數(塵螨類、霉菌類、寵物皮屑類、春季花粉類、夏秋花粉類)、過敏原變化趨勢。
資料若符合以下情況之一即對該次肺功能數據進行剔除,距肺功能檢查時日:①近2周內發生呼吸道感染;②近2周內發生輕中度哮喘急性發作;③近1個月內因哮喘急性發作于急診就診或住院治療。
1.3 可納入分析的肺功能數據篩選流程
自首次可分析的肺功能數據起,以每隔6個月為固定間隔選取一次肺功能數據納入分析,即最終納入分析的肺功能數據監測時點為“首次可分析的肺功能,距首次可分析的肺功能0.5年、1.0年、1.5年……”。要求:近1個月內無哮喘重度發作史,近2周內無哮喘輕-中度發作史及呼吸道感染史。
1.4 軌跡分析
選取肺功能監測累計時限為2年且符合數據分析標準的患兒肺功能指標分別進行軌跡分析。軌跡分析模型,又稱為潛分類增長模型,該模型適用于具有異質性的群體。總體分析思想為:假設某群體中存在若干種變化軌跡類型,根據專業知識進行判斷后并賦予每種變化軌跡類型具有實際意義的名稱用作區分,從而更加具有實用價值,尤其適用于疾病的病因探索、預后影響因素等方面的研究[9-10]。該分析模型的實現步驟為[11]:(1)根據分析數據類型,確定適宜的分布。(2)確定亞組數及相應軌跡:依次將目標對象擬合為線性、二次、三次或四次來測試軌跡數量的可行性。(3)擬合效果判斷:①按照貝葉斯信息標準(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BIC值越接近于0,表明模型擬合度越好;②貝葉斯因子對數值(log Bayes factor):判讀標準:該值>6,需接受復雜模型;該值<2,可接受簡單模型;③平均驗后分組概率(average posterior probability,AvePP),以該值>0.7作為可接受標準;④P<0.05。
盡管軌跡分析模型有眾多優點,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觀測間隔不等、隨機數據缺失等情況并不適用[12],因此,本研究選取肺功能監測時點為“首次可分析肺功能,距首次可分析肺功能1.0年、2.0年”數據納入軌跡分析,共計157例患兒,471例次肺功能數據納入分析。該部分運用SAS 9.4統計軟件實現,結果報告格式參考文獻[13]。
1.5 肺功能參數
第1秒用力呼氣容積占預計值的百分比(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pred)、用力肺活量占預計值的百分比(forced vital capacity,FVC%pred)、第1秒用力呼氣容積占用力肺活量的百分比(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to forced vital capacity, FEV1/FVC)、最大呼氣流量占預計值的百分比(peak expiratory flow,PEF%pred)、最大呼氣中期流量占預計值的百分比(maximum mid-expiratory flow,MMEF%pred)。
1.6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157例患兒的臨床特征
本研究共納入157例患兒,其中男性105例(66.9%),女性52例(33.1%);平均年齡(7.0±2.2)歲;診斷為哮喘142例(90.4%),咳嗽變異性哮喘15例(9.6%);根據總體控制穩定性分為控制穩定組27例(17.2%),控制不穩定組130例(82.8%);無合并其他過敏性疾病2例(1.3%),合并其他過敏性疾病155例(98.7%);應用變應原特異性免疫治療48例(30.6%),未曾應用過變應原特異性免疫治療109例(69.4%);無致敏原17例(10.8%),≥1種致敏原140例(89.2%);首診時平均病程為3(1,24)個月;初診時啟用哮喘控制治療級別為(3.4±0.7)級。
2.2 進行軌跡分析的肺功能數據基本特征
首次可分析肺功能、距首次可分析肺功能1年及2年肺功能各參數均值詳見表1。
2.3 肺功能各參數軌跡分析結果
對157例患兒的471次(每例3次)肺功能數據進行軌跡分析,各肺功能參數具體統計量及所得軌跡圖詳見表2及圖1。
1)FVC%pred:可分成低軌跡組(124例)和高軌跡組(33例),均呈下降趨勢。其中低軌跡組首次可分析肺功能均值為99.8%,高軌跡組為118.8%,2種軌跡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FEV1%pred:可分成低軌跡組(100例)和高軌跡組(57例),均呈下降趨勢。其中低軌跡組首次可分析肺功能均值為95.7%,高軌跡組為114.7%,2種軌跡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3)FEV1/FVC:可分為低軌跡組(30例)和高軌跡組(127例),且均呈下降趨勢。其中低軌跡組首次可分析肺功能均值為75.9%,高軌跡組為86.1%,且2種軌跡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4)PEF%pred和MMEF%pred:所擬合軌跡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2.4 不同軌跡組間的影響因素分析
根據前述得到的肺功能各參數軌跡,篩選出有統計學意義的參數(FVC%pred、FEV1%pred和FEV1/FVC),分別進行不同軌跡組間的影響因素分析。

表1 157例患兒在2年管理中各年度肺功能結果分布Tab.1 Distribution of pulmonary function outcomes in 157 children in each year of 2-year management

表2 肺功能各參數軌跡擬合結果Tab.2 The fitting results of the trajectory of lung function parameters

圖1 肺功能各參數軌跡分析圖Fig.1 Trajectory analysis chart of lung function parameters
多因素Logistics回歸分析顯示:FVC%pred,控制不穩定為其呈現低軌跡的危險因素(OR=4.878,95%CI:1.714~13.882);FEV1%pred,首次可分析肺功能異常為其呈現低軌跡的危險因素(OR=4.911,95%CI:2.137~11.287);FEV1/FVC,男性為其呈現低軌跡的危險因素(OR=3.774,95%CI:1.125~12.658),首次可分析肺功能異常為其呈現低軌跡的危險因素(OR=18.472,95%CI:5.182~65.850)。
3 討論
哮喘常伴有可變的呼氣氣流受限,可通過肺功能檢查評估。哮喘是一種異質性疾病,具體表現在發病年齡、生物學機制、持續時間、疾病嚴重程度、對治療的反應性和疾病轉歸等方面。因此,哮喘的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疾病可能會出現緩解、進展或復發等不同情況[14]。一項基于BAMSE隊列的研究[15]總結出4條哮喘變化軌跡,并分別將其命名為:罕見型3 291例(80.4%)、早發一過型307例(7.5%)、青少年始發型261例(6.4%)和持續不緩解型230例(5.6%)。其中在16歲和24歲時,持續不緩解軌跡組的FEV1平均值最低,且氣流受限患者比例最高(分別為18.1%和14.2%)。早期經過規范的控制治療管理雖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哮喘患者存在的可變性呼氣氣流受限,但越來越多的研究[16]顯示,成年早期甚至在更早時已可觀察到不可逆的氣流受限。最近的多項研究[17-18]表明,兒童期肺功能低下與未來出現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風險升高有關。這也印證了兒童哮喘通常被認為是成年早期肺功能低下的危險因素的觀點。肺功能降低還與多種肺外疾病的患病率升高有關,如心血管系統疾病、代謝性疾病等。除此之外,肺功能降低還會增加全因病死率[19-20]。因此關注哮喘患者在真實世界中經長程規范治療管理模式下的肺功能變化軌跡并探討其影響因素,對于早期識別和干預均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鑒于聚類分析等分析方法可能會掩蓋個體水平特有的變化,因此本研究選用軌跡分析進行探索[21-22]。
國外各項研究[15-22]僅對FEV1或FEV1/FVC的縱向軌跡進行分析,并未納入其他肺功能重要參數。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對157例患兒累計監測時限為2年的肺功能參數(FVC%pred、FEV1%pred、FEV1/FVC、PEF%pred和MMEF%pred)分別進行軌跡分析。最終確定了 FVC%pred、FEV1%pred和FEV1/FVC均為兩種軌跡,并將其分別命名為:高軌跡和低軌跡。低軌跡組患者占比均高于國外研究,分析原因可能為與本研究納入病例中疾病程度較重、病情較為復雜,控制不穩定組占比超過80%有關。
有研究[23-25]得出結論:肺功能軌跡異常與初始肺功能低下、男性、反復喘息、早期致敏、煙草暴露以及兒童時期哮喘、支氣管炎、肺炎、過敏性鼻炎或濕疹的診斷有關。下面將就本研究得到的關于肺功能軌跡的影響因素與既往研究進行比較。
有文獻[26-27]顯示,單純過敏性鼻炎患兒存在肺功能異常,尤其是MMEF參數最為明顯,進一步則會出現氣道高反應性。國外的一項觀察性橫斷面研究[26]納入189名5~18歲鼻炎患兒,其中22.2%的患兒存在肺通氣功能異常且肺功能損傷程度與鼻炎的嚴重程度相關。另一項研究[27]納入220 名中重度持續性鼻炎的患兒,其平均年齡為11.6歲,該部分患兒的肺功能檢查顯示,26.3%存在肺功能損害,其中64.2%患兒的MMEF低于預計值。
本研究并未發現過敏性鼻炎對肺功能參數縱向軌跡的影響。既往文獻[23, 25, 28]關于過敏性鼻炎是否影響肺功能軌跡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前述提到有研究[26-27]表明過敏性鼻炎與兒童期肺功能軌跡異常有關,另一項基于在奧斯陸進行的“環境與兒童哮喘”出生隊列的研究[28]共納入329名受試者,以FEV1、FEV1/FVC和MMEF為觀察指標,表明過敏性鼻炎與肺功能不同參數的軌跡異常有關,且明顯影響從出生到16歲期間的肺功能。但一項基于圖森兒童呼吸隊列的研究[29]對85名嬰兒進行了長達22年的隨訪,未發現其對肺功能軌跡有顯著影響,但在整個研究中觀察到了很強的追蹤因素。因此未來有待設計更多前瞻性研究來探索兩者之間的關系。
多項研究[25,30]顯示,男性為肺功能軌跡異常的危險因素,本研究在FEV1/FVC不同軌跡的影響因素分析中也得到了同樣的結論。CAMP研究[25]對出現不同肺功能軌跡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顯示,與肺功能正常生長組相比,男性較女性更容易出現生長受損(OR8.18vs3.07)(P<0.001)。一項在英國懷特島進行的出生隊列研究[30]納入808名10~26歲受試者的肺功能數據分性別分別進行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性別的FVC、FEV1和 FEV1/FVC均被分成了2條軌跡,并將其分別命名為:高水平和低水平。無論是高水平組還是低水平組,男性的FVC與FEV1均高于女性,FEV1/FVC低于女性。
本研究在對不同軌跡類型之間的影響因素分析時未發現致敏對不同肺功能軌跡的影響。既往文獻[30-33]多顯示致敏可影響肺功能及其軌跡。德國前瞻性觀察出生隊列(Multicenter Allergy Study, MAS)[31]在德國5個城市共招募1 314名嬰兒,直至隨訪到20歲,研究顯示,早期致敏是兒童過敏和哮喘發展到成年早期的重要預測因素,并且還發現在父母有過敏病史的受試者中,其哮喘發病率是父母為非過敏受試者的2~3倍。在學齡前兒童中,通過早期的多吸入過敏原致敏和嚴重的喘息發作可預測未來的肺功能生長受損[32]。一項最新發表的研究[33]基于塔斯馬尼亞隊列數據通過數據驅動的方法進行分析,發現有早發持續性哮喘和過敏的人出現肺功能降低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的風險最高。還有研究[34]顯示,與無致敏患者相比,多致敏原患者的特定氣道阻力(specific respiratory airway resistance, sRaw)較高。還有研究者[35]提出,對患者特應性僅進行分類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應進一步定量比較,并證明了常見吸入性過敏原sIgE水平與兒童喘息和肺功能下降之間的關系。
目前哮喘患者的控制治療藥物主要為吸入類藥物和(或)白三烯受體拮抗劑,治療方案調整遵循全球哮喘防治創議(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GINA) “評估-調整治療-評估反應性”全程管理模式[7]。治療目標為實現和維持哮喘控制,最大限度地減少惡化和肺功能損失[1, 7]。不同軌跡類型之間的多因素分析顯示,哮喘整體控制不穩定為FVC呈現低軌跡的危險因素。雖然已有多項研究[36-38]顯示,吸入類激素不會影響兒童的肺功能軌跡,但根據塔斯馬尼亞隊列研究的結果,達到哮喘的良好控制仍在促進肺部健康和預防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方面有益。因此臨床中仍應注重規范哮喘治療管理流程,以期維持哮喘的良好控制。
綜合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及結果,局限性在于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隊列研究,病史資料通過門診電子病歷系統獲取,可能存在回顧性偏倚,研究結論具有一定范圍的適用性。反之,優勢在于本研究納入長程規范治療管理的哮喘患者數量較多,通過應用軌跡分析的統計學分析方法,可以更有效探索肺功能的變化趨勢以及軌跡變化特征。此外,本研究同時評估了哮喘疾病表型譜(哮喘與咳嗽變異性哮喘)、控制治療、致敏原對肺功能的影響。本研究除納入 FVC%pred、FEV1%pred和FEV1/FVC以外,還關注了重要小氣道指標MMEF%pred的趨勢變化。
綜上所述,在對患兒2年時點肺功能的軌跡和影響因素分析中,FVC%pred、FEV1%pred、FEV1/FVC均可分為2組:低軌跡組和高軌跡組。其中男性、首次可分析肺功能異常以及控制不穩定為其易呈現低軌跡的危險因素。在長程治療管理的支氣管哮喘患兒群體中,肺功能預后始終是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若能早期識別出肺功能持續受損表型的群體,則可以為支氣管哮喘患兒臨床治療與管理提供一定參考。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向莉、李昂:提出研究思路,設計研究方案;李昂、楊世青:數據采集與分析;李昂:論文撰寫;皇惠杰、侯曉玲:病例隨訪;向莉:總體把關,審定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