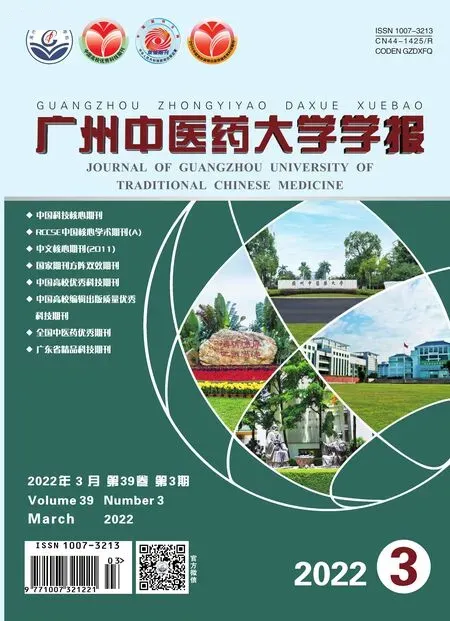范冠杰運用“三仁湯”治療濕溫病的臨床辨治思路
張錦明,田瀅舟,張鵬,王丘平,溫建炫,吳露露,宋薇,趙玲(指導:范冠杰)
(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廣東省中醫院,廣東廣州 510120)
三仁湯出自清代吳鞠通所著的《溫病條辨》,具有宣暢氣機、清利濕熱之功效。三仁湯為臨床著名的祛濕劑,由杏仁、飛滑石、白通草、白蔻仁、竹葉、厚樸、生薏苡仁、半夏組成,主治濕溫初起及暑溫夾濕之濕重于熱證。臨床應用以頭痛惡寒,身重疼痛,午后身熱,苔白不渴為辨證要點。范冠杰教授為國家優秀中醫臨床人才指導教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專科中醫糖尿病學科帶頭人,“動-定序貫范氏八法”中醫原創理論創始人。先后師承國醫大師呂仁和教授、王永炎院士、熊曼琪教授,學術思想承繼于施今墨、秦伯未、祝諶予等中醫名家。范冠杰教授基于臨床實踐、傳承名醫和融合經典,圍繞中醫臨床診療現狀,提出“動-定序貫范氏八法”的理論,即以“核心病機”為靶點,以“證素”為辨證的基礎和規范,靈活動態組合“藥串”為組方思路,針對動態變化的證進行有序連貫的治療。以下基于“動-定序貫范氏八法”理論,對“三仁湯”古籍原文中部分證候和病機特點及其現代臨證運用進行分析,以期為中醫臨床運用經典名方進行辨治提供參考。
1 分析核心病機,確定核心證素
對于三仁湯的適應證,吳鞠通在《溫病條辨》原文中提到“頭痛,惡寒,身重疼痛,舌白,不渴,面色淡黃,胸悶,不饑”多個臨床證候,基本病機特點為太陰脾虛,濕熱蘊結,加之外感濕熱邪氣。但在具體的現代中醫臨床辨治過程中,相當一部分患者并無外感邪氣的表現,故通常不會出現“頭痛惡寒”“身重疼痛”等癥狀;而在脾虛濕熱內盛方面,患者除了口干不欲多飲、納食不多等癥狀外,亦可出現精神不佳、倦怠乏力、頭重如裹、昏蒙眩暈、脘腹脹滿、身體困重、大便黏膩不爽、小便黃等證候。上述現代臨床實際提示兩個問題:(1)從證候來看,古籍原文中所列舉的證候并不能完全概括“太陰脾虛,濕熱蘊結,外感濕熱邪氣”病機的臨床表現;(2)從“三仁湯”的方藥組成及功效來看,雖然此方出于《溫病條辨》,但隨著中醫學的發展及此方的廣泛應用,其治療范圍已不局限于溫病范疇。
核心病機所表現在外的特征性臨床癥狀及體征就是核心癥狀,一組核心癥狀背后往往對應一個核心病機。“動-定序貫范氏八法”提出從核心證候抓核心病機,強調辨證時要善于從四診資料中發現最典型的表現(包括患者主要的不適和舌脈表現),迅速而準確地找準其背后的核心病機[1]。基于“動-定序貫范氏八法”理論,范冠杰教授認為“三仁湯”的使用適應證不應局限于古籍記載,只要辨證分析疾病存在濕熱內蘊病機導致的核心證候,均可靈活使用三仁湯,這與《傷寒論》在柴胡湯證中提到的“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的理念有異曲同工之處。三仁湯適應證的核心證素可歸納為“口干不欲多飲,納食不多,頭重如裹,昏蒙眩暈,脘腹脹滿,身體困重,大便黏膩不爽”。
然而,臨床上亦可遇到癥狀不典型甚至毫無特殊不適的三仁湯適應證患者。對于此類患者,若僅僅從問診就很難進行辨證和做出用藥判斷。此時,舌診的重要性則尤為凸顯。縱觀中醫學歷史長河,舌診真正得到較大發展是在16世紀溫病學派興起的階段。隨著溫病學派的興盛,“辨舌驗齒”在外感熱病的辨證中得到重視并廣泛使用。由此可見,舌診在溫病辨治過程中尤為關鍵[2]。眾所周知,三仁湯所針對的是濕重于熱的濕溫病,其病因之一就是外感時令濕熱之邪,濕熱外邪是外因實邪,與太陰脾虛內外相應合而為病。清代醫家薛雪在《溫熱經緯》中提出:“太陰內傷,濕飲停聚,客邪再至,內外相引,故病濕熱”。另外,舌為脾之外候,而舌苔乃胃氣之所熏蒸,所以脾胃的病變也必然影響精氣的變化而反映在舌象上[3-6]。清代的章楠在《醫門棒喝·傷寒論本旨》中記載:“觀舌本(即舌質),可驗其陰陽虛實;審苔垢,即知其邪之寒熱淺深也”;“血病觀質,氣病察苔”。清代嘉慶年間吳貞(坤安)所著的《傷寒指掌》提出:“如舌苔白而厚或兼干,是邪已到氣分;白內兼黃,仍屬氣分之熱。”以上文獻記載均說明,溫病患者的舌苔在濕熱外侵、邪在氣分的疾病辨治中具有典型的外在表現。在臨床辨證中,舌象在“太陰脾虛”和“氣分濕熱”這兩個核心病機方面都能體現出其重要性和特異性,范冠杰教授因而提出,臨床辨證使用“三仁湯”時,舌象的判斷必不可少,且“舌苔白膩或黃膩”應為三仁湯適應證的辨證要點和核心證素之一。
2 靈活遣方用藥,動態因“候”辨治
“動-定序貫范氏八法”理論強調,無論對中藥藥性的認識,還是對疾病病機的認識,都應打破固定思維,靈活動態地看待。范冠杰教授認為古代醫書中經典方劑的使用并不是不可變通的,中藥復方的藥性和功效主治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疾病的病機和證候表現可存在動態變化,而單味中藥的性味功效亦可隨著環境氣候、社會變遷、地域改變而存在差異。秉承“動”的思維的發散性,臨床醫生在學習經典古醫籍時更易于進行思考和創新,在中醫臨床診療中可擺脫守舊和拘泥,更具有靈活性。
在對三仁湯進行臨床加減用藥時,可以采用“去性存用”和靈活加減“藥串”的方法。中藥復方配伍中的去性存用,是指某味藥通過與其他藥味配伍后,其部分藥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或減弱及消除,但部分效用得到保留的一種配伍形式[7]。寒熱溫涼的藥性搭配是臨床遣方用藥的常見技法,而諸如清熱類、溫補類等方劑屬性也是相對而言,并非絕對。故臨床通常可通過增減藥味與藥量而改變整個方劑的寒熱屬性,以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8]。靈活運用固定“藥串”是“動-定序貫范氏八法”理論的一個重要特色。范冠杰教授繼承秦伯未、施今墨兩位中醫名家的學術思想,在臨床實踐中總結出了針對不同病機使用的固定藥串,如針對濕熱內蘊的藥串為蒼術10 g、黃柏10 g、薏苡仁30 g、車前草30 g、綿茵陳15 g,針對濕盛困脾的藥串為茯苓12 g、炒白術10 g、法半夏10 g、炒神曲15 g。這些藥串不僅可以靈活方便地加減變換,而且還能加強藥物間的協同和配伍作用。
在濕熱辨證過程中,可借鑒國醫大師呂仁和教授(以下尊稱呂老)創立的“以虛定型,以實定候”理論,即辨證時把證型和證候分開,認為“型”是模式,“候”是隨時變化的情狀。證型變化慢,證候變化快,故把變化較慢的正虛歸為證型,把變化較快的邪實歸為證候[9-12]。在證型相對固定的基礎上,根據邪實的變化隨時辨出證候,調整用藥,以利于提高療效[13]。基于前文所述的吳鞠通在《溫病條辨》認為濕溫病的內因是脾虛,濕溫邪氣為外因,而痰濕熱邪為病理產物,故根據呂老的“以虛定型,以實定候”的理論思想,脾虛為濕溫病的“型”,濕與熱是兩個變化的“候”。基于這兩個“候”的輕重變化而推論出來的證候與古醫籍中“濕熱并重”“濕重于熱”“熱重于濕”的分類辨治證候不謀而合。結合呂老的“以虛定型,以實定候”理論,范冠杰教授認為“三仁湯”的臨床使用不應只局限于濕重于熱的病癥,本方劑的應用范圍可以更加廣泛,亦可用于熱重于濕、濕熱并重、熱毒挾濕等證候,通過辨別“濕”“熱”兩者的孰輕孰重,做到因“候”施藥。縱觀“三仁湯”中的藥物組成,杏仁、白蔻仁、法半夏、厚樸性溫,薏苡仁、滑石、通草、竹葉甘寒,諸藥寒熱搭配,分工明確,達到分消三焦濕邪而兼清熱的功效。若患者年老體弱、久病體虛、素體脾氣虛(脾陽虛)明顯,則可減少滑石、薏苡仁、竹葉等藥量,或者酌減藥味,或者添加健脾溫中的藥串(茯苓、淮山、干姜);反之,若熱象明顯,則可增加薏苡仁、滑石藥量,或者添加清熱利濕的藥串(蒼術、黃柏、車前草、綿茵陳);若濕熱并重或熱毒熾盛者,可添加清熱利濕解毒的藥串(黃芩、連翹、藿香、綿茵陳)或合甘露消毒丹加減。
3 病案舉隅
患者李某,女,28歲,因“剖宮產術后1周,發熱腹瀉5 d”于2020年3月6日就診。患者于1周前于外院行剖宮產術,順利產下1男嬰,術中出血約300 mL。術后予靜脈補液支持及預防感染治療,患者生命體征及術口情況均穩定。2020年3月1日患者出現發熱,體溫最高達39.9℃,寒戰,腹瀉,水樣便,每小時1次,伴氣短、乏力、納差。當日行血液分析檢查,結果如下:白細胞計數:16.81×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92.4%;中性粒細胞絕對值:15.55×109/L;紅細胞計數:3.78×1012/L;血紅蛋白:111 g/L;血小板計數:163×109/L。C反應蛋白:151.5 mg/L;降鈣素原:0.5~2.0 ng/mL。二便常規檢查結果正常,胸腹部CT檢查未見明顯感染征象。血液培養結果提示:革蘭氏陽性球菌(+)。給予泰能1 g每8 h靜脈滴注抗感染治療,配合口服退熱藥物及整腸生、思密達等對癥治療。中藥治療采用口服補中益氣湯合小柴胡湯加減。治療后發熱改善不明顯,最高體溫可達39.3℃,仍每日水樣便10余次,遂來我院就診并入院治療。刻下癥見:患者精神疲倦,乏力,發熱,體溫38.2℃,無惡寒,無肌肉酸痛,無鼻塞流涕,無咽痛咳嗽,胃納差,睡眠一般,小便調,水樣便每日約10次,舌紅,苔白膩,脈滑。中醫診斷:發熱,辨證為脾虛濕熱內蘊(濕重于熱)。治法:健脾清熱祛濕。中藥以三仁湯加減,中藥處方:薏苡仁30 g,厚樸30 g,法半夏10 g,通草10 g,淡竹葉15 g,白扁豆15 g,訶子15 g,陳皮10 g,茯苓20 g,白芷15 g,藿香15 g,炙甘草10 g,生姜10 g,白蔻仁15 g,淮山30 g。每日1劑,水煎取汁約200 mL,分兩次早晚溫服。服藥1劑后腹瀉明顯改善,大便次數減少,略呈糊狀,晨起體溫為38℃。再服3劑后未再發熱,腹瀉癥狀消失,疲倦、乏力癥狀明顯緩解,繼續維持原中藥方口服。服中藥1周后病情穩定出院。
2020年3月25日二診。出院后患者于家中進食較多溫補食材。患者出院6 d后再次出現午后發熱,體溫最高達38.5℃,伴有微惡寒,余無不適。二便正常,舌紅,苔灰厚膩,脈滑數。查體:心率92次/min,余無特殊。中醫診斷:發熱,辨證為脾虛濕熱毒蘊(濕熱并重)。治法:健脾祛濕,清熱解毒。中藥以三仁湯合甘露消毒丹化裁治療。中藥處方:藿香15 g,茵陳15 g,滑石30 g,通草5 g,蒼術15 g,白蔻仁15 g,薏苡仁30 g,北杏仁15 g,法半夏10 g,川厚樸10 g,甘草15 g,黃芩15 g,連翹30 g,柴胡30 g,浙貝母10 g,薄荷10 g(后下),僵蠶10 g,蟬蛻5 g。每日1劑,煎服法同前。服用3劑后患者發熱消退,午后最高體溫37℃,灰膩苔消失,舌紅苔薄黃。再服藥4劑后患者體溫正常,諸癥皆愈。后隨訪未再出現發熱。
按:范冠杰教授在初診時發現,患者在外院住院期間均為下午發熱明顯,晨起可無發熱或熱勢較低,與中醫學的“午后發熱”相似。初起見寒顫,為邪正交爭之象,提示該患者雖是產后氣血耗損,但正氣仍存。患者術后臥床,脾胃腸道功能受影響,中焦運化功能不足。術后曾服用補中益氣湯之類的溫補藥味,雖有甘溫除熱之效,更有助濕助熱、閉門留寇之嫌。患者此時出現的舌苔白膩即為濕邪壅盛的特征表現。以上證候及舌象表明,患者此時的病機符合濕溫發熱的特點,邪在氣分,濕重于熱,故投以三仁湯。結合患者產后體質特點,方中去滑石以避免寒涼損傷脾陽,服用1劑中藥后腹瀉明顯改善,3劑之后腹瀉、發熱癥狀消失。
患者二診時發熱,誘因為進食過多溫補食物,符合中醫“食復”特點。就診時舌苔灰厚膩,提示體內濕熱之象明顯,已是濕熱并重、熱毒之邪漸盛。根據呂老的“以虛定型,以實定候”理論,此時“濕”“熱”兩“候”的輕重已經較前發生變化,此時雖然仍投以三仁湯方藥,但方中以滑石、薏苡仁等清熱利濕藥物為主藥,使三仁湯的整體藥性偏于寒涼,有助于加強清熱之力,再加上甘露消毒丹之清熱解毒功效,服藥3劑后熱勢下降,灰膩苔消失,患者病愈。